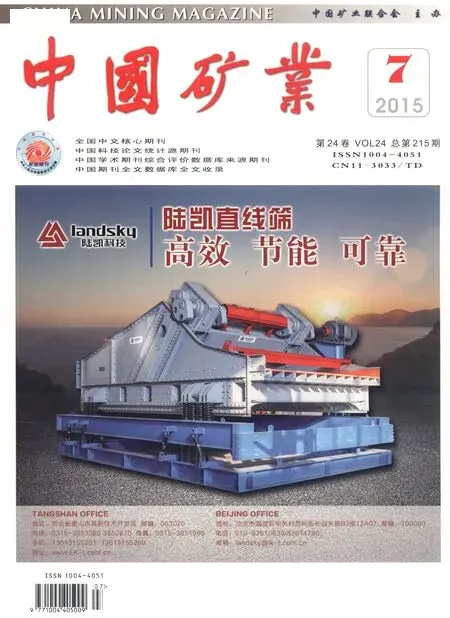重申矿产资源法的私法性
李遐桢
(华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河北 三河 065201)
管理专论
重申矿产资源法的私法性
李遐桢
(华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河北 三河 065201)
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过分强调政府管制,私权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没有得到发挥。我国修订《矿产资源法》应以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为基础,区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与作为勘探开发管理者的身份;突出采矿权在《矿产资源法》中的中心地位,使采矿权出让金与税各得其所,实行采矿权登记制度,用安全生产许可证吸收采矿权许可证,实现不同采矿权主体市场地位的一致性,明确探矿权向采矿权转化的路径;还应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损害的民事救济措施,且恢复原状具有优先适用性。
矿产资源法;私法;采矿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需要以权利为基础。而现行《矿产资源法》行政干预过多,私权隐身于行政权力之下,市场配置矿产资源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修订《矿产资源法》已经迫在眉睫。但矿产资源管理部门、学术界对如何修改《矿产资源法》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些观点针锋相对,《矿产资源法》的修订工作虽然逐步推进,但仍有待破冰。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对《矿产资源法》的定性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矿产资源法是公法;有的学者认为,矿产资源法是私法;还有的学者认为矿产资源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社会法。目前,我国主流学者认为,矿产资源法兼具私法性与公法性[1]。对矿产资源法属性的不同认识必然导致立法设计理念上的差异。公法说认为,矿产资源法的核心问题是矿产资源所有和利用的监管;社会法说认为,矿产资源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国家所有权,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和利用的监管是为了社会利益,《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应以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性为导向,社会法说最终将倒向公法说。私法说强调矿产资源的财产性,并以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与利用权为权利基础设计我国的《矿产资源法》。笔者认为,矿产资源法是关于矿产资源的所有和利用的法,其核心是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与利用权,该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是为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利用服务,此为“私法优位主义”、“公法服务于私法”在矿产资源法中的反应,并不能改变其私法属性。因此,我国在《矿产资源法》修订过程中需要重申其私法性,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具体的法律制度。
1 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是《矿产资源法》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本条是矿产资源立法的宪法依据,也是矿产资源立法的出发点。所以,《矿产资源法》必须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
1.1 重申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
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第3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本条是《宪法》第9条在《矿产资源法》中的具体体现。虽然作为矿产资源管理的法,但该法并没有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具体行使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而我国《物权法》第53条、第56条及第57条对国家所有权的权利行使等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矿产资源法》的修订应在重申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同时增加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权利行使与保护的准用性规定,明确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和保护应适用民法尤其是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国家所有权是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基础,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恰恰契合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
1.2 明确区分国家之所有者身份与管理者身份
国家是矿产资源的管理者,负有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职责。所以,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规定了大量国家对矿产资源管理的内容,例如第3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但是,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地位也不容忽视。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国家享有矿产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国家完全可以所有者的身份对矿产资源加以管理。那么,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管理行为,哪些属于所有权的范畴,哪些属于国家管理的范畴,很有必要划清其中的界限,否则,将导致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不分,以行政制裁代替民事责任的不合理现象。例如,《矿产资源法》第3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第156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擅自采矿的,属于侵害国家所有权的行为,国家可以所有权受到侵害为由要求开采者承担侵权责任,擅自开采者承担返还矿产品、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国家没有必要通过“没收”等行政手段保护矿产资源。当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也要依法对矿产资源的采矿进行必要的管制,此时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因此,我国《矿产资源法》修订时,应当突出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明确区分国家作为所有者与管理者的不同身份。
2 采矿权是修订《矿产资源法》的中心
近现代物权法以财产的所有为中心向以财产的利用为中心转变,就矿产资源而言,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为中心向矿产资源利用权为中心转变。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虽然规定了采矿权,但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比较粗糙,采矿权取得制度中的税费不分、国有企业独大、权证不清等问题一直成为困扰采矿权制度价值发挥的瓶颈,采矿权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得到显现,其调节矿产资源配置的权利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修订《矿产资源法》时,应以采矿权为权利基础设计了矿产资源的利用方式,通过采矿权流转使矿产资源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流通,实现以市场竞争方式调节资源配置。所以,采矿权应该是《矿产资源法》的中心,它是实现矿产资源市场配置的主要手段。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矿产资源法》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采矿权制度。
2.1 明确区分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税与费
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无偿时期、有偿萌芽时期与有偿使用确立时期。从现有的相关立法看,我国形成了以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四部分构成的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毫无疑问,现行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在实现国家资产收益,调节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完善,现有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的缺陷尤其是税费性质、功能界定不准确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日益显现。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决定》中要求:“完善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政策。”从国家完善资源税费改革的声音中,看出现行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确实存在缺陷。所以,必须对现行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进行改革。笔者在《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整合》一文中提出:我国应该进一步整合矿业权有偿使用中的有关概念。首先,取消资源税,改造矿产资源补偿费为矿产资源出让金,彻底实现一矿一金,实现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其次,修改矿业权使用费为矿区使用权出让金,实现国家对矿地所有权收益。最后,用矿业权价款来包含矿产资源出让金与勘探投资及收益,在立法上使用探矿权价款与采矿权价款的概念,全面反映矿业权本身的价值,以此为核心构建我国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2]。所以,我国未来之《矿产资源法》应明确区分作为矿产资源对价的出让金与作为国家无偿取得的税,实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向私法上的等价有偿回归。
2.2 实行“采矿权登记制度”与“许可证制度”的分离
按照现行《矿产资源法》第12条、第16条的规定,勘探矿产资源的,国家则实行统一的区块登记管理制度;开采矿产资源的,需要取得采矿权许可证。笔者认为,《矿产资源法》规定以行政审批的方式取得采矿权许可证的,权利人才享有采矿权,这与采矿权的权利属性相悖。
2.2.1 “采矿权许可证”从“采矿权”中剥离
采矿权应该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但是,采矿权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采矿权是准物权,是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3]。有的学者认为,采矿权是以行政许可的方式取得,应为特许物权[4]。也有学者认为,开采性矿产权属于自物权[5]。我国《物权法》将采矿权规定于用益物权部分,立法上已经将其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处理。
采矿权属于用益物权,而“采矿权许可证”是《矿产资源法》中行政权的集中体现和反应,采矿权作为财产性权利属于私权,它是在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权利,是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权能分离的结果。采矿权和许可证分属两个性质完全不同且不应存在交集的领域,而我国《矿产资源法》偏偏以公权力的手段作为赋予主体采矿权的手段,这种立法方式与作为财产权里的采矿权的本质相悖。因此,比较科学的设计思路是:将采矿权从许可证中剥离开来,恢复采矿权的本来面貌。采矿权作为具有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应以物权的取得方式取得。笔者认为,以合同方式取得采矿权的,可按照我国《物权法》第14条的规定,需要采矿权人与国家订立采矿权出让合同并办理采矿权登记,自登记之日采矿权人即取得采矿权。
矿产资源的开采具有高度危险性,属于高危行业,其开采资格应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权利人虽然享有采矿权,并非意味着其有开采矿产资源的资格。采矿权人欲开采矿产资源尚需要具备开采资格,该资格恰恰需要国家的认可与管制。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将采矿权的取得与矿产资源的开采管制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尤其以是否具备开采资格作为认定其取得矿业权的根据,这种做法突出的是行政许可功能,抹杀的是采矿权属证明功能,使行政许可行为遮蔽了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的国家出让采矿权的民事行为,架空了作为矿产资源所有人的国家作为民事财产权主体的民法地位[6]。因此,我国《矿产资源法》须对此作出修订,变矿业权行政审批为权属登记以凸显其物权属性,并将采矿权登记作为采矿权的取得、转让与消灭的公示方式。
2.2.2 采矿许可证与安全生产许可证
按照《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矿权许可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取得采矿权的功能。其二,保证企业具有开采条件与开采资格的功能。一旦《矿产资源法》废除采矿权许可证之取得采矿权的功能,该许可证将仅剩第二个功能。而矿业属于井下危险性大的作业,为安全有效起见,有关部门对开办矿山企业实行严格的审批和登记制度[7]。可见,采矿许可证具有保障开采安全的功能。而按照《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的规定,为了保障安全生产,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对矿山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采矿权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在功能上具有了相似性,存在重复“许可”的嫌疑,也不符合我国逐步减少行政许可的趋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将“二证”合为“一证”,保留安全生产许可证废止采矿权许可证。
2.3 明确探矿权向采矿权转化的条件
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规定探矿权人享有取得采矿权的优先权,但正如有学者所说,现行《矿产资源法》并未具体规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优先取得,怎样体现这一优先性。而对于“同等条件下的优先”缺乏统一理解[8],导致很多探矿权无法转成采矿权,这种结果势必影响民间资本投向矿产资源勘探。笔者认为,探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投资人的收益表现为取得采矿权,《矿产资源法》必须明确探矿权向采矿权转化的具体要求:一方面,赋予探矿权人优先权。取得采矿权的,也需要缴纳采矿权出让金,探矿权人行使优先权,此时探矿权人如果按照采矿权的市场价值缴纳出让金,探矿权人的勘探投入将付之东流,所以探矿权人缴纳的采矿权出让金应为采矿权市场价值扣除勘探投入与收益,这一点立法上必须明确。另一方面,如果探矿权人放弃取得采矿权,国家应向探矿权人支付勘探费用以及相应的收益。
3 生态救济应以私法手段为主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土地资源的破坏。例如,煤矿开采后形成矿坑,造成土地资源损害。其二,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造成地面植被等的破坏。其三,环境的污染。例如,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对周边环境的污染。然而,现行《矿产资源法》侧重于对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监督管理,而对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规定比较原则。如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只有第21条、第32条等个别条款对矿山环境保护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且从我国现有立法来看,生态破坏者主要承担的是一种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而忽视了民事责任对环境保护的意义。有学者提出,我国应从公法角度建立生态环境修复制度[9]。笔者认为,行政手段、刑事手段虽然可以遏制矿产开采中的生态损害,但不具有恢复生态损害的功能,《矿产资源法》应当确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以私法手段救济生态损害。生态损害赔偿的方式主要有赔偿损失与恢复原状,而生态损害首要的救济方式是恢复原状,恢复原状要求采取恢复措施使受到损害的自然资源恢复到基线条件(Baseline Conditions),它是损害赔偿中最能实现救济目的的责任承担方式。恢复原状不仅能够使受害人对其财产减少的价值得到赔偿,而且还可以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恢复其对生态的固有利益[10]。这与侵权法之目的在于“使受害人恢复到权利未被侵害的状态”保持一致。所以,奥地利民法、德国民法认为恢复原状应该比赔偿损失具有优先性,即被害人的损害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应首选恢复原状。从侵权法之使受害人恢复到被侵害之前的状态之目的看,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较赔偿损失具有优先适用性。例如,土地复垦是使遭到破坏的土地资源恢复原状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矿产资源法》应以私法手段为主构建矿产资源开采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而不能再继续由国家以运用公权力的方式大包大揽。
4 结 论
矿产资源法中存在大量的强制性规范,但这些强制性规范是为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利用服务,并不能改变其私法属性。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是矿产资源法的基础,但要明确区分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与国家对矿产资源管理权和矿产资源对价的出让金与国家无偿取得的税。矿业权尤其是采矿权是矿产资源法的核心,采矿权是物权,采矿许可证不能创设采矿权,采矿权登记具有公示权利的效力,采矿许可证与安全生产许可证在功能上具有相近性,应以安全生产许可证取代采矿许可证,《矿产资源法》还必须明确探矿权向采矿权转化的具体要求。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生态损害的,应主要以民事手段加以救济,而不能过度以来行政手段。
[1] 张文驹.《矿产资源法》的法学性质讨论[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4(11):4-6.
[2] 李遐桢.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整合[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6):43-50.
[3] 崔建远.准物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2.
[4] 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13.
[5] 康纪田.矿业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09.
[6] 石江水.矿产资源立法的私权化进路分析[J].河北法学,2012(3):106-113.
[7] 崔建远.准物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00.
[8] 李晓妹,李鸿雁.探矿权人优先权法理解析[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7(7):44-46.
[9] 李显东,杨城.关于《矿产资源管理法》修改的若干问题[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3(4):4-8.
[10] U.马格努斯.侵权法的统一:损害与损害赔偿[M].谢鸿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3.
Reiterated civil-law nature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law
LI Xia-zhen
(Faculty of Humanities,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nhe 065201,China)
The current “the Mineral Resources Law(MRL)” emphasis 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too much,and private rights don’t gotten to play in the allocation status of market resources.The revision of MRL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ate ownership of mineral resources,and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countries as the owner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manager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The mining right is the core in circulation system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transfer fee and resources tax of the mining right should be properly placed,the mining right registration replaces mining licenses,and merges the mining license and safety production license to one certificate,and implements different body to consistent position,and legislation should clear the method about the right of exploration converting to the mining right.We should build up the civil remedies about the ecological damage in the legislation,and restoration is precedent.
the mineral resources law;civil law;the mining right
2014-12-2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安全生产法创新团队”资助(编号:3142014015)
李遐桢,法学博士,博士后,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F407.1
A
1004-4051(2015)07-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