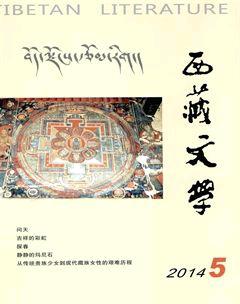彩虹桥边的老人
雍措
经过一阵子的寒冷之后,小城的雪,终于在夜晚落了下来。厚厚的积雪一夜之间,覆盖了小城。走在焕然一新的街道上,我小心翼翼,生怕踏下的每一个脚印,会弄疼路上的积雪。
有雪的早晨,小城显得很安静,没有过多的喧哗声,没有车辆从身边急速驶过时的刹车声,折多河冰雪凌厉起来,轻轻地从彩虹桥下走过。过往的行人缓慢地走在雪的世界里,嘴里冒出的热气和寒冷的空气相碰撞,变成一股淡淡的气流,一会儿功夫消失在空气里。
小城,在雪的世界里,时间被拉得长长的,思绪被大雪染得白白的。一切都从零开始,又似乎以零来结束。
那块玻璃做成的公告栏前,站着几个老人,老人们穿得都很臃肿,厚厚的围巾和大大的帽檐遮住了他们的脸。佝偻的背影,就像岁月留给他们的印记一样,透出数不尽的沧桑来。老人们的头有的歪着,有的抬着,看公告栏。远看,他们像是一幅雪地里的画儿,定格在那里,不动,不响,仿佛被时间所凝固。
那里是我每天上班时的必经之路,我的脚步一步步靠近老人,靠近那块冰凉玻璃做成的公告栏。
老人们并没有感觉到一个陌生人的到来,他们依然仰着头,眼睛注视着上方的公告栏。公告栏里面除了乱七八糟的招聘启事和房屋出租启事外,旁边新增了一张刺眼的黄色讣告。黄色在雪的世界里,冰冷冷的潜入老人们浑浊的眼睛里,冷冻着他们的心。
“×××,男,藏族,生于1953年,××单位老干部,因病救治无效,于昨夜23点10分去世,享年70岁。在职期间,关爱职工,将一生奉献给高原……”
我打了一个寒颤,背部有股冰凉的风穿透衣服,感到这个早晨冷极了。我用双手急忙将敞开的衣服裹紧,像身旁的老人们一样冻僵在这里。
“又走了一个一起晒太阳的朋友,明年夏天,彩虹桥上他的座位又该由谁来替补?”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人叹着息,自言自语地说。他小心翼翼地从我身边走过。雪在他的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老人佝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雪地里,看不见了。
彩虹桥,一座搭建在溜溜小城里的桥,一条来自雪山的折多河从桥下流过。左边连接着电影院,右边连接着广场。当夜幕到来时,宽阔的广场上灯火辉煌,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在这里跳着吉祥的藏族锅庄舞。影院里每天晚上放演来自不同国家的影片。一桥之隔,如梦如幻,电影院里上演着别人的故事,广场上表演着自己的人生。
此岸彼岸,常常让人感觉彩虹桥就像一个连接着彼时和此时的桥。
彩虹桥由水泥建成,不算太宽,也并不长。桥的两边向外延伸出七八米,上面摆放着一些木质的凳子,凳子有长的、短的、椭圆的,当溜溜小城暖和起来的时候,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将一张长凳子、短凳子、圆凳子坐满,桥上坐不下的,坐在桥边的石阶上,石阶还坐不下的话,就坐在广场旁边的铺面门口。
暖和的季节里,彩虹桥成了老人们的桥。
老人们大部分土生土长,小部分来自异地;有的是退休干部、有的是无业人员;有的穿着藏袍、有的套着汉装;有的带着眼镜,有的拿着拐杖,形形色色,出类拔萃。过往的行人数不清他们,他们看不完过往的行人。行人把他们想成自己老去时的模样,他们把行人当成年轻时的自己。一面关于历史和未来的镜子,安放在他们的心中,镜子里外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
阳光,从东方的郭达山铺洒而来,小城镀上金子的颜色。老人们陆陆续续地来到每天自己习惯坐着的位子上,找一些熟悉的朋友,听折多河咆哮的声响,摆着一些或淡或浓的家长里短。故事重复又重复,像他们脚下的折多河绵延无尽。在这里,身份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话题里的人生,人到老的时候该有个总结,好与坏,对与错,都只是一种经历。伴着阳光扑鼻的芬芳,老人们像谈着一部长长的电影一样谈着自己的过去,像要即将导演的一部片子一样谈论自己的未来。未来的目的地离自己很近,坐在彩虹桥上就能看见对面山坡上,一座座孤独的坟茔。
老人们珍惜着每一天阳光普照小城的日子,珍惜着每一个空位上新来的朋友,他们说,人老了,总爱弄丢东西,走着走着一个朋友就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匆忙的脚步,河流的远逝,汽车的鸣叫,阳光下小城热闹非凡。老人们在热闹中,却心静如水。远方亲人的短暂问候、儿女寄来的百元大钞、侄孙稚嫩的电话之声像风吹一样来的快,去的也快。老人们将这一个个幸福讲给朋友听时,脸上笑着,内心难掩一丝孤独和怅惆。
小城里的积雪正在慢慢融化,一股股细小的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在街上。我离开了那个玻璃做成的公告栏,那张黄得刺眼的讣告还贴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行人簇拥在这里一分钟、两分钟,然后静静地离开。
讣告里的人,我认识,他在阳光下的老人中,是最乐观的一位。
明年的夏天。彩虹桥上的老人们又将继续成为小城里一道风景线。
彩虹桥,一座连接着大地和天堂的桥,许多年后的某一天,我也会坐在那里享受阳光、享受人生衰老时的那份孤独。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