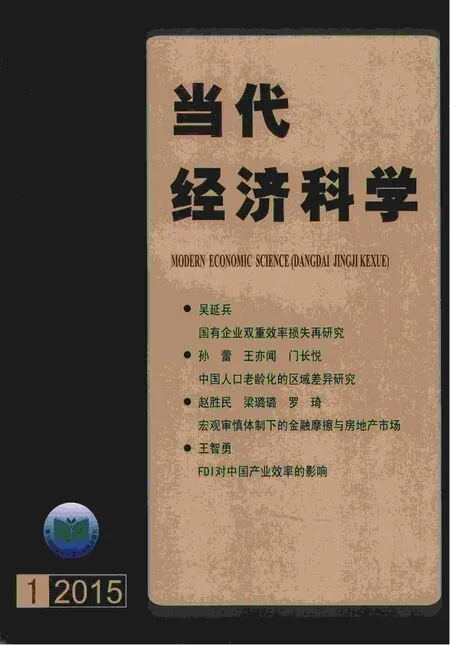FDI对中国产业效率的影响
——基于1989-2010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王智勇
一、引 言
2012年5月23日世界银行举行东亚经济发布会,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东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欧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的1/2。其中按照购买力评价水平,中国2010年的劳动生产率比1990年增长1倍以上,但是仍不到OECD国家的一半水平,也不如拉美国家的水平。中国科学院也曾发布多份报告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相比发达国家严重滞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滞后状况,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即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质量水平远非表面数据显示的那样高,而且因其所衍生的问题,已经对中国经济基本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用工成本的上涨,中国原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足和低附加值工业生产繁盛推动经济低效、规模性增长的阶段性优势丧失殆尽,却无更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和高附加值产业持续促进经济稳定、高效增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非常不利。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提高产业效率。只有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完全抵消工资上涨时,才有可能继续保持劳动力优势。
提高产业效率,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1]。由于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产业效率的提升更是直接关系到未来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问题。可见,对中国而言,如何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主要目标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引导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最终形成我国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一些研究表明,FDI影响东道国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影响产业生产效率来实现。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并且技术差异是影响地区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因素[2]。因此,研究FDI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研究FDI的技术创新外溢问题。FDI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产业效率,这不仅关系到东道国的外资利用政策,而且也关系到东道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关系到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对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而言,如何来通过积极的FDI政策促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充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工业化,推动了就业增长,并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FDI)被认为是国家或地区获取国际间外溢技术的一个重要渠道[3]。不少关于FDI与生产效率的研究指出,FDI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4-7]。不过也有研究指出,FDI并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是起到相反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FDI的流入削弱了东道国的创新能力[8-9]。有的则认为FDI会抑制东道国产业发展,主要途径是通过资本和人才挤出,以及产业甚至于整体国民经济形成对于FDI的依赖[10]。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多年,但劳动生产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原因何在?过去的研究表明,FDI与产业效率变动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不同的研究,基于不同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也有显著差异。那么,FDI与产业生产效率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此外,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切实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
在早期的研究中,大部分关注同行业内FDI技术溢出效应,以行业层面而获得的外资企业表现与行业表现的相关关系作为技术溢出的判定依据。然而,Javorcik认为以往的研究可能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寻找FDI溢出,从逻辑上说,FDI技术溢出更有可能是在行业间发生,而非以前所预期的行业内[11]。这意味着,跨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更值得研究,亦即从行业上升到产业更能够把握技术外溢。以往的研究多数基于省级层面和企业截面数据,当我们把行政单元细划到地市级,并把行业数据切换成产业数据时,情形会有显著的变化吗?特别是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看,FDI影响产业效率的程度和方式会有不同吗?
本文的安排如下,引言之后,首先是文献综述,对FDI与产业效率变化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从而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接着对影响产业效率变化的各种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尤其是针对FDI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分析结果之上的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从产业层面上把握效率变化,并把地理单元从省级细化到地级,从而有效地增加了样本量,使得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本文认为,产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科研创新投入的增长,FDI对于非农产业整体产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FDI对第三产业效率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并没有取得成功,只有自主创新才是获得效率提高的关键。因此,在提升产业效率方面,未来应当继续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科研创新、产业结构转变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引进和利用FDI方面,应当有针对性地提高门槛,大力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和高技术水准的FDI,充分发挥FDI在产业和行业内的技术外溢效应,以达到提高产业效率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在FDI增长与东道国产业关系的研究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FDI有助于促进东道国产业发展,主要途径是增加资金来源,吸引就业等,并且通过技术外溢和市场竞争等刺激东道国的产业发展[12]。另一种观点认为,FDI会抑制东道国产业发展[10],不过,也有许多学者认为,FDI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13],关键在于政策如何来引导。
Caves[14]和 Kokko[15]为代表的学者较早肯定了FDI正向溢出效应的存在,验证了FDI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Caves认为,外资企业对本地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分配效率、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转让的加快,而这三方面的作用都与本地市场上的竞争压力有关。
许多文献表明FDI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16]。国内关于FDI与产业效率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张帆等人认为,来源于跨国公司的FDI主要投向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向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转化[17]。沈坤荣和耿强基于1996年29个省市自治区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做横截面的相关分析,认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 0.37个单位[18]。张海洋[19]的经验研究强调了外资竞争效应对当地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何洁使用1993~1997年28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在各省市工业部门中均存在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外溢效应越明显[20]。潘文卿基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95~2000年FDI对工业部门的总体外溢效应为正,FDI的资本积累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国内企业的产出增加0.13个百分点[21]。姚树洁等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提高生产技术效率的推动器,而且也有利于加快国内技术进步[22]。毛日昇认为,FDI通过竞争和技术外溢显著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23]。喻世友等人基于1999-2002年期间37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FDI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其影响途径以提高技术水平为主[2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FDI有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服务业FDI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服务业FDI占全部FDI的比例高达47.25%。Markusen认为,服务业FDI通过其管理、组织或先进技术会对下游企业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有助于东道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25]。华广敏认为,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效率有正的直接效应[26]。许多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效率、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27-29]。也就是说,服务业FDI具有显著溢出效应[30]。针对商贸流通业的研究表明,内外资企业技术落差优势和制造业集聚度将会对纵向FDI溢出效应的发生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商贸流通业FDI对制造业的FDI纵向溢出效用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对周边省份的制造业也会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31]。同样基于企业数据,王志鹏等人则认为,外资参股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且外溢效应更多地表现在行业内部而非一省内部[32]。
不过,何骏等人认为,中国服务业FDI的结构与效率并没有呈现一定的相关性,传统服务业仍是绝大多数省份外资的主要流向领域[33]。韩德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增加能显著提高我国外资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但对内资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有限[34]。采用企业数据,姚洋等人认为就特定行业而言,国外三资企业的外溢效应即使不是负的,也不显著[35]。许多FDI项目根本不具备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基本条件,而且,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国内并不具备有效的市场和制度环境[36],这些年来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国内经济改革引起的制度变迁,而不是FDI技术溢出[37]。庞英等人认为,民族资本企业不论是生产技术效率还是资源配置效率,也不论是静态比较还是动态变化态势分析均优于FDI企业[38]。包群等人的分析表明,FDI虽然促进了中国技术进步,但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实际很小[39]。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开放条件下,一些具有创新活力、技术进步较快、业绩增长迅速的民营企业,却常常成为外国资本兼并收购的对象,出现技术“外流”现象[36],对于国内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出现负效应。
可见,FDI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尤其是FDI对产业效率影响程度、影响机制等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已有的研究也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是以行业间为主,也就是说,当把研究的范围从行业上升到产业时,才可能更清楚地了解到产业效率提升的主要渠道,这恰恰是本文分析的基本思路:把地理单元从省细化到地级市,把分析对象从行业提升到产业,从而有助于准确判断产业效率的来源。
三、FDI与中国产业效率变化
产业效率通常是指产业生产效率,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由于第一产业比例趋于下降,学者们在研究中主要关注非农产业生产效率。影响产业效率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投资、对外开放、城市化、人力资本以及区域创新研发等,而这些因素往往也相互影响。而FDI主要是衡量地区对外开放度。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地区开放度越高,则其经济发展得越快,而这个过程中,也恰恰是产业效率提高的过程。问题在于,产业效率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
人力资本是推动产业效率提高的积极因素。劳动与资本是生产的两大要素,而资本和机器设备必须有相应的劳动与之相配合才有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产业效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途径。
通过人力资本的积聚和外溢效应,城市化有助于促进产业效率的提高。城市中产业的规模扩张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中劳动力和资本集聚形成的信息和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得城市中的其它劳动力和资本都会受益。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体现[40]。因为知识、创新和复杂技术都在城市汇集、交流和发展,城市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41]。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移的过程[42]。基于微观数据,针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每增加1%,将使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 0.6%[43]。
研究产业效率,需要考虑到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配弟-克拉克定律准确地描述了产业变动的基本规律。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通常是从农业主导走向工业化,再从工业化走向服务业化,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过程。从国际经验来看,它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44],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45]。Sachs and Wing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之后发现,中国落后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46]。对此,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47-48]。
测量产业效率有多种方式,而劳动生产率则是较为常用也较有说服力的一种,即用产业GDP/产业就业人数来衡量产业生产效率。利用GDP缩减指数消除价格的影响可以在年度之间加以比较。

图1 中国非农产业效率变化(1989-2004)
从图1可以看到,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非农产业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相比之下,第二产业的效率明显高于第三产业。这可能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有关,国家的主要资金和劳动,包括FDI在内,都投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况。
仔细来看,产业结构的变迁与FDI的行业分布有密切关系。从行业分布看,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在FDI集中的沿海省份,这一现象更加明显。分产业来看,FDI主要投向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不过近些年来,投向第三产业的FDI数量越来越多,使得在FDI在第三产业的分布比例趋于提高(见图2)。

图2 FDI产业分布对照(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2 表明,在2002年时,FDI在第二产业的分布占据主导地位,超过70%的FDI都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仅约20%。但到2010年时,第二产业比例下降到50%左右,而第三产业比例也接近47%。也就是说,FDI正逐渐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FDI在不同产业间分布的变化,可能会给产业效率带来相应的影响。研究表明,转型经济企业效率的提高不仅仅来自于技术进步,还来自制度环境的改善,据测算,2000~2005年间我国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50%依靠存活企业的技术进步,50%依靠存活企业和进入退出企业资源重新配置[49]。然而,外资的流入将对本地企业造成竞争效应,从而对地区企业生产率产生影响。而在新企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和私营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显著,在由企业进入退出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中,这两类企业占所有企业的90%左右。
四、数据与模型设定
许多学者都指出[50-51],研究FDI对产业效率影响的计量检验最理想的是使用企业面板数据,可以捕捉到样本点的动态变化。然而,我国并没有涵盖改革时期的企业层面面板数据,难以用企业数据来估算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而且,企业层面的数据尽管可以捕获企业相关信息,然而,许多研究都证实,技术外溢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因此,从产业的角度去测量技术外溢可能是更为理想和现实的做法。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采用产业数据,并以地级市为地理单元,以期获得更加稳健的回归结果。
数据本身往往关系到结论。许多已有的研究都已经证实,九十年代以前的数据,由于统计口径变化较大,故而与九十年代以后的数据会有较大的出入。为了采用质量更可靠的数据,我们采用了1989-2010年间的地级市社会经济数据来加以验证,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地方篇)》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地市级区域为统计单元。由于1989-2004年间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地方篇)》,数据经过统一整理,具有很好的可比性,故而我们以这一数据为主。2005-2010年的地级市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口径略有差异,与1989-2004年间的数据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但可用以进一步检验我们的回归模型和结果。
在涉及到的变量中,产业效率、固定资产投资、FDI和财政中用于教育科研卫生文化的经费支出等变量都与价格有关,为了消除价格的影响,需要采用价格缩减指数,然而,地市级单元有近三百个,且连续22年数据,故而收集全并采用地级市的价格缩减指数非常困难。我们采用了省级GDP缩减指数来加以平减,以消除价格的影响,经过价格缩减之后,1989-2004年期间所有与价格相关的变量都采用了1989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2005-2010年期间所有与价格相关的变量都采用了2000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
为了进一步分析区位因素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我们把地级市分成两类,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基本的划分依据是东部地区为沿海,中西部地区为内陆,尽管这种划分方法沿袭了过去的三大区域划分,但由于地理单元的细化,使得样本数据更加丰富,从而可以更好地把握地区差距。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进而产业效率的变化与中央政府政策有密切关系,而传统上,以东中西部地区作为划分,但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所享受的政策明显不同,中西部地区所享受的政策比较接近,把中西部归入同一类有其合理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沿海与内陆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政策和制度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
我们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生产效率的分析框架:

其中,Y为总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t表示时问,对应的资本(K)、劳动(L)。方程两边都除劳动力的话,左边就是生产效率,而右边则是资本的函数。考虑到资本存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我们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资本存量。固定资本投资可以进一步拆分成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FDI),而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HuC)和科研创新力度(Eχpsc)密切相关:

式中,Kd(t)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Kf(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写成显函数形式:

两边取自然对数并改写为计量分析模型:

如前所述,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也会起到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因此,我们也把这两个因素纳入计量分析框架。考虑到效率的提高具有很强的时间延续性,即当期生效效率与上期生产效率密切相关,而且解释变量之间也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来加以分析。具体而言,在方程(4)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以下方程来对影响产业效率中的几个主要因素加以估算。

式中,efficyd表示第 i产业(i=2,3,23,本文试图探讨FDI对第二、第三和整个非农产业效率的影响)的产业效率,以产业GDP/产业从业人数来表达,并利用价格指数加以缩减以消除价格的影响。fdiced是经价格指数折算后的外商直接投资。Edupc为地区人力资本状况,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来表示。如前所述,产业效率的提升,离不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最后一项包括了所有其它项,主要包括用以衡量地区创新能力的人均科教文卫财政经费支出(eχpc_scipcd)、形成资本存量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invcdnew),用以衡量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化率(urbanrate)。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达,即户籍口径的城市化率。此外,为了综合衡量二三产业的变化,即衡量不同地区采取的产业发展战略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效果,我们采用产业结构变量instrc,即第二产业比例/第三产业比例,来测量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发展战略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来近似替代人力资本水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创新能力[52],也会影响模仿、吸收新技术的能力[53],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两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关系[54]。
按照现行的统计制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了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及其他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因此,要测算FDI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应把它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区别开来。在数据预处理中,我们把固定资产投资减去FDI,得到不包含FDI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把国内外投资加以区别。
此外,模型中还包括了区位虚拟变量coast和年份虚拟变量yeardum,在系统GMM模型中,通常都会考虑时期和空间相关的一些变量,以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时期影响。对区位虚拟变量coast而言,所有东部地区的地市级区域为取值1,所有中西部地区的地市级区域取值为0。产业结构的变迁和产业效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市场竞争越是激烈的地区,企业提高效率的动机越明显。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则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这在许多已有的研究中都得到印证,而且,许多研究把距离海岸线的长度作为是市场化的一个工具变量。从这个角度而言,沿海与内陆的划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影响。
为了克服回归分析中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需要采用可靠的回归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方法估计虽然可以消除解释变量与个体固定效应的相关性问题,但无法解决内生变量、前定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对参数估计带来的偏差。固定效应的面板工具方法(2SLS)从理论上可以同时考虑到上述两方面问题对估计参数带来的偏差,但工具变量本身并不容易寻找到,而且该方法在工具变量的数量超过需要识别的解释变量数量时,存在过度识别情况需要处理。
Arellano and Bond提出利用差分GMM方法来解决动态面板数据估计过程中存在的变量内生性和样本异质性问题对估计参数带来的偏差[55],进一步,Arellano and Bover[56]、Bundell and Bond[57]在差分GMM估计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GMM估计方法。系统GMM方法能够同时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信息,因而工具变量有效性一般情况下会更强而且,GMM估计使用差分转换数据,可以克服不可观察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的问题。一般来说,系统 GMM方法需通过两类检验:(1)Arellano-Bond检验(又称AB检验),即差分方程随机误差项的自相关检验,要求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2)Sargan或Hansen过度识别检验,要求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是不相关的,即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当采用了稳健选项时,通常采用Hansen检验。如果两类检验通过即表示模型设定正确且估计是合理的。
五、实证分析
受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市场的变化,产业效率及FDI在中国的变化也呈现出阶段性,另一方面,由于数据的来源不同,因而比较稳妥的方法是分时期来进行回归,并把两组回归结果加以对照,以检验模型设定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一)基本回归分析
针对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时期的数据,我们可以用来进行基本回归分析,以明确各个变量的关系及其解释力度。我们以1998年作为这段时期的分界点,构建年份虚拟变量,1998年以前为0,1998年以后为1。199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997年底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8年已经波及到中国并造成显著影响,有可能会影响FDI在中国的增长;1998年也是实现3年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第一年,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的一年,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显然,改革前后国有企业及其它类型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可能有显著的差异。
从表1可以看到残差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典型的大 N小T型面板数据,异方差的问题难以避免。故而,我们在回归中选择Robust选项以获得考虑异方差后的稳健性标准误。在这种情形下,采用Hansen检验来进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更为可靠,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的情况。因此,我们采用系统GMM方法是合适的。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用于教育科研的财政经费数量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效率都有显著而积极的影响,即他们的增加都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效率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显然会促进产业效率的提高,同样的,反映科研创新的财政教育科研经费支出的增长也会有利于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从而起到提高产业效率的作用。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相当大一部分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从而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

表1 FDI与产业效率回归结果(1989-2004)
然而我们注意到,FDI促进产业效率提升的效果不显著,仅对第三产业效率提升有一定(显著水平为10%)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就提升产业效率而言,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效果远比FDI显著。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升级能力,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所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它们会成为产业效率提升和产业转型的推动者。但现实是,外资是逐利而动的,他们在中国可能更看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消费市场,故而他们不大可能会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表1的回归结果,恰恰印证了这一特征。如前所述,随着FDI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特别是向服务业集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第二产业的生产需要。而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较为显著,从而FDI整体上对第三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化对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效应为负,这可能与采用的统计口径有关。基于户籍口径的城市化率无法反映流动人口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实际上,越是有活力的城市和地区,流动人口越多,他们往往也是非常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劳动群体,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8]。但是他们的作用却无法体现于户籍口径的城市化率之中。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一个城市和地区人口的年轻化和知识化技能化主要依赖于流动人口。如果采用常住口径的城市化率,有可能会改变这一系数的符号。
产业结构变化对于产业效率,尤其是第二产业效率的提高有着显著而积极的影响。instrc是GDP中第二产业比例/第三产业比例,因而这一比值的上升反映了第二产业扩张比第三产业更快,也可以说是以工业化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战略的结果。这一过程强化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相应地削弱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故而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会有差异。如前所述,第二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实际上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而高质量的服务业往往需要有高水准的制造业作为后盾。而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拉美国家问题则突出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失衡,以墨西哥为例,受二十世纪末金融危机的影响,墨西哥都市圈第二产业迅速收缩,转变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失去了第二产业支持的第三产业大多数以低端服务业为主,因而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许多拉美国家也都有类似的产业特征,这一教训给中国的启示是一定要处理好产业间的协调关系,即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才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区域和时期变量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显著,这意味着产业效率的提升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差异。沿海地区产业效率提升显著快于内陆地区,自1998年以来,产业效率的提升也显著快于之前。

表2 FDI与产业效率回归结果(2005-2010)
(二)稳健性检验
利用2005-2010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用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我们以2008年作为这段时期的分界点,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许多经济变量而言,可能都是一个显著冲击,尤其是FDI受到更加显著的冲击。
从表2可以看到残差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的情况。因此,我们的模型设定及采用系统GMM方法是合适的。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产业效率的作用是积极而显著的,而FDI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第二产业及非农产业整体效率的提高依然起着积极而显著的作用。可以看到,基本结论与之前的分析一致。
地区人力资本和地区对于教育科研的财政支持对于产业效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了自2004年以来民工荒现象带来的深远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只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得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竞争优势的外向型企业大量扩张,导致对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需求大幅上升。尤其是,当沿海发生民工荒现象后,企业并没有采取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水平为核心的变革,而是采取向中西部转移的方式来应对,从而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全国漫延。这种情形也使得区域这一变量在回归中不再显著。类似地,教育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研究轻实用的导向也使得教育科研投入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从而难以对产业效率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时期虚拟变量在回归中并不显著,可能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迅速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措施有关,“四万亿”投资计划的逐渐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经济增长在2009年下半年就回归高速增长路径。相应地,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依旧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产业效率也就不会有显著改变。
值得指出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最直接的体现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研究都已经证实。因此,人力资本和科研创新对于产业效率影响不显著可能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有关。
对比表1和表2两段时期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产业效率在2005年之后处于相对稳定,增长也不如之前那么迅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6年针对5000户企业的调查数据表明,1999~2003年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减员增效改革不断深入,下岗职工人数大幅增加,企业职工平均人数呈直线下降趋势,而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大幅提高。2004~2005年随着职工人数的稳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趋于稳定[59]。可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制度变迁有密切关系。而在制度稳定之后,恰好更能够理解影响产业效率其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虽然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上升,但是由于全球化生产使得价值链重新做区位分布调整,产品价值链中劳动密集的环节放在中国生产,因此反而使得出口产品对于技术水平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这可能是FDI对于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数据表明,我国大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是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制造基地,其布局和效益深受全球化分工的影响,大多数外资企业的核心研发部门并没有设在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FDI对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贡献有其深刻的国际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效率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FDI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FDI与产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利用1989-2010年期间的地级面板数据,通过分析产业内的技术外溢程度,测算了FDI对于产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于产业效率提升的作用有限,尤其是对第二产业效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仅对第三产业效率提升有一定的作用。这种情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FDI长期以来以组装加工生产为主导有关,也与跨国企业在全球制造业的分工格局有关。研究还证实,中国产业效率提升主要来自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产业结构的转变、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科研创新的推动,自主创新才是中国产业效率提高的关键,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总体上是不成功的。本文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得到的结论进一步印证了FDI对产业效率提升不显著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未能成功实现原有目标的已有结论。
产业效率的提升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在2010年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很多研究将“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中国当前或未来将会面临的风险。例如,世界银行曾指出,中国快速但失衡的增长导致了经济矛盾和社会压力的累积,如果搁置这些问题则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60]。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增长速度的放缓,使得产业效率较低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有效提升产业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科研创新以及加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是提升产业效率的重要途径,从而也是保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去过三十多年经济成长也依赖于投资的迅速增长,然而投资也会受到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更应该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培育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本,而且也应当合理推动城市化。
FDI与中国产业效率变迁的关系也为中国引进外资提供了参考。今后在引进外资时,应当优先考虑能够促进产业效率提升的企业,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应当限制组装加工模式的外资企业,更多地考虑能把研发部门落在国内的外资企业。而对于内陆地区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向内陆转移,组装加工型外资企业也同样会随之向内陆转移,内陆地区在利用外资时同样也要考虑到产业效率提升问题。基于沿海地区的经验,内陆地区在利用外资时,更应当重视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外溢效果。
应当推动城市化建设,以城市化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产业效率提升。切实有效地推进城市化,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城市化真正能够发挥其积聚人才和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我国现有的城市化并非是完全的城市化,城市中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并享受城市服务的人口,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仍与户籍密切相关,享受城市服务的人口也难以自由迁移。这不利于城市人口结构的优化,从而很难起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作用。而城市人口结构的优化恰恰是提高产业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61]。人口结构优化也是城市保持竞争力的有效举措,这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都可以得到印证。
[1] 王智勇.产业结构、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13(5):23-34.
[2] 金祥荣,茹玉骢,吴宏.制度、企业生产效率与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J].管理世界,2008(11):65-77.
[3] Romer P.Idea gaps and object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43-573.
[4] Hine R,Wright P.Trade with low wage economies,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UK manufacturing[J].E-conomic Journal,1998,108(450):1500-1510.
[5] Greenaway D,Hine R,Wright P.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rade on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5:485-500.
[6] Bayoumi T,Coe D,Helpman E.R&D spillovers and global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47:399-428.
[7] Coe D,Helpman E,Hoffmaister W.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institutions[R].NBER Working Papers 14069,2008.
[8] Aitken B,Harrison A.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Venezuel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605-618.
[9] Konings J.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firms:Evidence from firm-level panel data in emerging economics[J].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1,9(3):619-633.
[10] Rosenthal S,Strange C.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1,50:191-229.
[11] Javorcik B.The composi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4,48(1):39-62.
[12] Polenske R.Leontief's spatial economic analyses[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995,6:309-318.
[13] Jaffee A,Manuel T,Rebecca H.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s evidenced by patent citation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3):557-598.
[14] Caves R.Multinational firms,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J].Economica,1974,41(5):176-193.
[15] Kokko A.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43(2):279-293.
[16] Helleiner G.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Chenery H,Srinivasan T.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II[C].Amsterdam:North Holland,1989,1441-1480.
[17] 张帆,郑京平.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结构和效率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9(1):45-52.
[18]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19] 张海洋.R&D两面性、外资活动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05(5):107-117.
[20] 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29-36.
[21] 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3(6):3-7.
[22] 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23] 毛日昇.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就业[J].经济研究,2009(11):105-117.
[24] 喻世友,史卫,林敏.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渠道研究[J].世界经济,2005,(6):44-52.
[25] Markusen J.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85-95.
[26] 华广敏.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效率影响的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2(12):58-66.
[27] Francois J,Woerz J.Producer service,manufacturing linkages,and trade[R].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No.045,(2).2007.
[28] 卢锋.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J].世界经济,2007(8):22-35.
[29] 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中国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9):14-21.
[30] 方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1-2006年数据[J].世界经济研究,2009(3):50-52,74.
[31] 巫景飞,林暐.本土制造业从商贸流通业的FDI中获益了吗?——来自中国2002-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贸经济,2009(12):117-121.
[32] 王志鹏,李子奈.外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3(4):17-25.
[33] 何骏,郭岚,朱妍娜.中国引进服务业FDI效率评价与分析[J].经济地理,2012(7):93-99.
[34] 韩德超.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企业效率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11(2):65-70.
[35] 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J].经济研究,2001(10):13-19,28.
[36] 蒋殿春,张宇.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08(7):26-38.
[37] 蒋殿春,张宇.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FDI外溢还是制度效应?[R].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7.
[38] 庞英,王伟,孙巍.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民族资本与FDI谁更有效[J].世界经济研究,2008(1):10-16.
[39] 包群,赖明勇.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2(6):63-66,71.
[40] Lucas 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12:3-12.
[41] Black D,Henderson J.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07:252-284.
[42] Lucas R.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S1):29-59.
[43] Moretti E.Workers'education,spillovers,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plant-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3:656-690.
[44] (美)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45] (美)钱纳里,卢宾逊,塞尔奎因.工业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吴奇,王松宝,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46] Sachs J,Wing T.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J].Economic Policy,1994,18(1):102-145.
[47] 周英章,蒋振声.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实际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146-152.
[48]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31.
[49] 李玉红,王皓,郑玉歆.企业演化: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J].经济研究,2008(6):12-24.
[50] Gorg H,Greenaway D.Much ado about nothing?Do domestic firms really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04,19:171-197.
[51] Hale G,Long C.What determine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China[R].Federal Reserve Bank Working Paper,13.2006.
[52] Romer 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S71-S102.
[53] Nelson R,Phelps E.Investment in humans,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56:69-75.
[54] 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中国分省人力资本存量估算及其影响[R].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Working Paper,2005.
[55] Arellano M,Bond S.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77-297.
[56] Arellano M,Bover O.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29-51.
[57] Blundell R,Bond 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143.
[58] 王智勇.流动人口与经济发展——基于地级市数据的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3(3):12-20.
[59]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企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查[J].中国金融,2006(20):35-37.
[60] Word Bank.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EB/OL]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STASIAPACIFIC/Resources/226262-1158536715202/EA_Renaissance_full.pdf,2007.
[61] 王广州,王智勇.人口结构优化的国际大都市经验和对北京的启示[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3):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