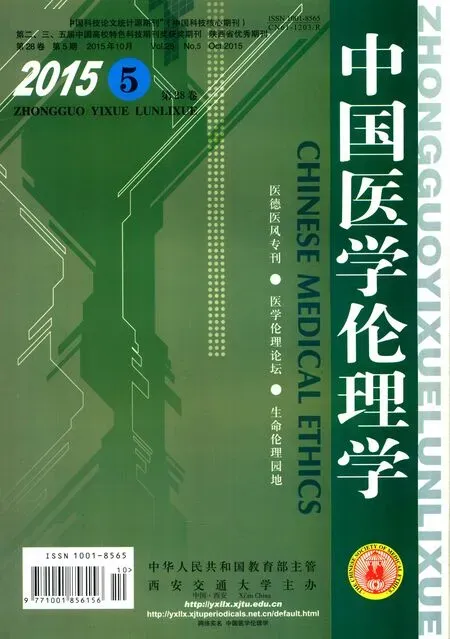论健康责任
李红文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hongwenli@126.com)
论健康责任
李红文
(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hongwenli@126.com)
区分健康责任的前提是正确判断责任划分的原则及条件。可控制性责任观为健康责任的划分提供道德基础,即主张以内在的可控的因果关系为判断责任的必要条件。健康责任的建构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面对当前中国的现实,必须构建以政府责任为主导、以家庭和社会责任为主干、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健康多元化责任原则体系。
健康责任;可控制性责任观;政府责任;个人责任;社会责任
在当下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健康责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通常为学者们所忽视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公民个人、社会大众及政府组织在医改中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关涉到医改方案实质性内容的确定和普通民众对改革前景的期待。为了构建一个有效合理且在伦理上可辩护的具体实施方案,必须对健康责任进行清晰的界定。
1 可控制性责任观
在划分健康责任之前,必须对责任概念本身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可控制性责任观为健康责任的划分奠定了较为可靠的道德基础。可控制性责任观主张以内在的可控的因果关系为判断责任的必要条件。内在的可控制性意味着服从于人的意志的改变或调节。这种责任观实际上承诺了责任主体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道德行动者,小孩、精神病患者等无完全行为能力者或无法成为责任主体。
责任的归因还存在着责任的减少或免除的情况。责任过程开始于一些事件,如果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个人的原因参与,就不存在个人的责任,属于无责任;如果有个人的原因存在,但是这种原因完全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够控制的,那么个人也没有责任;如果只是部分地不能控制,那么个人就要承担部分责任,这就是属于责任的减免情况。无行为能力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他们就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比如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这完全超出了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够控制的范围,所以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但是,地震发生之后,特定职业者就应该做出符合自己身份职业的道德行为。
可控制性责任观的道德基础实际上来自康德对自由意志的界定。康德划定了价值领域与知识领域、道德领域与科学领域。他认为,在科学领域一切都服从自然法则,在这里自然的机械作用必然始终构成向导,一切都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无所谓自由。但是在道德实践领域,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性,才确立起道德责任的根据、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以及人的尊严和人格。在自由意志领域,道德责任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以自由为根据的自我立法。因此,“责任”与“自由”是内在统一的,责任和自由与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康德提出了如下的定律:“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与之相符合的义务的唯一原则:反之,任意的一切他律不仅根本不建立任何责任,而且反倒与责任的原则和意志的德性相对立。”[1]如果人失去了自由意志,那么一切都受到自然界的必然规律的约束,一切都是被规律决定的,那么人就不是自主的个人,就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是一台机器,作为机器是没有理由让其承担任何责任的,就失去了担当责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康德的论述告诉我们:个人的自由意志是确立道德责任的基础和根据,个人自由意志的丧失,意味着个人成为与物、与机器无异的存在,是根本谈不上道德责任和道德信念的。
可控制性责任观受到了盖伦·斯特劳森(G.Strawson)的质疑。[2]他认为,道德责任与一个人的行为或性格的因果历史相关,为了能够真正地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就必须成为自己性格的原创者。斯特劳森的论证受到了研究者们的批评,他的论证存在如下假设:在决定论条件下,行动者不可能对其决定的根据负责;这个假定不言而喻地意味着,我们的行动的一切因果前提都是由我们无法自主支配的因素决定的。“如果真正的道德责任要求行动者用一种不受任何外在影响的方式把自己的自我独立地创造出来,那么我们大概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自我,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道德责任实际上取决于人类个体所能具有的某些能力,例如反思性地认同价值观念的能力,按照这种认识来采取行动和控制行动的能力,那么道德责任对我们来说就不仅是可能的,也是任何值得向往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本质要素。”[3]
实际上,责任的判断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并不像斯特劳森所认为的那样是“全有”或“全无”的问题。这种程度上的差别,就为责任的减轻或免责提供了道德理由。比如,在主观意志上存在有意与疏忽大意的差别。有意是指从事可以预见的并且知道其后果的行为,比如谋杀、逃税;疏忽是指由于主观上的差错而导致不好的结果发生,比如误杀和缴税。很显然,故意行为要承担全部责任,疏忽大意一般也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尤其是在职责范围内的疏忽大意,比如医生做手术时的疏忽大意造成对患者的伤害,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在在后果很轻微或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疏忽大意可以减轻处罚或免责。此外,在道德原则冲突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由于服务于更高的道德目标或道德价值而导致责任的减轻或抵消。比如,由于照看生病的父母而无法正常上课,或者在上学的途中帮助盲人引路而上学迟到。很明显,这些都是道德上值得赞许的行为,这种情况下的个人责任应当予以免除,以鼓励人们做好事。
2 健康的个人责任
按照可控制性的责任观,人们应该对自愿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承担责任,责任是自由的代价,是作为自由的公民宣称自我决定权应该付出的代价。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偏好、个人目标、价值观、人生计划,这意味着一旦这种选择的结果不怎么如人意,人们应当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个人选择了冒险,别人就能合理地期待他独自承担冒险的后果。
首先要区分的是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德沃金认为:要求政府采用这样的法律或政策,它们保证在政府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公民的命运不受他们的其它条件(他们的经济前景、性别、种族、特殊技能或不利条件)的影响,[4]导论这是一种集体责任。同时,就一个人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而言,在资源和文化所允许的无论什么样的选择范围内,他本人要求对做出那样的选择负起责任,[6]7这是一种个人责任。
就健康而言,个人责任意味着选择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在个人能够合理控制的范围内减少健康风险因素。健康和长寿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这激励人们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的健康。为了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首先要理解个人行为和健康之间的因果关联,然后接受这个观念:在一定程度内我们能够控制自身的健康状况。个人健康行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非传染病上。在发达国家,非传染病逐渐成为导致疾病和早死的主要原因,[5]国家的传染病干预措施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对于非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不是国家的干预,而是个人的健康生活方式。这就要求个人行为模式的改变。
个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禁止冒险行为,禁止冒险的例子包括,开车时系安全带、骑摩托车时戴头盔。降低治疗时的优先顺序,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肝脏移植,对于嗜酒者,同等条件下他们不能得到优先移植,有人认为这么做是对酒徒的歧视,但是考虑到器官来源的稀缺性,若给嗜酒如命的人移植就是资源浪费。强制保险主要是在事发之前以特定税收或使用费的方式来强制征收的,对一些危险的体育活动就必须这么做。
个人的健康责任在健康政策上有相应的体现。一般来说,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对于那些采用冒险生活方式的个体,他们在接受治疗方面享有较低的优先性,或者应该支付额外的保险费用。在公共卫生政策的层面上,也应该考虑到个人的责任。有限的公共资源应该投向那些非自愿地卷入疾病之中的人群,而不是那些自愿的冒险人群。为了让个人能够完全承担起相应的健康责任,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为个人提供健康信息、健康知识和健康教育。对于那些影响健康的风险因素,可以采用公共健康的措施来进行干预。
3 健康的家庭责任
健康的家庭责任意味家庭成员之间应该关心和照顾彼此的健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相互支援。这种相互照顾和帮助的责任,不仅是一种最自然的义务,也是最合乎人伦道德的义务。从人的生物性本能和自然情感来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使得他们对子女无限关爱、无限帮助成为可能;而子女对父母的照料也是由最自然的情感所引发的回馈行为。因此,个人作为家庭内成员的自然事实导致了相互责任的必然性。
家庭责任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儒家仁爱原则。儒家思想从关系型的角度来理解人,从个人在家庭的位置来规范个人的行为,仁爱原则正是从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自然关系中产生的。范瑞平认为:“亲子关系不仅构成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联系,而且生动展示了人性中最深刻和最高尚的一面,即每个人都具有同情的能力,亦即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这种自然的同情心本身包含爱的倾向。对孔子而言,亲子之爱是仁的基础……必须培育并推广以亲子之爱为本的仁,才能构建善的社会。”[6]118可见,儒家的仁爱基于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这种亲子之爱超出任何一种契约关系。
但是,对健康家庭责任的辩护并不必然承诺儒家的价值观,完全可以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对家庭责任予以辩护。
首先,可以把基于特殊的家庭成员关系的仁爱原则看作为一种自然义务,而不必将它纳入儒家家庭主义的人性观和价值观之中。罗尔斯认为,“相互援助和相互尊重”是针对个人的自然义务,[7]这一点可以应用于家庭成员之间在健康方面的关照。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援助可以基于爱的情感或同情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但是,爱和同情心并不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援助的义务也不限于家庭成员之间。
其次,儒家的仁爱是一种差等之爱,这种差等之爱是人的自然情感,正义的原则不能仅仅止步于这种自然的情感行为,而是应该诉诸于平等关怀的普遍精神。范瑞平认为:“在儒家看来,福利主要属于家庭负责的范围;由政府采取全面的福利计划来实现每个人福利的平等,是错误的做法。”[6]123应当看到,将家庭作为福利的主要责任主体,并排除政府的平等关怀,这种偏颇的论断显然过于武断绝对,它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家庭的人,也没有考虑到家庭关怀的有限能力。政府的平等关怀与个人的不平等关怀完全可以并存,政府的平等关怀并没有排除个人去追求以德性为基础的儒家式生活。
第三,家庭责任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德性为目的,对家庭责任的辩护并不必然要承诺一种充满内容的目的论框架,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完全可以容纳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对健康的关爱与照料责任。在儒家看来,德性是一种内在善,缺乏内在善的生活不会是真正意义上好的生活,即使这种生活在工具性善方面非常富足。对自由主义而言,个人在实现家庭责任的过程中究竟追求何种目的,这完全交给个人自主来决定。自由主义并不排斥儒家以德性为基础的目的论框架,反而给予充分的自由让个人追求之,它所反对的只是儒家把德性当作唯一值得追求的内在善。根本而言,究竟选择何种善的生活、何种善的生活观念,这应该由个体自身来决定,而不应该做预先的家长主义式的独断决定。
因此,在家庭的范围内,互助的仁爱构成了一种自然的义务,这是家庭健康责任的道德基础。但是,它不必承诺一种儒家家庭主义的人性观,不必承诺一种以德性为基础的目的论框架。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儒家思想也能够为个人的健康责任提供道德理由。[8]
4 政府责任与社会责任
德沃金对政府责任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如果对于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它也不可能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当政府削减福利计划或放慢其扩大的速度时,它的决策将使穷人的生活前景黯淡。”[4]1-2德沃金的要点在于政府对公民的平等关切,也就是说一个统治公民并要求其忠诚和守法的政府必须对其全体公民一视同仁。这一论点显然来自他对平等价值优先性的追求,平等在德沃金那里被称之为至上的美德。如果平等确实如德沃金所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平等的关怀,这恐怕是平等理论的核心所在。因此,对政府责任的辩护,最根本的是要指出政府责任最终必然要落实到什么地方,这样才能构成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伦理辩护。
按照责任政治的要求,政府的健康责任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政府应该把增进人民健康作为卫生工作的首要目标。健康是社会发展之根本,也是卫生服务和卫生改革的根本目的。健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缺乏健康素质的人无法成为强大的生产力。其次,政府要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卫生工作是一项跨专业、跨学科的活动,牵涉到各个部委之间的合作,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协调起来,把卫生工作的目标、内容和任务变成各自目标、内容和任务的一部分,各尽其责。第三,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卫生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各项卫生事业有法可依。对于已有的法律规章,要及时根据现实情况予以完善。第四,政府应组织实施健康教育,促进公民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运用现代传媒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提高公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最后,公共卫生是政府责任中的最重要的一项职能之一,长期以来遭到忽视,因此有必要引起重视。在传染病预防、非传染流行病控制等方面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力度,真正有效地促进人群健康。
政府责任回归健康领域,不仅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健康产品外部性的客观要求,更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市场体制下,政府在卫生领域的责任是有限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筹资与购买)、政策规划责任与监督管理责任。经济责任是保障健康公平的前提,包括政府筹资与投入分配;政策规划责任是健康公平实现的机制保障,要求政府为社区医疗建设以及社会资本进入卫生领域制定合理的政策;监管责任是健康公平实现的必要保障。
除了政府责任之外,社会责任也是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责任是公民或社会团体超越于利己行为之外的职责行为或者利他行为。社会责任并不必然要求个人具有高尚的利他主义行为,而只要求一个公民作为社会成员应当承担的适度责任,对社会团体的公共责任也是如此。就健康而言,公民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积极参加与人群健康有关的社会公共活动。例如,植树造林的环保活动、戒烟的宣传教育、AIDS防治等。其次,不做危害他人健康行为的举动,不侵犯他人的健康权益。比如,不在公共场所抽烟,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等。
对社会责任的一个辩护来自德国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对共同责任的论证。[9]他的共同责任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共同责任一方面是指人们作为对话者共同寻求认清和解决问题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保证人类的持续存在与努力谋求改善社会制度环境,实现对话的规范性条件的共同责任。对阿佩尔来说,共同责任是一种“原初责任”(Primordiale Verantwortung)。阿佩尔强调共同责任不同于传统的、可落实到具体个人的责任,比如一个人的角色义务或职责。这种具体的责任是一种外在的制度和习俗的规定。共同责任属于制度之上的责任,这种制度之上的责任并不是要否认传统的具体责任,而是要跳出传统责任观的窠臼,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制度的构建。也就是说,个人的责任行为参与了制度的建构这一事实要求每个人承担他所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这就构成了共同责任的基本内涵。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健康的个人责任、家庭责任、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时候某种责任占据主导地位,有时候多种责任共同参与了健康行为结果的建构。比如,慢性病不具有经济上的外部性,个人的不良生活方式是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个人责任在此占主导地位;而传染病则具有外部性,且在外部传染的过程中个人能够控制的影响程度较小,因此它应该主要由政府和社会来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中的责任问题就更为复杂。比如,艾滋病,有些是由于个人婚外性行为、吸毒、同性恋等个人原因造成的,有些则是由输血等非个人原因造成的。按照个人责任原则,那些由吸毒等个人原因导致的艾滋病似乎应该完全由个人来承担,但是这显然违背了公共卫生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质目标,没有考虑到这种非常规性治疗中的社会集体责任,因为对于这样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依靠任何单个个体的力量都是无法有效解决的。因此,对于艾滋病等具有强外部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政府和社会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福利国家的健康政策常常是过度强调了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忽略了个人责任。普遍的福利政策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最低的福利水平,不管个人是否应该对健康问题承担责任。这种由社会和国家大包大揽的健康政策虽然符合健康公平的道德直觉,但是却忽略了个人责任的成分。如果社会有责,意味着人人有责,而人人有责在实践中就会导致人人无责。这种完全由政府包揽的模式会误导职工的医疗行为、造成浪费、自我保健意识的淡化和监管的丧失。
综上所述,健康责任的建构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政府、社会、家庭与个人各负其责,才能有效地实现公民的健康权益保障。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最为妥当的办法是以政府责任为主导、以家庭和社会责任为主干、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健康多元化责任原则。任何一方的责任都不可偏废,才能有效地实现健康社会的目标。
[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
[2]Strawson,G.The impossibility of moral responsibility,reprinted in Louis P.Pojman and Owen McLeod(eds.),What Do We Deserve:A Reader on Justice and Deser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106-107.
[3]徐向东.自我决定与道德责任[J].哲学研究,2010,(10):99-106.
[4] [美]德沃金.至上的美德[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Richard Skolnik.Essentials of Global Health[M].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2008:27.
[6] 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9.
[8]刘俊香,张旭平.儒家视野下的个人健康责任[J].伦理学研究,2015,(2):101-132.
[9] 罗亚玲.阿佩尔的共同责任原则[J].哲学动态,2008,(9):45-49.
〔修回日期 2015-09-03〕
〔编 辑 金 平〕
On Health Responsibility
LI Hong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hangsha 410208,China,E-mail:hongwenli@126.com)
To differentiate health responsibilities in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hould judge correctly the principle and conditions of responsibility division.It is deemed that the controllability view of responsibility provides the moral basis for health responsibility,which claims that the controllable causality is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judgment of responsibility.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 responsibility is a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In face of the current reality of China,must build a diversified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system: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factor,the famil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the backbone,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s base.
Health Responsibility;Controllable View of Responsibility;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Personal Responsibility;Social Responsibility
R-052
A
1001-8565(2015)05-0748-04
2015-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