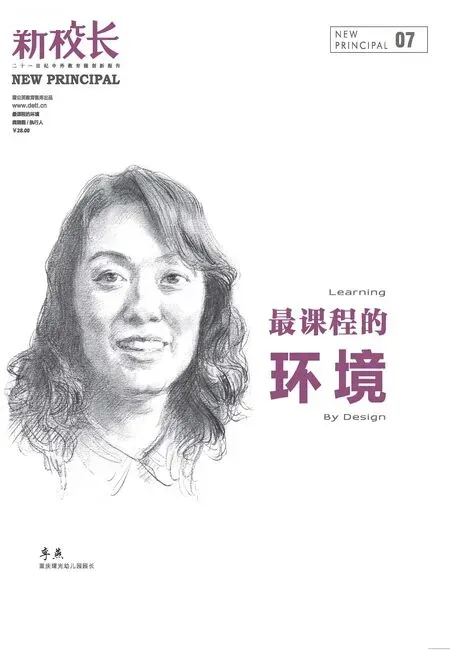“耕读”教育的意义
文 / 李泽武(中国第一所华德福学校校长)

“孔夫子解释说,一份钱可以买食物,另一份就可以买鲜花。当问到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孔夫子回答说,用一份钱一个人可以使生活成为可能,用另一份钱它可以使这个人的生命有价值。”
在我的《我在英格兰学师范》一书的序言中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斯坦纳华德福课程指导芮维·梅弗姆写了这段话。我后来查证,也不知道这段话原文出自哪里。有一天到新近结识的一位画家朋友那里,她提到“耕读之家”,倒点醒了我。
来我们成都华德福学校的人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竹篱绿藤,野树片瓦,并认为华德福学校就是这样一种乡村的风景。华德福教育强调人与自然的结合,但不是非得“燕子来时,碧水人家绕”。不过农耕与教育紧密结合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人首先是宇宙的子民,其次才是社会的一员。
耕读,与前面芮维所提到的孔夫子所言食物和鲜花都是共通的,都是在说人的物质支撑和精神追求。
物质的重要性用成都乡下老农的话来说就是“饭是莽莽(mang mang),肉是尜尜(ga ga)”,声音里充满“硬道理”。这些都是实在的事物,不是空洞的联想。我们由矿物质和水组成的躯体不停地有能量要求。我们需要满足,便利。“耕”不仅仅在农业社会意义重大,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支柱之一。不用说我国政府对农业大政方针和社会形态的关注,我回国那一年,《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投入了8亿英镑资助英国国内的20多家自然活力(biodynamic agriculture)农场,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也可见其一斑。
“耕”提供着物质,支撑着精神。“耕”的过程也同样产出着精神。“耕”首先是对大自然和宇宙的认识和遵从,古代文明中天文学的发达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还是我们的文明。这种认识和遵从是与大地亲近的结果,是与宇宙精神(the spirit of cosmos)亲近的结果,是与“道”亲近的结果。
“不违农时,谷不可以胜食也;斧斤以时入林,树木不可胜用也。”(《四书》)由此也会产生敬畏和感恩——“大地给我美味的食物,太阳使它成熟可口,亲爱的大地、亲爱的太阳,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而不是“我们的食物从哪里来?”“从超市里边来。”
“耕”也可以提升个人心灵。它强调做,而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做”是直接地实践,更多地涉及的是意志行动力,或是简称为“意志”。它植根于身体,有内在的冲动和力量。“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教育不时关注的问题,“耕”就是“行”,就是“施用”。“每一个人都应当与这个世界上的劳作保持着最基本的联系。”(拉尔夫·爱默生)
“耕”需要更多的等待。季节和成长的等待,那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耕”给人以实在,有限度。土地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二十四小时生产,不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束缚是大自然的戒律。西方希腊传统和新教思想解放了人的能力,达尔文进化论助长了工业社会以后夸大这种能力的倾向。“耕”给人以回归,回归到取和舍的“度”上来。
光是“耕”显然是不够的,管子说“仓廪足,然后知礼仪”。我更愿意把“礼仪”看作人的精神诉求。这也是人之为人的东西。而它,更多的是一种传承。因为它是人类文明的直接结果。孩子是灵性的生物,他的内心有着所谓的天生的“内心隐秘的结构”——不管是各种“本能”结构,“集体无意识”,还是“格式塔”,各型“智能”。它们只是进行精神生活的可能——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灵魂)结构。它们需要与外在的需求结合起来。“读”就是这样一种结合,它把人类过去经验和内心结构照应。这种照应不仅仅是学习的可能和意义,更是人的内在需求和向往。“读”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生活。它可以提升人的心灵,促使其努力做一个自明的人。
“人对于自己抱有一种成见:凡是他心灵的产物,他总认为不真实或比较不重要。”(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耶纳)现代西方社会主要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从希腊、罗马基督教新教来的自我主义,从“关心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到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另一种是物质主义的对物质力量的肯定和依靠。前者在笛卡尔、罗素和福柯等人的著作中都讨论良多,后者在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的思想中有很大程度的体现。工业革命的胜利像庄子所说的人产生的机械之心一样,使人们失去了对不可见世界的追索,像拉尔夫·爱默生、鲁道夫·斯坦纳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一般说来,物质的改变是容易的,可见的,要人们去发现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是困难的,“读”就是很好的发现精神世界的方式。
“耕”和“读”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因为它是人的两面,需求的两面,人所承载的命运和“道”。按鲁道夫·斯坦纳的说法,人类意识的发展是由精神主义、理念主义、物质主义,再到现实主义。物质主义的昌盛必须由现实主义的人真正对世界的面对所取代。我们古代“耕读”文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是把这两方面的区别消解了,消解到“治人,治于人”的现世伦理人生上来。“仕”成为重要标准,所有人生的比喻都附到了“治国平天下”上,不信你翻开《老子》《庄子》看看,更不用说正史诸书了。用“仕”来衡量,“耕”是低贱的,痛苦的,而“读”更多是作为工具存在。
“耕”是“耕”,“读”是“读”。这是做事的态度。以前我们强调软性的东西,情感的、感觉的,人以“情”为主。现在我们强调硬性的东西,物质的“坚性”,具体到金钱的“坚性”,“情”以“钱”为主。我们需要硬性的制度和金钱,我们也需要软性的人情和感觉。“耕”中有“读”,“读”需要“耕”。我们需要面包和鲜花来使我们的生命充实又完整。而不管如何发展,“天生百物,人为贵”(楚墓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