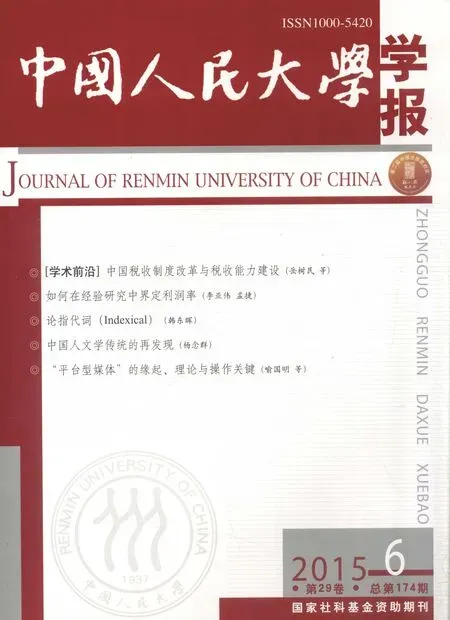消费社会与符号拜物教
欧阳谦
消费社会与符号拜物教
欧阳谦
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矛头指向“消费社会与符号拜物教”,体现了当代文化批判的一种符号学转向。根据他的判断,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从生产资本主义走向了消费资本主义。如果说“生产社会”要凭借“冶金制造术”,那么“消费社会”则依靠“符号制造术”。“消费社会”的关键就是不停地刺激消费以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而刺激消费的秘诀就在于制造出无穷无尽的需要,从而达成社会的持续稳定。制造无穷无尽的需要,必须依靠种种“符号制造术”。消费者被符号的幻象所操纵而迷失在各种“时尚”之中,致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无不受到符码的操纵,这样就形成了消费社会特有的“符号拜物教”。鲍德里亚力图开掘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化维度,以期修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用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逻辑取代生产社会的交换价值逻辑。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符号价值;需要体系;符号拜物教
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当今世界无一例外地卷入到消费社会及其消费文化的扩展趋向之中。因为消费经济的主导作用,当代社会的发展节奏变得如此的整齐划一。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提出:“在我们的时代,当‘最重要的敌人’是传统消费者时,恰恰是消费应该被转变为‘以本身为目的’的活动,它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它除了自身之外,并不服务于任何其他的目标。消费不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消费应该是‘天职’(毕竟,‘天职’就是一个既不需要也不容许理性解释的、禁不住的、强迫的、上瘾的和自我推动的冲动)。”[1](P148)鲍曼的评判指向了一个消费社会的来临。从各种社会学流派到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到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社会”成了一个评判当代社会变局的概念标尺。其中,法国社会学家J.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于符号学的批判性维度,为消费社会批判提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分析路径。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因为持反现代性的激进主义立场而引发了众多争议。研究者不仅关注他的理论思路及其方法论原则,而且也要追问他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及他前后期发生的主题转换。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他究竟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还是一个反后现代主义者?他究竟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还是一个反技术决定论者?他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针对鲍德里亚的批判理论,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仅在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出版的学术专著就不下几十部,发表的论文也有上千篇,不同规模的主题学术会议也举办过多次。*国内出版的专著有《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仰海峰,2004)、《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戴阿宝,2006)、《符号与象征——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研究》(高亚春,2007)、《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孔明安,2008)、《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张一兵,2009)等。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有关学术会议报道和研究综述可参见:《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和2008年第2期,《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国外鲍德里亚的研究权威如Douglas Kellner,Mark Poster,Mike Gane,Steven Best等分别发表有研究专著,并且编辑出版了研究鲍德里亚的英文翻译著作和批评文集,如“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1988)、“Jean Baudrillard: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1989)、“Baudrillard:A Critical Reader”(1994)、“Baudrillard Bestiary:Baudrillard and Culture”(2003)等。本文试图跳出站队式的概念争论,力求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鲍德里亚早期的几部代表作(《物品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等),重点考察他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化社会学思路。我们确实需要问一个究竟:今天的社会如何从一个“冶金术社会”变成了一个“符号术社会”?[2] (P185)或者说,消费社会如何让符号技术压倒了生产技术,并且凭借其强大的符号体系而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极具信仰意义的行为框架。
一、消费时代的符号化症候
鲍德里亚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职业社会学家。他力图与那些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划清界限,以此突显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不认为自己是植根于社会学的。我更多研究的是符号的效应而不是社会学的数据。”[3](P68)对他而言,批判社会学绝不是一种数据化的实证研究,而是一种立足于某种价值取向的社会批判。当代社会的症结问题在于价值取向的迷失,这才是批判社会学的矛头所向。正如研究鲍德里亚的著名学者D.凯尔纳所言:“鲍德里亚将符号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消费社会的社会学结合起来,由此开启了他一生的理论工作,即探索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物品和符号的体系。”[4](P7)他的批判社会学不仅以诊断消费社会的症结问题为己任,而且还专注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学维度,由此而构建了他所专属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针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是M.韦伯、G.齐美尔、F.腾尼斯、W.桑巴特等文化社会学家开创的一项理论事业。显然,他们一方面吸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资源(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行的“文化危机论”中,马克思异化概念被当做一个控诉性的哲学概念),另一方面又不约而同地坚守一种文化主义的思想逻辑,并由此确立了现代社会批判的文化研究范式。事实上,G.卢卡奇、A.葛兰西、T.阿多尔诺、W.本雅明、H.马尔库塞、H.列斐伏尔等建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种范式中衍生出来的。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是将这种范式推到了极点,似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都与文化再生产有关。他对于消费社会所展开的符号学批判,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强调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有效运行在于需要和符号的控制,因此,应该放弃马克思的“生产之镜”而换上他的“符号之镜”。
依照鲍德里亚的描述,如果说前工业社会遵循的是对自然物(如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神秘崇拜,工业社会围绕着生产活动形成了资本霸权和商品崇拜,那么,今天消费社会的迷狂则是陷入了对于符号价值的崇拜。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人类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物品。在今天的消费者看来,与超级购物中心和大型游乐园相比,天堂的景象也大抵不过如此。现代人被物品所包围,被不断更新换代的东西所困扰(今天的消费者不得不跟上电子产品的更新节奏)。“今天在我们的四周所呈现的是一个由倍增的物品、服务和财富所构成的幻景,它构成了人类生态的根本变化。确切地说,富足的人们不像以往被人所包围,而是被物品所包围……如同狼孩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狼一样,我们也逐渐地变成了官能性的。我们就生活在物品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按照其节奏和惯性来生活。”[5] (P17-18)
的确,我们置身于消费社会的各种景观之中,满眼都是符号化的物品和物品化的符号。无论是服饰还是食品,都被打上了某种符号的印记。服饰和食品的功能性作用已经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符号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所谓的“时尚”,而“时尚”则是维持一个消费社会不断运转的“永动机”。当消费者追逐时尚的时候,其内心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因为消费者是在拥抱一个符号(“漂浮的能指”),在某种“能指的游戏”中被弄得神魂颠倒。时尚的消费或者符号的消费带来了一个歇斯底里的世界。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其行为如同中魔一般而陷入疯狂的境地。“我们想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消费。消费的强制性格并非来自心理上的某种宿命性(比如喝过的人会更想喝等等),也不是来自社会威望单纯的强制力。如果消费似乎是克制不住的,那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完全唯心的作为,(在一定的门栏之外)它和需要的满足以及现实原则,没有任何关系。”[6](P227)现代人普遍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症,在于他所信奉的符号拜物教。现代人差不多抛弃了“上帝”的旧神话转而接受了“消费”的新神话。“今天,当宗教和意识形态作用机制退隐之时,它们正在成为安慰中的安慰,正在成为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的日常神话逻辑。”[7](P111)信仰逻辑变成了消费逻辑。人类已经被物品所包围,最终被物品所左右而变成物品的奴隶。以往是人类在控制物品的节奏,今天则是物品在控制人类的节奏。“汽车在此扮演了一个特别突出的角色。人在它身上付出的是为了最好和最坏的所有的目的。他在它身上获得了服务,但他也在它身上接受以及等待某一类的宿命,那就好比电影之中,在汽车里的死亡以及成为一种仪式性演出。”[8](P143)这种汽车消费文化似乎潜藏着人类的某种宿命:或许不是人类在驾驭机器,而是机器在驾驭人类。
从鲍德里亚的理论立场看来,消费社会之所以患上普遍的歇斯底里症,正是起因于技术上的迷狂。在这种无止境的技术追求的背后,则是人类的虚荣心在作怪。人类的生理需要是有限的,然而虚荣心的满足则是无止境的。凭借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先进手段,人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社会的种种迷狂。消费本身如同语言一样构成了一种意义系统。消费物品其实是在消费符号,是在传递某种社会差异的信息。“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9](P224)对于消费社会的这种符号化魔怔,实证社会学的分析力不从心,消费心理学往往流于表面,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则有待深化,对于鲍德里亚而言,似乎只有符号学的批判可以做到对症下药。这或许与他身处时尚之都巴黎有着某种直接的关系。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消费社会”,巴黎拥有享誉世界的奢侈品牌,如路易威登和香奈儿等;作为一个引领艺术风尚的创意之都,巴黎的景观乃至日常生活都充满着艺术设计的色彩。在这个完全审美化的商品世界中,艺术已经融入到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商品设计、广告设计之中,由此而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的“符号社会”和“景观社会”。
德国文化批评家W.本雅明当年就从巴黎商场橱窗里看到了一个商品魔幻世界。他曾有一个“巴黎拱廊街研究计划”,探讨作为商业空间“拱廊街”折射出来的拜物教精神。这种空间以玻璃和照明来显示奢华无比的商品以达到诱惑顾客的目的。[10](P170)在巴黎繁复商业景观的冲击之下,法国文化批评家G.德波提出了他的“景观社会理论”。他甚至将“景观”作为当今社会的生产力,因为景观不仅是对商品幻想的普遍表达,而且使得今天的消费者完全变成了幻想的消费者。按照他的理论分析,“景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跨入了它自己的丰裕性的门内。尽管质的变化至今只是部分地在很少几个地方发生过,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暗示了这是商品的原初准则——通过将整个世界变成单一的世界市场,商品已经实践了这一准则”。[11](P13)结构主义符号学家R.巴特则在他的《神话学》一书中,将符号学分析与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围绕法国社会当下流行的种种时尚,对于“摔跤”、“葡萄酒”、“脱衣舞”等“社会神话”进行了意识形态的真相剖析。在他看来,“神话”的特征就是把意义转化为形式,使得人们无知地消化神话。“现在神话的消费者以意指作用作为事实的系统:神话被阅读为事实的系统,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学的系统。”[12](P191)在鲍德里亚的老师H.列斐伏尔眼里,通过“日常生活批判”可以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操纵型的消费社会,尤其是其中盛行的“广告的恐怖主义”。
这些偏向消费景观和符号作用的理论考察,显然对于鲍德里亚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在延伸和强化这些理论的批判逻辑。只是鲍德里亚更加强调社会批判的符号学维度,并将消费文化与符号拜物教联系起来。从消费社会的符号化症候着眼,鲍德里亚重新界定了“消费”的含义。“消费”已经不仅仅是物质和享受的,而且还是符号性的和区分性的。“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3](P223)诸如家具和汽车等物品,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功能性物品了,而是作为消费的对象更多地具有了一种符号的价值。我们消费的不是它们的物质性,而是它们的符号性。也就是说,汽车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汽车自身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我是谁?我就是我所消费的东西。我开的是“豪车”(比如宝马和法拉利),我就将我自己与其他人群区分开来。我们往往以为是在消费物品,其实我们是在消费各种各样的符号。“在消费社会中,一切都变做了符号,以便供人游戏和消费,包括针对这个社会的最激进的批判。”[14](P22)对于消费社会中的成员而言,消费物品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耗费过程,更多地是一个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现代人大体已经从“需要经济”转向了“声望经济”,即消费的终极目的是对于地位和名望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则是以差异化的符号价值为基础的。这种符号拜物教正是现代消费社会的病根所在。
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物品体系》到《消费社会》,再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产之镜》,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成形,其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符号学思路逐渐明晰。他最早发表的《物品体系》一书,对作为意义构成体系的消费物品进行了分类:第一类是室内设计和家居摆设等功能性的物品体系,第二类是古玩和收藏等非功能性的物品体系,第三类是自动化的机器等过度功能化的技术体系,第四类是信用系统和广告形象等作为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他首先声明:“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15](P2)他的意图不是简单地分析消费物品的类别系统,而是旨在探讨消费社会中不同物品体系的符号结构及其话语逻辑。无论是功能性的还是非功能性的,无论是技术化的还是意识形态化的,所有的物品都属于一个文化体系。例如,“选择这一辆车,而不选择另一辆,你或许把它个性化了,但做出选择这个事实本身,却使你进入了整体的经济体制之中”。[16](P163)
围绕着“消费社会”的符号操纵,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符号的秩序”这一概念,即消费社会中盛行的符号编码化的消费逻辑。无论何种消费品,都是以一整套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不管是服装还是电器,总是属于一个符号系列。消费品不是孤立存在的,消费者也不会从专门的用途方面去看待一个物品,而是一定要联系其他方面的意义。例如,“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作为用具之外,往往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厂家以及商标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看起来是统一的,如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同一条链子,它们不是一连串的简单物品,而是一连串的意义,它们是在相互暗示着更多意义的高档物品,从而使得消费者滋生出一系列五味杂陈的动机”。[17](P20)消费品一方面服从于市场的秩序,另一方面遵循着“符号的秩序”。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购买行为固然与商品价格的波动有关,但更多地还是受到符号意义的诱惑。
在鲍德里亚看来,与以往时代的“消费”不同,如今时代的“消费”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商品直接就是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价值而被生产出来,而符号(文化)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今天任何东西(物品、服务、身体、性欲、文化、知识等等)除非可以被解码为一种符号,否则是不会生产出来的或者无法交换的,不能将它们仅仅看做是一种商品。”[18](P147-148)消费品的商品形式已经让位给符号形式,符号的交换甚至比商品的交换更有意义。当符号的意义成为商品的核心形式,商品直接扮演了意指的作用,即商品超出了它本身的物质性而带着某种信息或者含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文化系统,其符码的控制是一种比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更加有效的社会操纵。现阶段社会运转的根本问题不是对劳动力的剥削,而是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为何马克思没有看到商品的符号价值及其普遍形式?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再划分出作为商品核心和消费逻辑的符号价值。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试图从商品政治经济学转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用符号形式分析代替商品形式分析。原因在于,“事实上,严格说来,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交换价值的批判理论,对于使用价值、能指、所指的批判理论还是有待进一步发展的”。[19](P129)换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处在交换价值的层面上,对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及其消费的唯心主义逻辑尚未触及。
鉴于消费社会中所有物品的符号化和代码化,我们需要弄清物品体系是如何转换成为一个符号体系的,即物品的符号价值究竟是如何衍生出来的。在鲍德里亚看来,关于物品/符号的意义生成问题,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的批判才能得到揭示。他所构建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吸收了F.索绪尔和R.巴特的符号学思想。对于索绪尔而言,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即语言是一个完全形式化的符号系统,其意义和价值均来自语词之间的关系或者结构。符号是由能指(即声音和形象部分)和所指(即思维和概念部分)组成的。能指是符号的物质方面,所指是符号的思想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内在联系。“索绪尔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语言系统并不具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在形式上变化不定。语言本身是它的各个单位所组成的关系系统,这些单位本身也是通过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差别来构成的。”[20](P12)索绪尔通过结构语言学所揭示出来的任意性和差别性等符号学原则,为巴特等文化批评家打开了符号学批判的大门。
巴特不仅将符号学原理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研究,而且还用符号学的眼光审视消费社会的种种景象。因为他相信,“符号学研究所采用的适切性,按定义来说涉及的是研究对象的意指作用。人们只按对象具有的意义关系来研究对象,而不涉及、至少不过早地(即在系统被尽可能充分地建立起来之前)涉及对象的其他决定因素(如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等因素)”。[21](P74)早在鲍德里亚之前,他已经对流行时尚(如汽车和服装等消费品)进行了符号学分析:“这部汽车告诉了我车主的社会地位,那件衣服非常准确地告诉了我衣服主人符合潮流和偏离潮流的程度,这种开胃酒(威士忌,Pernod,或cassis白葡萄酒)显示了主人的生活情调。”[22](P165)在巴特看来,世界充满了形态各异的符号,这些符号都是极其复杂的和隐晦的,因此其意义是需要揭示的。揭示各种符号的意义就是与某种无知进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学不仅是一门社会信息科学或者文化信息科学,而且还是一门文化政治科学。换言之,符号学堪称文化批判之学。
对鲍德里亚而言,“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从符号学的意义理论中寻找符号价值生成的隐秘法则,揭示出符码操纵下的差异化逻辑,并与符号的统治进行斗争。事实上,物品如同语言符号一样,其意义取决于它在物品体系中的关系。或者说,物品/符号的意义不是在其实用的物质性中,而是在其关系的差异性中。“可以肯定,物品是显示出来的社会意指的承载者,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等级的承载者——这一点显示在物品的细节之中,如形式、材料、颜色、耐用、布置——总之,这些物品构成了一个符码。”[23](P37)以往经验主义的假设总是认为,物品最初只有满足需求的功能,其意义是在经济关系中发生的。其实,物品不只是使用的东西,还是一种社会符号的载体。我们必须看到,物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还被赋予了各种符号价值。任何物品,无一例外都存在着作为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作为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作为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和作为象征交换的逻辑。与之相对应的是四种价值原则,即有用性、等价性、差异性、两可性。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以“艺术品拍卖”为例考察了经济交换价值与符号交换价值的转换关系,并且归纳出所有价值之间的转换列表,这就是:(1)使用价值(UV)可以转换为经济交换价值(EcEV)、符号交换价值(SgEV)和象征交换(SbE);(2)经济交换价值可以转换为使用价值、符号交换价值和象征交换;(3)符号交换价值可以转换为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和象征交换;(4)象征交换可以转换为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和符号交换价值。根据这个商品价值的转换关系,鲍德里亚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了经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被想当然地与有用性等同起来),即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的生产过程。他们关注的是生产性的消费而不是非生产性的消费,从而没有去考察从商品形式上升为符号形式的过程,即消费社会中经济体系向符号体系的转换过程。至于符号体系的建立,最典型的莫过于商品的广告营销过程。在消费社会中,广告不仅构成大众传媒的基本内容,而且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符号体系。
摆在鲍德里亚面前的任务,就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被贴上消费社会的标签,是由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编码的符号价值交换系统之中。“商品买卖、购买、销售、占有差异化的商品及其物品/符号——这些现在都构成了我们的语言,构成了一种符码,我们的整个社会都依靠它进行交往和交谈。”[24](P79)消费如同一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系统。也可以说,消费既是一个价值体系,又是一个交往体系。消费作为一种能指的游戏,它不仅将物品转化为符号(抹掉其物理性征),而且还达成了符号的任意性。在能指的自由漂浮下面,或者说在能指幽灵的笼罩下面,世界不过是符号的结果,不过是能指的游戏在现实中的反映。消费社会的普遍歇斯底里症状,正是这种永无止境的能指游戏的结果。人的需要一旦陷入抽象的符号逻辑之中,一旦被符号拜物教所支配和掌控,其意义的追求就会变成种种不自觉的幻象。“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针对能指拜物教的批判,其宗旨是对符号迷狂的警醒。
三、符号操控的“三宗罪”
关于人类的符号行为及其符号模式的研究,始终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取向。德国哲学家E.卡西尔从正面研究了人类的符号系统,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强调“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25](P35)在文化人类学家K.格尔茨看来,文化的符号模式乃是社会组织过程的模板,就如同遗传机制为生理组织过程提供的模板一样。“符号体系既是社会互动行为的产物,也是决定因素;它们对社会生活过程就像是电脑程序对于其操作,基因螺旋体对于器官发展,设计蓝图对于桥梁的建造,乐谱对于交响乐的演奏一样;或者用一个更俗的类比,就像食谱对于烤蛋糕——符号体系是信息源,它在某种可测的程度上,赋予行为的连续进程以形态、方向、特性及意义。”[26](P297)人类的活动往往处于符号表征所构造出来的各种文化系统之中,将物品与符号联系起来是古已有之的经验事实。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中就有大量的器皿和实物,上面都铭刻或者装饰了各式各样的符号和图形,它们都是历史留存下来的宝贵“文物”。“纵然是最具实用目的和功利性的物品的使用,也都是在文化所预设的符号领域里进行的。最具实效的家用物品,如自来水、盥洗用具、家用电器等等,最早也是近150年来,随着西方技术的发展而为人们所普遍使用的;当初在引进这些物品的时候,人们还当它们是奢侈品。因此,即使是最为实用的东西,我们也很难断然将这些有关使用的功能与它们的符号意义完全割裂开来。”[27](P6)在人类的眼里,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物品。不管是什么物品,食品、祭品、礼品、商品等等,都是被赋予了某种意义的。
可是,在今天的商品世界里面,物品的符号意义似乎在不断地超越它的实际属性。消费者更多地受制于物品的身份定位及其符号代码。“不管是史学、人类学或泛文化研究,都已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商品对人们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能够被使用(used),更是因为它的符号(symbolic)意义。在所有的文化形态里,在任何时候,正是使用与符号的相互交织,为人与物普遍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具体的背景条件。”[28](P5)广告在推销商品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将物品的符号意义给以无限地放大和抽象,最后使得广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宗教。鲍德里亚对于符号拜物教的批判,就是拿广告等大众传媒开刀的。当代社会的控制重心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或者说已经从以所指为中心的信息控制转到了以能指为中心的信息控制,其中广告等媒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助推作用。根据M.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广告等媒介是通过文字和图像手段进行观念上的狂轰滥炸,其作用与洗脑程序完全一致。“广告不是供人们有意识消费的,它们是作为无意识的药丸设计的,目的是造成催眠术的魔力……这就是广告的潜移默化功能的一个侧面。”[29](P283)鲍德里亚多少遵循了麦克卢汉的这一媒介批判思想,不过他更加突显了广告等媒介的操控性。在他看来,广告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出色的大众媒介,不过“广告既不让人去理解也不让人去学习,只是给人一种希望,所以广告不过是一种预言式的话语”。[30](P197)广播电视上的节目广告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是在强行灌输当下主流的消费模式。它们所带来的“信息”并非上面的声音和图像,而是潜移默化地塑造出来的感知模式和人际关系。在大众媒介中,听众和观众所接受吸收的不是简单的声音图像,而是其中所潜在的社会逻辑。媒介将所有的东西进行重新编码,将其信息强加给消费者。鲍德里亚针对消费社会的符号乱象,诸如丰盛的神话、需求的变化、流行的艺术、身体的时尚等消费变体,列出了符号操控的“三宗罪”。
第一宗罪是制造社会需要。在符号的操控之下,我们并不是对某种物品有需要,而是对某种差异有需要(对于社会意义的欲求)。追求差异(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异丧失的基础之上的),使得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使得我们无法固定我们的需要。传统的理性主义神话(以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为例)总是幼稚地认为“我买它是因为我需要它”,这种基本需要的满足神话是无助于解释消费社会中的增长逻辑的。在消费社会,真正得到满足的东西不是人的“需要”,而是生产范畴的需求本身,是生产体系产生了需要体系,是工业及其城市的集中带来需要的增长,是竞争而不是喜好刺激需要的膨胀。人对于物质的吸收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消化系统是有限的。然而,人对于社会意义的需要则是无止境的。“‘所谓的消费大众’是不存在的,底层的消费者也不会自发地产生任何需要:只有经过精心挑选的包装,它才有机会出现在需要的‘标志包装’里面。”[31](P82)需要的一系列等级,同物品和财富的一系列等级一样,它们是有社会选择性的。在“符号价值”的诱导下,需要针对的不是物品而是价值。需要的满足必须附着某种价值或者意义,其实就是接受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卷入一种消费的集体仪式。总之,需要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
第二宗罪是制造平等幻影。消费的普遍性是不是达成了民主的普遍性呢?人们总是以为消费的功能就是要消除社会中的不公正(这正是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机制),似乎冰箱的民主和休闲的民主可以导致社会的民主。事实上,“消费并没有使社会整体更加趋向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带来同样的受教育机会,它甚至还加剧了分化……今天每个人确实都能够读书写字,每个人都拥有(或者将会拥有)一样的洗衣机,可以购买一样的口袋书。但是,这种平等完全是形式上的:看起来很具体,其实很抽象”。[32](P76)人们从增长即民主的神话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和幻影。“我们生活在符号的掩盖下而完全不知真相。令人惊叹的安全:当我们在注视世界形象的时候,谁会将闯入的现实与不在场而产生的快乐区别开来呢?”[33](P32)大众传媒并不让我们去参照外部世界,只是让我们去消费作为符号的符号,我们由此获得的不是对于世界进行认识的尺度,而是一种对于世界难以辨认的尺度。“这个世界正是通过符号来发现和解释的——实际上是被切割的,而且是被任意地切割的。‘真实的’世界是不存在的。”[34](P155)
第三宗罪是制造社会迷狂。消费社会已经变成一个迷狂的世界,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升级,不断地超越。身体的时尚变成了对美的迷狂,广告的信息变成了对品牌的迷狂,艺术的创新变成了对超越的迷狂。总之,在“能指的游戏”中,世界似乎失去了控制,整个社会的迷狂就如同患上了肥胖症。“我们的意识文化在过度的意识下崩溃,实在文化在过度的实在下崩溃,信息文化在过度的信息下崩溃。符号与实在被裹在同一块裹尸布中。”[35](P20)消费文化以不断相互衍生的符码垄断为基础。在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可救药地远离了自然的和真实的东西,甚至远离了人类原本的东西。“一种幻觉只要不被公认为是一种错误,其价值就完全等同于一种实在的价值。而一旦幻觉被这样公认,它就不再是一种幻觉。”[36](P52)符号消费是一种无限制的和狂热的消费,因为它面对的不是具体的物品或者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一种意义的符号。比如时尚从不生产任何物品,但却生产出无数没有所指物的符号。追求时尚生活,无所谓真假,无所谓对错,无所谓有用无用。当美丽的逻辑成为一种时尚的逻辑,人们对美丽的消费就会陷入一种迷狂的境地。符号的操控之所以特别有效,关键在于符号形式对于整个社会过程的作用大多是无意识的。
鲍德里亚相信,他手中的“符号之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如同一面社会现实的照妖镜,与马克思的“生产之镜”和弗洛伊德的“欲望之镜”不同,它所映照出来的是消费社会的迷狂。消费社会的病症看起来像是经济病灶,往深处看其实是文化病灶。对于鲍德里亚而言,在消费社会中似乎找不到消解符号统治的现成药方,或许只能从M.莫斯和G.巴塔耶等人类学家的“普遍经济学”中寻求某种返璞归真的“灵丹妙药”。[37]原始人没有现代人这么迷狂,其实行的“象征交换”似乎显得更加的质朴和单纯。不过,即使他从这些人类学研究中看到了某种可能的返璞归真的可逆性选择,但这个患上了歇斯底里症的世界似乎已是无药可救。“符号拜物教”愈演愈烈,因为它不断遮蔽甚至是窒息了客观现实,即用“仿真”代替了真实,为消费者制造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在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中,用来消费的物品在不断地堆积和增值,物品大有压倒人类的趋向,也可能最后走向绝境或者消亡的却是人类自己。
面对如此激烈的甚至是悲观的批判声调,研究者们对于鲍德里亚的思想立场自然产生了诸多的争议。[38]从他探讨“象征交换”的意图来看,他显然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现代性的社会批判家,是一个带有某种“乡愁”的回头派思想家,因为他认为:“我们的意识文化在过度的意识下崩溃,实在文化在过度的实在下崩溃,信息文化在过度的信息下崩溃。符号与实在被裹在同一块裹尸布中。”[39](P20)不过,他的理论思考又往往是纠结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扑朔迷离),原因也许在于他对于技术发展始终持有一种骑墙的态度。“总之,我们面对两种互斥的假设:一种是以技术和虚拟消除所有对世界的幻觉,另一种是所有科学和所有知识都有一种嘲讽人的定数,以这种方式,世界和对世界的幻觉可能永久延续下去。”[40](P73)在这样的思想徘徊中,鲍德里亚的理论视野一方面从“消费社会”转向“仿真社会”,另一方面也从概念分析走向了寓言式的书写,致使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后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化的“命定策略”。
[1]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 [18][19][23][34] Jean Baudrillard.Fora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theSign. St Louis:Telos,1981.
[3] Mike Gane(ed.).BaudrillardLive:SelectedInterviews.London:Routledge,1993.
[4] Douglas Kellner,(ed.).Baudrillard:ACriticalReader. Oxford:Blackwell,1994.
[5][6] [7][8][13][15][16] 尚·布希亚:《物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17][24][30][31][32][33] Jean Baudrillard.LaSociétédeConsommation.Paris:Editions Denoel,1970.
[10] Walter Benjamin,CharlesBaudelaire. London:Verso,1997.
[11]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2] 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4] 让·鲍德里亚:《游戏与警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0] 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1]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2]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5]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6]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7][28] 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消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和拜物现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9]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5][36] 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7] 马塞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乔治·巴塔耶:《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8] 孔明安、陆杰荣:《鲍德里亚:现代社会的一位激进批判者——鲍德里亚思想研究评述》,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2)。
[39][40] 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责任编辑 李 理)
Consumer Society and Sign Fetishism
OUYANG Qian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Jean Baudrillard’s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as a critique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sign fetishism”,represented in some sense the semiological tur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ritique.In his view,western society today had changed from productive capitalism to consumer capitalism.He pointed out that if productive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metallurgy”,accordingly,consumer society was constructed by “semiurgie”.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consumer society must stimulate and increase the needs of the mass.The secret of creating endless needs lies in the creating of a lot of semiurgie.When the sign illusion in consumer society has perplexed the consumer with the latest fashion,the whole society w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codes,thus bringing about the sign fetishism of consumer society.Baudrillard had sought to exp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replacing the logic of exchange values with the logic of sign values,towards the end of amending and correcting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Jean Baudrillard;consumer society;sign values;needs system;sign fetishism
欧阳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