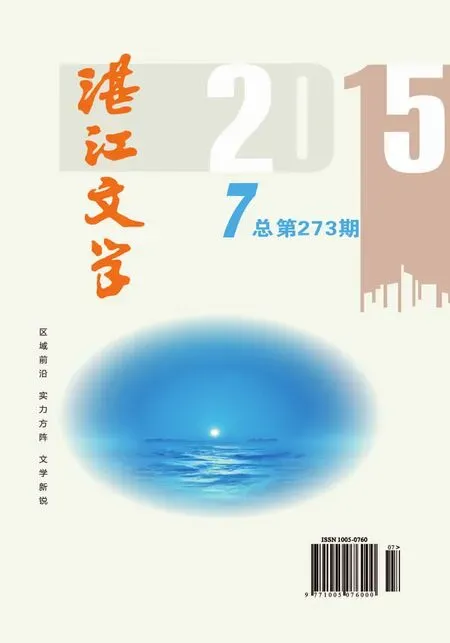沉默的酒壶子
※ 符昆光
王古的父亲老满死后,只为他留下一只葫芦状铜质酒壶子。
老满在世的时候,口袋里总是装着这只酒壶子。其实,这只酒壶子压根儿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口袋。不论在屋里,或者在外头,他从来没有用碗喝过酒。他说,蹶起瓶底仰着脖边听着液体流动的轻柔悦耳的清响,边接着冰凉凉火辣辣香喷喷的液体,慢慢地让它从喉道里滑过,那才够味儿。

喝了大半辈子酒,酒壶子让他粗糙龌龊的手指抚摸得古色古香,居然也有点上几代的韵味。因此超脱的微微醉意间迷迷糊糊地把它当宝贝,总幻想变成传说里孙猴王的宝袋,呼肉唤酒,自然生出芬芬馥郁的酒肉,宛如村南边的河水淌个不可枯竭。
但是,酒壶子亮底后,老满复归粗重的叹息如田野里雨后的蛙鼓声,终不得不又伸手进破烂的草席底掏出沾满尘粉的皱巴角票。更多的偷偷摸摸地走向全家人都勒紧裤头的黑瓷米缸,然后撞撞跌跌七弯八拐来到村巷口铺仔用米换酒。
铺仔就在每逢旧历七月初十唱旧戏的土台边。当铺的自然是本村兄弟,老满的女人还活着的那阵关照过不止三百六十五次,别再卖酒给她那个酒鬼男人,喝了狗尿泡胀脸回家死猪一般躺在旧床破席上,日出日晒雨下雨淋,也不怕有哪天屋崩下来压死这条贱狗命。
当铺的极其可怜这位也喂猪也扶犁的大婶,有几次吼裂喉咙也无法把老满扯走。老满每次硬是笑嘻嘻的就这次吧,有一次当铺的动了真格扇他一记耳光,他也不发脾气,依旧笑嘻嘻就这一次吧。
在僵硬的咳嗽声里,女人鼻尖微微翼一翼,偷偷拿辣椒汁渗进他的白酒里,却把老满他呛得吐白沫差点升了天。从此,女人拿他没了办法再也爱搭不理,人前涕一把人后泪一把地低头哭泣。不久,蔫蔫拉拉的女人,却在僵硬的咳嗽声里归了西。
王古生相象母亲,眉清目秀。过了二十五,还是光棍一条。媒自然是说过几回,可人家一踏进让猪翻成泥浆的庭院,及看到那飘摇欲坠的茅草房,脸上仅有的一丁点笑容倏然打止了。说鸡是狗的媒婆的巧舌此时此刻似乎让火烤熟了再也动弹不得。远村的一位热心亲戚怕断了王家的香火,带来本村的一位跛子姑娘。不巧的是正碰上老满酩酊大醉,从床上搬到床下仍旧呻呤着:“热…热…”女儿兰子已习惯他的醉态,但此刻的她心里酸楚楚的,母亲死后这个家更不象家了。她拿来湿毛巾垫在父亲的额头上,老满却乎拉地站超来:“我…我…未…未醉,你…你给我…滚…”说着东摇西晃地走到庭院里,一脚踢在猪屁股上。猪“拥“的一声腾起,泥浆拼溅死死地贴在同色的墙上。老满傻呆呆地笑着,涎水水泥瓦匠的准线般垂挂在口角上。“竟然占…占我的窝”。说着躺进锗浸凉的窝上。他象猪一样打滚着:“真舒…舒服”。亲戚领着跛子姑娘进来时,老满通脸是红色的泥浆,塞满血色的眼睛流露出狰狞的凶光。跛子姑娘容貌丑陋,三十了还闲置在家里碍人手脚,这次见狗也嫁啦,然而看到老满的猪像,把她吓着了。从此再也没有媒人愿意踏进这个家门。
王家的香火眼看要暗下去,急得老满脸上皱纹拧成个大疙瘩。挽攥在手里的酒壶子不时咚咚响,清洌洌的液体透过他的心底燃烧着理还乱的心绪。
忽然,他一掌拍打在大腿上,说:“有啦!”口对酒壶子连灌几口,抹一抹嘴巴,塞上酒壶子放进口袋,慌慌忙忙向三十里外的陈宅村走去。
老满回来时,村子已浸在浓浓郁郁的暮色里。第二天早上,满村飞快地传达着一个消息:王古拿妹妹兰子兑换媳妇啦!
兰子十九,家虽穷,但她不象王家父子那么窝囊。头发总是梳拢得光溜溜,笑嘻嘻的脸蛋儿总是洗得娇净净。别看她皮肤细嫩嫩,田上的活儿个顶个,犁田播秧挑担是副硬骨头。
昨夜她在厢房里听王家父子的咕噜声,浑身猛然发抖。没了母亲的女儿蒙着被单不敢出声地哭得很忧伤,很苦涩。
日子一下荡到旧历七月,换亲的日子越来越逼近。
王古侍弄着一张缺了脚的条凳,有滋有味地在听着巷外铁匠的叮当声。他的心喜的咕咚跳,口里突然抛出一句硬梆梆的调:
咚锵,咚锵,操的,有媳妇啦!
夜就这么短,黑影淡下,炊烟贴在晨雾里飘动。
王家的茅草房里冲出惨惨的哭声,兰子跟着铁匠跑了。
族长一怒之下,拨出全村青壮年三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兵分四路东西南北搜捕。捉到打铁的,定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茫茫苍苍的丘陵大地太大了,三天后,各路兵马纷纷鸣锣收兵,个个蔫头耷脑魂儿丢丢荡荡。
兰子早跑了,等于丢了媳妇。王古撂下牛绳,不肯去犁田。老满终日攥着酒壶子,心里不停地嘎啦啦吱扭扭,败了我的祖宗啊。从始,夜里人们常听到老满动情的呜呜哭声。后来人们总说,老满的尽数是兰子断的。
葬了父亲,王古没了依靠。队里让他管牛栏,密匝匝的雨丝却没头没脑从天幕上扯下来,下了十天八天还是没完没了,一阵风过来,屋顶上青青的秧苗随着腐烂发霉的黑稻杆给揭了。队长找上门来说:“唉,暂到队屋里睡几天,队里明个儿给你重盖两间。”
王古听了,差点掉出泪。他默不作声,手里抚摸着父亲留下的酒壶子。
液体在壶子里咚咚响,挺沉闷。
队长也不说话,陪着他一址到天黑尽。队长默默站起来,脚沉沉的。
王古也跟着走出牛栏,到了大门,才轻轻地说:“明叔,算了。”
说这话时雨已歇脚。新鲜的夜风夹杂着牛粪味,他们似乎没嗅着。他摸索着走进草料间,重重地摔到乱草堆上。
房子里飘着酒的香气。
酒精燃烧着他的魂儿好迷糊,迷迷糊糊了人世间的苦痛。他直到今天,才懂得父亲为什么珍爱这只紫铜色的酒壶子。
过了几天,队里派人把房子搭好了。然而王古却卖掉家里的母猪,在远离村子草子岭搭起茅草寮,揣着酒壶子住了进去。
小河在野气浩荡的丘陵大地上也不太显眼,似乎是哪位多管闲事的神仙怕凌励的丘陵风刮走那堆堆土丘,才随意抛下一条银链把它们锁住。经过几百几千年的翻滚摔打,小河早年那横冲直撞左突右奔的气概全没了,象一头被驯服后的大莽蛇也不再喘着粗气,匍伏在丘陵的脚下死一般软绵绵透不出一点狰狞。小河左弯右拐扭扭怩怩地探身到草子岭底下时,河面陡然开阔了,没有风的时光静得象一潭死水。
大自然有了人后,便少了野气。毛茸茸的球状鹅子从水草间钻出,生动地浮于碧波荡漾的河面上,呀呀地搅动着这方水土。王古时而看鹅子在小河里啄食,时而看着鹅子浑圆的屁股,拉出的粪渣是黑呀、青呀、还是黄。甚至有时划着竹筏赶着鹅群在河道里兜圈儿。飘够了,才赶着鹅群回岸吃草。如有鹅浮在水面闭上眼睛假寐,可舒畅了,那静谧的感受让他发现夜是那么长,虫子或远或近的声愈听愈空旷,翻来覆去只有酒壶子亲近他。
这天,太阳西斜之时,他发现一个穿红衣姑娘坐在上游河岸的土墩子上有如石块。鹅在水里嬉戏着,一种春情却在他的胸间激荡燃烧。太阳搁在西边的岭顶了,姑娘依然一动不动。他却坐立不安,忙撑过竹筏把鹅赶上岸圈了。
太阳的光线让土丘挡住了。落阳的上空血红。从西边到东边,红色逐渐淡去,快接近东边土丘脊梁处,淡淡的云片干脆白得惹人,没有云的地方却蓝得深邃。王古躺在草寮旁边的草地上,一口接一口喝着酒,天空上似乎映着土墩上的人影折射入他的心里难于磨灭。当欲火浇上酒精后,他按耐不住自己野性的欲望,然而土墩上之人消失了,他啊的一声杀猪般嚎嚎惨叫,跃起来扑向那块土墩子,用手动情地抚摸着还带余温的坐过的歪斜痕迹,又不时凑近鼻子深吸着气,企盼能嗅出女人特有的气息。
“咚……”
一声沉闷的拍水声让他索性慌张,望望四周并无人影。水声又响了,很微弱。顺声寻去,一块极为红艳的色彩突然飘进他的眼里。他来不及想别的,一个猛子便扎进河里。他奋力挥着手臂飞快接近那片渐渐沉下去的色彩又复归平静的河面。
水见凉了,透着淡淡的寒气渗入肌肤里。他右手托着溺水姑娘,左手轻轻在拨着河草。清脆的弄草声,随着一圈圈涟漪不紧不慢地扩散,悄悄潜入夜幕即将拉下来的恬静里。
上岸了,姑娘脸色惨白,紧贴着躯体的湿衣服不断地滴水。有如四根绳头的四肢在空中松软地摆动着,柔软的腰脊让他粗状有力的手臂夹在右腋下颤动着,他边小跑边用左手有规律地轻轻挤动姑娘胀胀的腹部。水不断地从她的嘴角注出,顺着脸颊流进倒挂在地上的茂盛的长发林里。
过了片刻,她的心脏出现了微微跳动,脸部开始了抽搐,由弱到强,然后大口大口地呕出一片黄水。
呕吐停止了,王古才把她抱进茅草寮里,解下湿衣裤,让她躺进底下铺着厚厚一层稻杆子的草席上。给她盖好被单后,天宇好清爽。他舒了口气,这伟大的壮举着实又让他很兴奋。
他从茅草寮顶取下裤子就地换了,转身走进鹅圈里。
鹅群蹲在一堆,在朦胧夜色里象一片淡淡的轻云停在天空中,好安祥。他释然了,回到茅草寮拿锅来,忙不迭舀水淘米,接着把瓷锅安放进灶里。灶很独特,是在地上挖一个比锅稍小一点的小坑,前有灶门,后有灶窗,野旷上的风来的时候也熄不了它的火苗,牵不走它的热量。王古把柴禾点着了塞进灶里,一股乳白色的烟柱从灶窗窜出,在月色里慢慢升腾。一阵风吹来,烟柱摇晃几下,散了,溶进夜色朦胧里,不远处的灌木丛的黑影更加浓郁了。
他拿着湿衣服到河里揉擦几下回来时,远远闻到米饭的清香。一阵噼呖啪啦的狼吞虎咽之后,他抱过一捆柴草架起焰焰的篝火,从竹笆篱上取下湿衣服挂在火上烤烘。暖烘烘的水蒸汽从衣服散发出,那带着奶香的咸味又把刚才让河水冷却的欲火复燃了。奇怪的是,他并不冲动,更不想喝酒,灼热的气流贴着他的心胸滚过,他的心境反而柔和了。
半夜里,姑娘的梦语惊醒了睡在门口的王古。她在喊着她的母亲,仿佛有谁在追杀她。王古迷惑了,姑娘为什么要寻短见?她是什么人?王古不是刨根问底的人,他煮了两个蛋姜粥,姑娘模模糊糊地喝了又模模糊糊的睡着了。
次日晌午后,姑娘才发现自己躺在被窝里,好暖和啊。这是什么地方呢?掀开被,自己竟然赤裸裸的,猛然间,她的心象轰然倒塌的房屋。她想到那位满脸横肉的治保主任。
翻遍草铺都寻不着衣服,一种悲恐突然袭来。当她抬头望外面明晃晃的阳光,王古已站在门口。姑娘脸上顿时闪现出一片羞涩的火花,她慌乱地退回角落,拿被单把自己遮掩起来,只露出脸部令人心悸的光芒。她不喊,也不叫,一动也不敢再动。
触到油腻腻的胴体一刹那,王古的眼光早盯在腾着热气的白瓷碗上,同时脸部也染上红土地的颜色。
他把衣服甩进去,慢慢蹲下,小心翼翼地放下瓷碗,说趁热吃了吧便闪开去。
姑娘掀开被单,神速抓起衣服。她站起把脚套进裤管,满眼却塞满飞动的星星。她心头悸动,整个身子筛一般抖动,身一倾,头砸到茅屋的屋脚上。
王古满脸惊色跑过来:“妹仔,你怎么啦!”
姑娘脸色蜡白,她张开眼睛抬起手想挣扎,可力不从心。她的肩膀冒热,王古又摸摸姑娘的额头,挺灼手。他忙给姑娘盖上棉絮,火焦焦地说:“你别动,我去抓药。”
她姓叶,改名玫。家住丘陵外。祖上省吃俭用买了几十亩地,日出日落起早贪黑,总算用不着去借别人的东西填自己的肚子。可有一天一大群比他们更穷的人涌进她家破旧的瓦房抬出缺手缺脚的仙桌条及旧床破絮大罐大缸米充了公。蒸气腾腾的日子一下长出灰溜溜的霉。谨谨慎慎提心吊胆全家人没了一句话,见巷上人总是躲躲闪闪。出工田上树下休息别人胡扯也不敢停下手中活。年月在寂寞的压抑中流过,十多年的劳动改造造就了她一身令人爱慕的窈窕。治保主任色眼迷迷竟在村巷的暗角想把她压下。不知从哪来的胆她摸起一起石头遭了罪。
苍茫的丘陵大地上何处有她的栖身之地?她村过村,户挨户地行乞。因为她豆蔻年华,身条儿呼气不缺,于是时有村妇泼她一身洗脚水骂她是懒婆娘不要脸。她委屈地跑到土地庙里哭了一天一夜,她竟然想了本不该属于这个年龄想的事。在空荡荡的神台前跪下祈祷着上苍能让她家人吃饱喝足生活平平安安,她却跑出庙门喘着粗气翻过几条脊梁跳进河里想过一辈子无忧无虑的日子。
昏昏迷迷中感知,照顾她的人并不英俊,可是他那坚实的步音让她平静了,人仿佛是躺在自家里,让母亲细心照顾着。她常常背过脸让眼眶里的液体片自由流淌。
一天,她一把抱住王古,使劲搂着他,把他搂得气也喘不出来。
王古吓傻了,表情木呆呆。几天来焦焦虑虑里里外外,唯求这个萍水相逢的姑娘平安无恙的愿望淹没了曾骚动他心扉的熊熊烈火。
女人绘声绘色地泣动着,每一粒泪珠,火炭般滚落到他结实的脊背上,灼烫着每一根冷冻了的神经。有棱有角的黝黑脸部倏然浮上一层褐红的色彩,象大海一般凶猛的浪潮冲着他已平静的心波,顿时掀动全身的每一个角落浪淘天。他的呼吸愈来愈短促,愈来愈为粗重,几天来他默默地照料她的双手,此刻在半腰间发抖。近日他同酒壶子疏远了,但是这时宛如有酒精在沸腾着他的热血让他窒息。他再也承爱不住,双手猛然抱抄过去,并使尽平之力抱住泪人,让她灼热的肉体烫着他荒凉了近三十年的心田。
王古带着女人回村庙放过炮,村子沸腾了。人们纷纷争相看热闹。王古憨厚地哭着,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句:“养了媳妇。”村里的老太婆拉着新娘的手,左观右看,瘪瘪的嘴唇不停地说:“闺女,闺女。”说着说着皱巴脸上漏出一串长长的泪珠:“满哥要是在世……”
草子岭热闹了。队长明叔抱着一只母鸡过来了。村里的一些汉子拿锅来了。婆娘们抱着菜拿着米来了。汉子杀鸡杀鹅说着最粗野的笑话。婆娘们围着新娘柔柔和和拉家长拉家短,都没有再提那受过热吃过冷的遭遇。
天确切要亮了。空中闪烁的星光寥远了。布满暗影的连绵丘陵脊梁清晰了。朝阳一片粉红色在穹隆下缘浮上来,肃穆而平和。红绿相间的坡腰顺着暗色线条缓缓地滑下去,一直滑到低洼地上的小河。一根没有弯曲的白线条从灶窗吐出,轻轻地嵌镶在恬淡的晨雾间悄悄蠕动。

鹅在圈里叫着,饿饿饿。王古着实得意,懒在草铺上,不时哼着不成调的鼻间,慢慢地回味着女人的滋味。不时抬腿踢着吊在头顶的酒壶子逍逍遥遥。酒壶子倒很寂寞。
阳光散落进河岸边深浅不一的绿草间,宁静而致远,两把锄头一起一落,漂亮而有力度。金属与褐土的摩擦声,隐隐约约,仿佛发自遥远的天边,好细腻,又极为悠长,但很快就被无边无际的空旷吞噬了,荒草覆盖着的土地,经几天的翻动,土地的原色袒露得一览无余。湿湿漉漉的褐土,散发出淡淡的新鲜泥香,撩撩拨拨说不出的醇香真叫人陶醉。
女人的脸红润润。鼻尖上的细汗珠在阳光临时羽羽生辉。扎在脑勺的长长发丝秀如云,随着锄头的起起落落,香香的飘飘着。
王古有时停下做活,不相信媳妇来得这么简单,可晚上一摸一索,又是这样实实在在,他呼哧哧地用着力,脚下现出一块块新土。今春种上菜,下年再种点稻可好呢。王古心里美美的,半天里没一句话。
人影儿变圆了。王古放下锄头,说:“歇着啦。”
想歇就歇啦。
女人也挺真腰,望望头顶的火球,刺得眼肉好生痛。低下头闭上目,眼睛里有一串小小的光圈旋转着。
女人开始做午饭。
王古坐在划地上,眼光一刻也不离女人浑圆的殿股。
“坐呆看个屁,还不去管管鹅。”女人回过头,笑着,很灿烂。
王古搔搔腮向河边走去,背后却甩下一句半生的话:“圆呢。”
饭吃过一半,女人拿起一只蛋扒开壳,忽然嘻嘻地掩嘴笑,极为妩媚。王古摸不着头脑,但也跟着咧开嘴,女人说:“你的卵呢。”
话很骚,王古不笑了。放下筷子,抱起女人进了茅寮。
做了事,女人望着头顶的酒壶子。
“咋不见你喝酒?”王古喘着粗气不吱声。女人翻过身:“装酱油最实。”
“明个儿去卖鹅,你也去看看鲜。”王古摸着女人的滑圆殿,“攒了钱,请人盖两间草屋,寮也太矮啦。”
女人眨眨眼:“路可远呢,我看家得啦。”
王古把粗糙的手指插进女人的发林,女人却说:“我该学凫水。”
似乎这话给王古注入一股强劲的活力,陡然间弹起来,抱起女人,说:“就教你。”
女人说:“我还未穿衣衫呢。”
王古说:“怕个蛋,哪有人呀。”
女人在王古怀里挣着:“羞死啦。羞死啦。”
过了十来天,河边响过一阵爆竹声后,一座红泥墙黄草顶的茅屋便立在河边。刚挟稳最后一整稻草,雨来了。村里来帮工的几个兄弟说:“古哥,雨可好呢。财该你发啦。”
王古望着雨丝明丽丽的,搔着腮:“发啦!”
雨轻描淡写地瓢着,瓢着。不知哪一夜,北风悄悄地爬过丘陵脊梁,萧瑟地掠过河面,冬天来了。鹅缩着。王古同女人手忙脚乱地织着稻草,做好鹅的防冻窝。
日子畏畏缩缩,年关近了。鹅也可出栏了。
女人半夜下床,轻手轻脚在厨房里生起火。门外的风有牙,啃着手指木木的。女人撑着胆子摸摸索索地从菜园子回来,一进门,随即把门关得严严的。火好旺,屋里暖烘烘的。
饭熟了,菜也熟了,才叫醒男人。王古看看笼里的鹅稳稳的,才端起碗甜甜地吃着。
临走,女人匆匆从锅里捞起几只鹅蛋,用冷水浸一浸,捞起来用布抹抹便塞进男人的怀里,说:“饿了,路上吃。”
王古摸着女人的脸蛋,真暖和。
在草子岭放鹅生钱,村人很羡慕,可没谁生胆。
年关,村子同草子岭间的路子挺热闹。队长旺叔说:“过了年,就有工作队进驻我们村了。你同媳妇也搬回来住吧。按上面文件,你独自在外面养鹅搞副业是犯法的事,过去我们闭一只眼让你,是因为你是孤儿,可工作队一来,我们就说不准了。”
王古不信,自己出力养鹅卖钱也犯皇法。年一过,他又拿一笼鹅到圩上。圩口设有关卡,戴红袖章的一群人没收了王古的鹅,而后带他到一块荒坡上开蔗沟,那里已集着十几人了。
他女人没睡一夜,天刚见亮。慌慌回村里。
村里早传着王古给关了。女人急出泪,明叔边安慰边同王古女人匆忙赶到圩上。他俩在文革委员会里终于见到王古,他刚挖蔗沟回来吃午钣。明叔给求了情,人家才肯放了人,并且嘱咐说,回去得好好造他的坯。
王古一出圩,便破口大骂:“娘养的,新社会了还有这子事儿哟。”
明叔望前望后,扯着他的衣襟襟慌慌地说:“别…别张声,可大呢。”
他很执拗,不过,他还是搬回村参加生产队劳动了。这时,他的女人生了一个胖小子阿揭。
他在外自由惯了,那里受得了约束。孩子刚满月,又携儿带妻回草子岭。
冬阳落了。雨来了。一夜间,天暖和了。河里骤然宽些,水也急些,载着一团团淡黄色的泡沫从上游悄无声息漂浮下来。靠岸边沿的杂物时而打旋,时而被水草勾住,时而挣脱开缓缓地漂去。
水的流速大,王古只好把鹅圈着,挑着竹筐到河边割水草。
丘陵上其实没有冬天,阳光终年灿烂,绿色四季莹莹。有了春雨的洗礼,草色更青嫩了。水草好深,轻轻地满过膝头,湿淋淋的叶片打湿了裤管。他每移一步,脚下传出咚咚响。草很茂,不一会儿工夫竹筐满满的。他在水里洗一下篇担,又串起竹筐绳,弯下腰,用力一顶,竹筐底旋即漏出条条水柱。在转身的一刹那,一只盒盆漂到他的视线里。他忙放下竹筐,抽出扁担,用力一顶,截住面盒。面盒里有肥皂、衣服。上了岸,王古才发现衣服底下还有块火砖般大小用黑皮包住的东西,放在手里沉沉的。王古不曾见过,瞅来瞅去,看不出什么名堂。侧边有一只轮子,用力一旋,啪的一声清响,有声音随即从里面滚出,有如天雷炸开。一惊,手发抖竟然滑落。待他定过神,才听清有男音歌声飘出。他摸了摸头。笑着:“哈,这玩艺。”
草撒进鹅圈,他蹑手蹑脚走进厨房。女人背着孩子在烧水。
他拿那“玩艺”悄悄伸到女人耳根,轮子一旋,吓着女人。妇人从灶里抽出一根带火的棍子敲打着王古,一直追出门外。见男人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依依呀呀,忽然住手了。她凝神聆听着,挺新奇。
她问:“这是乜呵?”
他答:“电台。”女人手上的棍颤下。庄稼人看来,电台,特务同国民党都是同一子事儿。
女人面色惨白,恐惧的眼睛盯着王古:“你…你哪来哟?”
“盆上,河上。”王古的唇也颤着,结结巴巴。
“祸,祸哟。还不丢咧?”女人抢去电台,嚓嚓地向河走去。
王古站着不动,额头沁出细汗。他忽然追上:“万一特务知了,不,不就更殃事。”
女人停下,苦着脸,没了主意:“那咋办啊!”
男人终算不是女人,他镇定些:“埋了。”
王古返屋里,拿出锄头。女人说:“埋远点,万一炸了。”
“是呢是呢。”王古望一眼女人很佩服有远见。于是在房子的西北角的一丛山稔旁挖了坑。铺过草,搁入电台,再盖上一层草,填上土。
电台埋了,可日子也不见安宁。每当夜色注下,门闩得紧紧,生拍特务带着短枪摸黑闯进来。间或有鹅声在圈里搔动,更是粗气不敢喘,仿佛只有这样草房子才在野旷上隐去。
惶惶中度过些天,倒没有什么陌生人来,西北角没有雷响。心头上的石头才轻轻摘下。
王古隐瞒着女人又悄悄地把电台挖出藏在鹅屋里。有时好奇开一开,捏着心头轻声呼叫:“台湾吗?台湾吗?”可电台只顾说它的,王古失望了,终于又藏回原处没了一回事。
日子一晃,雾从河西漫过来了。浓重的雾掩没了丘陵地。推开稻草挟的门,山没了,河没了。望着圈里的鹅也是隐隐绰绰。
王古握着丈把长的杆子摆着。鹅到河边散了,梳洗的梳洗,吃草的吃草,拍翅膀的拍翅膀,引劲高歌的引劲高歌。
他回头望,草屋没了。天地一片乳白色。“刷”的一声,挥起的杆子深深扎进泥层里。杆尾上的细布条湿湿地垂着。
他心里慌得甚,回来上岸了。女人在做饭。他推开屋门,走到床边,小家伙静静地躺着。刚喂过奶。
他逗着小家伙。他很喜欢用手指点着小家伙的鼻尖,让小家伙翕动着鼻子呜呜地咧开还蘸着奶汁的小嘴唇。并且小手指不时地在空中嫩嫩地乱抓乱翻着。他干脆抱起小家伙。把两片厚厚的嘴唇紧紧贴在小家伙细嫩嫩的小唇上。小家伙用手抓着王古的鼻子,呜呜的不耐烦了,王古感觉有一股暖流在大腿上蠕动,低头一看,裤腿湿了一片,小家伙尿了。王古轻轻弹一下小家伙的皱巴小鸡,笑着说:“这贱子。”
女人适好入屋,见状可开心了。她娇媚地说:“你的才是贱子哩。”
给小家伙换过裤子,外面却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两口子不约而同朝门口望,浓重的雾里现出一片人影。
原来是副队长仲伯带的兄弟。两口子慌忙迎出去。
“哟,仲伯好早呵,可吃啦吧?屋里……”
仲伯摆摆手,严肃地说:“支书叫你立时回村。快点!”
王古望着仲伯,又望着女人,犹犹豫豫地说:“你去看看鹅,日晌就回。”
人影消失在雾里。她抱着儿子还呆愣愣地站着,不知出了什么事。
太阳来得很迟。露面时,已近中天。
饭熟了。菜冷了。女人仍旧坐在门口等着。
日偏西,太阳的轮廓又渐含糊,宛如被水膜蒙住脸。
四野很静,从河边不时传来鹅声,女人心慌慌的。儿子又睡着了。
太阳的光色全褪了,只留下一方明晃晃的白圈。一群鸟儿穿过,白圈也隐了。鸟儿向西南岭飞去,变得密密匝匝,最后连影子也消失之时,在绵绵脊梁上却出现了晃明的人影。
女人舒口气,钻进厨房热饭热菜。
“大婶”屋外有了人声。她跑出来。眯眯眼,却是明叔同二个后生仔,身后是一辆牛车。
“古歌?”女人脸色变得直直硬硬的。
“搬回去住吧,他去公社食了。”
三条汉子的眼睛低垂着,不敢正眼看她。
女人无语。
汉子们原以为她会摊在地上嚎啕大哭一通。一路上想好的安慰话没了用途。
也没什么可收拾。折起棉絮草席用绳子一扎倒实了。几笼大小鹅和着牛车的轱辘声,颤颤地在没滋没味的小道上孤单地游动。
一个月的光景,去公社开会的明叔把王古领回来。当他得知鹅全让大队干部没收私分送酒,天井上活蹦蹦的绒球鹅子在他手脚的横扫之下极为狼籍。有一只鹅子躺在厨房的房后,也控制不止悲伤叫出声音,也无法逃过他的魔手。他抓起用力一甩,鹅子便在火腾腾的灶间叫得惊心动魄。在鹅子尖锐的惨叫声里。他猛然间用棍把鹅拉出,但已经晚了,屋子里弥漫着焦味。他眼里扑漱漱地掉出泪。他一把抓起灶头上的酒壶子,灌了满满一口,可在这瞬间,他又把液体吐满地。原来里面装的是酱油。他如一头疯狗从厨房里窜出来,对着泪挂满脸的女人吼道:
“死鬼,给我酒。酒……”
自这之后,王古没了一点庄稼汉子的劲。
那天晌午,还不曾有风。天也还晴晴的。日头高高,天蓝蓝的还带着夏日里的宁静。
但是,他吆喝几声瘦弱的老母牛拉了几十条深沟之后,呼哧哧地,一股干燥的风从西北方向砸过来,把西斜的太阳卷走了。一只山鹰哇哇的鸣叫着,凄凄惶惶扇着坚实的翅膀,也无法逃出风的旋涡。眨眼间,山鹰已成一个黑点。凄励的叫声更是被风声所淹没。
王古背过声身,褪色的衣角噼啪着上下翻动。强劲的气流顶着他厚实的脊背,似乎也要把他送上混沌的天空里。
他不断地吐出带尘土的口水,不断地漫骂着:“他老母的,昨搞啦?”
远处传来哞哞的嘶叫,一头犊子慌慌张张地跑到母牛身边。慢慢的,王古的眉头皱成一团,这是乜火候啊。
哗的雨没头没脑泻下,天地间一片骚动。
他一转身全湿了。他不再显恐慌。他一大早出来,这会儿酒壶子空空的。打开壶盖,酒旋即散开。他咽了一下口水。
装上犁,饭盒往车上一搁,“嗨”,老母牛忠实地迈出坚实的前蹄。
老母牛一踏入村口,风停雨也歇脚了。
他水淋淋缩在车斗上,上下唇发黑,牙齿不由自主地颤动着,不时发出咔咔响。
明叔慌张跑到车边拉牛绳,推着王古喘着大气说:“古啊,玫不行啦。”
王古莫明其妙:“什么玫行不行啦?”
明叔又说:“玫婶落…落河啦。”
“什么?”王古跳下车,伸手抓住明叔的领口。
明叔没了表情。泥水不断滴着。他咽哽着讲了。
就在上午,几个到草子岭放牛的村童在王古的鹅寮里玩,无意间发现藏在草里的电台。中午回村时开着电台叽哩哇啦摆过村巷。村人觉得新奇拢过来七嘴八舌。问它是什么玩艺牧童也只有摇头说是在古伯鹅寮里拾的。仲伯也在场,他吃了五十数不曾见过会说的电台,莫非这就是电台?他开始警惕。队长一说,众人如见虎色变,纷纷向后退。那几个牧童也把电台扔下,似乎电台这当儿要炸了。
王古是在村人眼下长大的,特务自然不会是他。于是副队长的焦点全集中在他女人的身上。其实她来到这座村子本来就很为不明不白了。怪不得王古三番五次都要搬到草子岭。原来是受“特务娘”煽动,要分裂他们贫农阶级。副队长这么一想,问题愈来愈严重复杂了。但是工作队的同志都回公社开会了,怎么办呢?副队长便自作主张,一方面组织村里的民兵行动起来,先扣特务,预防让她逃窜。
他带五个强壮民兵荷枪实弹划着竹筏过河迅速向南岭坡靠拢,并出其不意把王古女人捉住五花大绑。
同王古女人一起劳动的人不知发生什么事,乱呜呜一团。王古女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只是喊:“我的阿揭,我的阿揭,快松绳。”
她背着她的阿揭。
竹筏划到河中间,风便来了。风仿佛从河底生起,波峰波谷折腾着竹筏。竹筏上的人脚一虚,纷纷落水。王古女人一落,便再也不见露头了。
明叔拉着王古跑到河边,已上气不接正气。望着空荡荡的河面,不知过了多久,王古哇的长长衷声振动了一大群看热闹的村民,然后掠过河面,久久不消失。公社接到报告后,正在开会的每一个人都有极为震惊,一个偏僻的小村里竟然深藏着特务分子,就是在他们县还是头一遭。
书记一方面向县里报告,一方面叫武装部长招来二十多民兵及王村二个工作队乘着大卡车向王村进发。
车开到王村,天快黑了。村里组织的打捞队因无望而已停止工作坐在河边吸烟议论,生怕特务会从那一角落里冒出来投来炸弹。
公社书记走到队长明叔的面前,紧张地说:“人呢?”
队长不说话,眼里含泪。
副队长慌慌走来:“她死在河里了。”
他停下话,转身向一个民兵招手:“把缴获的电台抬来。”
公社书记接过电台,脸色徒变。他举起电台向地上一砸,脖子上的青筋然颇凸暴,似根根蚯蚓。
他吼道:“混帐。什么电台,这是收音机啊!饭桶,是收音机!”
副队长被抓走了。
天黑了,天慢慢悠悠下雨,王古攥着空酒壶子不停地说着:“酒,酒,酒……”
酒壶子默默的漏不出滴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