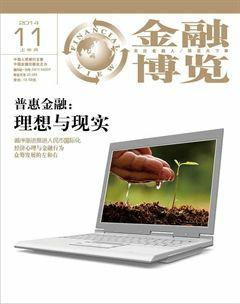雅俗之争
王以培

原
先的高卢人已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此后,随着罗马人的大举侵占,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发展的文明,罗马的士兵、教士、商人所使用的通俗拉丁语逐渐代替了高卢人的语言。高卢文字,除了少数碑铭之外,几乎消失殆尽,只是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还留下少量词汇,比如:charrue(犁)、raie(田埂)、sillon(犁痕)、glaner(拾禾穗)、char(畜力车)、tonne(木桶)。这种通俗简便的拉丁语,经过蛮族改造,再掺杂一部分蛮族语言,就形成了一个新语种——罗曼语,即古法语。在古法语中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谚语:“一切将由上帝来主持公道。”“上帝不说假话。”“被上帝爱的人是最富有的人。”“除了上帝的爱,一切都会消失。”可见在中古时期,基督信仰已深入人心。
在古代,文雅和粗俗,无论在语言上或社会阶层中都泾渭分明。基督教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审美价值和等级观念: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出身低微。神学家圣奥古斯丁(354-430年)便主张,为了让公众听清听懂,布道、演说都应当用西塞罗所说的那种“鄙俗的语言(sermohumilis)”。而此后,在法语和法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贵族所使用的所谓“文雅语言”与民众所说的“粗俗言语”始终处于对立、融合、分化,再对立、再融合的循环往复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法语和法兰西,既是奴隶,也是主人;既是征服者,也是被征服者。而所谓“高贵”、“高雅”与“粗野”、“低俗”早已在血液中融为一体,如兰波所说:
“异教徒的血液重新归来,圣灵靠近,基督他为什么不帮我,不让我的灵魂自由、高贵?哎呀,福音已成过去!福音!福音。
我贪婪地等待着上帝,自古以来,我一向属于劣等种族。”
或许正是这个“一向属于劣等种族”的法兰西“逆子”,才使得一个古老民族连同她的语言文学变得高贵而超凡脱俗。
到了中世纪,法国文学又出现了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以及后来的宗教文学和骑士文学。从12世纪起,随着法兰西的统一,中央极权的加强,战争逐渐减少,贵族、骑士崇尚武力的精神开始衰退,从好勇斗狠,变得慵懒、颓废,享乐之风日渐盛行。骑士、贵族开始讲求服饰华丽,谈吐优雅。而随着“典雅的美德日臻完善”,文学变得日益苍白、空虚。直到文艺复兴出现了一位巨人拉伯雷,他的一部《巨人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浮华之风,从风格到内容,其粗放狂野,雄浑强健,在法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
这位巨人名叫卡冈都亚,母亲在一次豪饮中临产,因喝断了肠,逼得他从母亲的耳朵里钻出来,一出世就高喊:“喝!喝!”他每天要喝一万七千多头奶牛挤出的奶,外加母乳一千四百多桶,真正是“一饮解千愁”。这一豪饮,一解漫漫中世纪幽暗的法国乃至全欧洲的千年饥渴。法语有句谚语:“Qui a bu,boira.”意思是,“谁沾上酒,就会一直喝下去。”再看看卡冈都亚的妻子日后生儿子的场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先是“六十个骡夫各赶一匹骡子”,接着是“九只单峰骆驼,驮着火腿与牛舌”,再就是“双峰骆驼驮着鳗鱼”,后面还跟着二十五车韭菜、大蒜、大葱,最后才是“全身是毛”“像只大狗熊一般”肥硕无比的婴儿,他的名字叫庞大固埃,每顿要喝四千六百头奶牛的奶……喝,喝!——这是巨人刚出生的呼喊,也是他历经艰辛,最终所得到的神谕。
《巨人传》就这样粗犷、豪迈,气势恢弘,如火山喷发,带来滚滚泥石流;其海量方言,庞杂的句式,加上多种外文、俗语,同样惊世骇俗。这样在带来无限生机的同时,也造成混乱,并最终陷入沼泽。到了16世纪中叶,由于封建割据,各地方言土语五花八门,而在诗歌方面,又出现追求精雕细琢的“辞藻派”、“里昂派”;统一民族语言,恢复优秀传统,重新成为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的“七星诗社”应运而生。
《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是“七星诗社”发表于1549年的“文学宣言”,全书分上、下两卷,每卷十二章,由杜倍雷执笔。所谓“保卫”法语,就是要改变其贫乏、粗陋的乱象,正本清源;主张从希腊和拉丁文中借用词汇,让旧字变新词,并创新词性,如动词名词化,形容词名词化、动词化;规范方言,活用俗语。在诗歌方面,主张恢复传统的亚历山大诗体。他们痛斥当时的民谣俗语为“败坏语言”,并要求诗人“出身高贵”。而贵族出身的龙萨创作的一首《致爱伦娜十四行》,成为“七星诗社”的代表作——
当你老了,夜晚坐在炉火旁,烛光下,
抽丝纺纱,轻轻哼唱着我的诗句,
你会容光焕发,并喃喃自语:
龙萨龙萨,曾赞颂我如花美眷,青春年华。
身边劳顿的女仆已昏昏欲睡,
闻听这惊鸿一叹,你轻唤着
我的名字,都从梦里惊醒,
祝福你那镌刻在诗中的永恒美名。
而那时我已长眠地下,孤魂
已脱离肉身,在桃金娘树荫下安息,
看着你,那蜷缩在炉火旁垂暮的老妇人,
悔恨着自己当年的高傲冷漠,
拒绝我的爱情。相信我,活着
别等明天,生命之玫瑰,趁今日采折。
一见“当你老了,夜晚坐在炉火旁”,人们自然会想起爱尔兰诗人叶芝,可见叶芝那首著名的十四行诗,字里行间,回荡着龙萨的余音。龙萨也因这首诗和他的《爱情集》,被“七星诗社”奉为“最法国化,最能表达我们的热情的诗人”。
人们常陷入“雅俗之争”,“古今之争”,但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学习和研究法国及欧洲文学的过程中,我们通常偏重于“逆反”而忽略了“正统”,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普遍的偏见和误解。
到了17世纪,“雅俗之争”又日渐演化成更为激烈的“古今之争”。戏剧家莫里哀在他的一系列喜剧中,辛辣嘲讽了贵族社会的“高雅”,揭露了伪君子(达尔丢夫)的虚伪和高利贷者(阿尔巴贡)的贪婪、吝啬。众所周知,在莫里哀的喜剧中,贵族的“高雅”被嘲笑得体无完肤。
而随着时光流逝,莫里哀又成了古典主义者。到了17世纪末,法国文艺界掀起一场古今大战。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古典主义的一些教条又成了文学发展的桎梏。最先的发难者是查理·佩罗。他认为,与其因古人之古老而向他们卑躬屈膝,不如让我们自己成为“古人”;因为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古老,我们比古人拥有更多的经验和历史教训。佩罗正是《鹅妈妈的故事》的作者,其“小拇指”的故事在全欧洲家喻户晓。而崇古派的权威人士站出来反驳,并写了一些讽刺诗把佩罗说成是“疯子”、“野蛮人”。
回望16~17世纪的“雅俗之争”,不禁让人想起中世纪“骑士的爱情”——建立在一系列相互矛盾又模棱两可的基础上:它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堕落的,又是理想化的;既违背道德又合乎情理;既狂热又有节制;既是一种痛苦,又是一种欢乐。或许法兰西自身也是如此,迷人而又自相矛盾,一直以来,既是众人嘲讽的对象,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兰波作品全集》《小王子》译者,文中诗句为作者翻译)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