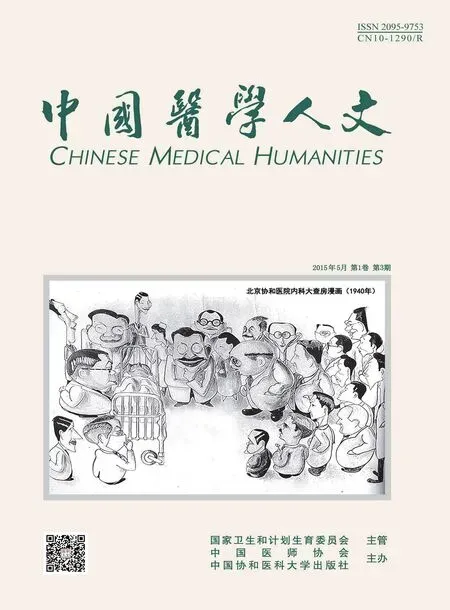一个赤脚医生女儿的梦
文/张秀梅
一个赤脚医生女儿的梦
肩膀上的幸福童年
1973年10月,我出生在北京郊区延庆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因为整个社会和时代都还没有脱贫,所以我在妈妈肚子里无法想象得到今天孕妇的幸福和奢侈,再加上妈妈孕期严重反应和不能停止的生产队集体劳动,我的降生和存活几乎成为一个神话,瘦到身上的皮可以扯起一寸多高,绝对的骨瘦嶙峋。重男轻女的三寸金莲奶奶在盼望张家香火传沿的绝望中命令爸爸“掐死吧”,父亲七尺之躯含着眼泪哀求奶奶,从红色油漆柜里拿出他的一件旧衣服裁剪开成为我来到人世的第一件“袈裟”。
挣扎在吃饭穿衣问题上的贫穷生活始终如噩梦让家里三个大人不间断的纷争,然而我最大的快乐却是跟着父亲走街串巷,进出各个病人家门,父亲一个肩膀上挎着药箱,一个肩膀扛着我,偶尔还会骑在他脖子上,那种高耸入云的感觉美极了!当然,最幸福的还是每家人都会倾尽全力拿出最最好吃的零食来招待我。父亲在一边望闻问切、诊断、治疗、开药,我却在一边独享美食,偶尔抬起头观察患者家庭的起居摆设。一个村子上百户人家,我渐渐都清楚了,贫富差距、家境条件,小心眼里盼望着有钱人家多生病呀!那家的零食真解馋!大人们早出晚归地挣工分糊口,我的童年就这样在父亲这名赤脚医生的肩膀上幸福度过。
命运的急转直下
1979年,弟弟出生了,农村也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干要强的妈妈为了让全家早日脱贫,承包了近百亩地,父亲除了白天走家看病外,抽空不能不帮助妈妈料理农活,精力的分散难免影响看病的质量。记得一次给一个姓彭的妈妈注射完后就赶去田里收割,谁料父亲刚到田边,村广播站就发出紧急呼叫,说是彭妈妈注射药物后过敏,严重抽搐及呼吸困难,父亲骑着单车急速赶回,抢救了彭妈妈,仔细检查后,才发现是青霉素注射用过的针管残留物没有清洗干净,导致了彭妈妈严重青霉素过敏体质反应,父亲因为自己的疏忽懊恼了很久。这也是我记事以来父亲行医32年唯一一次最严重的医疗事故。我记忆中更多的是病人被抬着进我家门,走着出去了,家属哭着进我家门,笑着出去了。所以我对医院、医生从未有过恐惧感,因为那是我的家,我的父亲,一个救死扶伤、给人希望、健康和快乐的地方。
父亲的精湛医术和大爱仁心,妈妈的吃苦耐劳和勤俭持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很快让整个小家焕然一新。我们翻新了6间瓦房,购置了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缝纫机三大件,我和弟弟也在村子里如众星捧月般茁壮成长。
然而好景不长,198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父亲突然胸闷,晕倒,嘴唇黑紫的可怕,急救车呼啸着把他和陪伴的妈妈及亲戚都拉去了县城医院抢救,只剩下15岁的我和9岁的弟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农村大院里孤助无缘的相拥哭泣。
乡卫生院院长和几个县医院院长调动全院力量会诊抢救,不仅因为院长们是父亲的同学,更因为他们清楚父亲是十里八村上千户人家的健康守护神,如果父亲倒下了,他们的救治压力将无形增加很多倍。苍天有眼,经历半个月的住院抢救治疗,父亲从死亡谷被拉了回来。但二尖瓣狭窄导致中风后遗症,严重失语且半身不遂,于是整个家庭的重担必须由我和妈妈挑起了。
父亲一年两次住院使得家里生活重负难言,我理解了妈妈为什么总对父亲呵护有加,我明白了为什么每年冬至父亲咳血时妈妈眼中忧郁的眼泪,我也懂得了为什么妈妈那么吃苦拼搏像个男人一样,我和弟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好好学习,放学回家多干家务。
为了支撑整个家庭,也为了方便三里五村的乡亲们,妈妈不仅种田种菜,还利用父亲神志清醒的优势,开始了医学治疗的学习,每次来一个病人,逐渐康复的父亲能够诊断、开药,妈妈则担任护士角色,注射、拿药,甚至后来的缝合、输液,整个家庭诊所热闹非凡。
对生命奥秘的探索与忧思
因为父亲的病倒,整个家庭的变故,我初中毕业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以全县第四名的中考成绩进入了当地师范学校,但想上大学的梦想始终没有丢掉。中师三年期间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帮助妈妈打理农活,赚零花钱补贴家用,照顾父亲和弟弟。感谢上帝的厚爱,三年期间父亲的病情基本稳定,我也以全师范学校成绩最优被首推到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圆我的大学梦。从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直到最后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每一门课程都深深地触动着我的灵魂,因为我太想知道生老病死的真实原因了,我更渴望有灵丹妙药治愈父亲的病,恢复我们家庭的幸福。四年大学弹指一挥间,在即将结束大学生活之前我和妈妈深谈了一次,告诉整个家庭我渴望继续深造读研。功夫不负苦心人,全班58人报考研究生,我成为两名成功者之一。
父亲的葬礼清晰了我的梦
2000年1月13日,一个漫天大雪的下午,我被妈妈急促的电话召唤带着弟弟回家,因为父亲已经咽气了。那是我硕士毕业在万方数据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实习期每月600元,存在手里也就2000块钱,好心的领导安排司机送我,顺便还包了一个500元的白包。无耐大雪封住了高速公路,我和弟弟转乘火车,半夜1点钟回到家中,看到的已经是父亲慈祥安静的离去状态。人在最最痛苦的时候,只有撕心裂肺而没有了眼泪,弟弟和妈妈轮番的晕厥,而我作为长女必须强忍痛苦,主持操办好父亲的葬礼。在有限预算的前提下,我买了最贵的骨灰盒,因为它不仅盛载着父亲的遗骸,也承载着我的终生愧疚。一直读书,没有来得及孝敬父亲,让他托着病弱的身躯和那颗大爱仁心,支撑着这个家庭和这个村落又前行了12年。
接下来就是连续三天的葬礼,十里八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几百人冒着严寒前来吊唁,很多我都不认识的父亲治愈的患者,趴在棺材前痛不欲生,我那时才理解患者对医生的感恩和思念甚至超越亲情。鼓乐、花圈、饭菜、墓地、墓碑,葬礼的隆重超乎寻常,可由于妈妈和弟弟的精神异常状态,我又多年不在家找不到北,但几天的安排都是井然有序,悲而不乱。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表达着对父亲的思念和最后的敬意,我除了伤心,更多的是感动。操办完父亲的葬礼,我似乎整个人都升华了,也许这就是经历了生死。再好的医术也不能起死回生,只是在向死而生的路途上多一份对受伤的孤独灵魂的专业慰藉与呵护。我们没有权利选择如何生,但却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选择在人们什么样的眼光中离开这个世界。我为自己作为一名赤脚医生的女儿深感骄傲。人的一生财富、地位、荣誉都带不走,唯有人们的尊敬、爱戴让你永远活在别人心中。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