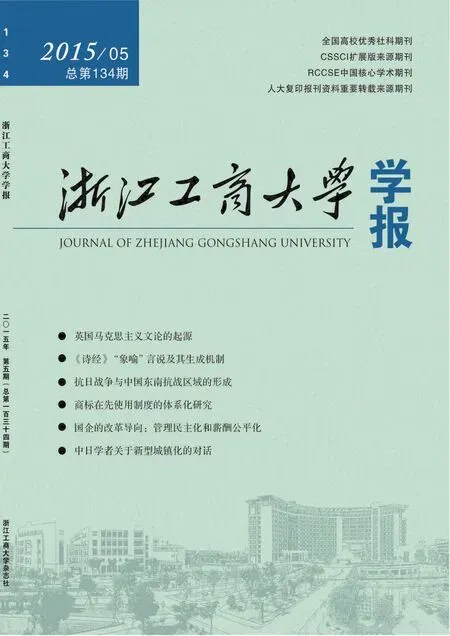理查德·舒斯特曼艺术哲学思想管窥
理查德·舒斯特曼艺术哲学思想管窥
孟凡生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要:舒斯特曼的艺术哲学以审美经验的重构和实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并以“相容性析取立场”为其理论方法,对“艺术终结”、艺术定义和通俗艺术以及艺术的边界等问题进行重新的解读和阐释。他的艺术哲学聚焦于加强对艺术的理解与体验,强调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连续性,体现出了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关键词:舒斯特曼;审美经验;艺术理论;通俗艺术;实用主义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孟凡生,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美学与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志码:A
A Study on Richard Shusterman’s Philosophy of Art
MENG Fan-sheng
(ChineseDepartment,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bstract:Shusterman’s philosophy of art based on the pragmatism philosoph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with “inclusively disjunctive stance” as its theoretical method reinterpreted the issues such as “the end of art” and the definition of art and the popular art and so on. His philosophy of art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of art. It also emphasized the continuity between art and life, so it reflected the vivid and pragmatic color.
Key words: Shusterman; aesthetic experience; art theory; popular art; pragmatism
众所周知,理查德·舒斯特曼是西方当代身体美学的创建者,他的身体美学思想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内学者更是对他的身体美学思想青睐有加。然而,在对其身体美学思想聚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他的艺术哲学理论置于了“盲点视域”之中,他的艺术哲学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舒斯特曼艺术哲学是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他一方面不满足于经典实用主义那种过于温和的折衷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于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的激进地破而不立,这两者可以说是各执一端。舒斯特曼则力图对经典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进行一种“权中”,而不是对二者进行简单地“折衷”。他的思想更多的是通过吸收新实用主义的理论思想而进一步地推进了经典实用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立足于经典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对新实用主义的一种改造,因而在对艺术的论述中显得略为保守、温和但却富有建构性和现实意义,他的艺术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艺术终结”的理论反思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黑格尔的“艺术终结”命题成为了艺术理论中的热门话题,众多理论家和艺术家纷纷投入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争辩之中,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艺术命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阐释。对此舒斯特曼做了较为中肯的描述,“在新千年伊始,美学中令人悲哀地停留在终结理论的视域之中,这些理论将艺术当前的信任危机不是当作暂时的衰退或转变,而是当作统治我们文化的深层原理的必然而持久的结果。”[1]他对“艺术终结”的命题以及关于它的争论进行了另一番解读,即艺术终结理论之中还隐含着更深一层含义——审美经验的终结,他以本雅明和丹托的艺术理论作为其发难的对象,具体地阐发了这一观点。
(一)“艺术终结”抑或审美经验的终结?
在20世纪初的现代社会中,艺术由于自身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救赎之物,它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解放,艺术俨然化身为现代社会的宗教。然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则对艺术的这种救赎力量充满了疑虑,本雅明认为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复制的艺术品的出现和流行彻底消除了它的独特性和神秘性,艺术品失去了自身的“光晕”,所谓“光晕”指的是“一定距离以外独一无二的显现,哪怕仅有咫尺之遥”[2]。舒斯特曼则认为复制技术对艺术的这种冲击只是表面上的一种联系,“光晕的消失”只是艺术走向衰败的一种具体体现,导致艺术衰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艺术形象的可复制性,而是其背后所隐含的传统的审美经验的消失。他把“光晕”和本雅明的另一概念即“震惊”相联系: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和新事物的不断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缺乏心理准备的状态之中的人们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现代社会所独有的“震惊”体验。这种震惊体验既是突如其来的,又是支离破碎的,它的存在打碎了传统艺术所蕴含的那种整体统一、和谐自然的审美经验。机械复制技术带来的超额信息瓦解了传统艺术的经验形式如讲故事的艺术,泛滥的信息也把整体、和谐的传统经验分解为瞬间的、破碎的震惊体验。
如果说黑格尔是从其哲学体系出发,逻辑地演绎出这一结论;那么丹托则是从当时的艺术作品出发,认为时下的某些艺术创作解构了艺术观念而具有了哲学的特性,“黑格尔惊人的历史哲学图景在杜尚作品中得到了或几乎得到了惊人的确认,杜尚作品在艺术之内提出了艺术的哲学性质这个问题,它暗示着艺术已经是形式生动的哲学”[3],艺术已经进化为关于它自身的哲学——艺术哲学。丹托的艺术理论主要受到了分析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审美经验这个概念对于定义艺术的概念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对审美经验这一概念避而不用。在丹托的艺术理论中艺术不是把审美而是把“哲学解释”作为它的关注中心,后来他甚至认为审美经验的概念不仅无用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对艺术的描述使艺术显得过于简单,进而使艺术更适用于愉悦层面而不是意义和真理的领域。尽管审美经验概念已不能恰当的定义艺术,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在艺术或美学中不再起任何作用或起到相反的作用。舒斯特曼认为审美经验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让人们去“感受或品味艺术自身的可感知的特性和意义,而不是让人们根据作品表露出来的信号和艺术界的语境去计算出一个必然的解释”[4]。
总之,艺术的“光晕”的消失以及丹托的“艺术终结”之论调在根本上反映了传统审美经验的终结。所谓审美经验的终结并不是指审美经验就此消失或对其弃而不用,而是指自康德以来所确立起来的那种形式的、自律的以及二分性的审美经验之内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在定义和界定艺术之上的合法性和独享性受到了质疑,以及它在艺术中所起到那种决定性地、崇高地位的终结。
(二)审美经验的重构与艺术的发展
审美经验与艺术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艺术终结”的背后隐含着传统的审美经验观阻碍了艺术的发展这一事实,审美经验已成为制约艺术发展的瓶颈,但这并不必然意味艺术要抛弃审美经验。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审美经验还是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因此需要在打破传统的审美经验观的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重新建构。
舒斯特曼受实用主义思想尤其是杜威的自然主义经验观念的影响,主张恢复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让美学重新回归到感性经验领域中来。一方面,他在杜威的经验概念基础之上强调审美经验的连续性、生动性、动态性,恢复它与一般经验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不满于杜威把审美经验作为定义艺术的手段,因为审美经验并不限于艺术领域,这种定义法会对艺术造成极为混乱的影响。舒斯特曼认为审美经验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概念,它既是一种提升的、有意义的现象学经验,也是一种内在的、情感的经验;它既是主体被动的接受反应,也是主体的主动体验;它不仅仅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审美经验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定义艺术或是证明评判的正确性,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指导性,即提醒我们在艺术和生活中其他方面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舒斯特曼对审美经验的重构思想和复兴策略主要体现在艺术理论和身体美学思想之上。在艺术理论上,他认为对审美经验的重构有利于界定艺术自身以及展开对艺术内涵的讨论,也为重新理解艺术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契机,同时还能更为恰切地解释当下的艺术活动。
二、艺术的定义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的历史中,自古希腊以来就出现了诸多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品,对于艺术的定义从那时起就不曾间断过。在现代艺术理论中,艺术的定义不断地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如何定义艺术成为了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难题。同时,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品,艺术的既有定义似乎显得苍白无力。对于这些质疑和否定之声,一些哲学家和艺术家乐此不疲的对艺术及其定义进行着阐释或争论。
(一)艺术定义的方法与问题
当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传统艺术理论的辐射范围,艺术理论的滞后性表现得极为突出,传统艺术概念无力去解释当下的某些艺术活动。固守传统的理论家打着维护传统艺术之纯洁性的旗号,大力地批判、质疑这些所谓的“艺术品”;激进的理论家则声讨传统艺术理论,否定对艺术定义的可能性;还有一些理论家则处在这两种态度之间,他们试图从新的视角去阐释艺术,界定艺术。由此可以看出,当下的艺术活动把艺术定义这一问题推到了艺术理论的中心,对于当代的艺术理论家来说,艺术的定义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关于艺术的定义问题。
1.本质主义的艺术定义。历史中存在着诸多关于艺术的定义,这些杂多的定义无不在寻求一个关于艺术的本质性规定。无论是柏拉图的“模仿说”,还是克罗齐的“直觉说”以及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都是本质主义的体现,只是他们所理解的本质有所不同而已。这种传统的艺术定义方式在20世纪之前一直统治着艺术领域,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如达达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等艺术创作形式),这种定义方式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无法解释这些现代艺术,以杜尚的作品《泉》(1917年)为例,无论是“模仿说”还是“表现说”都无法解释这幅作品,这些本质主义的定义方式无法解释作为艺术品的物品与物品本身到底有何区别。传统的本质主义定义在现实面前的无力和失效,使其陷入了危机之中,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开始出现。
2.反本质主义的艺术定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在20世纪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如“语言游戏”“家族相似”和“生活形式”等概念。这种哲学让艺术理论家们兴奋不已,他们纷纷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中寻求立论的根据。在反本质主义的阵营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认为艺术是不可定义的,以莫里斯·韦兹、威廉姆·肯尼克为代表;另一种也反对寻求艺术的本质主义定义,但他们认为艺术是可以定义的,以阿瑟·丹托、乔治·迪基和莱文森为代表。
韦兹和肯尼克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启发,他们认为艺术是没有本质的,存在的只是对艺术这一概念的具体运用,所以定义艺术是不可能的。韦兹又类比了维特根斯坦的对游戏进行描述时所运用的“家族相似”的概念,认为艺术的概念和游戏概念一样都具有开放性,各种艺术形式之间具有家族式的相似性,正是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构成了“艺术”的家族。在艺术这个家族中并不存在着一个始终贯穿于其中的线,存在的只是许多相互缠绕在一起的线。而丹托和迪基则从不可感知的方面来定义艺术:丹托认为艺术品的界定不是根据感知因素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一种关于艺术的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的知识即一个“艺术界”来确定的,也就是说艺术史的阐释构成了艺术;迪基进一步提出了“艺术惯例论”,他认为“艺术品首先是一件人工制品,其次还得被社会惯例的代表者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5]。这种艺术定义的方法既不关注艺术的内在特质,也不关注艺术的外在感知,而是基于历史层面对艺术进行定义,把其看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历史的延展性保证了艺术定义的开放性和可修订性。
(二)艺术定义的指向性
在舒斯特曼看来,传统的本质主义的定义方法具有“自然主义”的色彩,它们倾向于将艺术定义为“某种深刻的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的东西,它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能以某种形式得以表达出来”[6]299,艺术是人的自然需求和本能冲动,它产生于人类的这种需要和冲动之中。这种定义寻求的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的属性,体现的是一种寻求有意义的表达、形式的统一的自然要求,其中蕴含着人们对审美经验的渴望。而丹托等人的艺术定义归纳为具有“历史主义”色彩的方法,他们将“艺术概念狭隘的定义为由西方现代性工程带来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体制”[6]231,这种带有“历史主义”色彩的定义剔除了艺术中的情感和经验等因素,将其看成是历史性的艺术惯例解释的结果。舒斯特曼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局限性,如果说自然主义的观点不能充分的说明构造艺术实践和决定艺术接受的社会体制和艺术惯例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观点则不能充分的解释艺术的自然属性和其对于人类的益处。
舒斯特曼认为艺术定义的根本指向不应聚焦在艺术的本质特征或区分界线之上,而是要聚焦于深化和改进对艺术的理解这一维度之上。那种企图把艺术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孤立出来的理论诉求,旨在寻找一个通用的语言公式来定义艺术,“这种语言公式要么错误的涵盖要么没有成功的涵盖,因而是要么错误的包括要么错误的排除艺术领域中的东西它所追求的理想是完美的覆盖和清楚的区分,是一种包装型的理论,这好比是食品包装纸那样,意在展示、包含、保存对象,但并没有加深我们对于对象的经验与理解”[6]179。舒斯特曼将这些艺术定义的方案形象称之为包装纸式的艺术理论,它们旨在呈现、保存艺术,旨在维护而不是变革艺术的实践和经验。作为艺术的定义应该立足于加深我们对艺术的欣赏、理解以及提升我们的经验,进而阐明什么是艺术中重要的东西,解释艺术如何取得其效果或者艺术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一个定义对于艺术或美学来说是有用的,而不必在精确划分当前艺术外延界限的形式意义上是真的”[6]228。
(三)艺术即“戏剧化”
舒斯特曼从审美自然主义中提出了“经验”这个要素,从社会历史主义中提取出了社会历史这个核心要素。他认为一个完整的、成熟的艺术定义应该调和这两种极端,处在经验与实践之间,因而他主张将“经验强度”(experiential intensity)和“社会框架”(social frame)两个因素整合进一个单一的概念之中。他为此在英语和德语中找到了一个比较贴切的概念——“戏剧化”(to dramatise or dramatisieren)来定义艺术。据舒斯特曼的词源学考究,“戏剧化”这个动词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指的是把某个东西搬上舞台,“意味着抓取某个故事或事件并把它放入一个戏剧表演的框架之中或是一个剧本、剧情之中”[6]234;其次,它的另一层意思是指“把某个东西看作,或使之看上去更令人激动或重要”[6]234。
“艺术即戏剧化”的定义旨在强调:艺术是在某一框架或场景之中的上演,并且这种上演是非常生动的和令人激动的。具体来说,艺术首先意味着把某个东西放入一个框架之中即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舞台,这个框架的作用是把这件东西从日常生活领域中突显出来,从而把其标记为艺术;但是使艺术在根本上区别于日常生活的并不是那个社会框架,而是生动的、富有强度的经验的上演。此外,舒斯特曼还指出“戏剧化”这个框架并不仅仅是一种起到隔离性作用的栅栏,它还是对框架之中的物的一种聚焦,使其呈现的更为清晰;它更像“一个放大镜通过折射性框架的聚焦提升了太阳的光和热,因而艺术的框架加强了其经验内容对我们情感生活施加的力量,从而使这个内容更加生动和有意义”[6]236。
这种艺术定义发挥的是一种指引性作用。它的好处在于有效的综合了“经验强度”和“社会框架”这两个因素,突显了艺术中被忽视的某些关键性因素,联结了没有充分关联起来的艺术特质,从而起到了一种联结和呈现之功用。就像把看似毫不相关的星星相互联结使之成为一个可见的星座一样,这种定义把艺术的不同方面集中起来并相互联结起来,使之呈现成为一个清晰的、名为艺术的“星座”。这个“艺术星座”内部的要素或成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环境和艺术惯例的变化,处在一种不断地变动和生成状态之中。
三、通俗艺术之辩
(一)为通俗艺术正名
一直以来,通俗艺术(Popular Art)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虽然名义上属于艺术但却被轻蔑地冠以“通俗”之名,它不仅受到理论家和美学家的不断攻击,而且它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舒斯特曼对通俗艺术的遭遇深表同情,他承认通俗艺术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弊端,但它的优点和潜能往往被无视。现代艺术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把艺术看成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从而区别于日常生活等领域,作为艺术的特质——审美经验——概念则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区分性。具有自律性、无功利性和形式化审美经验不仅使艺术区别于日常生活进而使其自绝于日常生活领域,还使得通俗艺术陷入被质疑和批判的尴尬境遇。在艺术内部,通俗艺术往往被指责为缺乏审美经验和审美自律性而被排除在审美领域之外。他对通俗艺术持一种改良主义的态度,他并不否认通俗艺术所带有的缺陷和不足,但他反对现代美学对通俗艺术的排斥和淹没。现代美学过于重视自身的纯粹性和形式化,从而把生活领域、通俗艺术等都拒斥在门外,切断了艺术与生活经验、身体感知等非艺术经验之间的连续性。而通俗艺术则保留了这种经验上的连续性和丰富性,这些特性正是复兴审美经验的关键之所在,也是艺术理论走出困境的有益尝试。
舒斯特曼认为通俗艺术遭受的这些谴责归根结底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二分术语——“高雅/通俗艺术”(high/popular art)。正是这个术语让人们想当然的把高雅与通俗简单的等同于好的与坏的,进而质疑通俗艺术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这种逻辑未免过于简单、武断;再者,高雅和通俗两个词是在一种描述意义上的使用,它们并不是对艺术价值的评估,更不是对艺术本身的定性,因而没有理由把高雅和通俗看成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区别;最后,不可否认在高雅艺术/通俗艺术之间存在诸种差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一种本质的和不可逾越的划分。希腊戏剧在当时是一种最通俗不过的娱乐形式,正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一样,可如今却被人们视为高雅的艺术。总之,高雅艺术/通俗艺术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或永恒不变的,因而我们不应把它看成是一种本质性的判定或是断然的轻视通俗艺术,而是要更多的关注具体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
(二)为通俗艺术的审美辩护
在为通俗艺术正名之后,舒斯特曼开始逐一反驳对通俗艺术所做出的批评性观点,他将这些批评和质疑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将其中的误解一一澄清。
1.审美满足问题。对通俗艺术最普遍的美学指责在于“它根本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审美满足”[7]。也就是说,欣赏通俗艺术时所带来的那种明显的满足感、愉悦感以及情感体验,被看作一种虚假的满足而非真正的审美满足。在批评者看来,通俗艺术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短暂性还体现在了通俗艺术的流传时间上,即它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针对由短暂性而带来的虚假性的批评,舒斯特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批评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因为暂时性的满足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虚假的满足。批评者之所以会把暂时性的满足与虚假性相关联,是因为我们内心有一种对稳定性的渴求,而且这种稳定性自柏拉图以来就被误解为是一种永恒的确定性。因而,与之相对立的暂时性满足就自然而然的被判定为一种虚假的东西。至于通俗艺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这一指责,舒斯特曼认为这也和虚假性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做出这种断言也为时过早。其实,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社会文化制度——未被揭示出来,在经典流传的背后发挥关键作用除了艺术自身之外还有社会制度的干涉和教育系统的选择。总而言之,对通俗艺术的虚假性的断言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指控,这种指控背后影射出的是文化精英阶层的专断、专横和惧怕之情,面对席卷而来的快感和破坏性他们十分警惕,力图通过权威的规定和舆论的声讨来质疑、否定通俗艺术的满足感。
2.审美挑战问题。某些批评者认为真正的审美满足必须是经过知性上努力才能获得的,而通俗艺术带来的审美满足通常是被动的或不费智力的努力就能获得,它太肤浅了以至于很难获得知性上的满足,因而也就无法在审美上提供应有的挑战。不可否认,某些通俗艺术带来的满足或经验确实有些简单、肤浅,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显而易见的缺陷而在于批评者的理论指向。舒斯特曼认为把审美经验的获得归结为“知性上的努力”是有问题的:审美经验的获得除了知性上的努力外,还有可能通过身体的感知和运动的参与,比如摇滚音乐的欣赏更多的依赖于身体动作的投入。其实,在获得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感性和知性并不是相对立的,感性上的努力也不应被看成是无效的。此外,即使欣赏通俗艺术的时不需要智识上的艰难努力,但这并不意味这种欣赏和享受不能被理性的分析或思考。
3.创造性问题。还有一些批评者指责通俗艺术缺乏创造性,通俗艺术“被诋毁为不仅仅是非原创的和单调的,而且必然如此”[7]。他们认为通俗艺术的标准化、技术化的批量式生产必然会压制创造性。舒斯特曼认为批评者对通俗艺术的生产机制的揭示不无道理,这种生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作者的创造性,但是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论断是有失偏颇的。标准化的生产或创造并非仅仅存在于通俗艺术中,高雅艺术中也有标准化的规定,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十四行诗。因而,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并不排斥创造性,或许“带着镣铐跳舞”会更加刚劲有力。不可回避的是,通俗艺术中的模式化倾向和雷同的情节比较严重,但这种模式化背后其实隐含着极大的创造性空间。此外,批评者还把获得更多受众之目的和个人的创造性相对立,他们认为通俗艺术为了获得更多的受众群体,不得不牺牲创新性和实验性。这种推论逻辑是有问题的,创造性的表达自我和让更多受众满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而将两者对立起来的逻辑是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它根源于天才的浪漫主义神话,其强调的是与现实生活相隔离,蔑视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这种个人主义的神话早已破灭,因而这种指控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4.审美合法性问题。关于通俗艺术诸种指控,其实最终都指向了它缺乏审美的自律性和反抗性,并由此判定通俗艺术不具有审美的合法性。布尔迪厄认为“在艺术中,形式、方法、风格是占主要地位的,而不是表现、说出某种东西的功用的‘主体’、外在关涉的基本对象”[8]。也就是说,自律性对艺术和审美来说是最为根本性的,艺术除了对自身之外不对别的任何事物产生功用性,具有娱乐、满足大众功能的艺术不是纯粹的艺术,通俗艺术因此被排除在审美之外。在舒斯特曼看来,这些批评者将艺术看成是本质上与生活、现实相反甚至是相隔绝的东西,阿多诺尤其坚持这一点,他认为艺术只有通过“不同于我们的现实世界”并“从现实功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才能证明和确定自身的正当性”[9],自律性将艺术和现实生活严格的分离开来。这种自律性艺术其实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尽管艺术由此被认为是纯粹的,其实背后隐含着诸多社会动机和利益;再者,滋生它的社会环境早已改变,艺术和审美的概念不可能自绝于日常生活领域。将艺术与生活相隔离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上的偏见,还是对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它源于柏拉图对艺术的定义。我们应该超越这种偏见,将艺术与生活实践相联结,把艺术既作为欣赏对象又作为经验之物,让艺术栖居于日常生活和现实功用之中。正如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联结审美和日常生活领域,恢复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连续性。
此外,针对布尔迪厄等人对通俗艺术的彻底质疑和取消策略,舒斯特曼认为这些批评过于偏激,更有失偏颇。批评者忽略了审美话语、艺术话语的公共性和共享性,审美、艺术等话语形式并非专属于高雅艺术,他的论断假定了高雅艺术对艺术话语的合法性使用以及排他性的占有。另外,高雅艺术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并不是来自通俗艺术的肯定,在其背后发生关键作用的是社会制度、文化权力的运作。高雅艺术在权力、权威的保障之下,垄断着艺术的话语权,进而排他性的占有艺术的合法性资格。正是在这种权威的保障之下以及作为批判的对象——通俗艺术——在事实上的缺席现状,才使得高雅艺术的统治地位得以维持下去。
有的批评者认为舒斯特曼的美学辩护实质上是在挑战高雅艺术的权威,否定高雅艺术的价值。这种批评完全是对舒斯特曼的误解,表现了其受自笛卡尔以来所确立的那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之影响,而这种相互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正是实用主义者所极力反对的。在这里,可以借用舒斯特曼的“相容性的析取立场”(inclusively disjunctive stance)对此进行澄清,舒斯特曼认为逻辑中的析取性立场包含着极强的二元对立、相互排斥的含义,“非p即q”式的逻辑应该被多元性地理解为“p”“q”以及“p与q”在内的多种选择。因此,尽管舒斯特曼欣赏通俗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高雅艺术。他为通俗艺术作美学辩护并不意味着要抵制高雅艺术,他所针对的并不是高雅艺术本身,更不是为了否定高雅艺术的价值,而是批评高雅艺术对审美合法性地位的垄断以及它对通俗艺术形式的排他性抵制。
四、以实用主义为底色的艺术哲学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传统哲学把本来作为整体的世界人为地划分为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等两相对立的世界,又试图通过诸种路径来连接相对立的主、客关系,实现一种所谓的对立统一。杜威认为哲学应该超越这种人为的二分,回到先前整一的世界之中。他认为人作为一种“活得生物”(live creature)与世界是一体的,人无法从世界中分离出来,世界并非人的对立面而是人的环境,活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呈现为一种共生、交融状态。而经验正是在人与世界的接触、互动之中出现的,它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但既不是纯粹主观的也不是纯粹客观的,它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自然而然伴随出现的。舒斯特曼把杜威的经验观念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和具体化,把它具体运用到艺术思想之中,从而把杜威的这种基于经验自然主义的一元论之上的“经验”概念改造成为其多元论美学思想中的富有连续性、生动性的审美经验,并通过这种改造后的审美经验来扩充艺术领域,进而推动艺术的发展。
舒斯特曼习惯把自己称之为“新一代的新实用主义者”,以此来强调他与以罗蒂等人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他已然接受了分析哲学的语言观念,但他不再仅仅停留于语言使用的分析和概念分析之上,而是走出了语言的迷雾回到实践中来。看似是对经典实用主义的回归,其实不然。舒斯特曼既吸收了罗蒂、普特南等人的“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可错论”等思想,但又明显地不同于罗蒂那激进的“反”和一味的“破”,而是采取一种“相容性的析取立场”进行分析,从中汲取可用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反观舒斯特曼的艺术哲学思想,相容性的析取立场是多元论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其根本的理论方法,其艺术哲学所针对的就是那种基于二元论基础之上的传统美学观念即自律的、无利害的、二分的审美观念,其强调的是审美经验的连续性、多样性和生动性。因此,审美经验这一概念始终贯穿其中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审美经验是其美学理论得以建构的支撑点。
他的艺术理论体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权变色彩,富有极强的灵活性和建构性。如在艺术的定义问题的讨论上,将定义的指向性转到指导性和有用性等功能之上,即旨在强调艺术概念对理解艺术和经验等方面的价值。他调和了审美自然主义理论只注重经验强度和历史主义理论只注重社会惯例的狭隘偏见,并有效地将这两个因素辩证地统一于“戏剧化”的概念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艺术和生活有效地联结起来而不是让艺术自我孤立起来。作为“戏剧化”的艺术定义在恢复经验的连续性和生动性的同时,又强调了艺术对经验的集中和强化的特质,体现了一种介于经验和实践之间的理论倾向。
总之,舒斯特曼的艺术哲学思想以审美经验的重新建构为基点,对艺术的定义和“艺术终结”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为通俗艺术做了美学上的辩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艺术哲学“从艺术自身赖以存在的各种内容和形式上审美的内部规律出发但突破封闭的‘自律论’与杜威同样反对精英主义‘博物馆’式的‘为艺术而艺术’、坚持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他律’”[10],其旨在调节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沟通审美经验与一般经验、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遵循的是一条处于理论与实践、分析与解构两极之间的实用主义路径。
参考文献:
[1]SHSTERMAN RICHARD.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 Alternatives for the Ends of Art[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1.
[2]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M].New York: Harcourt,1968:222.
[3]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8-19.
[4]SHSTERMAN RICHARD. The End of Aesthetic Experience[J].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97,55(1):29-41.
[5]DICKIE GEORGE. Art and the Aesthetics[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34.
[6]SHSTERMAN RICHARD. Surface and Depth: Dialectics of Criticism and Culture[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7]SHSTERMAN RICHARD. Don’t Believe the Hype: Animadversions on the Critique of Popular Art[J].Poetics Today,1993,14(1):101-122.
[8]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3.
[9]ADORNO T W. Aesthetic Theory[M].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322.
[10]毛崇杰.实用主义美学的重新崛起[J].艺术百家,2009(1):131-137.
(责任编辑杨文欢)

——一个谱系学的考察与回应*①
——充满艺术的实用主义者Eva 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