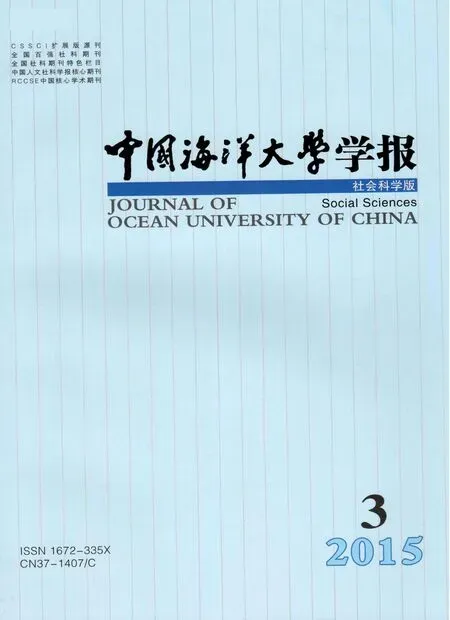论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系 *
论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系*
段宇晖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同构与并行的关系,这表现在二者的同源性、相互影响、相互生发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否能够收入海外华文文学以及收入哪些海外华文文学,需要具体地考察二者的实践关系,即文学文本的生产、接受以及批评、影响的场域是否融汇于中国文学之中。如果机械地从作家的国籍或民族属性进行甄别则无法完整、客观地描述文学的现实运行状况。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收稿日期:*2014-11-12
作者简介:段宇晖(1970-),男,河南偃师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专业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3-0125-04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parallel and complementary as they have the same origin,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generate from each other. To judge whether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could contai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hich part of it, the practical eleme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such as whether the literary text production, acceptance, criticism, and influence is integrated into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If the standard is rigid on author's nationality or ethnic attribute, it is impossible to describe the real situation of literature completely and objectively.
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当前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付祥喜博士为代表的,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并未形成多个中心的局面,海外华文文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至少海外华文文学里面的现当代部分应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另一种以陈国恩教授为代表,认为作为国别的文学史牵涉到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别主体确定,而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参见付祥喜:《文学的身份认同:民族的还是国家的?——与陈国恩教授商榷》,《华文文学》2012年第4期。陈国恩:《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讨论问题的方法与态度——回应付祥喜博士的商榷》,《华文文学》2013年第6期。以下针对两位作者的相关引文皆出于这三篇文章,不再详注。这两种观点的争论都聚焦于海外作家的国籍或民族属性,各执己见,而忽略了具体的作品生成、读者接受、文学批评与影响等实践性因素,也就妨碍了文学史所应把握的文学本相。
以下在论述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系时,笔者将分别对上述两位学者的相关文章加以辨析,厘清相关问题。
一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同构与并行的关系,这表现在二者先天的同源性,实践中的相互影响、相互生发。
中国与海外,这两个地理上的空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存在着历史的流动性和延续性。清末民初,自梁启超提出以“文学革命”改造国民性的口号始,中国第一批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践行之。他们通过译介、移植西方先进的文学思想,开启了以“五四”新文学为开端的现代中国文学传统。知识分子不断从海外回归、并反哺中国文学的潮流一直延续到了50年代初,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大陆中止。此后,继续前往西方国家求学的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青年,一些人定居国外并从事着汉语写作,包括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白先勇等一批作家涌现出来。他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超越两岸三地间意识形态的割据,勇于怀疑,求变创新,掀起了一股以强调人的个性抒发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也推动了台湾地区6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同时期中国大陆革命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形成同构互补关系。当代新移民作家则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产生的,最初的一些人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有的在移民之前在国内就已享有盛名。许多移民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仍然面对中国读者,首先在中国两岸三地出版问世,受到中国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与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兴起对海外华文文学的革新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海外华文的教育与报刊出版始于清末民初。“五四”启蒙文学之前,海外的华文报纸都是文言文,副刊上刊登的也主要是一些文言小说、散文和旧体诗词。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仍属于旧文学的范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崇尚科学与民主的潮流席卷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文学领域最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蕴含了反帝反封建内容的白话文新文学作品迅速取代旧文学而成为文学的主流。南洋地区得风气之先,很快也出现了白话文学作品,由此开创了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历史。中国的历次文学运动,像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两个口号论争、抗战文学运动等,都对南洋文学运动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尤其是抗战文学运动,在东南亚各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在历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1](P14)西方欧美国家的华文文学起步较晚,这与那里早期移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在社会生活中居边缘与弱势地位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来自台湾地区的大批青年学生的美国留学热潮,出现了“留学生文学”现象,使北美的华文文学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呈后来居上之势。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来自大陆的移民潮也主要流向欧美国家。现今那里已经涌现出许多大大小小的中文文学社团、中文报刊、文学网站,成为各种文学风格与流派交相竞艺的场所。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的新文学一样是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母体中孕育诞生的,绝大多数的海外华文作家也都是炎黄子孙,自幼受着故土文学传统的薰陶。因此,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延续,并且多多少少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然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生活环境所提供的是不同的文学土壤,近百年来滋生于异国土地上的海外华文文学必然受到各居住国人民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异域文化那些不同于本土文化的异质性使得海外华文文学逐渐呈现出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的面貌。故土性与异域性交相融会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特点。
二
针对海外华文文学能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学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别主体确定”上。但是对于如何确定,对立的双方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付祥喜的文章认为,“当种族认同与国籍认同不同或基本不同时,不能把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混为一谈。”他把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看作文学主体的民族身份而非国籍身份,理由是作为国家指称的“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物,而上溯先秦、两汉、唐、元、宋、明、清各代文学中并无“中国文学”的说法,就如梁启超所叹,当时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必须把“中国”看作“华夏族”或“中华民族”的指称,即“只有中国文学的‘中国’是文学的民族身份,中国文学才能够涵盖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他进而用“中华民族文学”的概念替换了“中国文学”,既然海外华文文学的语言形式表明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作品中又不乏民族的想象、加上一些海外作家的自我表达——“我们是用中文创作的,所以应是中国文学的延伸。” 因此,得出结论:“不仅海外华人用汉语写成的作品,而且连他们偶尔用汉语以外的语言写成的作品,都可以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陈国恩教授指责付的方法“是先别出心裁地对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作一番自己的界定,然后在他所界定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从而有别于他人基于这一概念的一般意义所作的研究。”其实,付的问题在于,当他在强调区分文学主体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的时候,却把种族认同(或族裔身份)与国家民族认同进行了混淆。的确,历史上罕见哪朝哪代把“中国”作为国名,“中国文学”也不是指中华民国文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但这并不取消中国文学的国家身份。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了解,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现代国家身份的认同意识密切相关。*见昌切:《现代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现代国家概念是民族主义意识下的产物,它被看作“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在这种想象的过程中,文学的力量往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现代观念中的民族也不是凭空的捏造,而是根植于历史之中,正如现代文学的产生也是脱胎于传统文学一样。现当代文学史是断代史,但文学历史断裂处形成的模糊地带并不那么容易被抹去,因此也就有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先秦、两汉、唐、元、宋、明、清各代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是先天的存在,更不会以国家政权的更迭而改变。海外华文文学也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继承,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准确地说应该是“族裔”或“种族”的文化传统。把海外华人从属于中华民族、把海外华语文学纳入中华民族文学的范畴,实际上是把族裔、种族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混淆的结果。至于文学的语言表现形式、文化意义、作家态度等因素并不能直接被当作考量的标准,正如美国文学一样使用英语表达,也不乏对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想象,却不能和英国文学混为一谈。
陈国恩教授断然否定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可行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别主体确定的问题”。既然海外华文作家“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的国家认同与中国人已经不同”,因此,没有理由把他们的创作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陈教授看法的偏颇之处在于把“文学的民族身份”简化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国别身份。这种界限的划定给他自己的论证也带来了困难。例如,他认为中国两岸三地的作家一旦加入了外国国籍,“就不便归入中国文学史了——但应该写到他们加入外国籍为止。”“哪怕她或他是华人,她或他的作品是在中国发表,而且影响很大,就像高行健,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都写到他加入法国籍为止,而没有把他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灵山》算作是中国文学——这样处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坚持国际准则。”陈教授在这里没有把话说清楚,因为《灵山》实际上是在高行健加入法国籍的五年之前已经在台湾出版了的。而中国文学界也恰恰是把诺贝尔奖授予高行健看作是意识形态问题,才一直未把《灵山》列入现当代文学史的。陈的标准实际上导致了对文学史中的作家进行机械的分割,有悖于文学史的书写传统。例如,帝俄时期一批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曾遭受政治迫害,被迫加入外籍,就像赫尔岑,俄罗斯文学史从未将他的文学活动作前后切割,也没有哪个其他国家的文学史主动认领。所以针对像白先勇、严歌苓等移民作家的文学身份归属问题,陈在文中也承认,“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我的意见也只是个人观点。”
三
文学史的研究涉及到给定的客观与看待它的主观之间的视差,“外在客观事物能否被人认识,关键不在于客观与主观自身的属性如何,而在于人所建构的认识框架如何。”[3]陈国恩教授看到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处于膨胀的时期,他把世界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提法看作是这种学科膨胀意识的体现。实际上他所持的否定态度也是从学科意识出发,例如,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的“中国”是一个国别的身份,而非民族的身份,他特别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分类标准。这与他之前提出的“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别主体确定”标准形成了矛盾。国别身份对于作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文学史要记录和描述的所有文学活动既可以以作家为中心,也可以以作品、以读者为中心而展开叙述。海外华文文学无疑是海外作家创作的汉语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是否也全都是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现实中就不尽然了。
当下在中国最受瞩目的海外华语文学是一些移民作家的作品,包括白先勇、陈若曦等老一辈作家和严歌苓、张翎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他们大量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中国的两岸三地首先问世,并且造成相当的轰动效应。移民作家都是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主体属性决定,无论是历史记忆、文化启蒙,还是伦理观念、家国意识,都要受本民族传统精神的制约。他们的特别之处只是在成年之后,选择了海外定居并写作。因此,移民作家与中国本土的同时代作家,在精神成长过程中具有明确的同源性。他们也深谙这样的道理:从事汉语写作就一定要与中国文学界建立深入广泛的联系。因为任何作家的声誉都建立在好的作品、批评家的认可与读者的接受的基础上,这三方面缺一不可。而读者的接受直接决定当下作品的市场价值,是作品的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作家维持其写作事业的前提条件,对于游走于中西文化边缘的移民作家也概莫能外。这一点从严歌苓、张翎等人近年来作品影视改编的红火就可以得到验证。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在中国大陆问世后,旋即引来一片好评:“小说从清末华工方得法远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讲起,详细地描绘了方家四代人在异国他乡的卑苦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与故土广东亲人的悲欢离散。小说以个体和家族命运为切入点,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屈辱的近现代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族兴衰有力地纳入了叙述。它不仅是一部将赴加华工的命运首次引进当代文学视野的叙述实践,同时也是一次探讨国际大背景下国族身份与认同的重要的史诗式书写。”[4]果真如此,那么对于这样的主旋律作品,有什么道理要排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外呢?
移民作家现象可以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或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他们的汉语写作在价值认定上仍须从汉语文化圈中获得。对于当代移民作家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学主流就是他们现世的参照系,是否与之达成一致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国籍身份归属,而是和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身份属于过去亦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与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不断‘嬉戏’”。[5](P211)当代移民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有历史的渊源,有论者指出张翎写作中的家国想象、中西元素以致语言的精细等都有对海派作家风格的继承,然而缺少了些张爱玲式的虚无与决绝,添了几分理想主义的意象。[6]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严歌苓、虹影等移民作家那里则不乏理性的深度与现实的批判,而且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对启蒙思想的追求一脉相承。毕竟,中国的现代性历程远未完成,这一代人走出国门之后还是要面对自身文化属性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差异,由此出现精神上的焦虑感和身份认同的危机。而异域的经验也给予他们新的思维方式与评判标准,在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记忆和生存境遇中追求新的艺术创作境界与思想深度是海外流散文学的应有价值。无论在全球化时代出现怎样的话语混杂与文化多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始终是他们坚持汉语文学创作的驱动力。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一种所谓的“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
现实中,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场域既非完全分离的两个空间,也非完全重合,而是有所交叉。这样就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应该对海外华文文学有所取舍。在进行甄别时,既要考察作品的生产、接受、批评与影响等文学活动的外在标准,也要坚持“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这一内在标准。说华文文学的根在“中国”并不为错,但据此判断世界华文文学尚未形成多个中心,则与事实不符。除了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主流行列的移民作家文学之外,如前文所述,在东南亚国家、北美、欧洲等地都存在独立自足的华文媒介环境。那里的文学活动立足本地,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属性也逐渐归依于新的多元文化社会与多种族国家,如陈教授所言:“他们内心也有矛盾,但只是在争取建立新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矛盾”。那新的国家自然蕴含着新的民族精神,而表现这种新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文学也就无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去涵盖了。
参考文献:
[1] 陈贤茂.陈贤茂自选集:上册[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张荣翼.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哲学思考[J].中州学刊,1995,(1).
[4] 张翎长篇小说《金山》研讨会在京举行[N].文艺报,2009-08-13.
[5]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 赵稀方.历史,性别与海派美学——评张翎的《邮购新娘》[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Duan Yuhu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modern &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责任编辑: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