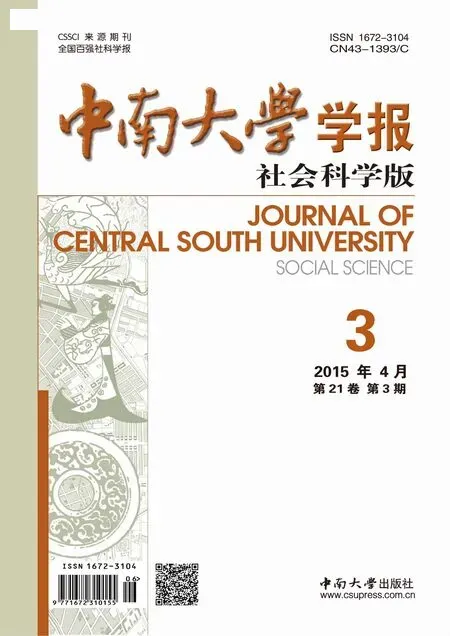“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陈昌云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233030)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陈昌云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233030)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弘治朝;文学中兴;历史考察
明代文学的研究长期呈现“两头热,中间冷”状况,成化、弘治朝文学更少人问津,而弘治文学是明中期文学的开端,也是近世文学复兴之始,处于明代文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值得关注。但相比史家对“弘治中兴说”的细加考辨,文学研究界对“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一直缺乏细致梳理,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考察其间文学的发展状况和总体成就,探究其转变成因和影响,有利于人们科学评价弘治文学的时代价值与历史地位,增强对明中期文学的了解,也便于科学认识文学发展状况与时风政局的关系。
一、文史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不同阐释与评价
史家的“弘治中兴说”主要评判明孝宗朱佑樘的个人品行与历史政绩,古今多有论述,也存争议。弘治进士陈洪谟云:“惟我敬皇帝在御十有八载,明作之功,惇大之化,比隆三代。而又克勤于政,无日不视朝,虽值雨雪传免,而銮舆犹御正衙,呼二三大臣参决政务。”[1](67)他盛赞弘治朝“比隆三代”,并将之归功于孝宗的仁德勤政。《明孝宗实录》也称弘治朝“君明臣良,极一代治功之盛”[2](1−2)。谈迁则描述弘治朝的繁荣局面:“明当中岁,国家积岁熙洽。鸣吠烟爨,蒸蒸如也,岂不称盛际哉。”[3](2833)清人更喜欢将孝宗与历代帝王相比。钱谦益认为:“孝宗皇帝,本朝之周成王、汉孝文也。”[4](3)《明史》则称本朝帝王“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5](196)。既肯定孝宗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贤君,又认为形成“弘治中兴”的主因在于孝宗具有“恭俭有制,勤政爱民”的优良品行。
当代学人在沿用旧说的同时,出现诸多质疑之声。一些学者不满于明清学人对弘治朝的吹捧,认为不合历史实情。明史学家王其榘说:“都是些溢美之词,就算有这种情况,那也是他初即位时的几年。”[6](157)郭厚安也对孝宗评价不高:“一个缺乏雄才大略的平庸之辈,因而没有赫赫的文治武功。”[7](77−78)李焯然更认为:“殊不知晚明的没落,成化、弘治年间已潜伏了由盛而衰的因素。”[8](133)赵永翔则指出弘治朝存在诸多弊政,认为“‘弘治中兴’是在明中期国运日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短暂的‘小安’时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中兴”[9](54)。左东岭也说:“弘治时期决非如后来的文人所想象的那样美好,简直达到了儒家理想中的盛世。”[10](132)由此看来,随着人们对“弘治中兴说”认识的逐步深化,争议不断出现,终未形成一致看法。
与史家所论不同,文学界的“弘治中兴说”实指明代文学于中期的弘治朝再度复苏、振兴。古往今来,学者对此论述较多。弘治进士康海云:“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11](卷十)同时代的顾璘也云:“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12](卷一)清人也多有附和。钱谦益认为:“成弘之间,长沙李文正公继金华、庐陵之后,……昭代人文为之再盛。”[4](269)《明史》描述七子派崛起文坛云:“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5](7348)当代学者对“弘治中兴说”也多有赞同。章培恒说:“明代文学复苏始于弘治时期。”[13](57)罗宗强也认为弘治朝是“短期中兴”[14](2)。由此可见,文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内容阐释与评价态度均与史学界不同,他们一致认可弘治朝文学复兴的历史事实。
学人在谈论明中期文学复兴时常将弘治、正德两朝并举,主要考虑到前七子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时间兼跨二朝。事实上,前七子文学复古活动主要在弘治朝,从弘治六年李梦阳登上文坛开始,直至正德初复古派暂受刘瑾之乱打击,这十七八年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和高潮期,他们的主要理论成果和代表性作品多形成于这一时期。正德后,徐祯卿、何景明、王廷相等人甚至重新转向理学,文学复古运动归于平寂。因此,明中期的文学复兴可概括为“弘治中兴”。
二、弘治朝“文治蔚兴”的表现
弘治朝文学复兴的局面首先表现为文风大炽,上至帝王大臣,下至民间士人都纷纷加入到古文辞创作队伍之中,文学社团众多,操觚染翰、赠答酬唱成为时尚。孝宗皇帝一生勤俭节制,清心寡欲,在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方面堪称明代帝王的楷模,竟也不顾谏官多次劝阻,难舍文艺之好。《明史·艺文志》载孝宗有《诗集》五卷,可惜失传。《列朝诗集》《明诗纪事》收孝宗《静中吟》诗云:“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钱谦益评之:“《静中吟》一绝,见于李东阳《麓堂集》。粹然二帝三皇,典谟训诰,不当以诗章求之也。”[4](4)但李东阳却称赞其诗:“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客观来看,此诗文学审美特征不强,很难称得上一首好诗。陈洪谟《治世余闻》卷一载:“上体稍不佳,即诵诗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其善于颐养如此。尝因重阳出一对曰:‘今朝重九,九重又过一重阳。’命太监萧敬等对之,皆不能应。至今亦未闻有能对者。”[1](10)不论孝宗吟诗作对的水平如何,但有五卷诗歌的创作数量足以说明孝帝皇帝是诗歌爱好者。
孝宗的雅好文艺带动了朝臣们的诗文倡和风气,馆阁大臣们经常举办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宴饮酬唱活动,切磋诗艺,以文会友。李东阳《联句录》一书收录与之酬唱的44位文友的诗作,他们聚会名目很多,有送行、祝寿、贺迁、赏梅花、庆佳节,乃至探病、打赌输赢等等,大凡集会总离不开宴饮酬唱、赓酒赋诗活动。其中仅成化十三年间,他与众友人或门生饮酒赋诗就达14次之多。李东阳《玉堂联句》《同声集》书中也同样描述文人们众多的宴饮酬唱活动。其他馆阁大臣也有相关记载。程敏政《梁园赏花诗引》云:“予以诗约同寅汪伯谐、彭敷吾、倪舜咨、李宾之、宋尔章五太史及同年张汝弼驾部,倡为兹游,是日,诸君子以予诗分韵,各当四章,而饮宴歌呼,相与竟日,故诗或成,或不成,或半成。”[15](卷二十八)杨一清《焦山倡和诗引》云:“吾诗恍如醉梦中语,而诸君吟讽玩赏各极其趣,虽体裁音节言人人殊,要之畅舒性情,模写风物,不作雕镂叱咤语,均为治世之音也。”[16](卷一十三)李东阳本人甚至承认自己溺诗至有癖地步,“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还同嗜酒客,枕籍糟邱里。”[17](卷四)可见馆阁大臣们多么醉心于赓酒赋诗活动。
中下层官员的诗文宴饮活动也热闹非凡。吴宽及第后经常与同乡京官结社唱和,“而吾数人者又多清暇,数日辄会,举杯相属间以吟咏,往往入夜始散去,方倡和酬酢,啸歌谈辩之际,可谓至乐矣!”[18](卷四十)弘治后期,这种诗文聚会活动更加频繁,李梦阳云:“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19](卷五十九)他还细致描述当年热衷与同僚诗文宴饮的情况:“缙绅不识忧,朝野会清宴,嗜酒见天真,愤事独扼腕。出追杭秦徒,婉娩弄柔翰。探讨常夜分,得意忘昏旦。雪雨亦扣门,仆马颇咨惋。”[19](卷十五)中下层文人的集会除宴饮赋诗外,还开展学术研讨:“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赜剖,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学,於乎亦极矣!”[19](卷五十二)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助推了弘治朝“人文蔚兴”局面的形成。
弘治朝古文辞的推广普及到政府外士子,民间人士也雅好其道。吴宽未仕前已嗜好古文词,王鏊撰吴宽神道碑云:“公生有异质,未冠入郡庠,辈流方务举业,公独博览群籍,为古文词,下笔已有老成风格。”[20](卷二十三)其《家藏集》中也记载一些民间人士的古文词之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言周氏于太学时即“尤好古文词”[18](卷三十九),《乡贡进士陈君墓志铭》言陈隧“其学不专治进士业,兼能古文词”[18](卷六十二),《苏州府儒学教授刘先生墓志铭》言刘谕“经学之外,为古文词,典雅得法”[18](卷六十四)。陆深《俨山集》中也有同样描述,《李世卿文集序》言李承萁“少遂不举进士,而肆力于古文章”[21](卷四十三)。《碧溪诗集序》言张子威“自少时一再游场屋,即弃去,学古人之道,攻古人文章”[21](卷四十三)。李东阳也为民间诗人谢世懋作《王城山人诗集序》,弘治朝的民间古文辞作家为数不少,他们为民间诗文的繁荣和技艺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弘治朝的文学爱好者不仅以文学自娱自乐,而且基于相近的文学理论主张、创作风格和政治倾向,结成不同文学流派,以壮大声势,提高创作水平。这期间主要有以陈献章为首的白沙学派、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李梦阳为首的七子派、以朱应登为首的六朝派、以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派,他们利用社团开展文学活动,吸纳、培养文学新人,交流创作经验,研讨文学理论,提出文学主张,互相标榜,壮大声势,共同推动弘治朝“文治复兴”局面的形成。
弘治朝文人在热衷诗文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诗文创作理论和文体特征的探究,从理论层面上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为文学复古运动的到来奠定基础。弘治朝除出现程敏政的《明文衡》外,还催生了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何孟春《余冬诗话》、徐祯卿《谈艺录》、杨慎《升庵诗话》等几部重要诗话。前七子们虽没有诗话专著,但在一些序文题跋中也谈诗论文,他们的文学思想大多形成于弘治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论家主要通过“诗文之辨”命题的研讨,清除理学对文学的侵害,恢复诗文的本真面貌和审美特质。他们首先要求恢复诗歌原有的格律声调之美,李东阳云:“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音也。……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17](卷二十二)李梦阳云:“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19](卷五十二)他们还强调诗歌的抒情特质,李梦阳云:“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正变者时乎?”[19](卷五十一)徐祯卿则云:“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22](谈艺录)他们也重视诗歌的“比兴”表现手法,李梦阳云:“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19](卷五十二)李东阳则云:“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17](卷二十八)在散文领域,他们也致力于古文理论的研究,为复兴古文奠定基础。李东阳认为文章应有益于实用,反对毫无用处的虚文浮词,“夫所谓文者,……敬徒掇拾剽袭子片语只字间,虽有组织绘画之巧,卒无所用于世也”[23](174)。康海论文主气、穷理、贵用:“理不穷则无以得其旨趣所在,文不博则无以尽其法度之所宜,故穷理、博文而约之于理,然后可以言其文也。”[11](《文说》)“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出于身心,措诸事业,加诸百姓,有益于国,乃为可贵也。”[11](卷一)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强烈主张回归秦汉文传统。但李梦阳拘于古人之成法,提倡用“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19](卷六十二)方法模拟古人之作,而何景明认为学古可以“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24](卷三十二)。不为古人束缚。弘治文人对诗文本质属性和文体特征的重新探寻、确立,有效纠正了台阁文学长期造成的负面影响,为文学发展重归正途作了理论先导。
三、弘治朝各体文学发展的盛况
精确评判弘治朝文学成就难度较大,许多作家身跨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甚至五朝,仅认定其是弘治朝文人显然不妥,有些戏曲小说的成书累经几世,很难将具体成书时间定位到弘治朝。本研究姑且考察在弘治朝文学创作成绩突出的作家和主要成书阶段在此朝的戏曲小说作品,结果令人刮目相看。弘治朝的诗歌、散文焕发新机,小说、戏曲加速发展,为正德朝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诗文领域,丘濬、程敏政、李东阳等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出现由前期的“鸣国家之盛”转向描述私人生活情趣的倾向,尤以李东阳为代表,其作品更多抒发个人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形式上也力求完美。王世贞称其乐府诗:“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25](卷四)徐泰云:“长沙李东阳大韶一奏,俗乐俱废。中兴宗匠,邈焉寡俦。”[26](卷四)就作品数量而言,《李东阳集》收诗近2 600首,散文近1 000篇;丘濬《琼台诗文会稿》收诗词近900首,散文380多篇;程敏政《篁墩文集》收散文52卷,诗歌33卷,三人创作高峰均在弘治朝,期间自然创作了大量诗文。前七子是在反对流靡雕缀的台阁文风背景下出现的,他们于弘治间创作的诗文大多具有真情实感,或讲述自身生活遭际,或感叹民生疾苦,或指斥时弊,或倡言变革,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与浓厚的批判意识,与台阁体诗文迥然有别。其中李梦阳、何景明成就最高,李梦阳创作诗赋1 800多篇,除少数模拟太重的拟古诗外,佳作不少,王世贞赞云:“李献吉诗如金鸡擎天,神龙戏海;又如韩信用兵,众寡如意,排荡莫测。”[27](261)何景明著有辞赋30多篇,诗1 500多首,散文130多篇,除时政题材外,他还创作《津巿打渔歌》等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作品,质量较高。其外,以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为代表的吴中诗文呈现出“言情重性,灵动自然”的民歌特色,其中以徐祯卿成就最高,他因诗文作品数量较多,号称“文雄”,又因早期诗风近似白居易、刘禹锡,被称为“吴中诗人之冠”。还有陈献章、庄昶歌咏“自然性情之真”的山林之文,无论从创作目的还是从审美情趣上都与台阁体诗文明显不同,体现出弘治朝文风的多样化特征。
弘治间的时文发展也渐趋成熟,当时的王鏊、钱福就是明代著名的八股文大家,四库馆臣评:“鏊以制义名一代。”[20](序言)其代表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邦有道危言危行》堪称明代时文典范。弘治朝的散曲创作也比较繁荣,涌现出著名散曲家陈铎和王磐。陈铎南北散曲皆擅,著有《梨云寄傲》《秋碧轩稿》等6部散曲集,徐渭《南词叙录》推之为“北词名家”,沈德符《顾曲杂言》推为“南词宗匠”,今存曲570余首。王磐著有《西楼乐府》,存曲70余首,王骥德将之与徐渭、汤显祖并称为“今日词人之冠”。其外,唐寅存曲70首,祝允明存曲20余首,这时的散曲创作堪比明初的辉煌,是明代散曲发展的又一高峰。
在戏曲文学创作方面,弘治时期的士人非常重视戏曲的道德教化功能,作品艺术形式则仅限于南曲戏文。赵义山指出:“综合学界同仁的研究来看,现存南曲戏文至少有十多种可以确定其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其首开风气之先的理学名臣丘濬的《伍伦全备记》,接踵而来的有邵灿的《香囊记》、姚茂良的《双忠记》、沈鲸的《双珠记》《鲛绡记》、徐霖的《绣襦记》、王济的《连环记》、沈采的《千金记》《还带记》等。”[28](94)丘濬《伍伦全备记》在南曲和明传奇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有人称之为明代第一传奇。[29](46)
弘治朝的小说笔记创作也取得一定成绩。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可能最早刻于弘治年间,蒋大器在嘉靖版《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弘治甲寅(1494)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而庸愚子在弘治七年序《三国志通俗演义》云:“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章培恒、马美信也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首《前言》中说明此本“原题《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可知《三国演义》的成书与弘治朝关系密切。另一部名著《水浒传》也被认为可能成书于弘治末年,弘治朝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当时昆山流行“水浒叶子戏”,“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30](173)。书中还附有“水浒叶子”插图。还云:“土兵之名,在宋尝有之,本朝未有也。”只到成化二年,才有“士兵”称谓。[30](91)又说:“坑户乐于采银,而惮于采铜。”[30](187)一些学者根据弘治朝大量出现“水浒戏”“士兵称谓”和“白银流通”等情况,认定《水浒传》成书于弘治未年。开明清艳情小说先河的《钟情丽集》是明代影响较大的中篇文言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传奇小说在永乐十年李昌祺《贾云华还魂记》之后,经近百年的沉寂再度复兴。《钟情丽集》曾多次入选《风流十传》《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流行艳情小说选本,为中后期明代传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和创作经验。欣欣子在《金瓶梅·序言》中就提到 “邱琼山之《钟情丽集》”,并将之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水浒传》相提并论,可见其在明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此书现存最早刊本是弘治十六年,它的成书很大可能就在弘治朝。这三部小说的成书均与弘治朝有关,难怪章培恒云:“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复苏仍是可以断定的。”[13](147)弘治朝文人还创作一些野史笔记,如徐祯卿《剪胜野闻》一卷,言洪武朝时事。陆容《菽园杂记》十五卷,专记洪武四年至弘治六年事,被王鏊称为“明朝记事书第一”。弘治朝进士陈洪谟著《治世余闻》专记明孝宗弘治朝事,书中之事多为作者亲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四、弘治朝文学的过渡性特征
弘治文学的历史价值除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丰厚外,还表现在文学性质的阶段性特征上。学人在划分明代文学发展分期时,常将成化朝归入明前期,而以弘治朝为中晚明文学的开端,弘治文学正好处于明代文学发展分期的临界点,因此弘治文学的发展必然带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整体来看,弘治文学发展经历三大阶段,初期以程敏政、丘濬、吴宽为代表,他们承继成化前盛行的“三杨”台阁体文风,为文主张“鸣国家之盛”和“传圣贤之道”。丘濬《送钟太守诗序》云:“君承乡先正之后,得韦、柳之位,广诗之用以导化邦人,感发其善心,宣导其湮郁,以厚人伦,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真有以称其名焉,则天下后世称守之能诗者必归焉。”[31](卷十二)认为写诗要以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为宗旨,他们的文风大多和平温厚。四库馆臣评丘文:“然记诵淹洽,冠绝一时。故其文章尔雅,终胜于游谈无根。”[32](2298)同样评吴宽:“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32](2303)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与“三杨”台阁体差异不大,几乎是前期台阁体的延续。
期间理学派内部还出现以陈献章、庄昶为首的白沙学派,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台阁体不同,开始转向私人情怀的抒发。陈献章为文重性情之自然抒发,意在表现性情之真,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趣味。黄宗羲论白沙心学:“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33](4)庄昶与陈献章文学思想相近,文风也大体相同,“其诗亦全作《击壤集》之体,又颇为世所嗤点, 然如《病眼》诗‘残书汉楚灯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句,……亦未尝不语含兴象。盖其学以主静为宗,故息虑澄观,天机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论,要亦文章之一种。”[32](2302)二人的诗作对恢复诗歌的传统审美意象有一定促进作用,李东阳就与庄昶有过诗文唱和,彼此都受影响。
弘治八年,李东阳入阁后大兴文事,“李西涯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掖,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34](234)以他为中心的茶陵派文人集团逐渐形成。李东阳属台阁体殿军,其文学观念仍受台阁体政教文学观影响,还欲重振“三杨”台阁文风。但其作品也有新的转向,茶陵派成员对台阁体“真情无存、兴象丧失”弊端进行了有力反拨,作品侧重抒发个人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但他们对“情”的界定更多局限于台阁体文学观中的表现性情之正,还与颂美观念关系密切。李东阳云:“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欲之美与人之贤者,必于诗。今之为诗者,亦或牵缀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17](卷二十二)邵宝认为:“君子观政于文。……故观政于文可,观文于政不可之人,吾见也屡矣。”[35](卷十二)这些都明显保留着台阁文臣的雅正文学观念。在创作实践中,他们也试图消除台阁体弊端,想以感悟式的诗意替代过去简单、浅实的描绘,但由于形式上的过度审美追求和内容上的偏离现实生活,难免引发“靡丽”之失,受到七子派诟病,被指责:“是时西涯当国,倡为清新流丽之诗,软靡烂之文,士林罔不宗习其体。”[36](601)事实上,茶陵派诗文也有一定历史价值,徐朔方指出:“以李东阳的诗歌理论为指导,茶陵派诗人既流连光景也关心民生疾苦,既讲求法度也重视意趣比兴,因而振一时之响,矫馆阁之音,为明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29](202)
随着弘治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一批文学新人借此迈入文坛中心。弘治六年,李梦阳中进士,弘治九年,边贡、王九思进士及第,弘治十五年,康海、何景明、王廷相中进士,弘治十八年,徐祯卿、郑善夫中进士。前七子成员都是新科进士,才大气高,豪宕不羁,他们不满于台阁文的舂容浮泛和茶陵派的“清新流丽之诗,软靡腐烂之文”,掀起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弘治后期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和高潮期,也是成员内部不断磨合和频繁论争期。《明史·李梦阳传》提到的“弘治十才子”中,朱应登、顾璘、刘麟、边贡均为七子中较早及第者,四人好作“六朝绮丽”体,号为六朝诗派,后经过激烈论辩,他们才臣服于李梦阳,接受七子派文学宗向。吴中四才子之首徐祯卿中进士后与李梦阳论争,李指责其浮靡、巧饰文风,徐受启发后转变观念。王九思本人在文集自序云:“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靡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37](《序言》)弘治朝的交流论争是前七子形成统一文学思想观念的重要阶段,为他们在正德朝全面掀起复古运动奠定了基础。
由此来看,弘治朝文学的过渡性特征非常明显。它处于对百年台阁体拨乱反正进程中的探索阶段,弘治前是尚质主义时代,弘治初的丘濬、程敏政等人承继台阁体尚质文风。中期的茶陵派以追求过度审美反拨前期颂世质朴文风,却流为靡丽文风,陷入文胜于质的误区。同时期的陈献章、庄昶于理学中兼取道家思想,唐寅、祝允明、徐祯卿继承吴中原有的张扬个性、坦率抒情的人文精神,加速了文学摆脱台阁体影响的进程,渐开晚明学术思想多元化之先河。弘治晚期,前七子派作为台阁体的坚决反对者登上文坛,倡导回归秦汉文、盛唐诗,要求诗文能够真正表现作家真情实感,刻画真实人生,承继风教传统,甚至成为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前七子派吸取茶陵派过度审美追求的失误,又将之纳入于正,使二者重趋相对平衡,最终成功地使文学摆脱理学的桎梏,走出了台阁体阴影。纵向来看,弘治文学正好处于前朝台阁末流之失和后期文学复古运动全面高潮的进程中,过渡性特征明显。
就个案而言,李东阳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三次转变也鲜明折射出弘治朝文学思潮的嬗变轨迹。弘治初,“三杨”台阁文风盛行,李东阳与当时馆阁名家程敏政、吴宽交往频繁,在诗酒宴饮、怡游赏玩中联句赋诗,歌咏太平,呈现典型的台阁文风。此时的他在文学思想上积极倡导“三杨”台阁文风,强调文学的载道辅俗功能,认为“诗之为物也,大则关气运,小则因土俗,而实本乎之心”[23](43),并为前朝台阁名臣倪谦作《倪文僖公集序》,盛赞其台阁文风。弘治中期,李东阳主盟文坛,开始致力于改造台阁文风,针对典雅平正文风对诗歌造成的长期破坏,他力倡“格调说”,试图恢复诗歌原有“音乐”“抒情”“形式”等审美特性,主张诗文要表现作家个人的人生感悟和喜怒哀乐,他还认识到 “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23](1372)。他肯定“山林文”的价值,但在创作实践中由于作品内容的空泛单调,引发靡丽之失。弘治末,朝廷时弊渐现,担任“首辅”的李东阳频频上书献策,为国事操劳无度,再也没有初期的闲暇舒适,文学思想也发生改变,他强调诗文真情:“彼小夫贱妻,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主张复古,标举唐诗,“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其晚年诗作中像《忧旱辞》《风雨叹》《哭子录》等“主真情”的作品比比皆是,这些主张都为前七子的“复古”“真情”理论奠定基础,加之他对前七子在政治上的推荐提携,所以王世贞云:“长沙之启何、李,犹陈涉之启汉高。”[4](245)由此可见,李东阳弘治时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承“三杨”台阁体,下启七子派复古运动,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过渡作用。
五、明中期文学“弘治中兴”的成因
形成弘治文学“文治蔚兴”局面的原因较多。首先,前后期不同的国家政治形势推动了文学发展。弘治前期,国泰民安、风清气正的政治形势给文人们的舞文弄墨、宴饮酬唱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身逢盛世明君的文人们也自觉有“润饰鸿业”的责任感。崔铣《漫记》云:“自孝皇在位,朝政有常,优礼文臣,士奋然兴。高者模唐诗,袭韩文。”[38](卷十一)出于颂世称主的需要,弘治朝前期文学以台阁体文风为主导,丘濬、李东阳、吴宽、王鏊等人仍属台阁体阵营。弘治后期,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内灾害频现,弘治十七年,兵部尚书刘大夏上书:“江南江北灾伤太甚,陕西往岁困兵,江浙困役。”[3](2808)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呈《上孝宗皇帝书稿》指出国内存在足以动摇统治的“二病”“三害”以及潜伏着的“六渐”(六大危机)[19](卷三十九)。弘治后期到正德间频繁的灾害、动乱造成国内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甚至发生了平民暴乱。正是弘治后期政局出现由盛而衰的危机,激发了前七子要求社会改革的意愿和参与政治斗争的主动性,他们在与刘瑾等邪恶势力的对抗中,能够不计身家性命、敢拼敢斗,尤其李何等人更展示出嫉恶如仇、坚忍不拔、严峻刚直的战斗精神。由此来看,前七子派又是一个主张惩奸除恶、革新图变的政治集团,他们批判:“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才取软滑者,不惟诗文靡败而要才亦随之。”[39](丙集第五)他们倡导“文学复古”,并不单纯追求秦汉古文、汉魏盛唐诗的审美风范,还要恢复秦汉文具有的风教传统和实录精神,甚至将文学视为言说政治主张的工具和从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弘治文学复兴”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政治形势变化的关系密切。
弘治文学复兴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文学内部动因。明前期台阁体盛行百余年,理学给文学发展造成巨大侵害,文学自身面临拨乱反正的重任。弘治前期出现的茶陵派虽属台阁体阵营,但他们已发现台阁诗文显现“蝉缓”“肤廓”之象,于是尝试以“流易”“清丽”文风加以改造,创作实践中主要以追求轻灵、感悟式的情感抒发替代过去简单、浅实的客观描绘,以期取得更大的美学效果。但由于自身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加之长期馆阁经验的积习难返,使得弘治前期的诗文革新仅局限于对审美形式化无节制的追求,并将之停留在修辞化努力的狭窄空间,引发“流靡”文风。顾璘云:“夫国朝之文本取醇厚为体,其弊也朴。弘治间诸君饬以文藻,盛矣。所贵混沌犹存,可也。然华不已则实日伤,雕不已则本日削,不几于日 一窍已乎。”[12](卷二)这暗示“流易”“流靡”之习与李东阳的倡导有关。前七子倡导“文学复古”既有延续茶陵派追求审美形式的努力,但更多强调诗文的现实内容,作为台阁体文学的彻底反对者,他们自然不满于属台阁末流的茶陵派的雕琢靡丽文风。王九思云:“文苑竞雕缀,气骨卑以弱。矫矫浒西子,力能排山岳。……崆峒起朔方,流风振大雅”[37](卷二)。他明确指出前七子文学革新的目的在于抵制茶陵派流靡雕缀之习,力图恢复诗文的本质属性和实用功能,他们的乐府诗创作就充分体现了诗文的风雅传统。前七子与茶陵派也有内在的联系,李梦阳云:“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均。”[19](《卷二)他在复古之初亦师法过茶陵派的力追典雅,其后期诗学也可能受到“陈庄体”鄙俚直言风格的影响,因此前七子也是茶陵派内部阵营的变革者。
在前七子之前,茶陵派在探寻诗文新变时也倡导复古。李东阳就推崇唐诗,认为:“唐朝诗李、杜之外,孟浩浩荡荡然、王摩诘足称大家。”[23](1372)茶陵派部分成员的复古思想虽然没有形成趋向一致的复古目标,也没有明确的口号,但正是文学内部寻求突破的尝试,启发了后人,七子派提倡文学复古的思想更多来自于文学内部的律动。
综上所述,与史学上的“弘治中兴说”相对应,明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弘治中兴说”完全可以成立。由于弘治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动因,使得该朝文学呈现出与明前期不同的发展状况。弘治朝的文论家们对前期盛行的台阁体文学进行多次清算反拨,在寻求文学新变过程中,他们结成不同的文学社团,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创作出为数众多的形式多样、质量较高的文学作品,共同推动了“人文蔚兴”局面的形成。尽管此时的各体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讨尚处于探索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但作为明中期文学复兴之始,它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弘治文学无法与明初和晚明相提并论,但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注释: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云:“因续取《五伦全备》新传,标记《紫香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云:“紧接《伍伦个备记》,出现了又一部图解程朱理学的传奇《香囊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4页)他们都认为《五伦全备》比《香囊记》早出。而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云:“《香囊记》是明代最早的文人传奇。”(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 陈洪谟. 治世余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 张懋等. 明孝宗实录[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本, 1983.
[3] 谈迁. 国榷[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8.
[4]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5]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6] 王其榘. 明代内阁制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 刘婧, 赵中男. 一身功过, 重予评说—〈弘治皇帝大传〉读后[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5(5): 77−78.
[8] 李焯然. 丘浚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 赵永翔. 关于“弘治中兴”之评价问题[J]. 河西学院学报, 2009.
[10] 左东岭.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1] 康海. 对山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2] 顾璘. 顾华玉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13] 章培恒. 中国文学史新著[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
[14] 罗宗强. 明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5] 程敏政. 篁墩文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16] 杨一清. 石淙诗稿[M]. 四库存目丛书.
[17] 李东阳. 怀麓堂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18] 吴宽. 家藏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19] 李梦阳. 空同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20] 王鏊. 震泽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21] 陆深. 俨山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22] 徐祯卿. 迪功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23] 李东阳, 李东阳集[M]. 钱振民辑.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24] 何景明. 大复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25] 王世贞. 读书后[M]. 文渊阁四库全书.
[26] 徐泰. 诗谈[M]. 四库存目丛书.
[27] 王世贞, 艺苑卮言校注[M]. 罗仲鼎点校.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28] 赵义山.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南曲之盛行与曲文学创作之复兴[J]. 文艺研究, 2005(12): 41−50.
[29] 徐朔方, 孙秋克. 明代文学史[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30] 陆容. 菽园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1] 丘濬. 重编琼台稿[M]. 文渊阁四库全书.
[32] 四库全书研究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33] 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4]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5] 邵宝. 容春堂集续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
[36] 李开先. 李开先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601.
[37] 王九思. 渼陂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8] 崔铣. 洹词[M]. 文渊阁四库全书.
[39] 钱谦益. 列朝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Hongzhi literary resurgence”: a survey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of Ming Dynasty
CHEN Changyu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Bengbu College, Bengbu 233030, China)
Different from the dispute over the view of “Hongzhi resurgence” in historiography, there is consensus about the view of “Hongzhi literary renaissance” in literary circle. The latter, however, obscures and veils mid-Ming literary achievem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due to the lack of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essay, “Hongzhi literary renaissance” can be manifested in the growing number of writers, the frequency of literary exchange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eation. And the factors leading to its formation lie in the favorabl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various efforts to liquidate the disadvantage of Secretariat style in the literary circle. The Hongzhi literature has the features of transition and continuity, counteracting with the Secretariat style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starting to revert to the old ways in mid-Ming Dynasty, hence laying a solid basis for the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nd function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d and late Ming or even the whole Ming Dynasty.
Hongzhi Dynasty; literary renaissance; historical survey
I222.2
A
1672-3104(2015)03−0198−07
[编辑: 胡兴华]
2014−12−17;
2015−03−29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宋濂文学新论”(13YJA751002)
陈昌云(1972−),男,安徽全椒人,文学博士,蚌埠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文学,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