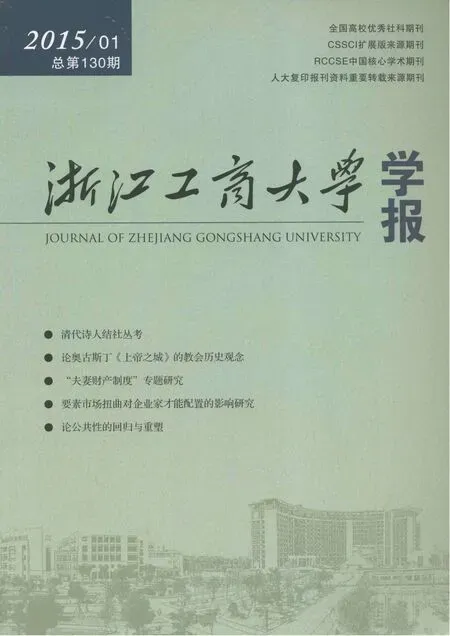尊严与权利:农民城镇化的核心要素
黄文秀,向 勇,欧阳仁根
(嘉兴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尊严与权利:农民城镇化的核心要素
黄文秀,向勇,欧阳仁根
(嘉兴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文章从法学角度研究人的城镇化的核心要素问题,认为农民城镇化的核心要素是农民的尊严和权利,并从城镇化人本主义和法律社会原则两方面加以论证。建议着重维护农民在城镇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尊严和权利。
关键词:农民;城镇化;尊严;权利
一、 问题提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中共中央关于城镇化的基本要求。如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需要明确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系统的要素。要素是构成系统的基本单元。城镇化要素相对它所在的城镇化系统是要素,相对于构成它的要素则是系统。“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已成共识。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的城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在城镇化系统要素问题上,学界一般认为,城镇化涉及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1]。或者认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要素包括“规划布局、产业发展、交通路网、公共服务、生态保障、文化传承”等六大要素[2]。在“人的城镇化”系统要素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是关键问题[3]。另有学者认为,人的城镇化,主要包括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社会融合、福利和幸福以及人的发展和参与[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个人的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农民的可行能力范围的拓宽是人的城镇化推进的内在逻辑三要素[5]。也有人认为,“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失地农民教育[6]。
众说纷纭,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的立场不同。站在“人的城镇化”系统的组织者的立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确是其核心要素,但站在“人的城镇化”系统中“人”的立场,其要素应该是人的自由、福利、幸福等。但具体应如何提炼其核心要素,尚需深入研究。
迄今为止,政府强制拆迁导致恶性伤人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中小城市只顾扩大城区范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远高于农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增长,动辄形成“鬼城”“空城”现象,一些地方强制让农民“上楼”,导致种田无地、就业无门的局面,诸如此类城镇化弊端根源于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和错误的政绩观,根源于完全忽视了“被化之人”的尊严和权利。提出“人的城镇化”的核心要素问题,目的在于树立科学的城镇化思想认识,切实保障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目标。
本文着重论证为什么尊严和权利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维护农民尊严和权利的对策与建议。
二、 理论分析
以尊严和权利作为农民城镇化的核心要素是城镇化人本主义的必然要求。城镇化人本主义是相对于物本主义而言。所谓“物本主义”是指注重城镇发展的物质基础,不重视城镇发展的主体力量,不重视城镇发展的文化精神力量,不重视城镇发展中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人本主义”强调人的意愿和利益,强调城镇发展的物质基础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法律、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在法律层面上,城镇化人本主义表现为“城市法人性格的塑造”和“市民权的塑造”[7]。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城镇化人本主义重点在农业转移人口的尊严维护和权利创新。
1.城镇化人本主义要求维护农民的尊严。人的城镇化,看上去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去身份”或“给身份”的运动。似乎只要去除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并给他一个城市户口就能实现,但事实上,它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因为“去身份”或“给身份”触碰的是人的尊严问题。身份的本质是人对人的支配关系。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其它社会组织以及国家、集体等主体。这种支配关系在古代体现为主人对奴隶的劳动——即身体——的支配,在现代主要体现为对他人利益——劳动成果、劳动收益——的支配。变化的只是被支配的对象。被支配的对象从“身体”到“身体的劳动”再到“实物租”最后到“货币租”。不管被支配的对象以何种形式出现,均可认为人与人之间支配关系的客观存在,即身份关系的存在。改变身份意味着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改变农民身份在当下的中国意味着改变国家、集体对农民的支配关系。客观地看,多数农民不愿意改变目前的支配关系。因为在目前的支配关系中,农民享受到了最大的自由。农民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经营承包地还是流转承包地,可以自主决定使用甚至经营宅基地,可以自主决定到任何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理论上,国家对农民的支配和干预越少,农民的自由度越高。而自由是人最基本的尊严。可以说,农民在目前的支配关系中体会到了自由和“当家作主”的尊严。要想改变农民目前的身份,只能增强农民的尊严,而不能降低其尊严感。“人的城镇化”政策在农民尊严问题上的考虑稍有不周,都可能引发城镇化趋势的逆转。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的城镇化必然要把农民尊严作为核心要素。
2.城镇化人本主义要求创新农民的权利。人的权利是人本主义的题中之义。法律规定的权利,农民都有,但真正能推动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实现城镇化的权利似乎还没有。所谓推动城镇化的权利,是指由法律保障的、增加农民城镇化竞争能力的权利。权利是权利人意愿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主体意愿和利益受到法律保障的标志。农民城镇化的权利能给农民带来稳定的预期和创造力。人的城镇化,必须要为农民创新权利。缺乏“新权利”的城镇化是“被动”的城镇化,而赋予农民“新权利”的城镇化才有可能成为“主动”的城镇化。赋予农民新的权利,完善农民现有权利的权能,这种“赋权还能”的改革是解决农民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根本举措。现代法治国家,激励民众行为最好的动力机制就是权利。激励农民城镇化这种“集体行为”,需要构建相互配合的权利体系。农民现有的主要权利是农村集体成员权、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这些权利旨在保障农民身份以及基于农民身份而产生的利益,它为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服务。在农民工从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换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创制服务于“人的城镇化”的新权利。
以尊严和权利作为农民城镇化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原则”的必然体现。“社会原则”要求法律给那些依赖于订立合同,但由于经济实力弱或缺乏业务经验而无法以特有方式充分地维护自身利益的人提供法律保护。因为仅仅依靠每个人都具有的签订合同的法律上的可能性,还不足以保障每个人都能实现他在一般财产和服务交易方面的自决权[8]69。“社会原则”本质上是国家对私人自治的干预。国家干预涉及私人自由,会降低私人的尊严,但“社会原则”下的国家干预不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旨在追求个体之间的实质平等和社会和谐,反而在实质意义上增强了弱者的自由,维护了弱者在市场行动中的尊严。只有在民事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均势,即他们实现权利的实力大体上相当时,才能期待每一方当事人都能在民事行为中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实际情况往往是,一些民事主体在实力悬殊的情形下与他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听任双方的意思自治,就会无形中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意志的支配,进而损害被支配一方的尊严。法的“社会原则”不能容忍这种有损一方尊严和利益的支配关系。基于“社会原则”,立法或司法往往通过维护弱势一方利益和真实意志来维持平衡。农民城镇化进程,自然要奉行法律的“社会原则”。众所周知,农民群体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为新中国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下,为扶持农民市民化,赋予农民城镇化的权利既是对弱者的照顾,也是对贡献者的补偿。不能在农民权利缺失的状况下将农民推向市场,而应维护农民的弱者身份并增加农民特有的权利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把尊严和权利作为农民城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是有利于彻底贯彻法律的“社会原则”。
三、 对策建议
1.维护农民居住的尊严和权利。农民进城定居的住宅条件不能太差,起码不能低于农房的居住条件。众所周知,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解放了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民可以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往返从事“农业—工商业”兼业以获取双重收入。农民开始享受到有自尊的生活,这主要表现在农房的新建和翻建中。与住在城市“鸽子笼”的普通市民相比,农民感受到了居住条件方面的优越性。可以说,在居住条件方面,农民过上了有面子的居住生活。农民集中迁移定居城镇的政策,应为农民保留有尊严的居住条件。为节约用地,农民集中居住的住宅占地面积肯定会减少,但应尽量维持其现有的住宅建筑面积,并在住房质量、美观、配套、卫生和舒适度等方面全面赶超农房。只有提升了农民集中居住房屋的品质,才能维持甚至提升农民居住生活的面子。居住方面的面子是“人的城镇化”的先决条件。维护农民居住权利在当前还可以通过完善农房所有权的方法来实现。农民对其房屋享有法定的所有权,但《物权法》并未规定房屋所有权的内容。房屋所有权人不能想当然地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九条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物权法》只规定房屋所有权的种类,却不规定房屋所有权的内容,主要是因为房屋所有权,特别是农房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受到宅基地使用权的限制。正因为这样,《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申请农村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受让人不属于房屋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办理。”可见,农房所有权的自由交易还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然而,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有了抵押房屋融资的迫切需求,完善并规定农房所有权的抵押权能,对农民而言无异于为他们的城镇化增添了新的权利。早在1986年,浙江省瑞安市就推行农房所有权登记,到1999年,瑞安农村各房管所共办理农村房屋交易4312件,办理农房抵押登记22450件[9]。当前,一些地区农房抵押融资和农房上市交易的条件已经成熟,立法应及时回应社会需求,赋予农民农房所有权的处分权能。
2.维护农民就业的尊严和权利。农民工在城市普遍从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累活、苦活、脏活,连坐公交、进超市都遭人鄙视,很多时候还“同工不同酬”。在这种没面子的状态下,农民工之所以还能忍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城市失去的尊严,能在乡村拾回。在城里赚到钱后,农民工回到家乡就可以翻新房子,添置电器、购买交通工具。蒸蒸日上的生活,是有面子、有盼头的生活。他们知道,乡村才是他们过“好日子”的根据地。再苦、再累、再掉价都无所谓,只要能挣钱回去,就可以在乡村重拾尊严。农民工的生活圈子、交际圈子和朋友圈子主要还是在老乡范围。在城里过得好与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乡村过得怎样,在老乡的眼里过得怎样。有了乡村这块维系农民工尊严的据点,农民工就能忍受城市的工作压力。因此,城镇化政策,一方面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不能轻易剥离农民工的乡村农民身份。在当前形势下,大幅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不现实,维持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城镇化改革可以赋予农民统一的城市户籍,但要在相当时期内保留全家进城落户的农民工的乡村身份。这是因为,保留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就是尊重农民尊严本身。“人与他的权利范围不可分离”是传统民法人格理论的一项基本理念。基于康德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认为,应该把“法律上的人”看做是其所享有的“权利范围”的核心。所谓权利范围是指这个人全部的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总和。把人视为权利范围的核心,要比把人视为权利和义务的“载体”的流行观点更切中要害。不能在理念上把人简单地从他的权利范围中分离出来。损害人的权利范围,也间接地损害人本身[8]48。“人与他的权利范围不可分离”理念,把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范围紧密结合在一起,彰显了人权尊严的思想。剥夺一个人全部的权利,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作为人的全部尊严和资格。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的刑法即使剥夺一个罪犯终身的政治权利,也不会轻易剥夺其民事权利。推进农民城镇化,不以农民现有的土地权利作为交换条件,不以农民身份的消灭为交换条件,实质上是对农民尊严的维护,间接地,可以消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方面“没面子”的消极影响。在农民工进城落户后,为农民工保留基于农民身份而存在的财产权利,可以为农民工家庭积累更多的资本。
3.维护农民教育的尊严和权利。农民工可以忍受自己就业方面的不利状况,却无法忍受子女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利形势。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最大心愿无非是想子女有更好的未来,而农二代、农三代的未来最终取决于他们能接受怎样的教育。目前为止,他们在农村接受的义务教育质量显然不如城镇。到城镇后,如果他们依然无法享受到基本公平的义务教育,这不仅会让农民工感觉脸上无光,还会有对子孙后代的负疚感。这种面子上的缺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对抗城镇化的心理。所以,城镇化政策应把农民工子女教育方面的面子问题摆在首位。可以这样说,即使就业差一点,收入低一点,居住环境恶劣些,只要子女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多数农民工是愿意为了子女的未来而坦然进城落户的。此外,中职、高职教育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及其子女的实际需要。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推行中职、高职教育学费减免、政府联合企业出资定向培养职业技术人员等面向农民工子女的优惠政策。
4.维护农民健康的尊严和权利。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我国医疗资源的配置在城乡之间不均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农民城镇化进程中,尊重、保障和实现亿万农民的健康的尊严和权利,是必然的选择,而农民“病有所医”是其最为重要的方面。农民“病有所医”的内涵不仅仅是指有地方看病、有地方接受治疗,更强调农民能享受到有尊严的医疗,合理行使自己的医疗权利。当前“医患”矛盾和冲突之所以时有发生,根源在于尊重不够、权利不够。除了加强保障医护人员的尊严和权利之外,还要着重维护农民医疗的尊严和权利。一方面,应加强农民就医时的“导医”“挂号”“看病”“付款”“取药”“住院”“复诊”等环节的服务和教育工作,让农民充分体会到医院“治病救人”“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态度,同时也增加农民的就医常识,进而能体谅医护人员工作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应增加农民医疗权利,切实落实农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就医权。尤其是可查可不查的“前期检查”,一定要保证农民有自主选择权。医疗机构为更好地服务于农民的医疗自主选择权,应及时建立医学常识顾问,专门为农民的选择提供帮助。
5.维护农民社会保障的尊严和权利。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农民养老保障等制度的初步建立以及农村五保供养、扶贫攻坚计划的持续实施,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大进步。但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对维护农民的尊严和权利仍然存在较大不足。一个月五、六十元的农民养老保障兜底,说起来好像已经为农民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但杯水车薪的补贴不足以保证农民的基本尊严。社会保障尊严的底线是要满足农民“吃、穿、住、行、医”等基本生存需要。要维护农民社会保障的权利,除了适时扩大农民的社会保障面、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之外,还要在程序上维护农民的社保知情权、规范和简化实现社会保障权的繁琐程序。在农民流动趋势日益扩大的过程中,特别是要建立异地衔接的方便民众实现社会保障权的配套制度。领取社保金是农民的权利,不是某个单位、部门对农民个人的恩赐。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履行法定义务,配合农民行使社会保障权。
参考文献:
[1]中国网.城镇化要围绕五大要素做文章[EB/OL].(2013-08-09)[2014-08-09].http:// finance.china.com.cn/roll/20130809/1711365.html.
[2]中央党校中青一班.特色城镇化六要素[EB/OL].(2014-01-06)[2014-10-29].http:// theory.people.com.cn/n/2014/0106/c40531-24033044.html.
[3]陈柳钦.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3(5):18-20.
[4]任远.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34-139.
[5]姚毓春.人的城镇化:内在逻辑与战略选择[J].学习与探索,2014(1):106-107.
[6]唐超,张娟娟.“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失地农民教育[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8):121-122.
[7]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支配[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15.
[8]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M].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林志海.瑞安市农村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的实践和探索[J].中国房地产,2001(7):28-30.
(责任编辑彭何芬)
Dignity and Right: The Core Elements Urbanization for Farmers
HUANG Wen-xiu, XIANG Yong, OUYANG Ren-gen
(JiaxingUniversity,ZhejiangJiaxing31400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study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urbanization issues, holds that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of farmers is dignity and rights and demonstrates the issue from the urbanization principles of humanism and the Law Society. It suggest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farmers living in cities and towns, employment, education, health,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dignity and rights.
Key words:farmers; urbanization; dignity; rights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5)01-0124-06
作者简介:黄文秀,男,嘉兴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城乡一体化研究;向勇,男,嘉兴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物权法、土地法研究;欧阳仁根,男,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三农法治研究。
基金项目:海盐县委托项目“就地城镇化的海盐模式研究”
收稿日期:2014-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