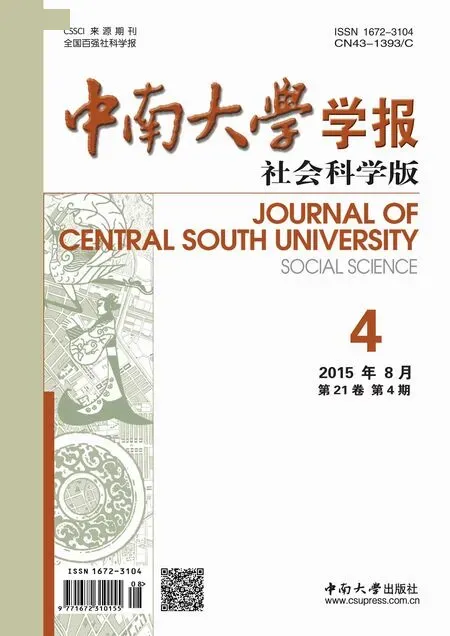土地确权与国家德性
——基于《宪法》第10条的法理分析
王进文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土地确权与国家德性
——基于《宪法》第10条的法理分析
王进文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土地问题是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1982年宪法第10条关于土地性质的城乡二元划分之规定,在法律层面上便会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城市界限不明确,存在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因行政权力介入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基于集体土地成员身份而产生的身份权利保障丧失。所以,必须摒弃土地国有与私有的分析框架,而以土地的财产权利属性为基础,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突出身份权利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土地的财产权利属性来弥补其所有权属性的不足,进而构建新的公民身份权利体系,实现国家德性维度的政治合法性和治理现代化。
土地确权;财产权属性;身份权利;国家德性
一、 土地问题的中国语境与分析框架
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所造就的经济奇迹,其间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便是改革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所带来的工业红利与基于人口基数尤其是农村人口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劳动力而形成的人口红利,两者的合力在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模式下所形成的后发优势使得中国社会在晚近三十年来得以快速乃至急速发展。从宏观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恰恰是三个“化”的过程:第一“市场化”,第二“全球化”,第三“城市化”。大致以十年为期,各完成一化,以1992年所明确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近十年来的城市化为分阶,每个阶段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毋庸置疑,在城市化进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在当下中国,其表现并不局限于静态的土地制度的运行,更大层面上是基于现行土地制度或土地政策的改革调适问题,从而,土地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动态的问题,质言之,便是土地改革问题,土地确权问题。
土地问题之重要性,久已为法学界所关注。在宪法学界引起关注的是张千帆教授关于土地二元划分与城市化问题的相关研究[1, 2],从宪法解释学维度对现行宪法第10条所确立的土地二元结构进行了梳理,肯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属性,将其纳入财产权范畴更是精彩的分析,是针对土地财政的现实所做出的回应。而许章润教授之研究虽不是直接针对中国当下的土地问题而发,但其地权之所指,自不是针对具有成熟地权的国家,面对国家德性维度之阙失,其所讨论的乃是土地二元结构下的权属不明所造成的政治问题。[3]
笔者认为,要理解土地问题的具体语境,必须将之放置到现行土地制度确立的六十余年来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方有可能认识到土地问题的普遍性及其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以此为前提,才能进一步分析围绕土地所产生的法权安排之特殊性与内在缺陷,尤其是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的由土地而产生的——个体或集体——身份权利及其确权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从大历史角度而言,中国近现代的核心命题是土地革命,而针对土地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则表明土地问题是一场未完成的国民革命。此一革命既表现出中国土地问题的历时性特征,又具有世界历史的共时性特征。其历时性特征无庸讳言,乃在于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土地集中或兼并问题,以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①为标志,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革命动员,土地革命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具有赋权性的意义。就其共时性特征而言,则在于中国革命所处的世界形势是由工业—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过程中,各主要国家均面临土地制度的改革及随之而来的基于土地的身份权利的确认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其经济方面的现实意义,更具有影响政治的历史意义。土地问题在中国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既与其基于历史而产生的历时性特征相联系,并按其内在逻辑不断拓充其外延,又与现阶段的城市化问题相衔接,从而必然地要求在土地基本制度方面适应该时代命题,使其原有的内涵做出相应的调适。这必然影响到基于土地而产生的人身权利或身份权利的规定,即人地关系的建构问题[4−6],而能否解决后者,便需要我们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对策。
二、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考察和法理阐析
对土地制度的历史考察,涉及到土地制度的分析框架问题。现阶段对土地议题的讨论大量集中在土地权属制度方面。毋庸讳言,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所有权被理解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最广泛和最绝对的权力。②对土地议题的讨论也大量集中在土地权属制度方面,即土地是否应私有化。然而,笔者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下所秉持的“私有”与“国有”的概念是很不完善不清晰的,甚至不准确的,它具有混淆甚至误导的作用。依据法理,“国有”是在国内语境中而言的,它不是一个财产权利问题,而是主权的问题。它只有当外国人在场时才有效,即它所针对的对象是外国人而非本国人,例如某一建筑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那么它的意义在于对外国人的排斥与否定,意即外国人要使用的话就可能要多交钱,或者根本不允许使用。但农村集体所有制或个人所有等概念都具有财产权利的内涵与属性。“私有”必须在具有具体指明是何种财产权利时方才有意义。所有和使用的区别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它是类型学意义上的。例如,在英美法里面便没有所有权的重要性,人们注重的是具体的财产权利。对于具体财产权利的考察而言,该种财产权利产生了什么样的利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鉴于国有与私有概念的话语地位,尤其是其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导,造成掩盖实质财产权利归属的不良后果,笔者由土地的财产权利之法律属性入手③,从其内涵与外延出发,引入财产权利的具体利益概念,以地租分配制度与土地使用制度为基点,阐析土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运行中的症结所在,并将其与身份权利的确立做一预瞻。笔者认为使用此一分析框架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可以很好地揭示土地权属的财产权利内涵,更有利于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探讨现阶段因人为划分城乡土地而产生的法理困境,即土地流转只适用于城市而非农村,以及由此引发的征地、拆迁补偿等法律救济的无力,从而有可能为克服法律规制层面的局限性与潜在危害性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但是,鉴于目前法律实践中土地的财产权利属性是派生于土地的所有权,而又被后者所掩盖,笔者为分析土地财产权利计,有必要从所有权角度对土地二元权属的形成历史做一梳理。
如果我们梳理当下中国土地问题的形成,从立法角度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土地属于私人所有,也有一部分土地属于国家所有。[5−7]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相比,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此外,还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到1953年春中国大陆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很显然,按照耕者有其田的规定,农民是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的,这也在1954年宪法中得到了体现。该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有下列各种,即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其中的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都属于私有制。第8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同时,该宪法第13条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之后,中国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就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土地无偿使用,二是无限期使用,三是不准转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的是单一行政划拨制度,国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无限期提供给用地者,土地使用权不能在土地使用者之间流转。
需要指出的是,从1954年到1975年间所经历的许多“运动”,很多是针对土地所有权的,如农村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运动、私房改造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等。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但在法律上对于基本土地制度并没有做更改,城市的土地所有权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变成了国有,这显然与1954年宪法规定不同。而1975年宪法中涉及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很少,仅在其第6条中有如下规定:“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紧接着,第7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需要注意的是,1975年宪法第6条继承了1954年宪法第13条的内容,事实上仍然承认非国有土地的普遍存在,规定国家只有通过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的程序,才能将非国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
不过,1978年宪法与1975年宪法都只承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按照1978年宪法第6条的规定:“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接续这一规定的内在逻辑,第7条则修改为: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现在一般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向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值得关注的是,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规定了城市土地的无偿国有化。[8]该宪法第10条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由此,通过修改1978年宪法,在1982年宪法中增加了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规定,其意义更像是一场革命,即不设定任何产权变更及认证手续,便实现了城市土地的国有化。1982年宪法在城市土地的无偿国有化方面的规定,在客观上使政府垄断了土地所有权的权益。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1988年宪法修正案、1990年的国土13号文④和1995年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⑤等实现的,将城市私有土地财产以“自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形式沿袭了下来。
从1980年代起,中国开始了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改革主要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土地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1986年国家通过了《土地管理法》,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二是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大体思路是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在使用权上,变过去无偿、无限期使用为有偿、有限期使用,使其真正按照商品的属性进入市场。⑥按照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国家在保留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拍卖、招标、协议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以一定的价格、年期及用途出让给使用者,出让后的土地可以转让、出租、抵押。这可以说是中国土地使用制度上有根本性的改革,因为它打破了土地长期无偿、无限期、无流动、单一行政手段的划拨制度,创立了以市场手段配置土地的制度。1992年进一步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土地市场培育的进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形成一个土地市场体系和有效的资源配置体系。1995年的《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最低价确定办法》,则利出一孔,加强了国家对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垄断。
通过梳理以上历程可以发现,以1982年宪法为分水岭,将土地所有制度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即土地从私有制转变为国有制。然而,私有与国有概念并不足以作为有效的土地问题分析框架,无法通过文本去认识土地制度的现行运作及其症结所在,也无法探究土地问题的根源。由于该分析框架与现实运作之间的脱节,导致我们无法认识与理解土地作为一项财产权利的法律属性以及由此法律属性而产生的身份权利之特性,尤其是在现实经验与实践领域内,它恰足以掩盖财产权利的内涵。
三、土地的财产权利属性之分析
土地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其核心乃在于地租分配与土地使用两方面,此即人地关系的两个核心维度。两者是可以并且必须分开的,这构成了土地制度的一体两面。这也是公(国)有—私有权属划分框架所无法兼顾的。在地租分配—土地使用的分析框架下,无论城市土地还是农村土地都可以进行分析,从而可以很好地解决公有—私有框架下所掩盖的内容。
台湾学者李鸿毅指出:“土地法者,乃规范土地关系之法律。人类社会之土地关系,大别有二:一为因使用土地所建立人与人间之土地权利关系,即土地分配关系;二为因使用土地而发生人与地间之直接关系,即土地利用关系。”[9]如果我们对土地制度做一个历史的宏观列举,无论是井田制、均田制、占田制、屯田制、村社制、族田制等等,土地制度无论其表现为何种形态,均包含收益分配(地租)和土地利用(使用)两个方面。地租的差异源于土地作为财产的有限性与差别性,而使用制度则是运用法律或政策对前者加以调整,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特殊的身份权利,即人地关系的法权安排。而此种身份权利的固化与改变(无论是主动或被动),均是关系一个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从而,这也就决定了此种考察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作为土地财产权利属性的第一个方面,地租及其分配是土地制度中的根本所在。从历史经验的层面上看,没有解决好地租分配问题,例如少数人垄断土地收益(与收益的垄断相比,经营方面的土地集中或兼并其实并不可怕),社会矛盾便会非常尖锐,如果无法解决的话,往往诉诸革命暴力。揆诸历史,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由土地问题所引发的解决斗争是非常残酷的。
作为土地财产权利属性的第二个方面,土地使用制度从逻辑上讲就是地租分配的制度化。它的核心在于土地的流转,即土地作为财产权利的交换价值之实现。这既包括实物地租的货币化,也包括土地使用权利方式的变更。中国历代的土地改革,核心是“收入”增加的实现。从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初次对土地征税开始,增加收入之目的贯穿始终。需要注意的是,“亩”是“私田”。[10]这次土地改革,是为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对“私田”征“税”。中国历代的土地改革,无论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唐朝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地,还是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当下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都是为了“收入”。
以地租和土地使用制度来衡量的话,如前所述,我们并没有从这一维度对建国后历次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进行考察,而是集中于权属的变更。建国后的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所建立的是村社土地制度,使用方式是共耕,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则是均地。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基于法律规定,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则村社成员均享地租收益,即法理意义上的增人必增份,减人必减份。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任何人种地都是在向村集体租地种,从而,无论是土地集体所有、国家所有还是个人所有都失去其意义。笔者将这种基于村社或村集体成员而产生的享有土地份额的权利称之为土地的身份权利,也即基于该身份而享有的地租收益的权利。此权利无论城乡均适用,只不过是身份权利指涉的具体对象不同而已。这种身份权利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村集体中,基于对地租的均享,实质上弱化了成员的承包权。而基于效率的考虑,同时也限于规模,客观上必然要求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必然是而且只能是在土地承租人之间流转,以便有效解决土地经营细碎化的问题。⑦
在城市中,由于居住位置的差异,形成由中心区域到边缘区域土地价格逐级落差的情况,而且不同地块之地租差距较之农地间差距更为复杂,也更为明显,从而城市地租的分配远较农村为繁复。依据现行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等的有关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制,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它实际上使得基于城市土地之不同区位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为少数私人占有,从而出现了土地利用方面严重的行政干预状况。如果将城市土地视为财产权利,而不是以公有私有等属性做划分,则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所存在的问题,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管制导致行政权力侵犯经济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无论是区分为集体所有权还是国有产权,按照民法的基本精神,不同所有权应当是地位平等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国有产权与集体产权的权能根本不平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城市土地的利用,例如建设用地等,就必须进行土地的征收或征用,把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转为国有制的土地。而按照1982年宪法的规定,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国有土地则可以正常流通。如此,行政权力事实上是在侵犯财产权利,实质则是对集体土地地租的垄断与独享,从而,便可以解释为何在现阶段征地补偿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土地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它的使用权的货币化实质是将其一定时间段内地租予以货币化,征地过程表面上是所有制形式的变更,但实际上掩盖了地租权利的平衡交换与分配问题——当然,其终级原因无庸讳言,乃是个人土地所有权或曰土地正义的阙失。
二是基于所有制的不同而呈现出管制过度和管制失效并存的现象。囿于所有制尤其是对国有土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保护,现行法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程序,从流通角度而言,无疑是 “管制过度”;但另一面,则是管制失效,即过于严格的程序在现实中无法实施,以致沦为具文。从而,违法现象尤其是违反土地管理法律现象便无法禁止。
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从土地性质变更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可能只看到表面上的不公平,而难以窥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回到笔者前述对于1982年宪法中关于土地权属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并没有明确指出城市的边界,是按行政区划还是按自然地理特征来界定?如果按自然地理特征来界定“城市”,例如北京的城市仅限于“紫禁城”,西安的城市仅限于内城,则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如果按行政区划来界定“城市”,则会造成宪法不同条款之间的彼此矛盾。在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诸如“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名目,事实上造成了“城市”没有法律的边界,处于随时随意地扩张的状态,从而,就呈现出上文所分析的管制过度和管制失效并存的现象。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中,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外,其他的土地均属国家所有。甚至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推到极致,全中国的土地在理论上都有可能全部划归为城市,即全部属于国有。从而,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经常举着“城市化”的旗帜圈占城郊农民的土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获取农村土地国有化的收益,以填充空虚的地方财政。因为,“城市化”就是城市行政区控制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而农村土地一旦归入城市的范围,也就自然而然地“国有化”了。如此,则“城市化”程度越高,土地国有化程度也越高。伴随这种国有化程度趋高过程的是,基于土地而形成的身份权利的丧失。
笔者之所以反对公有−私有或国有−集体所有这样的权属划分,已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它可能误导甚至掩盖了土地作为财产权利的本质,从而无法避免也不能解决因城市化进程的扩张而导致的权属变更所带来的权利保护问题。质言之,在集体所有的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过程中,或者说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在市场进行流通的过程中,因法律设置的原因而造成其地租收益被独占的局面,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基于此种土地关系而形成的身份权利被剥夺的现象,最终会造成一种伪城市化或反城市化,甚至地域与族群冲突等的后果。
四、土地的财产属性与身份权利的法权安排
在明确了土地具有的地租分配制度与土地使用的内在属性之后,我们将观察的视角放回到现实。无论是集体所有还是国有土地,无论是表现在前者的经营细碎化与不规模化和所谓的农村、农业、农民等的“三农问题”,还是表现在后者的个人房产的所有权与土地权属的分离,尤其是土地正义的阙失,其关键处都在于以权属问题掩盖土地的财产属性问题,忽略或否定在地租分配与土地使用方面应做出的法律规定与法权安排,从而导致基于土地之利用和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权利处于不稳定甚至被剥离状态。笔者此处所用的身份权利的概念,并非社会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权利,实质上可以说是公民身份权利的下位概念,即基于土地制度而形成的社会职业身份所具有的对地租分配与土地使用得以主张的权利,该项权利因其身份而获得,并由法律保障实施。例如,在村社体制下,农民作为村集体的成员,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社成为一个地租的收集者。村社成员均享地租收益,“增人必增份,减人必减份”。此种权利因其身份而获得,除非抛弃这一身份,否则只要没有丧失掉身份,便仍可以在村社里面取得地租收益。村社成员的身份权利乃是一项特权,不妨碍其他公民权利的获得。而这种身份权利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则表现为土地进入流通领域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即农民向市民之间的转变,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当然之意。而此种社会保障的实现,实际上是地租的货币转化对身份权利的保障。这一身份权利的保障才是法理意义上现代社会政治认同的最终完成。
正是基于对当下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尤其是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的考察,例如征地、拆迁等问题无一不在叩问土地制度的合理性与否;鉴于土地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土地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就其运作而言,由于立法领域内人为的权属区划,导致其财产属性被虚置,在公有—国有概念的语境中,土地所有权的真正归属无法在立法层面落实与突破,从而正如我们在1982年宪法中看到的那样,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规定,客观上使集体土地处在不稳定状态之中;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它不可避免地指向对于公共权力的边界的追问,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的追问。从而,笔者认为,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土地问题事关权力本身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正当性。质言之,它是关乎国家的德性的问题[3],身份权利的法权安排其意义恰在于回答此一问题,并形成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判断,属于一种政治过程与政治建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1982年宪法中对于城市土地国有性质的确认,使其得以进入流通领域,即土地作为财产权利进行交换。但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以前的土地政策,公权力对于地租的垄断是颠覆性的,在客观上否定了自土地革命以来政权的历史合法性,进而损害了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公权力不是作为服务者而是作为营利者存在的,由于公权力对于地租分配的垄断,便出现了诸如政府进行“强制拆迁”的现象,势必导致对公权力行使的合宪性拷问,公共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公共利益”的范围等,均大成问题。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政府投资所建的公共设施导致的土地增值,最后归少数私人所有。这也是造成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原始冲动的制度性病因。土地权属变更所形成的土地增值部分本应归公,但实际上是增值红利成了公权力与开发商之间的分红。现行的土地政策培养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阶层,一个专门的地租掠夺者。我国的房地产业很大程度上便是建立在货币化的地租的寻租模式之上的。
就土地使用制度层面而言,由于1982年宪法对于城市土地的性质界定,“城市”界限的扩张在理论上是无边界的。基于两种土地权属性质的划分,公权力的介入使得“国有”极易将集体土地纳入囊中,而且成本极低。这事实上是利用行政权力对土地财产权利属性中的地租进行掠夺,从而,农民基于土地而形成的身份权利在面临土地征收时变得极为脆弱,亦即无法实现从村民到市民的转化。而原有的村社体系被打破之后,基于村社共同体内部共有制而形成的身份权利丧失,始终无法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参与者。就城市而言,因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使用者仅仅对其地上附着物享有所有权,而对土地并无权利主张,最基本的土地权利在法律层面阙如,直接后果便是导致其财产权利的脆弱性。例如,“七十年所有权”之类的论述,恰恰是因为公权力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逻辑上导致对地租的垄断,从而使土地使用制度客观上处于不稳定状态。
上述两者作为土地财产权利的必然内涵,因其法理意义上的阙漏,使得身份权利无从落实,集体土地上的身份权利面对国有土地权属扩张时无从自我保护。这既是因为集体土地经营模式的不规模性与村社土地权属在立法层面的缺陷所致,又是因为法律所规定的地权使用制度中对于地租的垄断所致。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使得村社即农村集体经营体系瓦解,身份权利崩溃,另一方面使得城市化进程中地租为少数私人所垄断,身份权利同样处于脆弱状态,土地财政的存在又加剧了这一现象。从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征地拆迁撤村并居的城市化如火如荼,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新的身份权利没有建立起来,城乡冲突甚或有演变成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城市化的真正障碍,很有可能是没有采取适当的手段平均地权,实现地租的社会成员共享均享。
五、成熟地权与国家治理
依据前述分析,现行法律层面关于土地制度的规范,足以消解乃至否定地权的财产属性,从而使建立在土地财产权利体系上的一系列权利均处于不稳定状态。地租为少数私人所垄断,在城市化进程中,公权力以低成本的权属变更方式跑马圈地,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保障格局。而土地使用直接受公权力支配,造成行政权力对财产权利的宰制,否定与破坏了市场流通领域中作为经营主体的地权所有者的主体性,导致权利救济的缺位。这一进程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被圈占土地上的身份权利丧失,而由于土地使用制度的内在缺陷,新的身份权利保障无法建立,救济便无从谈起。
我们可以看到,展现在现实层面上的问题是由于土地地权的不成熟而导致的深层次的城乡隔阂,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放弃农业操作的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工,受制于身份权利的阙失,始终无法被城市接纳。同样由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法律阙失,失地者无法也不可能分享城市地租,而城市化进程在对乡村秩序与生活环境的破坏的同时,因为土地红利为少数私人所独享,以至于国家无力建立起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失地农民或农民工进城之后由于无法分享城市化的利益,转而形成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问题,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了城市。因身份权利的丧失与城市社保的排斥,可能爆发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的城乡冲突,甚至地域冲突乃至族群冲突。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分析革命的城市因素时,曾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群体做了代际比较,移民第二代较之于第一代因既无法融入城市身份又无法与农村保持联系而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乃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缺乏固定的地位。[11]此种地位,即为身份权利。事实上,综观晚近几年来的所谓城乡之间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具有族群冲突特征的外来农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之间的冲突,日益呈现出流民问题的迹象。而究其根源,则在于土地制度之非正义性所导致的身份权利之缺位,土地确权阙失,法权安排无从落实,最终指向国家德性之不足。
因土地制度而形成的身份权利之所以指涉政治正义问题,原因在于,以土地作为财产权利为基础而形成一整套的法权安排,可以开启合理的政治过程与政治建设。甚至可以说,良善的土地制度以及有保障的身份权利是决定城市化进程能否成功的最终因素。
从比较视角来看,近代英国是最早开启土地问题改革的国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由于圈地运动而造成大批农民失地,但晚近的考察表明,圈地主要针对公有地进行[12, 13],当然在此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农村土地权属的变更和大批失地农民。这一方面为机器大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与圈地运动并行的是,身份权利的重新确立与保障也成为消弭社会动荡、促使新秩序稳步确立的强有力因素。新的身份权利的确立是以济贫法为主要依据的。针对圈地运动迫使众多农民背井离乡,失业现象日益严重,157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开始征收济贫税,1576年又设立教养院,收容流浪者,并强迫其劳动。1662年斯图亚特王朝通过《住所法》,规定贫民须在其所在的教区居住一定年限者方可获得救济。1723年的济贫法更进一步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1834 年英国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14, 15]济贫法的实施,为那些因原有的土地关系变更而丧失身份权利的失地者赋予新的身份,经由适应城市生产方式而获得市民身份,实现身份权利的重塑。而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英国爆发,很大原因就在于基于土地的身份权利之重新塑造过程,英国取得了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农民——流民革命,而革命后的《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16]美国自19世纪20年代工业化进入加速期也面临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面展开是同步的,而美国的例外与幸运之处便在于西部领土的开发,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宅地法》,旨在无偿分配美国西部国有土地给广大移民,确立了小农土地所有制。德国自19世纪中叶相继颁布《职业自由法》和《迁徙自由法》等法案,为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就业扫清了各种体制上的障碍。而真正的身份权利的确立则是在19世纪80~90年代所谓的“俾斯麦型社会保障模式”建立之后,将脱离土地的工人的身份权利以社保形式予以保障,从而避免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隔阂和族群之间的对立。从这一意义上讲,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只是完成了政治上的整合,真正的国家整合与国家认同则是在社保体系身份权利建立之后。
六、结论
综上所述,1982年宪法对于城市土地权属的规定,将财产权利属性中的所有权虚置,客观上导致了无法通过核析界定权属的方式解决因土地变更而产生的纠纷、冲突与对抗,尤其是当公权力以国家的名义行使土地确权之时,由于依权属划分之区别而造成的土地使用制度具有内在的低成本扩张倾向。特别是在应对城市化进展与分税制下土地财政的双重驱动下,该种扩张无论是征地还是拆迁等,均直接造成原有的对于地租之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权利的破坏,进而更为严重的是,它形成了对公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否定,将建立于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历史合法性流失殆尽,同时现实合法性无从建立,国家德性便无从谈起了。
土地制度及由其引生出来的身份权利从逻辑上指向了财产权利,而财产权利的保障与落实又指向了政治层面的合法性与国家治理的正当性维度。由于土地具有内在的财产权利属性,事实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操作性的破解此种法律僵局的切入点,即以地租的享有与土地使用制度的合理化设置为基础塑造新的身份权利,消弭因土地权属划分所造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启动政治正义的建设过程,从而得以政治正义化解具体法律正义(立法)不足引发的公权力正当性不足问题,进而以迂回侧击的进去方式实现法权安排。
因此,如果从土地的财产权利属性入手,以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例如土地承包权的固化和城市地租的均享等的技术理性措施,为法律层面的突破提供制度资源与技术积累,从而渐次将转变为可操作的技术问题,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那么,规制意义上立法的局限性与潜在危害性(此种危害性已显现)完全可以通过能动性的司法方式加以解决。最终,通过建立成熟的土地权利,实现良善的国家治理。
注释:
① 《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84-88.
② 在德国,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最广泛和最绝对的权力,是与土地的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参见《德国民法典》第903条和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款。
③ 关于财产权利,参见[美]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美]A·A·阿尔钦.“产权:一个经典注释”,[美]R·科斯. 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6-112.166-178.
④ 参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城市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问题的复函》(1990年4月23日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土(法规)字〔1990〕第13号). http://china.findlaw.cn/fagui/p_1/289961.html. 2012-12-5.
⑤ 参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95年3月1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该《规定》“第二十七条:土地使用者经国家依法划拨、出让或解放初期接收、沿用,或通过依法转让、继承、接受地上建设物等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可确定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十八条:土地公有制之前,通过购买房屋或土地租赁土地方式使用私有的土地,土地转为国有后迄今仍继续使用,可确定现使用者国有土地使用权。”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部分内容已被《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2010年12月3日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发〔2010〕190号)所修订),http://china.findlaw.cn/fagui/p_1/288465.html. 2012-12-5.
⑥ 1982年,深圳特区开始按城市土地等级不同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1987年4月国务院提出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同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已具有了土地财政的雏形。
⑦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萧铮其他论著及黄俊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史料汇编.台北:三民书局,1991:395-423.
[1] 张千帆. 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重新解读宪法第10条[J]. 中国法学, 2012(3): 178−190.
[2] 张千帆. 城市化不需要征地——清除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宪法误区[J]. 法学, 2012(6): 19−24.
[3] 许章润. 地权的国家德性[J]. 比较法研究, 2010(2): 104−119.
[4] 达马熙克. 土地改革论[M]. 张丕介, 译. 北京: 建国出版社,1947: 63−68.
[5] 萧铮. 中华地政史[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4.
[6] 赵冈, 陈钟毅. 中国土地制度史[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97−132.
[7] 陈登元. 中国土地制度[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2: 425−428.
[8] 王维洛. “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J]. 当代中国研究, 2007(4): .
[9] 李鸿毅. 土地法论[M]. 台北: 三民书局, 1984: 1.
[10] 程念祺.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60−62.
[11]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刘为, 等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234.
[12] 咸鸿昌. 圈地运动与英国土地法的变革[J]. 世界历史, 2006(5): 61−68.
[13] 王田田. 英国圈地运动中的法律规制[J]. 求是学刊, 2009(1): 92−96.
[14] 尹虹. 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J]. 历史研究, 2001(2): 111−123.
[15] 尹虹. 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J]. 历史研究, 2003(2): 128−143.
[16] 马克•布洛赫. 法国农村史[M]. 余中先, 张朋浩,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172−218.
Establishing right of the land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WANG Jinwen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dual land system of the urban and rural stipulated by the 10th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PRC 1982 gives rise to the following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the city’s boundary is not clear, and there exists the possibility of unlimited expan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ective land is in an unstable state because of the invol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so that problems occur such as the loss of the owning right of the land. This essay analyses the constitutional change about land ownership from 1954 to 1982, holding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ate-owned land and private land should be abandoned, that a new on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land with person-land relation as the core. In this way,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ty right can be constructed so that the proprietary right of the land can be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ownership property, to establish a new system of status right and to actualize the legality and justness of modern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the dual land system; proprietary right; status right;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D90-059
A
1672-3104(2015)04−0053−08
[编辑: 苏慧]
2015−04−08;
2015−05−1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视角下的社会公平正义研究”(10CFX0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研究”(13&ZD032);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2014JSJJ044)
王进文(1980−),男,山东潍坊人,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