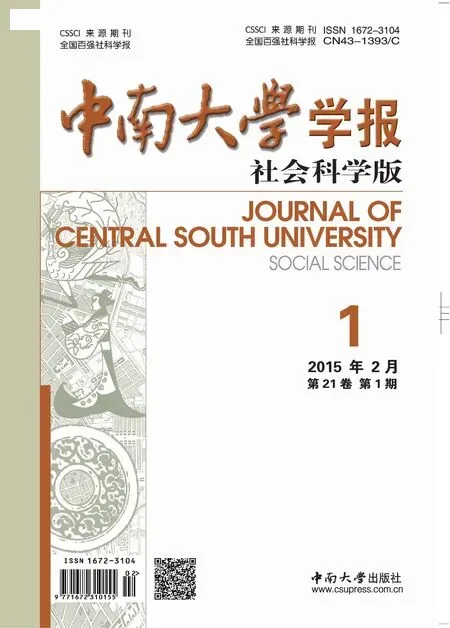论布兰顿规范语用学的理论缘起、实质及其作用
武庆荣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论布兰顿规范语用学的理论缘起、实质及其作用
武庆荣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与其他语用理论相比,布兰顿规范语用学的演成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路。他继承和批判了康德、维特根斯坦、弗雷格、塞拉斯等哲学家的思想,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主张概念的内容来自概念的使用、存在于概念与概念的推理联系即概念性活动中。概念性活动具有规范性。通过批判规则主义和规律主义这两种错误的规范理解模式,布兰顿指明了一条通向规范的实用主义路向,以这种方式,规范语用学能够为推理语义学提供奠基作用。
布兰顿;概念;规范性;语用学;规则主义;规律主义
罗伯特·布兰顿(R. Brandom)系美国当今哲学的后起之秀,他将推理语义学(inferential semantics)奠基于规范语用学(normative pragmatics)之上,从而将融贯、实践和社会这三个在哲学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分离的概念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其语言哲学被誉为“差不多当代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哥白尼式的转折”[1]。本文在解读布兰顿著述的基础上,将文本自在性与阐释哲学问题相结合,索解布兰顿规范语用学的理论缘起、研辨其实质、剖释规范语用学对推理语义学的奠基作用。
一、布兰顿规范语用学的理论缘起
布兰顿明确指出,把“我们”从万事万物中区分开来的是一种广义的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是一种理由和理解的能力即智识(sapience)的能力。智识不同于感知(sentience),两者的区别在于:“我们与非语言动物如猫一样都具有感知能力,即在清醒的意义上有所意识的能力,……而智识与理解或智力有关,与应激性或觉醒无关。”[2](5)理解智识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推理,另一种是真值。
首先,以推理的方式理解智识,就是把我们置放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为各种使用概念的活动给出理由并寻求理由。理由具有一种规范性,作为理性的生物我们受到各种理由的约束,受制于理由的权威,这种权威对我们来说具有一种规范的作用。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展示出一个可被理解的内容是因为它处于理由空间和推理的联系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就是对理由的把握,就是对理论的和实践的推理恰当性的掌握。把我们看作具有智识的理性之生物,也就是认为我们生活和活动在理由空间之中。[2](5)
其次,以真值的方式理解智识,就是把我们看作真之追求者和谈论者,理解概念内容也就是理解它们成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我们是真之信仰者和行动主体,相信就是把某些概念内容接受为真或认为真,做出行动就是使某些概念内容成为真。拥有智识也就是拥有各种诸如信念、欲求和意图这样的具有概念内容的意向状态。理解这些概念内容也就是理解在什么情形下我们所相信的、所欲求的、所意图的东西为真。[2](5)
所以,布兰顿指出,无论我们是根据推理的方式理解智识,还是凭借真值的方式理解智识,其实质都离不开概念的使用。同时,以推理和真值的方式理解智识,它们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我们所能提供作为理由的东西与我们能够接受为真或成为真的东西它们共同具有一种命题性的概念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命题性的概念内容不仅存在于推理联系中而且也具有真值条件。当我们受到环境的刺激时,我们不仅可以对环境刺激做出区别性响应,而且作为智识之人,我们可以通过恰当地使用概念以形成具有命题内容的知觉判断,而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周遭环境以响应我们使用概念所形成的判断。这正如布兰顿所言,“智识、推论的意向性都在兜售概念(concept-mongering)”[2](8);人类与他物之不同在于能够使用概念进行推论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①。
同时,布兰顿指出,概念性活动与非概念性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规范性,原因在于,赋予概念以内容的实践隐含地包含着规范,这些规范涉及概念使用的多个方面,比如,如何正确地使用表达式,在什么情形下执行言语行为是恰当的,这样的行为的恰当后果是什么,等等。并且从历史上看,规范语用学也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它主要来源于康德(I. Kant)、弗雷格(G. Frege)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2](xiii)。
布兰顿认为,康德的基本洞见是:理解判断和行动首先要根据我们为之负责的特定之方式[2](8)。在康德看来,概念具有规则的形式,不仅如此,“概念按照其形式任何时候都是某种共相的东西,它被用作规则”[3]。规则详细说明了如何恰当地或正确地应用或使用概念,在这种意义上,“理解概念的能力即掌握规则的能力——认识由其所决定的正确使用与错误使用之间的区分”[2](8)。概念作为规则规定了我们如何判断和行动,判断和行动具有概念内容,判断和行动的评价受制于概念之规则,因而达成一种意向状态或执行一个意向性的行动相应地就具有一种规范之意蕴。据此,布兰顿认为,康德的这种界定标准,不仅把概念使用看作一种规范性之活动,同时也把概念使用者看作规范性的生物或受规则支配的生物[2](8−9);康德的“主要革命不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是他的规范转向,将概念推论活动看作是某种我们必须以规范术语加以理解的东西”[4]。
弗雷格在批判心理主义(psychologism)的过程中,对康德的概念规范性思想进行了传承。他在《算术基础》一书中旗帜鲜明地宣称:“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分开来。”[5]他指出,“规定我们如何行动的道义原则或国家的法律与解释事件实际进程的自然规律不同”[6](145),自然过程“既不真也不假,它们仅仅只是过程而已,正如水中的漩涡是一个过程一样”[6](144);逻辑的本质在于对真值规律的研究,“逻辑如同伦理学一样也被称为规范性之科学”[6](128)。
但布兰顿同时指出,虽然弗雷格对概念内容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他的关切点是语义而不是语用。在20世纪,真正对概念规范语用意蕴这个论题进行辩护的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初始之观点是这样一个洞见:我们通常会把状态和行为理解为我们有义务承担或被迫做或思考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决定了各种语境下如何使用表达式才会是正确的,理解和掌握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区分出表达式的正确使用和不正确使用。当然,不仅意义和理解具有规范性,而且信念、意图这样的意向性内容状态也具有规范性,即一种规范之“力”(force),但规范力并非等同于因果力,规范力决定了我们如何恰当地做,因果力则决定了人们事实上做了什么[2](13−14)。这正如克里普克(S. Kripke)所指出的:“意义及意图与将来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规范性之关系而不是描述性之关系。”[7]
综上,布兰顿认为,以上三位哲学家拥有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的洞见,就是概念使用具有一种独特的规范性。概念内容具有规范之意蕴,概念使用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恰当与不当之别,掌握一个概念,就是掌握一种规范。规范具有一种规范力,只要我们使用概念我们就会受到这种规范力的支配和约束,规范力不是因果力,它规定了我们有义务做什么或被强制做什么而不是事实上做什么。据此而言,将概念内容之规范意蕴与因果意涵区分开来对恰当使用概念至关重要。
鉴于规范之于概念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规范来自哪儿?布兰顿认为,规范不是来自理性原则,而是来自实践,“知道什么”来自于“知道如何”,语义学最终要追溯到语用学,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或意向状态的内容只有在它们的实际使用中,才能最终得到说明[8]。
二、布兰顿规范语用学的实用主义路向
布兰顿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旨趣是概念之本性[9]。在他看来,概念使用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规范性,但如何理解规范,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有的哲学家将规范理解为规则,有的将规范理解为规律。布兰顿在批判和继承中,提出了规范的一种实用主义理解。
(一) 规范的两种错误理解模式
在布兰顿看来,康德的核心洞见是概念使用的规范性,其主要革新是他的规范转向,这种规范转向使得概念具有一种超出经验个体的普遍必然性。但如果追问起规范的起源,康德对此并没有进一步深究[4]。
1. 规则主义(regulism)对规范的错误理解
规则主义将规范等同于清晰之规则或原则。“根据这种理智主义的、柏拉图式的、康德和弗雷格所共用的规范概念,评价正确性总是至少隐含地参照了一条规则或原则,它通过清晰地言说而决定什么是正确的。”[2](20)但“这种将规范等同于清晰规则的做法,遭到了布兰顿的反对。他认为,在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的‘无穷倒退论证’之后,诉诸清晰规则来解释规范来源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10]。
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讨论了规则遵循问题,布兰顿将其概括为规则倒退论证。此论证如下:“如果一条规则规定了如何正确地做事,那么这条规则必定应用于特定之环境,并且在特定环境下所使用的规则其本身本质上也是可能做对或做错的事情。”[2](20)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对规则的正确使用进行说明,如果根据规则主义者对规范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另一条规则对应用规则的正确性进行说明,维特根斯坦称这种说明为“诠释”,但给出规则的诠释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规范的自洽问题,因为“任何诠释连同它所诠释的东西一起仍悬置空中,不能给它提供任何支撑”[11];换言之,诠释本身也有正误之分,这样又需要其他的诠释来说明其应用的正确性,如此以至无穷倒退。
塞拉斯提供了另一种规则的无穷倒退论证。他指出,“若说一门语言是由表达式构成的体系,语言的使用受制于规则,这似乎是合理的。因此学习使用一门语言就是学习遵从表达式使用的规则。然而,事实上这个论题会遭致一个显而易见的、极具破坏性的反驳。”[12]这个反驳就是:把“正确”看作是“依规则地正确”会产生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倒退,即,从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视角来看,对象语言的规则要由元语言说明,而元语言中的规则又要由元元语言说明,……这样便陷入一种无穷倒退之中[12]。
2. 规律主义(regularism)对规范的错误理解
为了避免规则主义的困境,另一种将规范理解为规律性(regularity)的规律主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2](26−28)。规律主义者认为,如果把隐含在实践中的规范仅仅理解为行为之规律,那么参与实践的人就不需要事先理解些什么,并且,如果这样的行为规律能够被看作是由隐含之规范支配的实践,那么就不会产生规则之无穷倒退或规则循环问题。这也就是说,隐含于行为规律中的规范能够以规则的形式被清晰地表达,但这并不必然要求做出规律行为的实践主体表达它们。一言蔽之,实践主体可以在完全不知道规则的情形下做出符合规范之行为。
但布兰顿指出,这是一种谈论隐含之规范就是谈论规律的观点。显而易见,这种规范的规律主义避免了规则主义所导致的无穷倒退,但这种规律主义消除了受规范评价约束之行为与受物理法则约束之行为之间的差别,即放弃了语言实践和意向状态的规范意蕴与因果意蕴之分。然而,如康德所言:“在包含无生命世界以及有生命世界的自然界中,每样事物都依规则而生……大自然事实上只是一个依照规则而出现的关系网络,因此不存在无规则的东西。”[13]所以,如果根据规律主义,每样事物都是有规律地在运动,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语言实践和意向状态能够包含我们前述所言特定之规范意蕴呢?
综观可见,布兰顿认为,将规范等同于规则的规则主义以及将规范看作规律的规律主义两者都不是对规范的一种自洽性的说明。原因在于,将规范理解为规则会让规范本身变得难以理解,而将规范理解为实践中隐含之规律,则是把规范还原为物理法则,使意向状态和行为失去其应有的规范意蕴。同时,规则的无穷倒退论证以及反规律主义的结果表明,存在一个实用主义的规范概念。
(二) 布兰顿规范语用学的实用主义路向
通过批判两种错误的规范理解模式,布兰顿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向规范的实用主义路向。在他看来,规范不是来自理性原则,而是来自社会实践,规范的原初形式是实践中隐含之规范,它是后来以规则或原则面貌出现的清晰之规范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理解清晰之规范与隐含之规范之间的关系,布兰顿对知道如何(knowing-how)和知道什么(knowing-that)作出了明确的区分。首先,知道如何是隐含的,“知道如何做某事是一种实践的能力,知道如何是一种可靠之能力。因此,知道如何骑自行车、使用概念、进行推理等等,人们就能够在其实践中、在其行为产生和评价的过程中分辨出做这些事情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方式”[2](23);其次,知道什么是清晰的,“这种显性的知道什么对应于隐性之知道如何,知道什么就是以一种言说正确与否的规则或原则的形式,对实践能力的一种理论的表述或表达”[2](23)。
通过以上诠述,布兰顿向人们展示出“说”是对“做”的清晰表达,清晰之规范是对实践中隐含之规范的清晰表达。然而,作为规范的存在者,人类并非直接受制于规范,而是受人类所持有的规范的观念的约束。因此,对实践中隐含之规范的理解和说明,“不仅仅要看做了什么——可能或不可能符合规范之行为——而且要看恰当性的评价。这些评价是把行为接受为或者看作为正确或错误的一些态度”[2](63),即规范态度。
但对布兰顿而言,他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既能够保留规范态度这个洞见,同时又能够规避康德规则主义的主张,而代之以规范的实用主义理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布兰顿认为我们在采用一种规范的实践态度的时候,即给一个行为归属一个规范意蕴或规范地位(status)的时候,“不能把实践上的评价行为等同于实践上的被评价行为”[2](23)。
然而,这种基于规范态度对隐含之规范的说明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满足规范的社会建构?因为如布兰顿所言:“评价本身可能是正确地做或者错误地做的事情”[2](52);不仅如此,另一个与规范态度或评价相关的问题是,是谁在评价?个人还是共同体?赖特(C. Wright)等人提出的公共评价理论(communal assessment theory)认为,概念规范建立所依持的并非个体的规范态度,而是整个共同体的规范态度即整个共同体所做出的公共评价[2](53)。
但布兰顿认为,尽管赖特确保了在规范地位和个体的规范态度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然而他不仅抹杀了规范地位和整个共同体的规范态度之间的差别,而且排除了集体共同出错的可能性。与赖特等人不同,他认为,规范具有客观性,理解规范的客观性离不开对概念内容的客观表征维度或指称维度的说明以及推论实践社会方面的联系,这正如他所言,“概念内容的客观表征维度——这种论断或概念应用的正确性,它并非取决于个体或共同体的态度或评价、而是取决于被表征事物的性质——最终又依赖于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推论实践社会方面的联系”[2](54),即强调自身承认一个承诺(commitment)与归属(attribute)一个承诺给他人之间的社会视角的区分,可以使得理解概念规范的客观性成为可能。
三、规范语用学对推理语义学的奠基作用
布兰顿语言哲学研究的中心论题是对语言的本性或概念的本性进行探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使用,二是概念的内容。与之相应,其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语用学和语义学。但这两者何者说明在先,其本身就蕴含着一个重要的、策略性的方法论问题。布兰顿认同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意义在于其使用”[14]的主张,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来自于它们的使用,“表达式通过它们在实践中的使用而意味它们所意味的”[2](134)。对他而言,语用学是根本的,语义学是从属的,是基于语用学的语义学,这正如他指出的,“知道什么来自于知道如何”[15],“语义学必须符合语用学”[2](83)。此相对于布兰顿的理论来说,便是推理语义学必须奠基于规范语用学之上。
语义学必须符合语用学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语义学的目的在于为语言表达式、意向状态或行为的语用意蕴提供说明,即通过归属语义内容给语言表达式、意向状态、态度和行为,以确定它们在各种语境里出现的语用意蕴。比如,如何能够恰当或正确地使用具有语义内容的语言表达式,在什么情况下人们获得的具有语义内容的意向状态和态度是恰如其分的,人们应该如何或有义务继续行动等。[2](83)
另一方面,与上述语义说明方向相反的是通过语言表达式、意向状态或行为的语用意蕴赋予它们语义内容。具体而言,语言表达式所具有的语义内容如何由它们的使用所赋予,意向状态、行为所具有的意向内容如何由它们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所赋予。这是一种概念内容来自于概念使用的思想,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说明策略。
但如此以来,我们发现布兰顿同时坚持了两种相反的说明方向: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说明方向以及从语用学到语义学的说明方向。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对矛盾,但布兰顿特别指出这两个方面并不相互冲突。因为语义内容对语用意蕴的说明是一种局部的(local)说明,而语用意蕴对语义内容的说明则是一种全局的(global)说明,所以相对来说后者才是一种决定性的说明进路[2](133)。这也就是说,虽然布兰顿并不否认语义内容对语用意蕴的说明作用,但他认为这种说明是从属的,如果从更广阔的语用环境背景考虑,事实上他更认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说明策略,即用语用学来说明语义学,或者说以语用学来奠基语义学。
综上可见,正是规范语用学的创生,才使得布兰顿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将融贯、实践和社会这三个在哲学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分离的概念有机地综合在一起,从而建构起较具体系性、创造性的关于概念内容和使用的理论。规范语用学除了在布兰顿语言哲学中的建基作用之外,它在整合语义学和语用学、说明人的理性能力方面也给我们以启迪。
但由于过分强调规范和自然的区别,布兰顿虽然如传统实用主义者那样将“实践”放在突出的位置,然而他所说的“实践”主要是指语言层面的使用概念的推论实践,即如何在规范的引导下使用概念的实践,它和环境、世界没有直接关联,这种推论实践使得规范和语言处于一个封闭的论域[10]。在这种推论实践中,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只是单向的,即语言如何指向世界,而并未包含世界如何制约语言。
注释:
① 推论实践即使用概念的实践(concept-using practice)。参见:Robert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1] Miroslava Andjelković. Articulating Reasons [J]. Philosophical Book, 2004, (2): 140−148.
[2] Robert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119.
[4] 陈亚军. 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及推论主义语义学—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上)[J]. 哲学分析, 2010(1): 170−177.
[5] 弗雷格. 算术基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8.
[6] Gottlob Frege. Gottlob Frege: posthumous writ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7] Saul Kripke.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7.
[8] 陈亚军. 布兰顿与《使之清晰》(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2-06(B01).
[9] Robert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10] 陈亚军. 将分析哲学奠定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J]. 哲学研究, 2012(1): 69−77.
[11]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58: 80.
[12] Wilfrid Sellars. Some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Games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54, 21(3): 204−228.
[13] Immanuel Kant. Logic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4: 3.
[14]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1.
[15] Robert Brandom.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27.
Theoretical origin,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Brandom’s normative pragmatics
WU Qingr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 pragmatic theories, the evolu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Brandom’s normative pragmatics is based o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ath. By inheri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philosophic thoughts of such philosophers as Kant, Wittgenstein, Frege and Sellars, Brando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ragmatism, advocates that the contents of concepts come from the usage of concepts and exist in their inferential articulation, namely conceptual activities, and that conceptional activities possess normativity. Brandom indicates the pragmatic way to normativity by criticizing two kinds of misconceptions of normativity, i.e. regulism and regularism. And in this way the normative pragmatics can provide a foundamental role to the inferential semantics.
Brandom; concept; normativity; pragmatics; regulism; regularism
B712.6
A
1672-3104(2015)01−0020−05
[编辑: 颜关明]
2014−04−08;
2014−12−16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项目“布兰顿推理论与分析实用主义研究”(2014M55157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逻辑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12AZX00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意识、表征与行动——人类认知的结构与运作机制研究”(12AZD073)
武庆荣(1972−),女,安徽亳州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在站博士后,淮阴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分析哲学,逻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