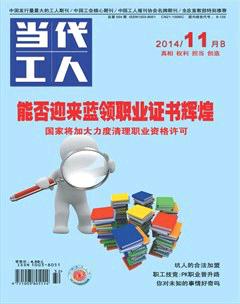我和《劳动法》,不觉风雨20年
赵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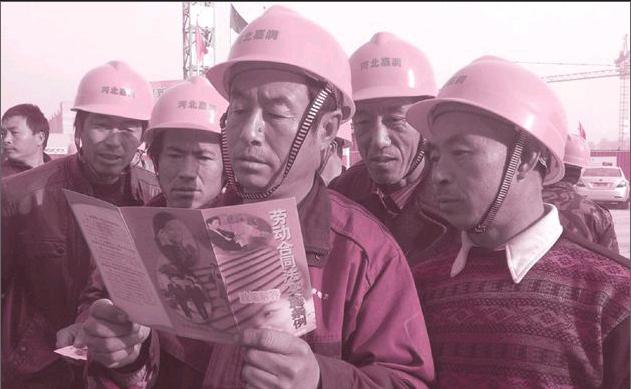
1994年,于我的人生来说,是一次重大抉择,经考核、试用,进入上海《劳动报》,成为一名记者;1994年,于全国劳动者来说,是一次重大利好,新中国第一部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全面规范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劳动法》颁布实施。
2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一名劳动维权记者,我撰写编辑了数百篇批评报道,并多次获奖;而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系列。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我与《劳动法》共同经历了劳动关系变化的四个时期。
蛮荒时期:法不为众人知
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国家赋予企业越来越多的用工自主权,社会上要求制定《劳动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89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原全总副主席陈宇等20余位政协委员联名质问:“野生动物有保护法, 高级动物的人怎么没有保护法?”迫切至此,1994年7月5日,历经30余稿的《劳动法》终于正式颁布。
《劳动法》施行之初,我所在的报社针对欠薪,会在春节时开设热线,作为接听者之一,每次拿起电话,我都冷汗浃背。因为不懂法律,只能把每天打进的数百个投诉电话内容记下来,转到市总工会法律部,请律师解答。
有一次,我接到一封匿名投诉信,说某区一家合资三星级酒店为了逼走5名中方员工,把他们“囚禁”在地下室。我调查后得知,这些职工年过40,都是国企转制过来的,工作中没有过失,但酒店为了卸包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逼入地下室“反思”。我问职工是否懂得依据《劳动法》维权,他们摇头。
证据到手后,我找到资方总经理核实。总经理认为这些职工赖着不走,他才采取“特别”措施的,至于支付经济补偿金,总经理认为是胡闹。我拿出《劳动法》,翻到相关条款请他浏览。总经理却说:“我按惯例在做,你不要与我说什么法不法的。现在有多少企业在执行《劳动法》?”
我在调查撰写报道期间,可以说“受尽折磨”,由于不懂法律,我多次讨教专业人士,一部《劳动法》几乎翻烂,文章改了又改,发表后,引起社会反响,有关部门介入,根据《劳动法》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予经济补偿金或恢复劳动关系的条款,维护了5名职工的权益。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专家和律师,社会上懂《劳动法》的人不多,企业与职工也没有重视,特别是职工,一旦发生争议,基本都是找组织或找领导,很少有人尝试凭《劳动法》走法律途径。尽管当时的新闻洋溢着对《劳动法》出台的喜悦和希望。
1990年代初,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刚刚确立,《劳动法》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烙印,但起草法案的原则明确:向劳动者倾斜,突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打破所有制的界限,所有用人单位一律平等适用。这也成了此次维权中我可以理直气壮拿出《劳动法》说事的依靠。任何秩序的建立都是从无到有,《劳动法》构筑了中国劳动法律的框架,结束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其长远意义也在此。
丛林时期:弱者无奈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上海市郊有家企业使用13岁的“童工”。根据《劳动法》企业用工规定的相关条款,童工是禁用的。可“童工”说自己18岁,问他读书学校等问题,他又回答不上来。
我打电话给劳动部门,请求派劳动监察人员前来。男孩承认了一切,但劳动监察让我回去,说他们要等男孩父亲取身份证来。很快,我接到劳动监察的电话,说男孩父亲改口,咬定男孩18岁,身份证丢了。我指出:做骨龄测试或发函致男孩原籍派出所调查。谨慎起见,我以疑似“童工”为题,写了批评报道。
事后,老板找到我诉苦,这位“童工”母亲患重病,父亲是个流动摊贩,他可怜这一家,才收留男孩的,他并不清楚童工禁用。对于最应该了解《劳动法》的人群来说,他们有的处于强势,不愿遵守;有的为了生存,只得忍受。这就是丛林时期,一方靠野蛮攫取获取利润最大化,一方为了生计只能俯首帖耳。《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八项权利,作出了“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制度设计,都充分考虑到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势单力薄、易受损害的实际情况,但劳动者若自己不主动争取,甚至配合企业,这部法律可真要束之高阁了。
劣币时期:企业魔高一丈
《劳动法》施行10多年,企业已经懂得规避明显的严重侵权,有的企业甚至聘请了专业律师建立了法务部处理劳动事务或纠纷。但对职工来说,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常常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地步。
有一家国企酒店,与一个在库房工作的女职工签订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有一次,部门领导要求她写账,她与领导交涉,认为这活不是她工作职责范围,尽管如此,她还是完成了任务。
不料,隔天法律顾问拿来一份调整工作岗位通知,要求她去客房担任服务员,如果不去就算旷工,并要她签收。女职工不同意,签收后仍在原岗位上班。
数日,单位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女职工不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结果,从仲裁、一审到二审,她全部败北。
我把这一时期定义为劣币时期。因为劣币的泛滥,导致良币“寸步难行”。但在艰难中,我依然看到了曙光,因为多数职工发生劳动争议时,不再“哭闹吵”,而是诉诸法律。虽然与“武装到牙齿”的企业角力,他们输掉了官司,但相信《劳动法》,相信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已经成为共识。
博弈时期:带录音笔工作
《劳动法》在内容上覆盖了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但很多规定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这就需要制定与其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2008年,继《劳动法》之后,又一座里程碑式的法律《劳动合同法》颁布并施行,它是《劳动法》的深化和延续,也是《劳动法》的姐妹篇。
《劳动合同法》最大的意义,一是出台前的全民大讨论,使法未颁布全民已学法;二是引入了惩罚条款。不签劳动合同,企业支付双倍工资;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支付双倍补偿金……难怪一些违法企业至今视该法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尽方法诋毁。而一些学者专家,不知何因,也跟着鼓噪。
我们必须承认,惩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曾经有一位女性办公室主任找我投诉。工作期间,她为了以后的维权,一直在搜集证据,哪怕老板请她陪客户,她也拿着手机录音以证明自己在加班。被辞后,她提出的诉求多达20项,总金额近千万元。她说,打了再说,反正多写诉求可能少裁判,但少写不会多给。
近年来,全国劳动争议案急剧上升,也许跟这种心态有关。在反对这样心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已身处博弈时代。当劳动者从任人宰割到相对平等地争权,当法律途径维权成本降低,当每个劳动者都知道拿着手机录音取证,当更多的职工敢对老板说“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进步,不是社会法治的进步?
我认为,这就是20年来《劳动法》颁布实施的意义和成果。
但作为一个维权记者,我却因病退出了一线。
责编/王欢 wh@lnddgr.cn
《劳动法》的一波三折
1956年,劳动部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小组,做起草《劳动法》的准备工作,不久却在“大跃进”等极左思潮干扰下夭折;
1979年初,国家劳动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等开始了第二次《劳动法》的制定,草案虽然在1983年7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却因在很多问题认识上难以统一而再被搁置;
1990年,《劳动法》第三次起草工作启动。1991年,《劳动法(草案)》再次报送国务院,因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不甚明确,《劳动法》的立法原则难以确定,未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不久,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劳动法》的立法原则由此明确。1994年,《劳动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