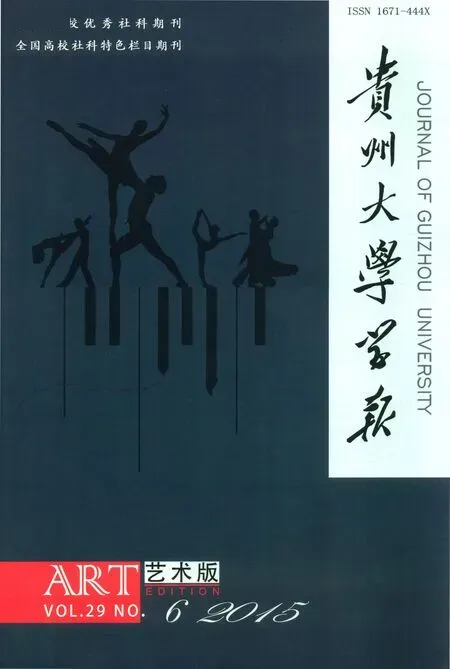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
许 艳,廖明君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带,生活着壮族、汉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其中隆林彝族现有人口五千多人,主要居住在德峨、新州、猪场、者浪等乡镇的十几个村屯。
隆林彝族自云南迁来,最早的一支在当地生活已有一千多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隆林彝族文化遭遇了严重的破坏,不但经书被烧掉,毕摩不允许做法事,鲜艳、华丽的民族服饰也被禁止制作与使用,使得彝族服饰艺术一度陷入断裂与消亡的危机之中。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增强,隆林彝族文化开始复兴,隆林彝族服饰艺术也重现了生机,彝家女孩火红的百褶裙、闪亮清脆的银饰、端庄美丽的瓦片帽,男子英俊潇洒的“查尔瓦”、威严庄重的“天菩萨”,成为了一年一度彝族火把节的火把场上最靓丽的风景线。
一、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变迁历程
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变迁历程,大致经过了传统社会形态下的沿袭与承续、民国前后的涵化与整合、1949-1978年间的断裂与消解三个阶段。
(一)传统社会形态下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沿袭与承续
彝族服饰艺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它的产生发展、衍变,反映了本民族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1]据考证,彝族先民与西北氐羌族群有渊源关系,与其他各族不断融合而形成今天的民族共同体——彝族。彝族是活跃在我国西南边陲的民族共同体,长期以来靠放牧生活;明清以前,滇东、黔西的彝族与今四川凉山彝族服饰大致相同,服饰艺术的发展变化速度也很缓慢,到了改土归流以后,各地彝区人民在中央政权和强势文化的双重压迫下服饰习俗渐渐有了较大的变化。
历史文献对隆林彝族的记载着墨不多,然而通过其迁徙的时间与地域来看,改土归流以前,隆林彝族服饰与云南东川、会泽、曲靖、沾益、兴义、安顺、册亨等地的服饰大致相同。如光绪《东川府志》上记载说:“黑玀玀披毡戴笠,壮者青蓝布裹头,短衣长裤,女则衣裙皆长,跣足。营长火目家多用锻帛,……白玀玀,麻衣麻裙。”[2]光绪十一年《沾益州志》云: “白玀玀之种二,而男耕女织习尚简朴,衣冠礼仪一如汉人,惟彝语尚未尽改,居山者,男子裹头跣足,以草束腰,女彝耳带铜环,披羊皮,事耕鑿 (凿),于诸彝中向化最先,盖其质性原与汉人不相远也。……黑玀玀……衣短青衣,髻向前,以布绕其髻,出入配短刀,性嗜酒……女长裙细褶……蛮娘能在织连钱锦贝,饰花裙百褶”[3]。咸丰四年所修《兴义府志》上也记载:“倮儸男子服色青白布,女人辫发用青布缠之首,戴梅花,耳垂大银环,衣长,裙以二十一幅布为之”[4]。咸丰《安顺府志》说: “倮儸,男子服青白布,女人辫发。用青布缠首。戴梅花。耳垂大银环。衣裙皆长,裙以二十余幅布为之。”[5]此外,《皇清职贡图》、《册亨县乡土志》[6]、《安南县志》[7]等均有关于彝族先民 “倮玀”穿着习俗的记载。
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可知,此时彝族妇女尚能自制衣服,且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黑彝服饰可用锻帛等高档面料,白彝只能用麻料;黑彝尚黑,白彝尚白。其服饰艺术的总特征为:男子椎髻向前,以布缠髻,戴 (左)耳环,出入佩刀,女子上衣长,束腰,下穿百褶长裙,赤足 (土司及统治者穿鞋),男女皆披毡或羊皮,喜用银装饰身体,如银耳环、银花额贴、银链等。而到了清中期以后,白彝已有不同程度的汉化,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衣冠礼仪一如汉人”[8]的情况。
(二)民国前后隆林彝族服饰艺术涵化与整合
民国前后,隆林彝族服饰艺术主要呈现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与周边民族的服饰艺术风格与装饰手法日益相近,二是吸收了满清及汉族民间服饰艺术的成分,整体处于不断的涵化与整合之中,进而发展出了独特的服饰艺术风格。
一)鲜明的地域特色
经过累世的生活劳作,隆林彝族不仅适应了桂西北高寒山区的自然地理气候,也通过族际间的交流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了该地区特有的服饰艺术风格。如民国时期雷雨在《西隆苗冲纪闻》中说:“住于苗冲者,尚有果羅及来子二种人,通常亦被曰为苗子,然除言语之外,他固无以异于汉人也……苗族虽以服装而异,但苗男之服装,并无差异,即与一般客人,土著,及果羅,来子诸族,亦无二致。其服装多好蓝,白,青,黑诸色,与他族无大差别”[8]。可见,当时隆林各族男子服装已基本相同,而女子服装除苗族之外,皆“无以异于汉人”。
不仅服装款式结构基本相同,隆林各族民众的织造技术、用色习俗、配饰及装饰手法等方面亦存在许多的共同之处。如各族民众大多自己种青蔴织布,但也有人从市场上买回棉花自己织布,织好的布用蓝靛经浸、染、洗、晒等步骤将白布染成蓝色或黑色。隆林德峨的阿稿寨至今还保留有8个彝族人曾经使用的染布池,苗族、壮族的许多村寨里也还保留着类似的传统染织技术和染布池。由于隆林盛产野靛草,各民族传统服饰中上衣以蓝色、蓝黑色等为主体色彩体系,下裳以黑色、蓝黑色为主要表现色彩,服饰品中的鞋子以黑色为主,而选用一些较亮的红、蓝、绿等色绣上花叶、蝶鸟等图案做点缀,装饰都集中在襟口、下摆、袖口、裤脚及围腰头、鞋头等位置,装饰技艺多以刺绣为主,辅以剪贴、镶绲等手法。而在配饰方面,女性虽爱银、饰银,但却不求华丽繁复,装饰得恰到好处;新生儿满月或周岁时都有外婆送背带的习俗,背带形制以深色或红色等棉料为底料,配上六块、八块或十二块背带芯及贴花彩布背带柱组成。此外,鞋垫、荷包等装饰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二)满汉之风盛行

图1 清末隆林彝族马面裙 (藏于隆林民族博物馆)
民国前后,社会动荡不安,地处偏远山区的隆林彝族社会不仅受到了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变革的冲击,还因当地种植、交易鸦片的影响,对外经济文化联系空前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隆林彝族服饰又吸收、融入了满清及汉族服饰的成份,出现了“叮当档”裙、马面裙、琵琶襟坎肩、长衫马褂等具有典型汉族及满清风格的服饰。
1.“叮当档”裙
清末以后,隆林彝族女子裙装款式变化较大,早期风行凤尾裙,咸丰同治年间“鱼鳞百褶裙”深受妇女喜爱,到光绪时又出现过一种名为“叮当档”的裙装,其裙上十数条剑状飘带,端系金属小铃铛,动则发出悦耳的叮当声响。笔者在田野考察期间多次听当地老人描述一种类似的“叮当档”裙。住在德峨街上的95岁老人黄阿妹说:“这种裙子只有少数有钱人才穿,裙子很长,差不多快到地了,裙子上面挂满了铃铛,都是银做的。走路叮叮当当的响。”①受访人:黄阿妹,访谈时间:2014年1月18号13点,访谈地点:德峨黄阿妹家中。彝族毕摩王文魁说:“我很小的时侯,记忆中有见过这种裙子,叮叮当当的,很有节奏,好听极了。”②受访人:王文魁,访谈时间:2014年1月14号22点,访谈地点:德峨黄阿妹家中。
2.马面裙
马面裙是中国汉民族传统裙装中很重要的一种,是明清女子装束经久不衰的典型搭配。马面裙是以数幅整幅缎面接合而成的长裙,前后各有20-27cm的平幅裙门,这个平幅裙门俗称“马面”,在平幅裙门和裙摆上绣有各种精致的绣花花边或镶、绲、拼贴工艺装饰。“马面裙”整体呈现平面的围式造型,侧缝不缝合,两头分别用两根腰带维系于腰间达到重合以形成闭合的裙装效果。据隆林彝族老人介绍,马面裙在建国以前在隆林彝族村寨还比较盛行,一开始可能只是贵族妇女才能穿,以表身份。后来,平民百姓也开始效仿,但主要是在婚礼等喜庆场合穿着,且需要“向别家借来”,婚礼时8人 (可能是伴娘)围坐一桌,两两穿不同颜色的衣裙套装,有粉色、绿色、黄色等。现隆林民族博物馆存有两件马面裙,材质华贵,工艺精美 (图1)。

图2 琵琶襟坎肩

图3 清末隆林彝族长衫马褂
3.琵琶襟坎肩
如图2所示的服饰是照片中的老人根据前人的描述及自己的记忆仿制的一套仿古服饰,于2011年制作,由头衣帽子、上衣的袄、坎肩和下裳褶裙组成。图中,老人身上穿的坎肩具有明显的满清服饰风格,从中仍能窥见当时服饰艺术交融的盛况。
4.长衫马褂
长衫马褂是清末民国时期男子最普遍的服装。长袍为右衽大襟,狭窄直身,长至脚踝上两寸,袖长与马褂齐,多为蓝色。马褂通常作为正式场合的一种礼服形式与长袍搭配,衣长及臀围,有琵琶襟、对襟、右衽大襟多种,纽扣有5、7、9颗不等。今德峨阿稿彝寨保存有一张彝族地主杨廷凤③杨廷凤生于清朝末年,卒于1949年。的照片,如图3所示,照片中的杨廷凤头戴西式宽沿圆礼帽,身穿直领对襟深色外衣——马褂,前胸门襟处有7颗盘扣,内穿浅色长衫,长衫下配长裤,与当时汉区流行的礼服几乎一致。据当地老人说长衫配马褂的着装风格在隆林彝区流行了很久,有的在长裤的外面只穿一件右衽大襟的长衫衣,腰间系一根同色布腰带,衣服通常为黑色粗布制作。
由上观之,这一时期的隆林彝族服饰已与改土归流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一方面在与周边各民族共同相处、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服饰风格,另一方面又跟随时代风气吸纳满汉服饰之精华,可谓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涵化、整合中不断地发展变化。
三)1949-1978年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断裂与消解
1949-1978年,在乡村改造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组织体系和权利网络的全面建构下,逐步开始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破旧立新”式改造,使得民族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涵、从表象到根基之间逐步趋于分离甚至断裂的境况,尤其在“文革”十年期间,所有的传统思想、行为、文化、艺术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一时期,隆林彝族服饰艺术也同样受到影响,变化的速度异常迅速。

图4 20世纪60年代隆林彝族服饰

图5 王秀珍缝制的彝族服饰
住在新洲、团石等地的彝族老人告诉笔者:“那时候我们都挨抓去剪短发,以前用的耳环、手镯、项圈全都要上交,衣服上有花花不能穿……要是被红卫兵发现,就要被批斗。”因此,隆林彝族群众只能穿着净黑或净蓝色土布衣裤,除了实用功能外,几乎无其他装饰,而传统的女子绣花服饰也都难以见到,图案和装饰技艺也基本失传。

图6 1989年第一次大型火把节上的彝族服饰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在结构形式上较以前变化不大,但却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服装款式单一,传统的女子盛装服饰逐渐消失。第二,服饰色彩减少,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服饰,普遍使用黑、深蓝、灰色等颜色,很少运用其他鲜艳的颜色;第三,饰品配件等从逐渐减少到彻底消失,服饰成为了评判人的政治信仰和思想观念的外在标志,经济、实用的服装要符合“革命”时期的风尚。于是,隆林彝族服饰艺术逐渐走向衰落,面临着断裂与消解的危机。
从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发展的轨迹来看,其经历了从“羊皮披毡”、“丝绸盛装”到“粗陋布衣”的巨大演变,服饰制作面料也从古代牛羊皮、植物根茎到现代工业合成面料的过程。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功能也从防寒护体的基本物理功能上升为象征地位、财富与身份标志的文化功能,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又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上述巨大变迁,不仅展现了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演变历程,记录了隆林彝族整体的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折射出了隆林彝族民众思维观念和心理行为的变化。
二、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当代重构的文化进程
尽管隆林彝族仍然传承着本族群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族群称谓、风俗习惯等,但由于隆林处于彝族文化的边缘地带,且长期与境内其他民族混杂而居,在历经了民国至“文革”结束后几十年的文化解构历程之后,其传统服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民族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国家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自上而下的取缔与否定,并不能彻底切断人们心理意识深处的信仰,一旦来自于国家权利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有所松动,长期蛰伏在民众心中的传统便有可能复苏,并通过不断调适、重组而使民族文化焕发新的生机。隆林彝族服饰艺术正是经历这样的重构历程。
(一)时代背景
“文革”结束后,国家重新修正了有关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开始重视保护和挖掘民间传统文化遗产。1979年以后,国家多次下达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文件,全国各地彝区纷纷成立或恢复彝语文和彝文古籍整理、翻译机构。1983年6月5日,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隆林彝族应邀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第一次正式将川、滇、黔、桂四省 (区)的彝族同胞聚拢到了一起,因而也成为了隆林彝族文化当代重构的起始。此后,隆林彝族多次派出代表赴云南、贵州、四川参加相关会议,考察学习这些地区彝族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构。
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实力及生活水平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经济社会水平的改善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隆林彝族涌现了一批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充分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处境,心系民族未来,迫切希望为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
同时,现代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进一步席卷全球,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逐渐缩小。民间的信仰体系趋于瓦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10],传统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与规范不断接受着新型社会环境的考验。一方面,民众被动接受或主动追求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保留或挖掘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一切能够成为民族认同符号的文化表达由此获得了重构和再造的内在契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包括服饰艺术在内的隆林彝族传统文化艺术在历经了民国前后的涵化、整合及解放后至“文革”期间的断裂与消解之后,逐渐走向了复兴与重构之路。
(二)传统文化的复兴
一)举办彝文古籍整理、毕摩培训班与彝文培训班
1984年4月,在隆林各族自治县政府的支持下,隆林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参与者有黄国政、王文魁、韦定富等人。他们搜集了隆林、西林彝族村寨传承下来的彝文古经书,聘请彝族老毕摩王文辉先生传教彝文。后来,又派代表到贵州毕节学习彝文翻译工作,并整理出了《隆林彝文单词》一书。此后,隆林又举办了短期的毕摩培训班,教授彝族毕摩文字、祭祀仪式流程等内容。
二)改彝式神坛、取彝名
隆林德峨阿搞寨现有王、杨、李、吴、郭、黄、韦共七个汉姓,每一个彝族汉姓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彝族“涅益”家支。传统上,每个家族的男子从小就要背诵本家支的系谱,但后来由于彝族人口较少,且平时与壮族、汉族等接触较多,使用汉姓更为方便,因此就逐渐丢弃彝族传统家支制度。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隆林彝族毕摩王文魁等人根据毕摩经书的记载及民间的记忆,寻根问源将各姓彝族的汉姓与彝族“涅益”家支一一对应起来,具体为:“额伯涅益稀”(替仆)——韦,“荻撮碑罗西”——王,“荻切碑罗西”——黄,“日K仆”又 (古西涅益西)——杨或李,“渣洲涅益西”——吴或郭,并在“涅益”家支的基础上将各村寨彝人的汉式神坛改为彝式神坛。如1963年6月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实习组的调查,那地寨黄世福家的神位文字为[11]:

此神坛样式与当地壮族、汉族无异,这说明在解放初期,隆林彝族文化受周边汉族影响已相当之高。但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当地彝族的神坛文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笔者仅摘录其中之一作为对照①此神坛文字抄写自德峨镇阿搞寨李景林家。:
接着,当地部分知识分子还为自己起了彝名。如韦革新的彝名是“替仆支不”,杨义杰的彝名是“古西乌沙”,其中“替仆”、 “古西”是彝族“涅益”家支的简称,“支不”、“乌沙”则是名。这种现象在新一代年轻人中则更为普遍,如杨强的彝名是“古西西措”,其二哥杨坚彝名为“古西阿格”,杨玉婷的彝名是“古西依婷”,吴海飞彝名为“渣州诗洛”,其姐姐吴海清则取名为“渣州诗薇”,“渣州”也是彝族“涅益”家支的简称, “诗洛”、 “诗薇”是名。
从汉式神坛、汉名到彝式神坛、彝名的变化,不仅反映了隆林彝族文化的发展过程,还折射出隆林彝族文化心理的变迁轨迹。“彝味”浓郁的彝式神坛、彝族名等都是隆林彝人传承、重构本民族文化的文化行为。
三)传统节日的重构
隆林彝族如今主要过三个民族节日,即“火把节”、“祭送布谷鸟节”和“彝年节”,但这三个节日“恢复”举办的时间也都是在1980年代末以后。
1.火把节。“火把节”是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因具有集体狂欢的特征而被誉为“东方的狂欢节”。但是,历史上彝族并没有“火把节”这个称谓。那么,隆林彝族在历史上是否有举办“火把节”的传统呢?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所见,并未发现有关于隆林彝族“火把节”的记载,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曾多次对“火把节”进行求证,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唯有一个“六月六”的日子与火把节的内容颇为接近。
案例1:黄灵芝家人等访谈录①访谈时间:2014年1月20号,访谈地点:黄灵芝家,文中材料根据录音材料整理。
1982年,我组织过的火把节,那是第一次,82年以前也过火把节但是规模不大,改革开放以前,以前没有火把节的时候就过“六月六”,点烧火把、杀牛、祭祖,还搞一些娱乐活动。以前大年初一、初二我们也烧火把,规模不大,后来才统一到六月二十四号。1989年在阿搞那边举办了大型的“火把节”,各村各寨的人都去参加了。
显然,当地人也认为“六月六”与火把节有一定关系,只是火把节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举办,开始过火把节以后,“六月六”的节日也就取消了。
而隆林彝族毕摩王文魁则说:“我们彝族传统上是在每年的猪月猪日过火把节。”毕摩是彝族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集大成者,虽然隆林彝族毕摩经书已经失传,但因口传而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资料。王老先生的这句话似乎又说明隆林彝族原来就有火把节,现在只是重新恢复了。总之,可以肯定的是,隆林彝族原来就有烧火把的习俗,只是时间在农历的六月六,内容主要是杀牛、祭祖、娱乐活动等,与现在的火把节内容形式差不多。
2.“祭送布谷鸟节”。该节由“祭送布谷鸟仪式”发展而来,广泛流传于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和西林县的彝族村寨。关于该仪式的由来,隆林彝族民间主要流传有两则故事:其一,布谷鸟是彝族祖先神,它佑护着彝族人民从遥远的他乡迁徙到隆林这片土地,祭祀布谷鸟寄托了隆林彝民的思乡之情。其二,布谷鸟是催春的神鸟,每年初春万物复苏时节就会来到人间催促人们耕种,它夜以继日地关心人民生产,以致操劳献身,人们感谢它,于是在每年丰收之时送来食物与之共享。当地还广泛流传着《布谷鸟歌》,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祭送布谷鸟节”的本土性。[12]
但是,笔者翻阅了各种文献也没有查找到有关于祭送布谷鸟节的记载,隆林彝人也都说以前没有这个节日。笔者在翻阅2003年编撰的《隆林彝族》一书时,发现当时彝族人过一个叫做“尝新节”的节日,“尝新节”与“祭送布谷鸟节”均有“丰收之后,请布谷鸟尝新”的习俗[13]。现在, “尝新节”是当地仡佬族最大的民族节日,而彝族已不再过“尝新节”。因此,很有可能隆林彝族祭送布谷鸟节是在火把节与“布谷鸟尝新”的结合下被建构出来的新的节日。现在的“祭送布谷鸟节”与“火把节”同一天过,于2014年申报为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3.“彝年节”的回归。按照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共有十个月,每个月36天,剩下的5-6天为“过年日”,即“彝年节”。过去,彝年节是隆林民众休闲玩乐、杀猪祭祖等活动的时间,但因为长期与汉族相处,就与汉族同胞一起过起了春节。随着与滇川黔彝族的交流,隆林彝族逐渐意识到本民族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始重视彝年节。隆林彝语称彝年节为“戈西”,时间在每年的冬月三十一 (农历腊月初一)。彝年节除了杀猪、鸡、鸭外,还要在年节当天凌晨鸡叫三声时舂糯米粑,然后将一块直径约45公分的大粑粑和米豆、米豆水摆在神台上供神,并举行祭祖祈福仪式。
“火把节”、 “祭送布谷鸟节”和“彝年节”几乎都是在传统仪式、节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民族传统节日是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民族文化心理等的集中反映,通过民族节日可以全方位的向外界展示民族传统服饰、歌舞、饮食、宗教仪式等民族文化艺术,传统节日的回归与重构对于增强隆林彝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等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民族服饰艺术的重构
伴随上述一系列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重构,隆林彝族民众对民族服饰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建构一套能体现本民族身份与精神风貌的服饰,已成为时代赋予隆林彝族人的使命。
继1979年第一次彝文古籍工作会议之后,20世纪80-90年代是隆林彝族广泛与川、滇、黔彝族同胞交流学习的时期,在这期间,隆林彝族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等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其中,隆林彝族诗人韦革新 (替仆支不)是将凉山彝族服饰带到隆林的第一人。笔者找到了当时参与新式彝族服饰“设计”的彝族干部王秀珍,试图还原当地彝族服饰艺术重构的全貌。
案例2:彝族干部王秀珍访谈录①受访者:王秀珍,访谈时间:2014年1月18日上午,访谈地点:古城村往隆林县城的车上。
笔者:现在这种红色的盛装衣服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王:(20世纪)八几年的时候。
笔者:是怎么来的?
王:韦革新从凉山带回来的嘛,他那时候去凉山,回来给他爱人带了一套,大家都觉得好看,就开始效仿。
笔者:具体的经过可以说一下吗?
王:那时我刚来县里参加工作,正好遇上要设计新的民族服装。我们德峨的彝族人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讨论传统文化恢复的事情,主要是火把节和火把节服装。火把节的时候,凉山那边给我们寄来达体舞的资料,我们一群人跟着寄来的录音磁带学达体舞。89年火把节的时候,各个村寨的人都来了,杀猪、杀羊……好热闹。说到火把节的服装,那时候我家隔壁是裁缝,我请她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开始缝,那是我第一次做衣服。后来大家统一以我做的那套服装为标准,这套服装后来被百色市博物馆收走了。
德峨镇阿搞寨的“寨老”杨合明也说现在的隆林彝族服饰是以凉山彝族服饰为样板制作的,时间是在1980年,韦革新从凉山进购过来几件,穿起来大家个个喜欢,于是就开始仿制。
但也有人说,隆林彝族新式的民族服饰是根据隆林彝族过去的服装改制的,他们认为,过去隆林彝族妇女也是穿裙子,只是到了近代才改穿裤子。
案例3:王文魁 (70多岁)访谈录②受访者:王文魁,访谈地点:隆林县城王文魁家火塘边,访谈时间:2014年1月14号下午10点。
我小的时候见过我母亲穿裙子的,那时候的裙子褶子很大,跟凉山那边的很像,不像现在 (机器压的)这么细,大大的褶看起来很大方。那时候的裙子颜色也比较深,一般是黑色的,上面挂上银制的铃铛,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响,好听极了。
案例4:黄阿妹 (95岁)、王阿湾 (90岁)访谈录③受访者:黄阿妹、王阿湾,访谈地点:德峨黄阿妹家中,访谈时间:2014年1月18日下午1点。
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还穿过裙子,后来不多见了。像是帽子、衣服、裙子这样的全身搭配很少见,有的也是在结婚的时候穿,有人要办喜酒了,就去向别家借来穿,久不久见到一两套,慢慢的就全都不见了。
此外,隆林民族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彝族“古裙”也成为当地彝人对于过去穿裙这一传统的有力“物证”。显然,在凉山彝族服饰的“启发”、当地老人的“记忆”以及实物依据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顺势在开展,并通过1989年的火把节、1993年的县庆活动正式宣示了新式隆林彝族服饰的合法性。
1989年,隆林彝族在德峨街举办了第一次大型火把节,各村各寨的人都赶来参加,大家穿上统一的民族服饰、围着火把跳起达体舞。火把节不仅为新式民族服饰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而且还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团结和谐的民族集体形象,包括周边其他民族、游客、县领导及媒体在内的所有人均对此举表示赞赏。
1993年,适逢隆林各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县里要求境内的每个民族派出81人的代表穿着民族服饰参加县庆,彝族代表以一身艳丽、喜庆的新式民族服饰亮相,惊艳了县内外来客。如果说火把节上穿着新式民族服饰使得这种服饰在内部赢取了隆林广大彝族同胞认可的话,参加县庆活动则是正式向外界宣示了隆林新式彝族服饰的“合法性”。
此后,隆林彝族民众不管是参加当地还是外地的民族活动,都身穿民族服饰以新的民族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20世纪90年代,新型的隆林彝族女装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举行的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服装展中获得一致好评,其中被赋予了典型文化内涵的“五色百褶裙”、“钩连纹”的隆林彝族服饰还在此次展评中荣获一等奖。[14]
三、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当代重构的价值与意义
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重构,不仅仅是穿着形式的改变,还意味着民族文化的重塑,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化意义。
(一)成为民族文化展示、宣传的重要媒介
每个民族都有一系列与服饰艺术相关的民俗活动。隆林彝族日常生活中与服饰相关的民俗活动众多,从岁时节日、婚丧嫁娶、祭祀仪式到各种形式的族内族外的文化交流与交往,尤其是历次对外活动,如“第一届中国艺术节”①1987年于北京开展,参展的隆林彝族代表有王雪芳、王文魁、韦斌。、 “ 中国彝族十月太②1992年,云南召开,韦革新、王文杰两位同志参加。、 “③2014年5月,隆林派彝族代表参加。、 “阳历学术研讨会” 那坡跳弓节活动” 第四届云南民族服装服饰文化节”,以及县市及省内外的各种民俗比赛活动等,新式的隆林彝族服饰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亮点。在每年的火把节期间,各地游客都因隆林彝族火红热烈的“百褶裙”、威武飒爽的“查尔瓦”而慕名前来,年轻的隆林彝族姑娘穿着整套彝族服饰大方自信地在游客面前展示。鲜艳耀眼、美丽大方的隆林彝族服饰给族内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视觉上的好感是认识和了解隆林彝族历史与文化的内在动力,统一的民族服饰为隆林彝族建构了一幅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团结友爱的画卷。
(二)促进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在任何时代,文化变迁都是传统之“旧”、现实之“新”以及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上外来之“异”三者激荡的结果,传统、现实、外来这三者形成层叠、交融、并列,方能产生当下状态的文化。[15]从表面上来看,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不过是重新建构了一身美丽的衣饰装扮,但实际上却反映了隆林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重组与创新之道——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世界各民族都面临文化急剧变迁的问题,许多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彻底消失,而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则通过调适、重构而获得新生,如从传统服饰中继承了“上衣下裙”、 “右衽百褶”的基本结构形式,以及装饰、缝制手法,又从现实社会和外来文化中吸收了“鲜艳浓烈”、 “上窄下宽”、“上短下长”、“凹凸有致”的服饰艺术风格。既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同时又与时俱进,可谓“传承蕴含创新,创新源于传承”,二者互渗互融,不断地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与“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理念不谋而合。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被使用,服饰艺术一方面承载民族文化意蕴,另一方面还是物质消费品,应该穿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一成不变地存放在博物馆中,只有被人不断使用的服饰才具有生命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隆林彝族许多人穿上了工人装,着装形象与汉人无异,男性更是几乎没有人再穿传统服装,现在则是几乎人人都有一套民族服装,隆林彝族民众愿意穿着民族服饰并以此为豪。拥有、穿着传统服装人群的增加,客观上有利于隆林彝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更还可以扩大彝族文化的影响力,促使其走近大众,走向世界。因此,民族服饰艺术的重构对隆林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三)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话语权
对于隆林彝族来说,统一式样且异于周边族群的民族服饰,可让人一眼就识别出穿着者的身份,引导、培养族人的民族情感,进而强化民族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其所蕴藏的内在精神力量激励着族人去发掘、维护、承继、发展本族文化,并给人以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正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正如华梅教授所言:“以服饰来表明集团的整体性,就意在以可视形象增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使所有成员在集团内感受到规范的约束,在集团外又确立不同于其他集团的独特形象。”[16]隆林新式民族服饰还唤起和深化了民族成员的共同意识,自觉将原来不同阶层 (黑白彝间等级森严)、分布零散 (西林、隆林各村屯)的族人聚合在一起,共同维护民族的集体利益,共同维持民族内部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共同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
此外,新式民族服饰的重构对于提升隆林彝族的话语权也有一定积极的作用。长时间以来,无论是在隆林境内还是在川、滇、黔、桂四省 (区)彝族群体内部,隆林彝族这一支“弱小的”群体都未曾真正拥有过话语权。而当隆林彝族同胞以一身洋溢着和谐、喜庆、热烈、时尚又不失古朴、端庄气质的民族服饰出现在大众眼前时,周边的各族朋友们是羡慕的,笔者在考察时问过当地苗族人对于彝族服饰的看法时,他们都毫不掩饰对于这种民族服饰的羡慕与欣赏。
在各地彝区的文化交流交往中,隆林彝族通过积极参加各地彝族活动,并邀请外界彝族同胞加入到隆林彝族文化建设中来等举措,逐渐得到了各地彝族同胞的认同和赞赏。在出席对外活动时,隆林彝族民众必定要穿上本民族的服饰,而本就融入了凉山彝族服饰元素的隆林彝族新式民族服饰,让外地的同胞们一眼便能识别出这是彝族。从服饰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通过服饰上“随大流”以换取团体“合群”的肯定进而立足于群体之内,是着装者着装心理的典型表现。正因为如此,隆林彝族能够很快融入彝族大群体之中,并逐渐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近年来,每逢全国性的彝族活动,都会邀请隆林彝族的代表参加,如隆林彝族毕摩王文魁就多次参加了凉山、毕节、昭通等地的毕摩大会及毕摩文化研究会议等,彝学会负责编纂彝族文化资料等也会邀请隆林彝族同胞参与,彝族大学生交流会自第一届(2012年)举办以来一直都邀请隆林彝族大学生参加,隆林彝族在四省 (区)彝族中越来越被重视,逐步融入彝族主流文化圈,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过渡。
四、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当代重构的文化思考
纵观隆林彝族服饰艺术重构的文化历程,呈现出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伴随民族旅游而兴起,从感官上打造“异文化”的新鲜感;二是对传统服饰做加法或减法,增加的是一些容易引起视觉好感的配件,或增加已经失传了的民族服饰,而减法则是指传统的整套民族服饰被简化或剔除;三是色彩浓重、视觉冲击强,多为舞台盛装;四是以女性民族服饰的重构为主;五是体现了民族精英的理想。
民族服饰艺术在当代社会重构的过程中,隆林彝族也出现了诸如服饰礼服化、服饰成衣化、凉山彝族服饰“泛化”等值得思考的现象。我们知道,“民族文化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中形成,因为其适应特定的生态环境而具有外来文化无法取代的生命力。”[17]彝族服饰艺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环境中产生,千百年来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优势文化资源。隆林彝族服饰艺术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并促进其多样发展是当务之急。当然,重视和鼓励民族或族群间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并非不遗余力地倡导和促进因为这种“交流”所带来的某一文化的“泛化”。那样的话,丧失的不仅是某一民族或族群的文化遗产,“还将丧失我们最有竞争能力的发展空间和发展领域,更为严重的是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将导致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退化和丧失。”[18]
总之,隆林彝族服饰艺术作为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物质文化的一般特征,又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体现出了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随着当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政策调整、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服饰艺术处于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之中,我们希望通过分析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当代重构,揭示这种重构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机制,进而揭示出我国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语境中其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挖掘、保护与开发提供一定的经验与理论。
[1] 冯敏.彝族服饰考[J].思想战线,1990(01).
[2] 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户口(卷8)(校注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93.
[3] (清)陈燕,韩寶深修,荘致和等校.沾益州志·风俗(卷2)[M].沾益县文物管理所复印,光绪十一年重修本:209-210.
[4] (清)张镆修,邹汉勋,朱逢甲等纂修.兴义府志·苗类(一)(卷41)[M].贵阳文通书局据刻本铅排本,民国三年:389.
[5] (清)常恩修,邹汉勋,吴寅邦纂.安顺府志·风俗(卷15)[M].咸丰元年刻本:14.
[6] (民国)罗骏超纂.册亨县乡土志略·风俗(第九章)[M].册亨县档案馆藏铅印本,册亨县政府编印.
[7] (清)何天忂修,郭士信等纂.安南县志·舆图·风俗(卷1)[M].贵州图书馆(雍正九年稿本,据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复制油印本),1996.
[8] (清)陈燕,韩宝深修,荘致和,马文忻等校.沾益州志·风俗(卷2)[M].沾益县文物管理所复印,光绪十一年:209.
[9] (民国)雷雨.广西西隆县苗冲纪闻[M].广西民政厅秘书处出版,民国八年:36,3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11]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隆林县德峨区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Z].1964:32.
[12]许艳.隆林彝族“祭送布谷鸟节”传承现状考察[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4(05).
[13]《隆林彝族》编写组.隆林彝族(内刊)[M].隆林: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印刷厂,2003:85-86.
[14]《隆林彝族》编撰委员会编.隆林彝族[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249.
[15]朱炳祥.“文化叠合”与“文化还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05).
[16]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16.
[17]覃德清.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268.
[18]杨昌儒.民族文化重构试论——以贵州布依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