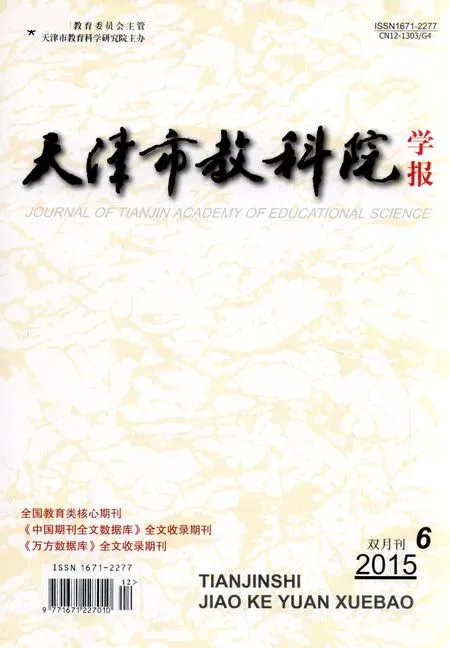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张宇 王月琴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张宇 王月琴
探讨了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采用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MPAI)、主观幸福感量表(SWB)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对3738名大学生施测。结果如下:(1)手机依赖总分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学生总分最低;(2)手机依赖高分组和低分组在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3)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及各因子均为显著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4)手机依赖对领悟社会支持及各因子、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因子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5)领悟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注重社会性发展、提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和幸福感对促进大学生科学合理使用手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手机依赖;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中介作用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关于手机依赖方面的研究并不丰富,可能与智能手机普及时间较短有关。目前主要集中于严标宾、姜永志、黄海等[1-4]关于其与人格、心理和谐、疏离感、孤独感等方面的研究,从中探讨了自尊、焦虑、网络社会支持等变量的中介作用或调节作用等,而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尚不多见。唐媛林(2014)关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元分析也表明,手机依赖或成瘾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甚少,值得深入研究。[5]
本研究拟以手机依赖、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为研究变量,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为有效指导大学生科学合理使用手机提供理论支持。手机依赖也称作手机成瘾,目前对手机依赖基本没有统一的概念,一些研究者将手机依赖看作是一种行为成瘾,与网络成瘾、赌博成瘾相似,[6]也有研究者认为手机依赖是对手机的过度使用而产生的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症状。[7]Dinner(1984)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评价者以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整体评价包括情感反应(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和认知判断(生活满意度),该观点在我国得到很多研究者的认同。另有一部分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例如邢占军等人提出了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首先要整合快乐主义幸福观和完善论幸福观这两个方面,即在生活中,有以追求快乐为主的主观幸福感,也有以自我实现、发挥才能为主的幸福感。[8]本研究采用Dinner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领悟社会支持是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持而言的,它强调个体自己所理解和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强调个体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或满意程度,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是对可能收到的社会支持的信念。[9]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包括:若通过手机依赖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则其主观幸福感高;若通过手机依赖没有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则主观幸福感水平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对手机依赖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为两者间的中介变量。
一、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以青岛市某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40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38份,有效率93.45%。其中男生1282人(34.3%),女生2456人(65.7%);大一2247人(60.1%),大二652人(17.4%),大三677(18.1%),大四162(4.3%);文科类2832人(75.8%),理科类895人(23.9%)。
(二)工具
手机依赖量表(MPAI),该量表由Leung等修订,共17题,包括4个维度,分别为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失控性指个体无法控制在手机上花费的大量时间;戒断性指个体不能正常使用手机时出现的不良情绪等反应;逃避性指利用手机逃避现实时间,使用者沉浸在手机网络世界中;低效性指过度使用手机导致较低的学习或者工作效率。采用五级评分法,得分越高则手机依赖程度越严重。[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该量表由Zimet等编制,是一种强调个体自我理解和自我感受的社会支持量表,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共12个项目,采用七级计分法,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总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11]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
主观幸福感量表(SWB),该量表由Diener等编制,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个维度,共19个项目,采用七点计分法,三个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其相应的情绪感受水平越高,消极情感量表反向计分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量表得分相加为主观幸福感总分。[12]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生活满意度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8,积极情感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消极情感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
1.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专业、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在性别、专业变量上手机依赖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男生得分(39.33±10.6)总体高于女生(38.61±11.38),理科生得分(39.23±11.34)总体高于文科生(38.72±11.05),说明男生、理科生对手机的依赖性更强;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后经LSD检验表明,大一学生手机依赖得分(38.36± 10.99)显著低于大二(39.75±11.45)和大三学生(39.46± 11.05),与大四学生(39.63±11.66)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

表1 手机依赖总分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2.手机依赖高分组和低分组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得分上的差异分析
按总分最高和最低占27%的原则将手机依赖总分分为高分组(总分≥45)和低分组(总分≤31),手机依赖高分组和低分组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得分上的差异分析见表2。手机依赖高分组和低分组在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手机依赖高分组的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低分组,手机依赖高分组主观幸福感总分及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分因子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手机依赖高分组消极情感分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低分组。说明手机依赖高分者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方面的正向体验更低。

表2 手机依赖高分组、低分组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上的得分比较(M±SD)
3.手机依赖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3),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p<0.01),即手机依赖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得分越低;与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p<0.01),即手机依赖得分越高,领悟社会支持得分越低;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p<0.01),即领悟社会支持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相关关系显著是检验中介变量的重要前提,值得做后续中介变量检验。

表3 手机依赖、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4.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领悟社会支持、手机依赖各因子为预测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进行enter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表4),领悟社会支持各因子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手机依赖各因子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且领悟社会支持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效应大于手机依赖的回归效应,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很可能是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变量。其中,领悟社会支持的“其他支持”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最大,Beta系数为0.26(β> 0.2),表明“其他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他支持”包括来自老师、同学、亲戚等的支持,说明老师、同学、亲戚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获取上发挥着更大作用。

表4 领悟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5.领悟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依照温忠麟关于中介变量依次检验程序,[13]我们对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表5)领悟社会支持及各因子回归系数t检验都显著,领悟社会支持及各因子是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显著且均为部分中介效应。领悟社会支持及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因子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c)分别为24.89%、16.11%、17.33%、17.78%。

表5 领悟社会支持及其三个因子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三、讨论
1.大学生手机依赖总体状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性别、专业变量上大学生手机依赖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是男生高于女生、理科生高于文科生,这与刘沛汝、姜永志、刘红等研究结果吻合;[14-16]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最低,这与徐少卿、王欢、邓兆杰等研究结果不同,[17-19]可能与所研究的被试地域、结构等有关。针对此我们需要加强大学生手机依赖水平分类管理,尤其注重对男生、理科生及大二、大三学生进行科学合理使用手机的指导与教育。
手机依赖高分组在领悟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上都显著低于低分组,表明手机依赖水平越高的大学生,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和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相反,手机依赖水平低的学生在这两方面的水平都较高,这与我们的第二个研究假设相符,表明学生手机依赖并不是为了建立社会支持系统、获得情感归属等,而是用作其他,如姜永志[20]的研究表明,手机使用大多用于娱乐等。智能手机作为个人了解周围世界、周边关系的媒体手段,本身并无对错之分,既可以造福学生,又可能给学生带来危害,关键是看学生接收的内容是什么,即重要的是信息,而不是媒介手段。若是用作学习创造、与同伴间的合作互动、搜索与课业相关的信息等则会促进其发展,反之若用作在线讨论不良话题、浪费学习时间、回避现实等则会对学生产生危害,长期过度依赖手机甚至会使其对现实世界生活脱敏,对现实的学业、人际交往等产生漠视或无意义感等。
因此,我们能否使智能手机成为更有效的社会媒介,使学生形成对手机使用的良好态度、价值观和行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在手机使用时间上要做适当限定,尤其要限制课堂手机使用;二是在手机使用关注内容上,要引导其收看亲社会及利他行为活动内容;三是在现实生活中要多搭建人际交往平台,科学分配每天的生活范畴与主题,增进现实的人际交往,促进社会性发展,领悟更多的社会支持并最终收获生活幸福感。
2.手机依赖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手机依赖与领悟社会支持及主观幸福感都是显著负相关,表明手机依赖水平越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低、主观幸福感越低;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是显著正相关,这与段海燕、胡琳丽、许芳等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当个体领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时,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反之亦然。
同时回归分析显示,手机依赖对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尤其是老师、同学、亲戚等其他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更大,这表明“其他支持”在本研究被试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比家庭更大。这一方面与被试所在学校充满人文关怀、互助利他的教育文化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大学生分离—个体化的完成有关,但仍不可忽视家庭支持的重要作用。Blos指出青年期是实现分离—个体化的重要时期,是有效实现与原生家庭心理断乳、形成独立的人格并向外延伸建立多系的社会情感支持系统的时期。[21]库利和米德认为人终其一生都是在进行社会性发展,自我概念的发展始终都不能离开其社会性情境(家庭、学校、社区、社会、文化、亚文化等)与社会性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人的自我发展是与其社会性发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是现实社会的“镜像自我”,[22]离开了社会性情境与关系,没有良好的社会接触能力,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性支持,将降低个体对自我认知、定位,对生活风险的防御能力降低,主观幸福感水平自然降低。
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社会性交往的亲密度和频率,尤其注重大学生同伴交往、师生交往、亲属交往等,使每个人形成自己的核心社会支持系统,在社会交往中收获信息、收获快乐,提高其生活问题与困难的应对能力,促进社会性发展,提高幸福感水平。
3.领悟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约25%。手机依赖既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又通过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这表明要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一是严格控制其手机依赖水平,科学合理使用手机;二是完善发展其社会性支持系统,提高社交技能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即既要堵又要疏,通过疏堵结合降低手机依赖,提高领悟社会支持,实现幸福感水平提高。同时,以往大量研究也表明,社会交往互动较多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社会化水平较低的个体。
正如乔治·赫伯特·米德所指出的那样,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发展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自我并非与生俱来,是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它们总是同时出现,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也不能向前发展。[22]人是社会性的人,社会关系是个体的生存空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一个人离开了社会支持(包括家人、朋友、同伴等)是很难很好地生活下去的,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生活的脆弱度提高,幸福感指数降低。
因此,要实现大学生社会性发展,收获更多的幸福需要我们注重搭建丰富的大学生社会性交往平台,营造良好的社会性交往氛围,尤其注重打造课堂无手机的文化氛围,倡导更多的利他行为,提高大学生情商水平,开展必要的大学生社会性发展认知干预等,使其习得更多的人际交往技能、角色承担技能等。
四、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一方面,本研究被试群体仅是青岛市某高校大学生,取样范围有限,样本结构合理性需进一步完善,同时其他群体中也有很多手机依赖者,值得以后开展更广泛的群体研究,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生态效度等。另一方面,领悟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仅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约25%),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影响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其他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尤其是手机依赖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的循环关系,即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导致了手机依赖水平高,手机依赖水平高导致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从而降低了主观幸福感;低幸福感又导致了更多的手机依赖,过多的手机依赖又强化了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低等,即手机依赖是否实质上反映了先前行为,又预示了未来行为,值得开展后续研究,并对高手机依赖学生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并探明干预效果,避免学生社会性发展的恶性循环,并最终为有效控制学生手机依赖水平提供可参考的教育路径与引导方向。
五、结论
1.在性别、专业变量上手机依赖总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大一学生得分最低。
2.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上,手机依赖高分组显著低于低分组,在主观幸福感消极情感因子上手机依赖高分组显著高于低分组。
3.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及其各因子均显著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4.手机依赖对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对主观幸福感消极情感因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5.领悟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既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又间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1]严标宾,郑雪.大学生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3):60-64.
[2]张灵,郑雪,严标宾,等.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2):116-121.
[3]姜永志,白晓丽.大学生手机互联网依赖对疏离感的影响: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5):540-542.
[4]黄海,余莉,郭诗卉.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大五人格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3,34(4):41-43.
[5]唐媛林.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相关因素元分析[D].武汉:武汉体育学院,2012.
[6]郭欢.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与成因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2014(34):208-209.
[7]熊婕,周宗奎,陈武,等.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的编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3):222-225.
[8]李志,谢朝晖.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4):83-88.
[9]连伟利.留守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10]Louis Leunginking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to Addiction and Improper Use of the Mobile Phone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2007,11-34.
[11]严标宾.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3.
[12]朱浚溢.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特征、来源与测量的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
[13]温仲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与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14]刘沛汝,姜永志,白晓丽.手机互联网依赖与心理和谐的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277-279.
[15]姜永志,白晓丽.大学生手机互联网依赖与孤独感的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4(1):41-47.
[16]刘红,王洪礼.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与孤独感[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1:66-67.
[17]郭少卿,陈军,张喜顺.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与人格因素的相关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4(15):67-69.
[18]王欢,黄海,吴和鸣.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3:447-448.
[19]邓兆杰,黄海,桂娅菲,等.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29)1:68-72.
[20]姜永志,白晓丽.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对手机互联网依赖的影:疏离感的中介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杂志,2014(5):45-51.
[21]刘世杰.大学生亲子依恋、分离-个体化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2.
[22][美]戴维·谢弗,陈会昌,等.社会性与人格发展(第五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乔健
张宇,青岛滨海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王月琴,青岛滨海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山东青岛266555)。
B844.2
A
1671-2277-(2015)06-0040-04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教育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3GG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