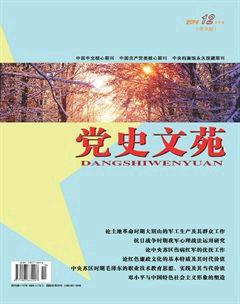浅析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
潘晨
[摘 要]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当中的最高峰。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了难以抚平的惨重损失,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中共自身的原因,这些都为事变的发生埋下了潜在的危机。
[关键词] 皖南事变 原因 新四军
1941年1月,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命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9000余人从云岭北移。6号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经过7昼夜的奋战,弹尽粮绝,除2000多人突围出去外,大部分都被俘或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也是我党建军历史上少有的可以用惨败来形容的事件。虽然事变之后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也难以抚平军事上的惨重损失所带来的伤痛。
一、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1940年前后的国际形势对于国民党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日本方面来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为加紧推进“南进”计划,转而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英国方面来说,1940年强硬派人物丘吉尔上台执政,为维护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利益,英国对外政策开始了由“绥靖”向强硬化转变的趋势。要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英国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产生矛盾。为了牵制日本“南进”,英国极力拉拢蒋介石,赞助中国抗战。美国方面来说,其在远东地区的摩擦也随着日本的“南进”越来越大,同样是为了维护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美国也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力度。对苏联来说,加大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力度,就能使中国战场吸引日本更多注意力,牵制其大量兵力,也就不至于使自己东西两面共同受敌。国际上的拉拢,使“蒋介石感到身价陡增,忘乎所以,好像历史给了他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难得机会”。这就坚定了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1]P100
(二)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敌后发展壮大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最直接原因
这个事变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为削弱共产党的势力而发动的。1937年国共西安谈判时,国民党就没有放弃过控制、改编、削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但都是事与愿违。自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组建工作展开后到1940年底,得到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并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这对于坚持华中抗战,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新四军的战斗力不断壮大,在华中地区的抗日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让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感到了恐惧和不安。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在“政治限共”的同时,加快了“军事限共”的步伐,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并在华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然而之后皖南新四军1940年秋季的成功反“扫荡”更加刺激了蒋介石,让蒋介石认识到了共产党在华中军事战斗力的强大,更是让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力量更加信任共产党。从此,蒋介石更加不安了,如何消灭共产党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心病。国民党内部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如果任由共产党势力发展下去,国民党就更加难以生存,其正统地位也就更加难以保全。通过后来的曹甸战役交平手的情况,蒋介石下定了最后决心在皖南发动事变,于是加快了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步伐。
总之,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是无法允许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反共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不可避免性。
二、当时共产党内部的危机、矛盾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的最终爆发,不可否认是由国民党反共所造成的,但是共产党内部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及新四军军部潜在的危机也为皖南事变的发生埋下了种子。
(一)新四军内部严重的家长制作风和小生产者的狭隘偏见
新四军军部存在着的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本身所固有的封建垢习和小生产者的狭隘偏见也是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之一。首先,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军部,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虽然新四军军部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既有集中,又有分工负责,而实际领导权却在项英一个人身上。[2]在新四军军部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封建家长制度。军部领导人中,只有项英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其他的领导人甚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项英因此在新四军军部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具有绝对领导权。其次,新四军内部的战士绝大部分是由当地农民群众组成的,尤其是皖南新四军,70%以上都是当地人。这些战士加入新四军队伍,也是由于保卫家乡的强烈愿望。因此,要他们离开皖南北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便皖南新四军各级干部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很多战士仍然不愿意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北移的时机。
(二)新四军正副职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新四军内部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皖南事变最终爆发有着一定的关联。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红军第二十八军和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从两人自身的条件来说项叶的搭档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然而却因各种原因导致两人之间出现分歧,以至于二人结合的长处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叶挺虽然身为军长,却并非共产党员。而党内历来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这就决定了项英这个中共的老党员,作为副军长的实际职权和地位却高于叶挺这个军长。在军队建设上项英主张“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扩充兵马,壮大队伍。项英认为应当驻守皖南,向南发展,而叶挺却坚持东进北上。1939年中旬,叶挺由广州抵达重庆时见到了周恩来的时候就吐露了自己因为不是共产党员而工作起来十分困难的苦恼。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将会妥善解决这一矛盾并也多次调和二人的关系,但也未出现实质性的转机。后来在确定新四军北移路线时两人又出现分歧,最终采取了项英的南进路线,也正是这条路线给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新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四军的决策效率,无疑也是导致皖南事变及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endprint
(三)党中央对形势的认识不清
共产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地方服从中央,这就决定了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预测,也必然会影响到新四军对时局的分析和判断,进而影响到新四军的方针和政策。[3]黄桥战役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估计转向悲观,对黑暗局面的估计过于严重,担心蒋介石有投降之心,并开始针对时局拟定应对方案。其实蒋介石并未有做亡国奴的意思,在大敌当前的情形下他也是不希望国共彻底决裂的。虽说对黑暗时局的过头估计会提高新四军的警惕性,有利于反顽斗争,但是,对决裂过于肯定会阻碍到新四军正确分析国民党内部势力的左中右,影响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运用,导致了新四军内部对统一战线的运用一时出现了不当的认识。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时局的估计却是又转向了太过于乐观的另一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决心估计不足。新四军的北移既是党的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要求。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过于乐观,以新四军的北移为筹码和国民党讨价还价。这些暂缓的指示给了项英政策上的支持,最终导致新四军北移超出了国民党给出的期限,不仅在政治上让新四军处于被动地位,给了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借口,同时也给国民党调兵伺机铲除新四军更为宽裕的准备时间。[4]
(四)中共北移的时间和路线选择不对
1.北移时机不合适。早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时候,何应钦、白崇禧就在给朱彭叶的《晧电》中要求我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转移到旧黄河以北。[3]为了缓和国共矛盾,使蒋介石没有发动反动政变的借口,中共决定在皖南方面让步,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转移到江北。虽然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根据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曾经多次提出新四军向北转移的要求。但多次都是由于种种原因只强调困难没有看到机遇以至于错过了北移的最佳时机。皖南新四军这边在1940年11月22日给毛泽东、朱德的电文中列出四点理由声称新四军短期内无法转移,即:部队开动需要时间,北移的交通安排需要时间,非战斗人员转移有困难,北移不具地利人和。“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5]P68新四军军部不知道坚持发展皖南的战略已不合时宜,犹疑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北移。如果新四军能够果断北移,而不是幻想着坚守皖南,甚至是妄图向南发展,那么顽固派将没有时间调兵遣将,完成包围圈,从而找到借口去发动皖南事变。
2.北移路线选择有误。新四军从皖南向江北转移,原本有两条路线选择,一条是“国民党三战区同意的云岭至马头镇至南渡镇再到竹赞桥,经苏南,撤往江北”。[6]P392另一条路线,由新四军驻地,经铜陵、繁昌间渡江,到达江北无为地区。第一条路线本是北移的最佳路线,但何应钦为防止新四军南渡后加入苏北新四军共同对付韩德勤,早在1940年12月3日就亲自下手谕不准走这条路线,江北的李品先部为做好阻击我军由铜陵繁昌过江的准备早于12月下旬就已增兵扼守长江北岸。国民党又通过种种渠道向日军透露我军将从铜、繁过江,日军闻讯也在这段江面上增加了许多舰艇。走这条路线也很困难了。[7]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转移过程中采取了第三条路线,即从驻地向南行进,到茂林转头向东,经榔桥到宁国附近,再砖头向北,进人苏南。[6]P400当时新四军选择这条行军路线主要基于皖南新四军有着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可以避开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一O八师。但现在就目前大部分学者来看,选择此条北移路线是不明智的。第一,国民党已明令禁止新四军经苏南渡江,即使新四军采用第三条作战路线,但大方向仍是经苏南过江。这给国民党污蔑新四军“不遵军令”以口实,政治上不利。第二,既然定苏南过江,已是“违令”,何不索性就走新四军先遣部队走过的路线呢?第三,新四军最后走的这条路线山势陡,坑谷多,道路少,陇路多。而行军部队又是9000多人的大部队,加上行军期间雨水连绵,增加了行军的困难,使得行军战士疲惫不堪。最后,经铜陵,繁昌过江虽然障碍重重,但是行军距离最近,并且这一带的长江南岸是我军三支活动地区,北岸则是我军江北纵队的活动区域,选择这条路线并不一定比南下绕道再由苏南过江的风险更大。其实无论走哪条路线,新四军都得冒着被国民党顽固派围追堵截的风险,然而走茂林绕道路线却并不是三条路线中相对保险的一条,这就加大了遭受损失的几率。
皖南事变过去已经70余年,这次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爆发的规模最大的直接性的武装冲突。这次事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使得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其背后发展壮大,但是,共产党内部也应当为皖南事变的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皖南事变,尽管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后人对此会做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但其中的是非恩怨业已牢牢地织进了历史天幕的经纬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参考文献: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冯时,金飞.试论述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因[J].北方文学2011(7).
[3]靳东明.皖南事变严重损失的原因分析[D].2010(5).
[4]张智.项叶关系与皖南事变[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10).
[5]皖南事变[J].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6]段雨生,赵酬,李杞华.叶挺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7]章玉丽.关于皖南事变几个问题的探讨[J].世纪桥,2007(11).
责任编辑 吴自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