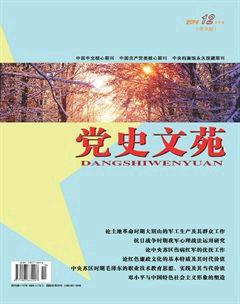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心理战法运用研究
李宏宇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军政治工作全面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瓦解敌军工作被确立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相关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心理战思想,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心理战战法也从中显现出来。主要战法有: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对敌实施政治感召;从情感影响入手,软化弱化日军敌对意识;实行优待俘虏政策,利用俘虏反制敌歪曲宣传;抓住伪军两面性的矛盾心理,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心理战 战法
抗日战争,是我军首次对入侵我国的外国军队作战,并且是对武器装备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战。面对强敌,我军在军事上抗击日军的同时,还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军事文化中“攻心为上”的战争艺术,利用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心理上、政治上瓦解敌军,开启了我军对外国军队实施政治作战的新篇章,积累并创造了心理作战的丰富经验。虽然在当时我军还没有使用心理战这一概念,其理论和实践与今天的心理战也有所区别,但它蕴含的心理战思想以及在战争实践中创新的心理战战法,对现代信息化条件下心理战的应用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对敌实施政治感召
日军为粉饰美化其侵略行径,大力鼓吹“中日友好,中日提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致使日军基层官兵把侵略战争误认为是“从中国政府的压迫和共产党的赤化下解救中国人民”的“圣战”,绝大多数日本士兵至死都不知战争的反动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依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及相关国际法的原则,在法理和道义上与敌展开斗争。一方面通过援引相关法规向日军官兵讲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失道寡助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全世界反战人士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此举取得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日本共产党著名领袖片日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反战大会上严正指责侵略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掠夺中国的东北,进攻热河和上海,杀人放火……”使日本法西斯在国际社会受到强烈的谴责,揭掉了覆盖其上的“圣战”外衣。
针对日军大多数士兵和基层军官都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家庭,是受欺骗、胁迫才走上侵华道路的特点,我军认真分析日军官兵的成分构成,深入揭露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日军官兵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敌实施政治感召。抗战初期,我军挺进华北不久,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分别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指出日本士兵是日本的工人、农民,是日本资本家、地主、财阀剥削、欺压的对象,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八路军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决不会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以优待,愿意回国的,就送他回去,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的,就给他事做。1938年3月24日、4月9日、5月28日,八路军总部又接连印发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反战口号》《日本反侵略女战士池田幸子献给日本士兵的公开信》《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呼诉于我祖国(日本)同胞》等传单,通过日本反战人士和士兵之口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和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指明了日本军阀才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还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及中国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军宣传的内容,不断增强政治感召的针对性。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日军内部厌战、反战情绪明显增长,士兵逃跑、自杀和向我投诚的现象不断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不失时机地把开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规定为坚持敌后斗争的三大任务之一,号召全军“再接再厉地用大力来继续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以“促进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战胜日本法西斯三个条件尚未成熟的最后一个条件——日本国内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军队的瓦解”[1]P123—124。
二、从情感影响入手,软化弱化日军敌对意识
日本在策划与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的同时,对它的基层官兵进行了广泛的洗脑。通过大肆渲染中国旧社会的积习弊病,在日军官兵心目中形成了中国人愚昧落后、野蛮残忍的刻板印象,造成日军对我的轻蔑观念,加深民族偏见和仇恨。正如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大谷正在《我的转变》中所说:“我因曾受过长期欺骗教育,对中国的确抱着无可隐忍的仇恨和敌意。”[1]P284因此,我军希望通过在日军内部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遏制其侵略行为,或通过宣扬武力直接对敌人进行心理威慑的做法都很难成功。1939年10月2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敌伪军工作的训令》中指出:“根据日军的现状,我们对敌工作方针与直接目的不应过高。如与日军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堡垒,希望日军大批哗变与大批投入华军等等,这是我们的远大目的,但在今天尚不可能,尚不是实际,须经过种种阶段才能达到。”因此,“今天对敌军的工作方针应当是用各种方法削弱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使日军士兵对中国军民,不作盲目的仇视,从感情上的接受逐渐引导到政治的接近。”[2]P173
通过不动声色的柔性宣传打通敌军情感通道,引起共鸣,从而瓦解日军官兵的心理防线。八路军废止了一些令日军反感的诸如“踏平三岛”“杀尽东洋鬼”“打倒天皇”“打到东京去”等口号,提出迎合日军官兵情绪,贴近基层官兵情感需要的宣传内容。我军根据日本人喜爱樱花的文化传统,在樱花节时给日军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战斗意志大大消退。在对日军进行攻心宣传的同时,我军还制作了大量的樱花慰问袋。慰问袋里除了装有传单、书信、日本工厂学校的招生广告、通行证外,还有诗歌、棋子、扑克等娱乐工具,以及当地特产的核桃、枣、柿饼、栗子等,尽可能地适应日军士兵的需要。针对日军在传统节日思乡厌战情绪极易增长的情况,如在桃花节、端午节、盂兰盆节等对于日本人非常重要的节日,我军都会给日军送去“礼物”,诉说他们的妻子儿女无人照料,年迈体衰的父母盼儿早归,家中祖坟的早已无人打扫,痛斥法西斯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努力将有良知的日军官兵拉到与我军同一立场上,无形中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力量。
日军死亡时,我军还组织人员将敌人尸体及时送还到日军据点,无法送还的尸体则就地装殓掩埋,并在埋葬处插上墓标,书写碑文。墓标上注明死者的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埋葬年月日,并用日语写上哀伤的悼文,诱发敌人的厌战情绪,如“停止战争回去吧”,“请告诉地下战友的家属,八路军郑重地埋葬了他”等,根据被俘日军反映,这种方法最能使日军感动。[3]P182
三、实行优待俘虏政策,利用俘虏反制敌歪曲宣传
日军推崇武士道精神,诱使官兵“至死不降”。日军高层捏造事实,诬蔑“支那人”野蛮,抓到战俘即砍下脑袋,恐吓士兵被砍头后便不能轮回转生、无法再次投胎为人,造成日军官兵对被俘的恐惧心理。因此,日军官兵即使战败受伤,也不缴枪投降,绝望之际,宁肯自杀也不愿被俘。
为戳穿日军的诬蔑与阴谋,我军在抗战之初就实行了优待俘虏政策,在抓住日军战俘后,稍加教育后即行释放。1937年9月25日,我军发表《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通告日军“我们决不虐杀一个没有武装或解除武装的日本士兵”。在后续的作战实践中我军又认识到,只优待士兵而不优待官长,不利于瓦解敌军。又修正为“敌军一经解除武装,不论官兵,不许杀害,不许侮辱,除武器军用品外,私人东西不许收缴”。为了使官兵自觉执行党关于优待俘虏和保障战俘基本权利的政策,我军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我军对日军俘虏的政策。1941年5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还专节论述了我党的俘虏政策,使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
1940年4月6日和7日,中央书记处、八路军总政治部分别发出了《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强调提出了对日军俘虏进行教育以及争取日俘为我军服务的问题。我军开始考虑选择一些“觉悟有为”的战俘,加以教育引导,指导他们在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参加我们的对敌工作。例如,新四军第五师敌工训练班的日本战俘,在教学员学习日语的同时,还担负着对敌宣传任务。他们常常是白天教完功课,夜晚又随武装部队出发,到敌人据点附近,截听敌军电话,获取敌人情报,并亲手将一张张传单散发或张贴在日军据点周围。他们还常常与武工队的同志一起,化装成日军,袭击日伪军、铲除汉奸政权。他们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总政治部在1944年做出这样的规定:“凡有日人干部,而这些日人干部政治上又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敌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4]P87我军对日俘优待有加,使他们逐渐被感化,政治立场也慢慢发生了转变。由过去对中国人民的敌视转变为对日本法西斯的痛恨,由狭隘傲慢的民族自尊转变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同情。
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曾怀疑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严恪的纪律下未必有效。他举例说,俘虏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掉,所以日军官兵还是不敢投降。但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情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5]P381事实证明,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很快就收到了成效。敌军指挥官在内部会议上表示,“最近共产军企图瓦解皇军,实施各种的反战宣传,特别是优待俘虏,在听取皇军机密事项后,放还归队,并利用俘虏的宣传以影响皇军,实为皇军之大患”。优待俘虏政策是我军抗战时期的一项创举,它使日本法西斯感到恐慌,感到“中共对日军的思想工作”是对日军的一场“无形战争”,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值得一书的业绩。[6]P586
四、抓住伪军两面性的矛盾心理,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伪军是抗战时期敌军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多数来自社会的底层,他们生活贫困,没有受过教育,为了生存容易被日军的小恩小惠诱惑。既有亲日、为日军所用的一面,又有与日军存在民族隔阂与成见、猜忌与矛盾的一面。根据伪军两面性的特点,我军亦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一面,实行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一面,实行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对于暂时无法拉拢争取的,采取各种形式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和组织,积蓄力量,待机而举。
1943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中,曾精辟地论述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问题,他指出:“革命两面政策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着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7]P93他强调,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而应付敌人的一面,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这是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与一般两面派的两面性根本区别之所在。这种革命的两面政策,为我军开辟对敌斗争的新战场,创造对敌斗争的新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锐利的武器。
在执行革命两面政策的过程中,我军发挥聪明才智,创新性地运用了很多有效的方法。例如:登记红黑点(暗中抗日,不害民众的打红点,作恶的打黑点);制定善恶录(纪录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善恶行为,提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开展死心汉奸检举运动(对死心的汉奸、特务及对抗日危害极大而为群众最痛恨的分子等坚决予以镇压,对协从分子给以警告,并给以回头的机会);良心大检查(“学岳飞,不学吴三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亡国丧家是人生之奇耻大辱”等);颁发伪军伪组织人员回心抗日证(不打抗日军队和人员,设法营救我被捕人员,不压迫百姓,设法逃跑不当汉奸等);签订伪军家属协议书(规劝其子弟不做汉奸,不干坏事,回头抗日等)。另一方面,积极为反正伪军谋出路。为争取大股伪军反正,我军采取了不缴枪、不编散、不歧视的政策,为伪军走上反正之路解除了后顾之忧。根据军事科学院抗战史编写组提供的统计数字,到1945年5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俘虏伪军316378人,伪军反正114597人。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军心理战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期间,我军心理战的手段灵活多样,战法创新层出不穷,相关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抗战期间我军积累的丰富心理战实践经验和闪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智慧,为我军现代心理战理论的研究和心理战建设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战例支撑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7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2]华北治安战(上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9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