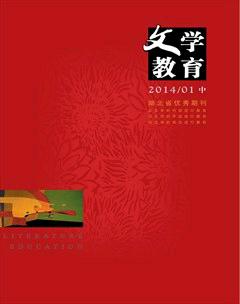《新夏娃的激情》的后女性主义阐释
[摘 要] 安吉拉·卡特从后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审视女性的现实地位,并在《新夏娃的激情》中成功地刻画出以新夏娃为代表的一群具有“双性同体”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融合了两性特质的角色展现了卡特强烈的后女性主义意识。本文从特里斯特萨、母亲、伊芙琳三个角色出发,对安吉拉·卡特的后女性主义“双性同体”观进行解读。
[关键词] 后女性主义;双性同体;新夏娃
安吉拉·卡特是英国二十世纪最具独创性的女性作家之一,其作品一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的现实地位,她以奇妙的想象力将经典神话角色加以重塑,同时让幻想世界与现实相扣。卡特的作品深受媒体喜爱,《与狼为伴》和《魔幻玩具铺》曾被拍成电影,《马戏团之夜》和《聪慧子女》曾被改编成舞台剧于伦敦上演,2006年更被誉为 “安吉拉·卡特之年”,在英伦掀起卡特热潮。李维屏等(2011)认为“她的作品具有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其中揉进了哥特主题、后现代折中主义思想、暴力和情爱等成分,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将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方式。”[1]尤其在《新夏娃的激情》中,卡特以新夏娃的诞生和逃亡为关注点,辅以新夏娃心中的“女神”——特里斯特萨的男性身份事实,展现对性别文化的批判和反讽。卡特通过对“双性同体”的特里斯特萨、母亲和伊夫林(芙琳)三个角色的成功塑造,揭示了作品的后女性主义深层内涵:只有消解女性身体神话,消解男性中心意识,消除男女性别间的二元对立,才能实现两性完美的融合。
一、“双性同体”观
“双性同体”思想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如此阐述:最初的人类分为三种。他们的母亲分别是太阳、大地和具有两种性别的月亮。宙斯为削弱人类的力量,把人全都劈成了两半,所以,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求与自己结合的另一半。柏拉图的理论常常被人们概括为“双性同体”,指男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以及女性与女性之间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原初状态。最先将“双性同体”思想引入文学评论领域的是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2]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引起了安吉拉·卡特的强烈共鸣和进一步思考。她在《新夏娃的激情》中有意识地融入了“双性同体”的创作意识,展现了同一肉身下不同的性别元素的完美糅合,通过男性肉身女性灵魂的特里斯特萨与女性肉身男性灵魂的伊芙琳的最终结合,再现了这种双性并存的理想境界。
二、特里斯特萨
《新夏娃的激情》是一部典型的回顾式流浪汉小说。讲述了身为伦敦大学教授的小说主体“我”从伦敦到纽约再到加利福利亚沙漠的完整经历。在整部小说推进进程中,以美国女演员身份出场的特里斯特萨一直是叙事主体“我”心中的女神,“她”集所有女性美于一身,对“我”具有迷幻般的吸引力。无论现实中的“我”与不知名的女性在伦敦的电影院里欣赏影片,还是与脱衣舞娘雷拉在纽约的暗夜里缠绵,都从未能消减“我”对特里斯特萨的迷恋。
在卡特笔下,雷拉是传统女性的代表,是现实生活中女性地位的真实展现,而特里斯特萨则是理想世界中的完美女性。无论雷拉的外表还是精神都是按照服从男性中心意识的标准来塑造的,雷拉的自我完全被“我”的欲望所遮蔽。小说中“我”抛弃流产大出血的雷拉的情节设计,实质是女性远离男性霸权中心的开始,是卡特所主张的“双性同体”模式建立的基础,也是两性间超二元对立模式建构的基础。
摆脱了雷拉的“我”历尽艰难到达加利福利亚沙漠深处特里斯特莎的水晶宫。在“女神”隐居的神奇住所,“我”发现“女神”竟然有着男性肉身。这一发现让“我”在震惊之余顿悟:“这就是他一直能做男人心中完美女人的原因!他让自己成为自身欲望的圣坛,成为他唯一会爱上的女人!……世界上哪个女人能像她这样堪称真正的完美女人呢?”[3]至此,卡特借助“我”之口,表达出她心中的理想女性应该是如特里斯特莎一般,糅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并将它们完美且平衡地进行展现的人。特里斯特莎自愿选择以女性外表示人,象征男性自愿选择脱离男性中心地位,象征作者对后女性主义“去中心”理想的追求。
三、母亲
母亲是小说中后女性主义色彩最重的“双性同体”类型,它不同于雌雄同体的特里斯特莎,也不同于雄雌同体的伊夫林,她是女性与女性同体的代表。无论是母亲的名字还是沙漠中母亲执掌地的构造,都充溢着强烈的母系社会色彩。在这个形似子宫的女性乌托邦里,母亲是一切权力的象征。借助母亲,小说形象地描绘了母亲式女性们的女性中心意识,她们是单性的,却选择意为“有夫之妇”(Beulah)的地方居住,她们是妻子也是丈夫,她们不依附男性,她们颠覆了人类固有的由两性共同繁衍后代的传统,在这块土地上,两性间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对立面而被动存在,她们渴望建立只有女性话语权的完美女性世界。
卡特在对女性霸权的暴力和血腥的描述中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单一女性世界存在的不可能。尽管母亲“ 一手托着太阳,一手握着月亮,双肩抖落无数的星星,一个哈欠便会带来地震。”[3]尽管母亲强大到能重建“我”的性别,在小说的最后,母亲依然在建立新秩序的无望中发了疯,而象征传统女性的雷拉却带着男性文化的印记进入了这片女性圣地。母亲从出场到疯掉的全过程,充满了作者后女性主义色彩的思考:世界是多元的,单性(单纯的女性或单纯的男性)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无论是男性霸权还是女性霸权都注定逃不脱被消解的命运。
四、伊夫林(芙琳)
叙述主体“我”——伊夫林是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在到达加利福亚沙漠之前,他是典型的父权文化符码,大学教授的身份使他的男性中心意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伦敦更具有代表性。在伊夫林的眼中,女人的生活就应该是“孤独和苦难”[3],他理所当然地在影院里享受不知名少女带给他的快乐,而后毫无眷念地离开她前往巴黎;他肆意玩弄雷拉的身体和感情,而后在她濒临死亡时绝情离去。伊夫林对女性一贯的虐待和歧视充分显示了男性霸权的社会现实。
卡特在小说中明确地向这种意识宣战:伊夫林进入沙漠后,不幸落入母亲的手中。他在母亲的手术刀下变成女性,成为“新夏娃” 伊芙琳。父权视角下的“新夏娃”的命运与雷拉并无二致,她遭到了妻妾成群的零(Zero)的残忍强暴,终于切身体会到雷拉曾经饱受的肉体折磨。代表男性霸权的零继续凌辱 “新夏娃”,他强行命令她与特里斯特萨结合。这种貌似不可能的结合形式在卡特的笔下得以呈现。两个“双性同体”的生命组成家庭后,他们亲手摧毁了零的独立王国。“新夏娃”欣喜地看到:“他和我,他和她,是沙漠中唯一的绿洲……我们实现了伟大的柏拉图式的‘双性同体”。[3]
随着“新夏娃”的诞生,传统的女性身体神话被无情打破,两性间的关系被重新建构。在“新夏娃”的女性身体里,伊芙琳的男性意识逐渐由强变弱,肉体与精神的矛盾逐渐消失,最终达到了灵与肉的高度统一。在真正接受自己的新身份后,“新夏娃”与一直倾慕的“女神”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他们的结合模式中,男女的角色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卡特正是通过这种颠覆传统的婚姻模式,将后女性主义者的“去中心”立场和倡导“多元思维模式”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
参考文献:
[1]李维屏、宋建福.英国女性小说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2]张昕.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12期.
[3]Carter,Angela.The Passion of New Eve [M].London:Virago Press Ltd.,1982.
[4]鲍晚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5]庄渝霞.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交锋[J].江西社会科学, 2002年7期。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医学研究中心2012年科研项目(12JD108)。
作者简介:宋海蟾(1971—),女,汉族,四川乐山人,硕士,贵州遵义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后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