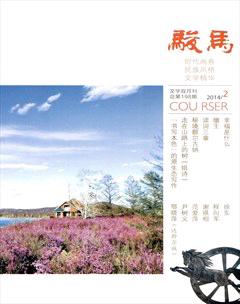墩王
程向军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吉文中学副校长。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见于《骏马》《实践》《鄂伦春》《呼伦贝尔日报》等报刊,作品曾获第八届呼伦贝尔市文学艺术创作政府奖(骏马奖)。
“下车——还等八抬大轿抬你啊!”
一个洪钟般的声音震得我两耳发胀,我赶紧连滚带爬地跳下车,莫名地等着什么。
初中毕业后办了知青手续,我就无奈地待起业来。我的几个朋友先后走进大山里的某个工队成了伐木工人,现在轮到我了。母亲把拆洗一新的棉被和换洗的衣裤放进车里,眼泪打着转说:“孩子,你该长大了。”
汽车在山沟沟里穿行。我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干脆把被子铺在车上躺下来。天是格外的蓝,几朵白云丝丝缕缕地在天空缠绕着,我的心也白云般浮动着不踏实。
“进来吧。”那声音再一次响起。
周围的群山如黑色的巨人般矗立着,稀疏的树木悄悄地站立在眼前。一个黑黢黢的帐篷就像一个久病的老人在夜色中喘息着。我用力掀起厚厚的棉布门帘,一个红彤彤的大铁炉子直刺我的眼,炉子里大块的木材吐着红色的火焰,一股股热气就扑面而来。在热气中,我隐约看到有几个人躺在临时搭建的铺上看着我。
帐篷里静极了,一点声息也没有。
我扛着行李愣愣地站在帐篷里,紧张地等待着。
“去割点蒿草来。”一个声音低低地传来。
我吓了一跳,目光搜寻着这声音的来源。小小的帐篷在炉火中闪烁着,几个人影也就闪烁起来,难道声音是从地狱里发出的?一切都觉得怪怪的。
“又多张吃饭的嘴。”黑暗里传来一声叹息。
“去割点蒿草来。”那声音再一次响起。
“走吧,跟我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养活这些张嘴呢,又来了一个吃货!”队长一边嘟囔着,一边拉着我的手向外走,顺手拿起一把镰刀。
月亮升起来了,月光就在雪地上舞蹈,近处的树木投下斑驳的树影,月光追随着一条河流而来,一条蜿蜒的长龙隐约闪耀在朦胧的树影间。
“跟上!”队长的语气让我无法抗拒。
我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那长龙走去,雪钻进鞋子里,雪水冰冻着肌肤,刀割一般。队长如履平地,大声喊着:“跟上——跟上——”
月光笼过来,一片雾气就弥漫开,蒿草的叶子温柔地低垂着,让我想起前桌的女孩,她的一双大眼睛和低低垂着的睫毛。她似乎是我上学的全部动力。队长挥动镰刀“刷刷”割起来,他弯下腰,左腿在前,右腿在后,一手抓住蒿草,一手甩开镰刀,一会儿工夫就割了一大捆。“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扎捆。”
“没有绳子啊。”我低声说。
队长二话没说,抓起一大把蒿草一分为二,两手一拧,就成了一根绳子。一堆蒿草马上就扎成了捆,立在冰面上就像威武的哨兵。
我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去割点蒿草来”这句话,那么沉稳,好像从地里挤出来,有着无穷的魔力,让劳累了一天的队长冲出了帐篷。
帐篷里的炉火已经暗下去了,铁炉子还闪烁着红光。队长三下五除二把地铺打好,把我的行李往上一扔说:“睡吧!”
我连忙躺下来,每一块肌肉都松散开。星光从棚隙间溜进来,我心想:妈妈在做什么?她睡了么,一定像我一样无眠吧!帐篷外“哗啦”一声,像风吹动了枯叶,又像傻里傻气的狍子跑过来,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到这儿了,啥也别想,睡吧。”那声音再一次响起。
我心头突然一紧,整个身子都在收缩,浑身哆嗦着,似乎要入睡了。这声音魔咒一般!
天亮时,我终于找到了那神秘声音的主人。那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不,只能说是半截人:方脸、阔口、大眼睛、高额头、宽肩膀,整个身子坐在一个红柳筐里;一双腿不翼而飞,代替它的是两只强壮的臂膀;手上戴着大大的棉手套;他就这样在我们的视线里走来走去,身子一起一伏的。我突然感到孩童的天真正被撕得粉碎,仿佛看到振翅欲飞的鸟儿被折毁了翅膀。继而,我心生感动了。这样一个处处需要别人照顾的人却不忘告诉我去割些蒿草。我突然觉得眼眶里湿湿的,不是为理想的破灭,而是母亲送我时的那句话——孩子你该长大了。
我内心的不安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早餐开始了。一张塑料布就是饭桌,上面有一盆馒头、一盆卜留克咸菜、一盆粥。十几个男人围坐在一起,手也不洗,抓过几个馒头,抄起一个碗在粥盆里一舀,再抓起一块卜留克咸菜大口吃起来。空气里弥散着奇怪的味道——臭脚丫子味儿混杂着面香、米香。
我居然没有呕吐的感觉,觉得这是我待业以来吃得最舒心、最踏实的饭了。
山里人的肚子是无底洞。很快,馒头吃完了。
“这日子,饭都吃不饱,哪有劲啊!”有人怨愤道。
“干活的该累死,吃白食的活千年啊!”又有人说。
“半截人”猛地站起来,目光如炉火般炙热。
“怎么,不是么?”那人接着说。
“半截人”一起一伏地走了过去,突然伸出双手,抓住那人的下半身,身子一扭,用力一抛,那人就如“蹿天猴”般蹿了出去。
“我操你祖宗,有本事你去采伐。”那人在帐篷外叫骂着。我张大了嘴,内心除了不安就是惊愕了。
我被分到了套子组,师傅是套子刘,四十多岁,大个子,大手大脚,大身板,是个爽快人,很快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我将心中的疑虑和盘托出,套子刘说:“你说墩王啊——”然后就“唉”了一声,没有话了。春天的阳光在林子里涂抹着大块的晶亮。我和套子刘东一根、西一根地把伐好的木材绑在爬犁上,走了好久山路才来到集材点,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中午,大家是不回帐篷的,寻一块空地,把随身带来的饭盒吊在树枝上,下面生起火来,饭盒里放些冰,煮沸,放进挂面,再放些盐,热腾腾的面条就做好了。我们就又说到了墩王。
“墩王,是这一带有名的吊墩王。”队里的一个人见我愣愣的就解释说,“十几年前,兴安岭上火着呢,大工队一个接着一个,每个工队都有上百人,几十个大小伙子有使不完的劲,一有闲暇就进行吊树墩比赛。”那人吃了几口面条又接着说。“吊树墩就是两个人站好,将卡钩挂住树墩,同时发力,谁被压倒谁就失败。败的要低头叫师傅,胜的扬眉吐气。”
“那场面热闹得就像古代的打擂台。”套子刘憋不住兴奋说。
“你见过古代打擂台?”那人瞥了套子刘一眼接着说,“墩王号称大兴安岭第一条好汉,只见他蹲下身子,双腿站成马步,背微躬,一手拿钩,一手扶杠,单等裁判一声号令,腿一撑、背一挺,对方应声倒地。那阵势就像项羽拿鼎。”
“更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套子刘猛插一句。
套子刘一下来了兴致说:“墩王在树墩旁一站,那叫一个霸气。他人高马大、气宇轩昂,方脸、阔嘴、宽肩膀,大喊一声:‘啊——简直就是戏里的武生。”
“你真是个戏迷啊!”有人拍了一下套子刘。
套子刘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摇了摇头,继续说:“墩王虽力大无比,但从不和自己队里的人比,只要是外工队的,来者不拒。有一次,刚吃过饭,大家躺在帐篷里休息,一辆大板车‘嘀——嘀——叫着来到咱队里。车一停,刷刷,跳下几十个大小伙子,大声叫道:‘听说这里有个墩王,谁给封的号啊?今天我就要给他改改名号,不服,出来试试!墩王一下子从铺上跳下来,几步窜到帐篷外,大声喊道:‘谁在叫号,东山的黑熊,西山的虎,行不行出来遛遛。大家一下子涌了过来。”
“太阳刚要下山,把一片霞光泄在山坳里,雪地上温暖起来,一个巨大的树墩静静地享受着一天里的最后暖阳。墩王高傲地站在树墩旁,晚霞把他涂抹得一片金黄,对面走来一个壮小伙,这小伙长得那叫一个壮——个头不高,虎背熊腰,身子粗得像口缸,大腿有你的腰粗。”套子刘看了我一眼。
“快说、快说!”我催促道。
“这人一看就是典型的车轴汉子,‘咣一声,裁判把一副卡钩和抬杠扔到两人面前。他们一起弯腰,墩王右手拿杠、上肩一气呵成,那人左手拿杠、上肩麻溜利索。裁判走过来,将卡钩绳抠了抠认真地移到抬杠中间,卡钩牢牢地勾住树墩。两个人都弯下了腰,腿似弓、腰似箭,单等号令一发就如离弦之箭直射蓝天。人们瞪大眼睛屏住呼吸,身体微前倾,张大了嘴巴,周围车轮粗的大树也静默着,几只鸟争抢着温暖的树枝,叽叽喳喳地叫着。‘开始——裁判猛喝一声。两人迅速发力,卡钩绳立刻拉直。他们眼睛瞪着,嘴巴大张着,双腿拼命地向上蹬。腰拔得直直的,绑绳被拉得‘咯吱、咯吱响。突然,墩王大喊一声:‘啊——这是困兽之斗,更是王者之争。渐渐地两人的腿开始发抖,圆张的嘴咬得紧紧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整个身子都在抖,卡钩深深地嵌入树墩里,树墩纹丝不动。”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套子刘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喊道。
“咱大兴安岭的红松抓住的是整座大山,鲁智深也没法子。”有人打趣道。
“突然‘叭的一声,来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人们欢呼起来。第一局,墩王胜!第二局,换肩再战。”套子刘说。
“换肩?”我诧异起来。
“这你不懂了吧!”套子刘昂起头,“抬杠是有讲究的:杠放右肩,左手抠杠为大肩;杠放左肩,右手抠杠为小肩。抬杠人大小肩必有一强一弱,所以要换肩再战。两人重新拉开架势,裁判一声号令,比赛重新开始。这一次,两人真叫势均力敌,绑绳拉得‘吱吱响,两人抖得如筛糠,‘啪——一声脆响,抬杠当中断开。‘我服了!来人大喊一声。大板车拉着几十人‘咣当——咣当——走了。现在——墩王啊,唉——”墩王的故事在套子刘的一声叹息中结束了。
我对墩王心生敬畏了。每当回到帐篷看见墩王双手撑地,半截身子时起时落地艰难行进时又心生怜悯了,我有意无意地和墩王接触,我发现我们之间似乎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信任与同情,又有着难解的疑问。
“你会读书么?”墩王问我。
“会一点儿。”我点点头。
初中三年,我没学什么知识,看得最多的是小说,什么《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书早已看了不知几十遍。
墩王突然显出极大的兴趣来,高兴地说:“太好了!”整个身子突然从地铺上跃了起来,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量,他那一双手也许会得个什么王,可惜没有比赛,我脑子里跳出了古怪的念头。
“帮我读读。”墩王从铺下拿出一本书兴奋地说。
我一看书名——《黑木耳栽培技术》,心里顿时失望了。我何尝不想有一本好看的书啊,可这样的书万万引不起我的兴趣,就连忙说:“该吃饭了。”急忙跑了出去。
吃过饭,我刚躺在铺上,墩王就笑呵呵地凑了过来,说:“来,帮我读一读。”我耐着性子读道:“黑木耳一级菌种栽培技术……”读着读着就进入了梦乡。蒙眬中,墩王正在比赛,人山人海,大兴安岭从没这么热闹,这一次不是比抬树墩,而是比打枝桠。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墩王灵巧得像一只猴子穿行于树杈间,双臂上下翻飞,手起枝落,继而飞起,堆在一处。另一选手挥动斧头,斧头雪亮、飞快,带着阵阵寒光上下翻飞,桠枝雪片般飘落。我猛一抬头,墩王正笑呵呵地看着我呢。
“好——”人群欢呼起来。
我一下子惊醒,墩王还坐在我的身边,聚精会神地看着那本书。我说:“刚才梦见你比赛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墩王笑了笑,赶紧拿着书凑过来说,“这几个字怎么读?”我这才发现墩王手里拿着一本翻烂的《新华字典》,就连忙读道:“将成熟的黑木耳摘下,洗净,放置在无菌的容器里,黑木耳表面长出一层白霜来,将白霜收集起来,制成一级菌种……”
队长突然闯进来,大声喊道:“马上收拾东西,拆帐篷,搬家。”
“又搬家啊?”大家嘟囔着。
“少废话。不搬家,饿死啊?”队长大声说,转过身来对墩王说,“你别着急,你的东西让他们帮你收拾。”
我心里很诧异,队长对我们总是呼来喝去的,每次和墩王说话却总是和风细雨,墩王还不干活,吃白饭。
一辆大板车开过来,拉着我们在大兴安岭颠簸。几场春雨把多年失修的简易路泡成了“水泥路”。大板车在泥水中颠簸着,蓝天也就在视线里晃动起来。我们躺在敞篷车上,谁也不想说话。
“总他妈搬家!”套子刘打破了沉默。
“也不知道新采伐点怎样?”一位工友好似自言自语。
“为什么总搬家?”我忍不住问。
“唉,现在的伐区大都是老伐区,每隔一两年就采伐一次。找新伐区就像找宝藏,一个伐区干不了几天,采完了就得换。”套子刘总是快人快语。
大家都沉默了。
突然,大板车山崩般滑出去十几米,在“水泥路”上玩起了“漂移”。我吓得体如筛糠,生怕自己漂出去。套子刘笑得肚子疼,这上水下冰的路,哪有不漂移的。
我突然想到了墩王,他在驾驶室里,我不由问道:“队长好像怕墩王?”
“唉,咱队长重情义啊!”
大家谁也不再说话。
临近傍晚时,我们到了新采伐点。一样稀疏的树林,混杂生长着各类树种,成片的柞树林里夹杂着松树、桦树。
“唉,柞树不成材,还得满山找成材啊!”
“唉,就这命了,开发了几十年,一棵树得长上百年,这就不错了。”
“少他妈废话,再磨磨唧唧晚上就得睡露天地。”队长一顿大骂。大家赶忙搭帐篷,很快新家安好了。
墩王也没有闲着,穿梭在忙碌的人群中,人家需要啥他就拿啥,他不时拎一下裤子,他的怀里一直揣着那本书。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墩王就悄悄起来,撩起门帘出去了。我连忙悄悄地跟出去,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一直对墩王有种说不清的感觉,谈不上可怜,也谈不上敬畏,那感觉怪怪的。
初春的大兴安岭,太阳在天边艰难地跳跃,东方的天空染成了红色,山坳里雾蒙蒙的,树木在朦胧中静默着,我突然问自己,对于我们的到来,森林是欢迎还是痛恨呢?
墩王来到空地,将自己放在地上,伸开手臂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眼前是一片柞树林,这令墩王兴奋不已,他突然放开嗓门大声喊道:“柞树林,我墩王来了——”远处传来了回音“墩王来了——”我从没有见过墩王如此兴奋,他身子起伏不停地前进着,越过了崎岖不平的草地。前面是一条小河,墩王找来两根松木杆来到河边,站直身子,双手拿起一根松杆用力一扔,又拿起一根松杆扔了过去。河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桥,他两手抓住松杆,撑起身子扭动起来,身子在扭动中前进着。我愈发相信墩王那可怕的臂力可以战胜一切了。
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柞树林,干枯的叶子还零星地挂在枝桠上,新叶悄悄绽开了嫩芽,墩王看看这儿,又摸摸那儿,好似和久别的兄弟重逢。他一回头看到了我,掩饰不住兴奋地喊道:“快来、快来,快看这宝藏!”“宝藏?哪里啊?”我诧异了。
“这里啊,这不是宝藏么?”墩王拍着柞树树干喊道。
我更加疑惑了。
“以后你会懂的。”墩王感慨地说。
晚饭的时候,墩王说出了“宝藏”的秘密。
“这是我们三年前采过的老伐区。”一位工友憋不住了,打开了话匣。
“找个好伐区赶上找条金沟了。”队长的话总是那么直接。
“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墩王试探着问。
“改变?不吃饭了?”
“我们用一半时间采伐,一半时间种木耳。”
“种木耳?不采伐去种木耳?天大的笑话!”队长大声喊道,“别瞎想了,有我吃的就有你的。”
“我要靠自己活!”墩王的声音大极了。
队长摔门而去。
我们又开始了东奔西跑的采伐生活,为了一根木材往往要跑好几里山路。这可苦了我们这些套子工,套子刘就免不了满腹牢骚,干活占不住他的嘴,什么儿子上高中了,老父亲病倒了,妻子抱怨了,总有说不完的劳心事。我那时不懂得生活里有如此多的烦心事,只知道从此不用费心地变着法儿逃学了。
大兴安岭的春天依然逃脱不了严寒的侵袭,北风玩儿命地刮。白天阳光照下来,积雪消融,一到夜里便冻成冰坨一块。这天,帐篷里来了两个人,是老两口,他们身体干练,一看就是多年跑山的主,是山里通。山里的帐篷是跑山人的家,他们一走进帐篷就倒在墩王和我的铺上呼呼大睡起来,一觉睡到天黑。晚饭时,女人加了一个菜:山木耳炒鸡蛋。
山木耳是大兴安岭的珍奇,黑黑的木耳裹上金黄的鸡蛋,外嫩里脆,一会儿工夫见了盘底。我好像还没来得及品它的滋味,只觉得一股奇异的香味直冲脑门,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似乎在雾气蒙蒙的山林里行走,空气里有奇异的清香,它吸引着我向前去,我知道那里有奇异的花朵,正绽放着诱人的花瓣。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是跑了几十年山的跑山客,大兴安岭就是他们的家。奇怪的是,他们一走进了八岔沟就犯了迷,转了两天硬是找不到出山的路,看到了帐篷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接着端上了我们的特色菜——蛤蟆炖豆腐。一锅河水里放进整只的蛤蟆和整块的豆腐,再扔些盐、辣椒、花椒,文火炖上两小时,就成了大兴安岭特有的佳肴。
老人显然是饿坏了,说“囫囵吞蛙”一点儿也不夸张,老妇人噎得直翻白眼。大块的豆腐简直是直吞下去,连沾在牙齿缝里的豆腐渣也细心地用舌尖剔出来,细细嚼烂。
第二天天一亮,老人就忙着要走,墩王突然大声喊道:“别急,等等我。”老人愣愣地站住了,一会儿工夫,墩王就一起一伏地回来了,肩上多了一个包。他拿过老人的背兜,把兜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了进去,竟然是支棱棱、滑溜溜的春木耳。春木耳是木耳中的极品,两个老人跑了两天才采了一大捧,墩王一转眼就是一大背篓,实在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墩王一只手用力一提,背篓窜上老人的肩,他笑着说:“赶紧回家吧!”老人一个劲儿地道谢,墩王板起脸说:“跑山不容易,回家干点别的活。”“好!”老人连连点头,下山去了。
“人家跑两天才采一捧木耳,你一袋烟工夫就采一背篓,莫非你会变戏法么?”我道出了心中的疑问。
“我就会变戏法。”墩王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自豪。
日子在简单和忙碌中行进着,我们依然是满山窜,东一根、西一根地集材。“我们的套子马可以当赛马了。”套子刘突然感慨地说。
“这是你说的最有哲理的话。”我也深有感触。
“那是,我看生产柞木杆倒挺好,漫山遍野,可惜没人要。”套子刘泄气地说。
柞木林骄傲地生长着,就像秋天成片的玉米地散发着成熟的清香。我脑海里又闪现出墩王面对柞木林发出的由衷呼喊,不由得说道:“墩王好像很喜爱柞树林。”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队长也深有同感地说,“自从来到这里,墩王就像打了鸡血,天天往柞树林里钻,然后就看那本破书,着魔一般。”
“您好像特别怕墩王。”我道出了心里的疑问。
“你小子是不是和我混熟了?”队长笑着打了我一拳。
“您看,您对别人总是大呼小叫的,对墩王总是很温和,似乎很尊敬。”我也不甘示弱。
队长长久地陷入了沉思,接着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突然落下了眼泪,哽咽地说:“他救过我的命啊!”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大兴安岭的冬天是木材生产的大忙季节。又开始生产大会战了,我和工友们就像搭在弓上的箭,一开工就勇往直前。大兴安岭大多是馒头山,山势缓、坡度小,状如馒头。我发明了一种简单省力的运材办法:在爬犁上装好大木头,顺着山坡飞驰而下,我坐在木头上,控制着爬犁的走向。坐的位置很有讲究,要找好平衡点,手握爬犁拉绳,身体稍向前爬犁就快行,身体向后仰木头就压在雪地上,爬犁就慢了下来。我就像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车车大木头风驰电掣而下,我高兴得大喊:‘哎嗨,顺山走咧——顺山走咧——人群呼喊着,远山回应着。
“厄运就在人们的欢呼声里发生了,雪地上一块突起的树根改变了爬犁车的方向,爬犁急速地向一片树林撞去。人们惊呆了,大喊:‘拉住爬犁绳——可一切都晚了,爬犁急速地冲向树林,‘砰——地一声巨响,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完了。当我睁开眼睛却惊讶地发现,墩王双手支撑着一根粗大的松杆,松杆深深压进了他的肩膀,他就那么站着,硬是顶着爬犁停了下来,在爬犁停下的那一瞬间,墩王也倒下了……”
大家都沉默了。
“墩王有老婆么?”有人问道。
“有。后来,老婆和他离了婚,回乡下去了。”
又是一阵沉默。
“我决心把墩王带在身边,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他一口饭吃。”队长接着说。
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墩王穿着古罗马战袍,挥舞着利剑在战场厮杀,所向披靡……
以后,我有事没事就找墩王说话。一有空闲,墩王就让我给他念那本不知念了多少遍的《木耳栽培技术》,我不再厌烦,而是耐心、细致地读,墩王的脸上总能露出幸福的笑容。
每隔十天半月就有运材车来拉木材。一天,运材车来了,司机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哎——真是可惜啊,两个老人采山货迷山,死在山里了。”
“什么,两个老人迷山死了?”我们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我的眼前浮现出老人临别前的那一幕:他们把整整的一背篓春木耳背在肩上下山时,他们的心里是多么高兴啊,如今……
他们为什么一次次迷失在山里呢?是大兴安岭的连绵逶迤,还是他们内心的某种迷失?一种奇异的景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森林母狼幼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它会吃掉自己的幼崽,也许是大兴安岭无法养育她所钟爱的人类时就痛下杀手了。
司机似乎意识到什么,突然问:“他们来过?”
“来过。”墩王的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唉——”我们都长久地叹息。
墩王突然仰起脸,许久许久,整个身子向后仰,双手伸向天空,直直的,就像一个坚硬的树墩矗立着。
“啊——”墩王发出一声呐喊。
我仿佛看到墩王吊树墩的情景,他顶天立地的形象就像一座铁塔高高地耸立着。
一天的劳累换来了几根细长的木头,这天夜里,天黑得特别早,大家默默地躺在帐篷里,谁也不说话。许久,许久……
“这日子,没法过了。”队长打破了寂静。
“唉——”不知谁在黑暗里叹着气。
“我们种些黑木耳吧。”墩王轻声地说。
“木耳、木耳,我就不信,我养活不了你,有我吃的就有你的。”队长不耐烦了。
墩王“呼”地站了起来说:“我不需要你养活,我从没让你做什么。”他扯掉被子,大声地对我们说:“走,跟我来!”
一片茂密的柞树林里,掩藏着一个破旧的帐篷。帐篷围得严严实实。掀开门帘,钻进帐篷,墩王打开手电,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一排排整齐的架子上摆着一个个白色的袋子。
“这是什么?”
“是木耳菌。”
木耳菌种进柞木杆里,就可以长出好多好多的木耳。我想象着书中所描绘的景象。
“简直是扯淡。”我从没见过队长如此生气,“大兴安岭的木材是采不完的!”他简直在咆哮。
墩王毫不退缩,挺直身子,堵住队长的去路,大声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死不了,我会养你一辈子。”
“你最好清楚,没有谁要你养。”
墩王消失在夜色里。
很快,我们又要搬家了,天空依然那样蓝,可我们谁都不愿意讲话,任凭汽车摇晃着我们那本已沉睡的思绪。
“墩王呢,墩王怎么没来?”套子刘突然大喊起来。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
“哇——”一个人突然大哭起来。
队长双手捂着脸,深深地把头埋在双腿间,痛苦得像一个孩子……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