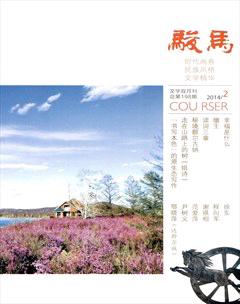待岗
苏湘红(瑶族)
苏湘红
瑶族,1968年生,广西大化县人。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大化县委政法委,兼县文联副主席。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广西文学》《三月三》《飞天》《红豆》《灵水》《河池文学》《特区时报》《桂林晚报》《北海日报》《广西法治日报》《右江日报》《河池日报》等区内外报刊发表。曾有小小说《两眼池》荣获“宋河杯”全国小小说大赛三等奖;小小说《打鼠》荣获2001年度广西报纸副刊年度文学作品三等奖。
一
报社没了,我的生活也一切都改变了。
我原来是在一家县报做个普普通通编辑的,上级忽然一纸通知,县级不再办报,人员分流。后来上级又一页文件,关于撤销××报的决定,下面是一颗印章,鲜红得像妻子涂了口红的嘴唇。
我家坐落在建丰路东小区,县实验小学附近。建丰路很长很宽,呈个叉开的人字,整天车来人往,川流不息,像条流动的河。连接东小区的是一条老太婆裤带一样的小巷,我们每天就在这条裤带上进进出出。此刻我就走在这条裤带上,裤带头是我贷款七万元建的房子。七万元贷款要扣我十年的工资,我已经算好了,不吃不喝十年,直到小孩初中毕业,我才能从真正意义上领到那份属于我的工资。
刚到家门口,我就闻到了黑豆炖猪脚的香味。这是我家自扣工资贷款建房后,连续几年一成不变的一道菜谱。儿子反映同学们都从他身上闻到猪脚味了。走进厨房,就见一只猪脚坦坦荡荡地躺在那口大鼎锅里。
我垂头丧气地跟妻子说报社解散了,我待岗了,等待分流。妻子一双本来就大的眼睛立刻瞪圆了,不认识我似的看了我好一阵子,很久才呼出口气来,说,阿果,看来以后我们要喝西北风了。
二
报社解散,我在家里呆了两个月,上面没有丁点分流的消息。我只能整天待在家里吃饭,睡觉,看电视,实在憋不住了就到街上游荡。
一天,在电影院的小广场上去看人下棋,我碰到了同个小区里第二排第三间的黄师傅。黄师傅说,大记者来采访啊?我说,我待岗了,等待分流,没事干,来看你下棋。
一看就看到日头偏西,我才回到建丰路东小区。妻子正准备出去。见到我说,阿果,我去加班做报表,你在家照看儿子,吃完饭后记得叫他做作业。我无条件地点点头,听着高跟鞋的声音穿过厅堂越过小巷消失在车来人往的建丰路。
三
分流的事还是没有丁点消息,我有些按耐不住了。妻子说,去找领导吧!我想想也是,待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领导家的门朝哪开呢!我先翻遍厚厚的电话簿找领导的电话,但打过去都是一个甜腻腻的声音在说:您所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于是我又翻遍所有的笔记本找领导的手机号,终于在一本两年未翻的笔记本的角角里找到了领导的手机号。我拨通了号码,领导说,阿果啊!有什么事吗?我连忙说您在家吗?我想过去向您汇报一下工作。一说完我就后悔了,我工作都没了,还汇报什么呢?没想领导竟然说,那就来吧,你知道我家在哪吗?我说,知道知道,于是就挂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想破脑瓜也想不起领导的家在哪里。于是就打一位到过领导家的小兄弟的电话问,确定方位后我才着手准备怎么去领导家的事。妻子说,买什么去啊?领导有什么爱好?我说,抽点烟喝点酒吧,还有爱洗桑拿做俯卧撑运动什么的,我们家送得起吗,不至于找个女人送去吧。妻子就很生气地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说,那就买些烟酒过去吧!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领导家,板凳还没坐热,领导就安慰我说,你就先在家待着吧。书记县长一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两个副书记一个组织部长到亚欧六国新马泰参观考察去了,还没召开专题会讨论研究这事,你瞎急些什么,工资又不少你一分,说完就把我送出门去。
四
我在家里又待了两个月,还是没有分流的消息。昔日称兄道弟的几个狐朋狗友现在不仅连影子都不见了,而且连电话也懒得打。那个在税所当所长助理的邻居一碰见我,就说,年轻的离休干部,潇洒啊!这么恶毒的话让我很是生气。所以当阿翔问我要不要找点事做时我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阿翔以前和我在报社一起工作,后来贩卖假币被警察逮住,判了两年徒刑。出来后听说在某杂志社什么专题部当记者,说白了,也就是挂杂志社的名在全国各地招揽广告,拉赞助,然后要回扣。以前他被关押时我曾买过水果去探监过两次,他说现在终于找到报答我的机会了。阿翔说他有个叔叔在大桥北路开饭馆,隔三差五总有婚嫁什么酒席在那里办,因流动资金少,他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若哪客户先预交酒席定金的,结算时每桌少算十元钱,意思是说有哪笔生意找上门交不起定金的,由我先付,客户结算时再将每桌十元钱算给我。
力气终于有了使用的地方,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偷偷取出这几年拼命写稿攒下的一万三千块钱,一起交给了阿翔他叔。然后每天七点就准时到大桥北路阿翔他叔开的那家得银酒店去等待顾客上门,看哪摊是预交定金的,哪摊是酒席后算账的。我每天都等到很晚。当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建丰路东小区时,总能看见黄师傅靠在一只烂沙发上,身边搁着一只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黄师母则摇着芭蕉扇坐在黄师傅身边。他们都是退休干部,看上去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五
春天走了夏天来了,我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我每天在去阿翔他叔的得银酒店路上时,总能看到在阿翔他叔酒店打工的小郑,或听到小郑爽朗的笑声。我常常打趣说小郑你的裙子越来越短了,小郑说我那是在节省布料啊!我又说小郑你的衣裙太透明了,小郑则不屑地说,土老冒,这叫前卫!我心里偷着乐,照这样下去,她就可以一丝不挂上街前卫去了。
我每天就像一只机警的猎狗,盯着三三两两到总台上伏着说话的客人,然后等着阿翔他叔打着过来的手势。
这天柜台来了两个肥头大耳的主儿,订了一百桌酒席,却没钱交定金。当肥头大耳们走后,看见阿翔他叔打个过来的手势,我简直乐坏了,乐得嘴巴都差点跟耳朵根扯上了。替肥头大耳们办完定金手续,我的心情好极了,待岗憋气了这么久,我也该自个儿滋润滋润了。
服务小姐将我引领到3号厢。我要了三罐啤酒,两碟小菜,就自斟自饮起来,然后拿起话筒对着电视屏幕的歌狂吼了一番。又来到表演大厅围着表演台的高台座上要一瓶葡萄冰玫瑰自斟自饮起来。在我的左边,两个陪酒小姐在跟她们对座的两个小伙子玩猜点饮酒的游戏,猜对的人喝酒,猜不对的小姐喝。趁服务员给我拿酒的工夫,他们两瓶酒见了底。而我右边的那个陪酒小姐更能喝,对面坐着六个男人,他们连点子也不猜,小姐不停地跟他们碰杯,一碰就干。
六
天气越来越炎热,平时在建丰路东小区蹿来蹿去的风,如今却一点儿也不见了。由于揽了一笔大生意的缘故,我已有几天不出门去得银酒店了。早上起来,我决定从今天起继续去得银酒店等生意。路过黄师傅门口时,黄师傅躺在躺椅上正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由于肥胖的缘故,他正伸着舌头像一条夏天的狗。黄师母靠在一边,在看一张六合彩码报《雷锋内幕报》不停地嘀咕,雷锋主编的报纸怎么也不准!连毛主席老人家都为他题词了呢。我说,这个雷锋不是那个雷锋。那个雷锋是人民学习的榜样,你这个雷锋是骗人的。
对门阿霜拎着只塑料桶从我们身边走过,她低垂着头,穿着花色中裤,她是去实验小学那个公共水池洗衣服的。她不用家里的水而跑去实验小学蹭公用水是因为要节约。她爸原来是某建筑工头,在一次进货时遭遇泥石流翻车死了,连个囫囵尸体都找不到。全家一下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妈又经不得苦,后来就仗着那张还算俊俏的脸蛋,让某老板包下当了金丝雀,久不久回趟建丰路东小区的家,给阿霜和年迈的奶奶一点生活费。儿子儿媳妇一个死了一个去“觅食”了,阿霜奶奶每天就早早起来推着辆从废旧收购站买来两轮单车到电影院广场,去捡红男绿女们一夜放浪形骇后丢得满地的废纸、矿泉水瓶、易拉罐等垃圾去废旧站卖,换取祖孙俩的生活费用。我说,阿霜,放假了?阿霜说,已放有两个星期了,还有半个月开学了。我说,学费呢,她摇了摇头。整个建丰路东小区的人都知道,阿霜读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学院。整个建丰路东小区的人也都知道,阿霜的学费要靠她那个母亲供奉。
小郑穿着超短裙从我们身边飘了过去,她的头发染得像一只火红的狐狸毛皮,让建丰路东小区的男女老少看了很不舒服。黄师傅常用“呸!”的一声来表示对他的不满,妖里妖精的,像个鸡婆!我心里想,她就是鸡婆。每每此时,黄师母就警惕地看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死老头,活得不耐烦了。黄师傅则更大声地说,我都是黄土齐脖颈的人了,我怕什么!黄师母吓得一把捂住了黄师傅的嘴。
我来到得银酒店门口时,大门紧闭。大门的柱子上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用毛笔字歪歪扭扭地写着:内部装修,暂停营业。一看就是阿翔他叔土得掉渣的毛笔字。我心里想,暂停营业也好,我也过几天清闲日子。
七
得银酒店装修完毕,重新开张了,但老板却不是阿翔他叔。我的脑袋立即胀大了。要知道,我替那两个肥头大耳交的一万元定金阿翔他叔还没有退给我。还有,预交一百桌定金的一千块回扣阿翔他叔也没有结算给我。
我想我得尽快找到阿翔他叔,只有找到了阿翔他叔我那一万多块稿费才能要回来。我首先打店里的电话,但所有的电话都已是空号。我又打阿翔他叔的手机,但手机己经停机,我立即有了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忽然想起了阿翔,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手忙脚乱地给阿翔打手机,一接通我便对阿翔大骂,他妈的,你可把我害惨了!然后语无伦次地向他诉说了我的困境,最重要的是问他叔究竟有几个电话。阿翔说,现在他正在九寨沟现场体验容中尔甲《神奇的九寨》的意境,并说他已找到了人间天堂的感觉。他说,你若再待岗几个月还没有什么着落的话就投奔我吧!然后才说他和他叔已经有两个多月没通电话了。我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软在地上,连手机也没记得关。
八
为了收回这几年拼命写稿攒下的一万多块钱,我跟哥们借了三千块钱,告别妻子和儿子,我踏上了寻找阿翔他叔的艰难历程。
我想我首先得有把刀,我并不是想杀了阿翔他叔,而是为了防身。平生第一次买刀,当我向那个小地摊一步步靠近的时候,我听到了心在胸膛里的狂跳,甚至怀疑蹲在地上的那个摊主也听到了我心跳的声音。但是他只是表情呆滞地抽着烟,根本没理睬我的心跳。小摊上躺着五花八门的铁器,有锤子,有扳手,甚至还有一把用来开石的钢钎。水果刀就躺在钢钎旁边,一尺半长,一泓寒水似地卧在那里。我正想蹲下看刀时,肩头被人撞了一下。我扭头,是个冒失的学生伢子。见我满脸铁青,他立即被骇出笑容满面,连声用普通话说对不起对不起。摊主也突然扔了烟枪摆出微笑,讨好地对我说要哪样,都是些好货。
我蹲下去,拿起水果刀掂了掂。分量不重,很顺手。不锈钢的,快得很,摊主说。我说,不用你讲我也晓得这刀快得很。他说,十五块钱要么?我瞪了他一眼。他立即改口说,十块算了,算是我帮你进货。我丢下十块钱,拿起水果刀,走了。
我的第一站是南宁,听小郑说阿翔他叔在朗东开发区有个情妇。姓吴,湖南人。小郑说你到南宁,即使找不见他你也知道他到哪里了。因为没下雨,所以气温就一直没有降下来,太阳火球一样一直在头顶上悬着。到安吉站下车,我立即搭上开往朗东的32路公交车。公交车上的人过于紧密,一进去,前后左右就被封死,几乎动弹不得。我正想着见到阿翔他叔后如何开口讨回我的稿费和回扣钱时,一只手无声无息地贴上了我的屁股并慢慢地游动。我装作没有感觉,头望窗外,右手悄悄地从手提包里抽出那把水果刀,探索着朝那只罪恶的手划去。我斜着眼望着棚顶,看到一张惊恐的脸迅速扭曲变形,他小声地在我的耳畔道歉,师傅,得罪您了。这个吃独食的家伙,把我看作同行了。
没费很多周折,我就找到了小郑所说的东湖路阳光花园C栋六单元P楼P02室——阿翔他叔藏娇的窝。
门口摆有一男一女两双皮鞋,这就说明这家伙肯定在家。
我习惯地用脚把门踢了一下,防盗门拉开了一道缝。我拨开门边的女人冲了进去。屋里光线很暗,在暗色中我看到一张惊慌失措的脸,我一记直拳就击了出去,几滴血溅到了我的脸上。
莫打了!莫打了!
女的尖叫着。
开灯!
我对那女的喝道。
灯亮了。灯光下,我才发现那男的不是阿翔他叔。啊!打错了!我瞟了一眼像摊烂泥一样趴在地上的男人,点燃了一支烟,看青色的烟圈在白炽灯光中荡漾。
韦昌辉呢?我问。阿翔他叔的名字叫韦昌辉。
到昌都去了。
女的惊惶失措地说。
什么时候去的?
两个星期前。
干什么去了?
听说是去承包一个叫什么帝王的酒楼。
帝王酒楼我晓得,是昌都县的红灯酒楼。吃喝嫖赌毒,什么都有,听说后台老板很有背景。
敢骗我,回头一刀剁了你!我恶狠狠地说。
九
坐了七个多钟头的快巴,我来到昌都县城。这个老牌县城,解放了几十年一直是横竖两条街。直到前几年“空降”一位新领导,这个县城才一夜之间彻底变了样,灯光如昼,街道鳞次栉比,人流如织。
下了车,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帝王酒楼,总台立马有个服务小姐站起来,脸上堆满了笑容谦恭地说,欢迎光临!先生,请问你找谁?我没作声,直接向二楼跑去。
在二楼大厅转悠,我把手插在口袋里,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悠闲的单身顾客,在各个包厢门前游荡。包厢里时不时传出阵阵浪笑声和小姐们夸张的尖叫声。一名醉汉跌跌撞撞地从包厢里晃悠出来,由一名小姐搀扶着一路走一路叽咕,你陪我,一夜几多钱你说,他妈的老子有的是钱!忽然有位小姐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旁,含笑注视着我,满眼充满了暧昧。贱X!我暗骂一句,便向三楼走去。
三楼是桑拿按摩室,我猜想阿翔他叔可能就在里面,因为现在这些老板们手里有了几个钱,就觉得屁股烧火了。我敲开一间间桑拿浴室的门,在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中我很失望。没有见到阿翔他叔。
我不得不问柜台的一个领班小姐。
领班小姐说,老板到广州去了。
几时回来?我说。
她说,我哪晓得。
我说,老板去干什么?
她白了我一眼说,找俄罗斯小姐呗!
我捏了捏藏在裤袋里的水果刀,对小姐说,谢谢你。
街道渐渐冷清了下来。摸着裤袋里为数不多的钱,我决定投宿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于是我向一家写着“红星”招牌的旅馆走了过去。门口坐着两个年轻女人,一张脸胖一张脸瘦。见到我来,便递过一本皱巴巴的登记簿说登记,登记完了胖脸女人说,住103号房。
这是一家地下室的旅馆,沿着阶梯下去,穿过昏暗的过道,我在一排油漆斑驳的木门上找到了一扇写着103的门,并把钥匙插进了锁孔,试探着转动。
门没锁,你不用瞎费劲。
有一个声音在里面说道。
我推开门,房间很小,一左一右放着两张小床,还有一张桌子,就这几样东西把房间摆得满满当当的,中间的过道仅能容一个人走动。灯光下,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床沿上就着花生米喝酒,花生米的碎皮屑落得他胸前衣服满襟都是。
兄弟,喝两口。
还没等我坐稳,那个人就拎着瓶德胜米酒向我递过来,出门在外都是朋友。我说,我不会喝酒,他摇摇头说,可惜了,要不然我真想跟你喝个通宵呢!
这一夜,我躺在简陋的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企盼着天亮。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我连忙走出旅馆直奔车站,搭上开往直达广州的快巴。
十
广州叫花城,可是我没见到一朵花。我见到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以及豪华的汽车和步履匆匆的人群。我笨拙地迈动着双腿,以一个乡下人的姿势走在这个城市的马路上,从一个路口转到另一个路口。我忘记了睡眠和吃饭,我每天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大街小巷数不清的酒楼饭店、洗头屋不停地奔走,瞪大双眼在人群中辨别阿翔他叔——那个千刀万剐的韦昌辉。
现实的情况越来越不妙,每个与我打照面的人总是再回头瞧瞧我的脸,那眼神让我觉得居心叵测。好像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阿翔他叔在哪里,可对我却又守口如瓶。在几个大酒楼,我曾壮着胆子上前去打听,被询问的这些人大都一问三不知,摇摇头用我听不懂的广州话摆脱了我。我也曾遇到过几个热心肠的年轻人,可是他们耐心告诉给我的地址都是公共厕所。有一次我似乎看见了阿翔他叔的脸在人群里一闪,于是我便推开前面的人大步朝那个人追去。我跑到那个人面前,激愤得涨红了脸。那个人满脸惊讶地望着我,我才发觉自己认错了人。又有一次我在一辆飞驰而过的黑色轿车里似乎看见了阿翔他叔,我立刻举起双手对着汽车挥舞,可是疑似阿翔他叔的家伙却视而不见,汽车停都没停,我不得不跟在车后边狂奔,一边挥舞着双手一边大声地呼喊韦昌辉韦昌辉。可是只追了两个路口,汽车就驶出了我的视线。还有一次我走过一家灯火辉煌的大饭店,看见前面花圃边的灯影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极像阿翔他叔,我不假思索加快脚步朝他走去,到了近前冲着他就喊,韦昌辉!
滚开!
一个男人的声音恶狠狠地对我喝道。还没等我转过身来,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就直飞过来,打中我的脑门并粘在上面,原来是一口浓痰。我抬起胳膊去擦,浓痰转移到我的手臂上。
好多天过去了,我寻找阿翔他叔的努力依然毫无头绪,我就像一名无家可归的孤儿,浪迹于广州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又一个夜晚来临,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选择人群最拥挤的地方钻,而是情绪低落地徘徊在一个冷清的街心小花园里。夜渐渐深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一段黑暗的地铁车站。此时连末趟车都早已发走了,但里面的铁栅栏门还没上锁,通道里一片昏暗。我走下长长的台阶,这时黑暗里仿佛有个人对我咳嗽了一声,于是我便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
要黄碟吗?国内国外的都有。
一个小青年从阴影处冒出来,撑开的黑色塑料袋里露出一堆乱七八糟的碟子。我忽然想起帝王酒楼的那个小姐不是说阿翔他叔来广州是想弄几个俄罗斯小姐过去的吗?于是我便问小青年哪里有坐台的俄罗斯小姐。小青年说你买一张碟,我就告诉你一个地方,以此类推。我一下买完了小青年手中的四十二张碟子。
循着小青年给的地址,我终于在一家夜总会门口堵上了阿翔他叔,挽阿翔他叔胳膊的是一个高挑的洋妞。见到我,她很暧昧地向我笑了笑。我说,笑什么,跟谁你都笑!洋妞见我怒目圆睁的样子,吓了一跳,立即缩到阿翔他叔的后面。阿翔他叔压低声音说,阿果,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说,我一路讨饭过来。阿翔他叔说,你来找我干什么?我说,你心里应该明白。阿翔他叔说,可是我现在没钱。我说,你没钱?没钱你跑到昌都去承包什么酒楼,没钱你能在南宁养小蜜,没钱你能跑到广州来泡洋妞?阿翔他叔说,过一段时间再还你好不好?我说,现在就还,我讨饭到这里不是来商量的。说着我把那把一尺多长的水果刀亮了出来。阿翔他叔旁边的洋妞啊地尖叫了一声。我对阿翔他叔低吼,你叫她别吱声,不然我连她一起废了。阿翔他叔就对洋妞说了一句什么,那个洋妞立即缄了口。
阿翔他叔尴尬地笑了笑,说,兄弟,我真的怕了你了。说着从俄罗斯小姐拎的手提包里取出两沓钱,数出一百四十张百元大钞递给我。我接过钱往裤袋里一塞,看也没看阿翔他叔和洋妞一眼就转身走了。这时,我听见从门里传出一声,阿叔,发生什么事了?我回过头,立即愣住了,阿翔木头人似的僵在那里。
十一
从广州回到建丰路东小区的第二天一大早,我揣着两千块钱匆匆走进阿霜家交给她,说这是两千块。阿霜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我忙拉起她,说你别这样,这种行为没出息。她大叫一声“叔”就扑进我怀里大哭起来。
当天,我在建丰路东小区出入处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告示:尊敬的东小区里各位住户,我们小区最优秀的阿霜同学现在读书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小区历来的光荣传统。希望大家都献出一份爱心,帮助她渡过难关。愿意捐助阿霜开学费用的,请在告示的空白处写上自己的名字和捐助的金额。
三天后,我去看那张大白纸。大白纸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捐助的金额,黄师傅和黄师母正在告示前阅读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忽然黄师母指着小郑的名字对老伴说,你看你看,连她都捐了,一百块呢!黄师傅不以为然道,不就是松一回裤头嘛!黄师母则一把捂住老头子的嘴说,你又乱嚼舌头了,听说人家早改邪归正准备嫁人了呢!
阿霜开学的那天我得到通知,叫我到组织部报到,另行安排工作。
责任编辑 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