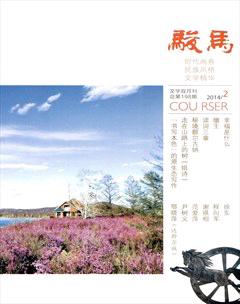不速之客
阮红松
1992年开始创作,在《长江文艺》《芳草》《天池》《百花园》等刊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作品获得过多种奖励。现在《洈水》文学杂志社工作。
下班回到家,我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大门忽然被拍得山响。
搬到新居,楼上楼下那么多新搬进来的住户,我谁也不认识。
这些年,我已习惯了电话交际,没要紧事,一般也没什么来访,电话里就说清楚了。都忙着呢,无论多好的朋友相邀,不想去,喊一声累,就理解了。“累”这个词都在使,也好使。这种时代病,都患着,就都能理解。有亲戚、朋友、同事来,都先打个电话预约一下,然后在家等着。人到中年,我越来越懒于社交。有那么一点社交,也越来越功利,交些闲人扯些闲事干什么?我忙,我累,而且像坏天气一样,心情时不时很烦躁。
没有预约就拍门,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也许是安静惯了,我一听拍门就紧张,就有点心烦。打扰我干什么呢?我一个机关小职员,对什么人都是没多大用处的。知道自己的斤两,我不打扰别人,也从内心深处不希望别人打扰我。我欠了欠身子,很不想开门。不速之客,不外乎以下几种人:一是物业,物业拍门基本是收费。按揭下一套新房后,除了按月交钱给银行,剩的钱,都交物业或由物业代收了。二是搞推销的,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也是一支可怜的队伍。他们不依不饶的打扰,让人有脾气,又不好意思发作。三是借东西的……反正是找麻烦的,这年月不找麻烦拍人家门干什么?
当然,不想开门,也是可以的。反正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知道主人是不是窝在家里。
拍门的家伙好像有病,越拍越有节奏,而且好像吃定主人在家。
我有点无可奈何。新居的公共设施还在完善中,安防还没有完全到位,可视门铃电话还没接通,我是无法判断敲门人的。有意地躲,不开门,一般是知道对方的身份。如果搞不清楚,吃不定真有要紧事,那就躲出麻烦来了。
我再也躺不住,愠怒地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秀气的“四眼”,左胳肢窝还夹着一根拐杖。
“您好,我是新搬来的邻居,住您对面201栋2楼,请多关照!”“四眼”说,热情地伸出手。
我吃惊地打量着他,没有要握手的意思。他不管我愿意不,抓过我的手就握。握过了,转身下楼去了。
我愣门口,半天没回过神。敢情这人拍半天门,就为了说这几句废话?关照什么?我连左邻右舍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都懒得关照,有闲心关照到201栋?
我能关照别人什么呢?我苦笑了。这年月,神经不正常的人比较多!
第二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准备午休。一条腿刚从裤子里抽出来,门又被拍得山响。老婆正在收拾碗筷,手上油乎乎湿淋淋的,嚷嚷着让我去开门。我重新将一条腿伸进裤子里,骂人了:
“真他妈缺德,早不拍晚不拍,老子裤子脱了就拍!”
门口那人不拍了,高声叫道:“大哥,是我呀,我昨天来过的,熟人。”我一听,耳熟,是那个“四眼”。看来他还真把我当“熟人”了,想什么时候拍门就什么时候拍门。拉开门,小哥笑嘻嘻戳门口。我的脸拉得老长,不耐烦地冲他说:“哥们儿,有事?”
“呵呵,不好意思啊,我昨天忘了点事。”他说,手里捧着个小本本,指间还夹支笔,认真地对我说,“大哥,您能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不?”我的脸拉得更长了,一个居民,又不是物业,要我家电话号码干什么。
“四眼”说自己想建一个邻居电话号码簿,便于邻居间的交往与交流。他翻着本子给我看,说已经收录好几户居民的电话了。
我接过小本子看了一下,看不出有什么意思。老婆一听说是邻居,从我身后伸出脑袋,顺口就把家里的电话号码报了。
“四眼”走后,我把老婆推了个趔趄,警告她说:“婆娘,电话号码属家庭隐私,不要随便告诉别人,知道不?”
“不就一电话号码啊,瞧你紧张的。”老婆顶嘴说。
老婆在环卫局扫街道,没什么心眼儿,她认为世上的人都跟她的扫帚一样简单。我越想越认为老婆比较傻,开导她说,这“四眼”虽说是社区的住户,看上去也不像是个坏人,但是,现在的人都不地道,老是挖空心思算计人,吃不定这个跛子就没正当职业,是开麻将馆或帮别人搞推销什么的。咱家电话号码泄露出去,再也不得安宁了。
这种事,是有历史教训的。老婆曾将自己的手机号无意告诉给了一个开麻将馆的姐妹,从那以后,我家再没安宁过。那姐麻将馆一缺人,电话就打过来了。一般理由拒绝还不行,说在街上,那好,位子留着,从街上办完事马上来。不去,电话又来了。说在医院打点滴总行了吧?不行,打完点滴也得来搓两盘……最后,我们两口子假装在屋里打架,我当了恶人,那电话才终于平息了。
任何事情就怕分析,一分析,热心快肠的老婆也不敢吭声了。再一分析,从“四眼”的眼镜分析到他的拐杖,认定他是个不务正业的人。最后形成家庭决议,从今以后,只要“四眼”拍门,坚决不搭理了。
第二天到局里上班,我心里还为“四眼”这个人不踏实。在办公室一议,同事们也觉得我的担忧不多余,一个陌生人,老拍门,打探家庭电话,是不正常的。有位曾经有保安经历的同事,怀疑“四眼”是个盗窃嫌疑犯,拍我家门是来为偷窃踩点的。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到小区物业查查,“四眼”现在是干什么的,以前是干什么的,有没有犯罪前科。
下班途中,遇上以前在一块儿共过事的老赵,要用私家车捎我一程。没想到他跟我住一个小区,正好住在201栋。我喜出望外,向老赵打听“四眼”这个人。老赵说:“我也不是很熟,他就住在我家楼下。你还别说,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拍你家门么?”我好奇地问。
老赵摇着头,笑了,笑得相当下流。
“昨天夜里,我跟老婆在床上温习功课,那席梦思床没放铁实,一运动就咕叽咕叽响。你猜咋着,兄弟?”
“拍你家门么?”
“哈哈,我正舒服,电话响了。楼下那哥打的,问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我实话实说,在做那事呢。咋地?打扰啦?他乐了,说,那就好,我以为你家出什么事了,接着做吧,晚安!”
靠。我乐了,手里的烟塞嘴里都塞反了,将嘴巴皮烫了个火泡。
我放心了,“四眼”估计不是个坏人,只是闲得蛋疼。如今还有这么闲的人,少见。
从那以后,我在社区转悠碰上“四眼”,主动打个招呼。没别的,通过老赵那事,我感觉“四眼”这人挺好玩的。
这年月,好玩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
转眼“十一”国庆节到了,节日里,社区忽然冷清了许多。一是忙着装修的,终于歇家伙了。二是社区的居民大多数都出去玩了,黄金周嘛,一年也就一次。我的老婆也出去玩了,不过不是去旅游,是回娘家去玩了。当着房奴,出门旅游这种事,我跟老婆商量下辈子还做夫妻,下辈子夫唱妇随出门旅游。
老婆抹着泪,高兴地答应了。
孩子在上大学,除了春节,一般节假日从没回来过。孩子不知父母的忧愁,也不应该让他知道父母的忧愁,他是我家唯一出门快乐旅游的人。我呢,在单位值班,值一天班,多三十块钱补助。
白天不觉得,天一黑,平日的万家灯火,成了几颗小星星。其实平时都在家,大家也没怎么走动,但感觉都在,心里踏实。现在大多数人出去玩了,人往社区一走,心里莫名其妙地空落了。
我平日的业余生活本来就单调,不串门,不打牌,不看电视,回家要么窝在沙发上看书,要么陪老婆在夜市转一下。现在一个人在家,就更无聊了。正百无聊赖,电话响了,响了两声,又不响了。
我警觉地盯着电话,心里有点发毛。听人说,这种响一下不响一下的电话,鬼大得很。要么是情人的暗号,情人间手机打不通,又急着要见,只好冒险打座机,不敢接通,只能打一下挂一下,让有心人听见,然后拨打过去。老婆已是半老徐娘,虽说有几分姿色,可人老实,没花心事,在外面不可能有情人。那么,最大的鬼,就是小偷的试探电话,看家里有没有人。
正胡思乱想间,电话再一次畅快地响起来了。
“大哥,你在干什么呢?”电话那头说。又是“四眼”,有了那两次拍门的唐突,忽然来个骚扰电话,就不唐突了。
“刚才的电话是你打的?”我问。
“四眼”说,刚才打了下,又犹豫了,怕打扰我。听那声音,有几分孤寂几分落寞,我的心软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不也正寂寞着么,便说:“你如果寂寞,就出来串串门吧。”他叹息道:“不好,乱串门讨人嫌!”
是的,我也觉得乱串门讨人嫌。估计这个闲人,在社区乱跑,受到过不少白眼冷遇。这次,我好心情,跟“四眼”在电话里聊了近半个小时。从交谈中了解到,“四眼”原来是个小学老师,三年前出了车祸,断了一条腿,接着又离了婚。为了忘记过去的伤痛,就搬到这个社区来了。
原来是这样。放下电话,我心灵最柔软的一角,泛起一丝涟漪。回首往事,我年轻那阵子受了点挫折,比较自闭,找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
忽然想喝点酒,从酒柜里取出一瓶白酒,在厨房里热了俩菜,一个人喝上了,边喝边回忆一些事情,不知不觉喝多了,澡都没洗,就倒床上睡了。
第二天清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吵醒了。一听,又是“四眼”。
“大哥,大清早,你搬东西到哪去呢?”
搬东西?我一惊。
“兄弟,我还没起床呢,你说梦话吧?”
“四眼”在电话里急火火地告诉我,202栋楼下停着辆小四轮,正装家电呢。他睡不着起得早,跑过去问过了。小四轮的司机说,他们是卖家电的,因货发错了,在跟202栋4楼1号的居民换家电。
202栋4楼1号住的就是我啊,我什么时候让人来换家电了?我边接电话,边伸头从窗户往楼下瞧,一瞧,楼下果然停着一辆小四轮,一伙人正往楼下搬家电。我打开卧室门,光着脚丫冲到客厅一看,天呐!大门敞着,客厅的电视机、空调、冰箱等几件高档电器全不见了。我惊呆了,愣屋里想,一定是有人进错了门,搬错了东西。又一想,昨晚大门锁得严严实实,谁把大门给打开的呢?再说,一个大活人睡屋里,咋没人跟我打招呼呢?
跑到门口一瞧,门锁好好的,有人用钥匙打开了我家的门。
我忙打电话给老婆,问是咋回事。老婆一听也慌了,说没有让人来换家电,也没给外人家门钥匙。
这就日怪了!
我跑掉一只鞋,冲到楼下,看到几个汉子正往小四轮上飞快地装东西,那些东西,果然全是我家的。
“请问,你们这是帮谁家搬家电啊?要搬到哪去?”我一头雾水问其中一个忙碌的汉子。汉子没吭声,头也懒得抬一下。小四轮的司机,正在指挥装车,忙凑过来说:“啊,我们帮四楼的于先生换家电。”
我晕倒。
世上竟然有如此胆大如此专业的强盗!一个大活人睡屋里,也敢进屋偷窃,咋不把我也装小四轮上!
瞧着小区走动的人越来越多,我不慌了。
“各位辛苦啊,这么早就干活啦。”我跟强盗搭话说。没人再理我,都要忙着呢。有意思的是,晨起锻炼的社区老人,还跑到小四轮前围观,帮司机出谋划策,把家电装稳当些。谁也没有怀疑这是一伙强盗,连我也犯迷糊,这伙人真是强盗么?
我嘴痒,还得上前说两句。
“我说,你们搬东西,主人知道不?”
“主人出去旅游了。”司机说,“人熟,交待咱们一定要在假日把家电调换妥当。您瞧,一大屋东西,累死人呢。”
闲聊时,“四眼”拄着拐杖在旁边听,听到这里,他向社区门口走去。
我强捺住心中的怒火,干脆一屁股坐进小四轮驾驶室。我倒要瞧瞧,这场电视里都少见的戏怎么演下去。
东西装好绑好后,汉子们一声吆喝,上车走人。一辆110警车已经堵在了社区门口,“四眼”正跟警察交谈着什么。门卫老头儿满脸通红,跑过来截住了小四轮。
“有没有搞错啊,咱们给客户换家电呢。”强盗在车上对门卫老头儿狂叫道。
我笑了,笑得肚子疼,挥挥手说:“客户在这里呢,各位老大。你们搞错了,202栋4楼1号的主人没出去旅游,在家睡大觉呢。”
……
社区发生的离奇窃案,将社区的居民惊得三魂走了两魂。警察一调查,觉得应该表扬一下“四眼”。不几天,案情通报就贴在了社区宣传窗上,有一段话是专门表扬“四眼”的,说他警惕性高,安全意识强。我呢,在通报中成了反面教材。虽说我的名字是用H代替的,我也感到无比的羞愧。
第二年开春,“四眼”要搬走了。他找到了新工作,单位比较远,腿不方便,要到单位去住。走那天,社区好多人送他,还有不少平时不大露脸的老人。有个中年汉子,抱着“四眼”泣不成声。
“兄弟,别忌恨我……我刚开始摔你电话,是我不对。要不是你,我老妈死在阳台也不知道……”一问,原来中年汉子住“四眼”隔壁,母亲中风偏瘫行动困难。有天中午,老人摸到阳台晒太阳,不小心摔倒了。汉子上夜班后,正在卧室死睡。老人微弱的呼喊,完全被儿子的呼噜声淹没了。“四眼”正坐自家阳台看书,听到了呼喊声,忙翻他的邻居电话簿,电话打进去,汉子好睡,一连拨打了十二个电话,才把汉子吵醒,创下电话吵醒人记录。寒冬腊月的,老人睡在冰冷的地上,已经休克了……
我也将“四眼”送出了社区,心里五味杂陈。社区有这么个心闲的人,平时被莫名骚扰得确实令人心烦。但他做的好事,却是我们这些所谓忙碌而又活得安静的人没法办到的。说心里话,我宁愿这样的人没有帮到我,帮到我,则成为我一生的亏欠和内疚。
“大哥,您还没我手机号吧?来,我留给您,多联系。”“四眼”上车时,突然又下了车,郑重地对我说。
我留下了他的手机号。
转眼一年过去了,我没打电话给他。因为,我实在没什么事要找他。
但是,当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时,却时时想起他。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