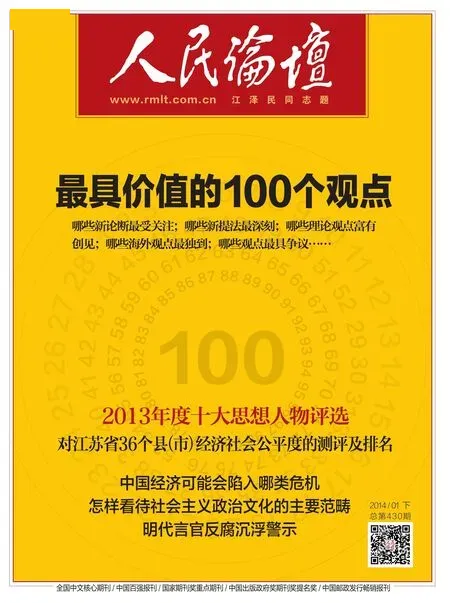中国社会传承制度渊源追溯与历史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跃生
男系传承是近代之前中国家庭血缘关系延续和传承的基本模式,无论皇族、官宦之家还是普通百姓均遵循这一传承之制。近代以来,皇权被废除后,经历民国和解放以来的法律和政策推动,男系传承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当代而言,在男女平等原则之下,制度上的男系传承失去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但在民间社会,惯习对其仍有一定维护作用,并影响着民众实践。
传统男系传承的原则和表现
中国男系传承的基本原则,是以维护男系血缘代际延续、由男性血缘后嗣获得相应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保持姓氏等男系符号的一种制度。作为建立在儿子传承基础上的制度,无子之家则可能出现传承中断。传统时代,为避免这种局面发生,法律和民间惯习中形成了在男系血缘近亲昭穆相当者中“立嗣”的规则。女儿在这一传承系列中没有位置。
男系传承的基本形式。男系传承制度有一些外在表现,成为这种传承的标识和符号。其外在形式是男系传承原则的体现,这些形式本身也是规则的产物。它包括:婚姻实行男娶女嫁;子女随父姓,妻冠夫姓;妻、子居住依附男系;家庭成员死亡后葬于男系家族墓地;只有同姓男系有血缘关系成员及其配偶被登录于家谱世系中。
男系传承的基本功能。男系传承的功能实际是男系成员在传承过程中所应尽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它是男系传承维系下去的条件和动力。其功能为:养老由儿子、孙子等男系成员负担;家庭成员死亡后的丧葬由男性成员承办;家庭财产以儿子继承为主;祭祀是男性后裔的义务。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男系传承是由原则、功能和形式组成的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男系传承的矫正与保留
近代以来,一些新的政治力量宣扬男女平等观念。随着帝制被推翻,制度对男性传承的维系逐渐削弱,并形诸法律之中。但民国时期尚处于新旧做法交替之中。
清末《大清民律草案》吸收了西方民法中的内容,但它尚未贯彻,清朝即告灭亡。民国初年,新的民法并未制订出来,北洋政府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进行修订,于1925年形成《民国民律草案》。该草案对当时的民间惯习予以吸收,对社会发展趋向和要求考虑不够,因而它是一部具有现代法律形式但传统意识浓厚的法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对《民法》的制定。这里我想通过这两部法律对民国时期法律中的男系传承规则的继承及其变化进行分析。
立嗣—男系传承原则的维护和削弱。立嫡、立嗣是男系传承的一个重要原则。它的保留与否是男系传承维持与弱化的显性指标。1925年制定的《民国民律草案》具有现代法律形式,但观念较为传统。它对当时民间惯习有较多迎合。这一法律既维护传统的立嗣原则,又在某一方面做出调整。其突出之处是外亲之子和妻亲之子被纳入立嗣候选者范畴。而在传统立嗣中,这属于立异姓之子为嗣,是法律和多数家规所禁止的。1929年《民法》已无过继、立嗣方面的任何条款,表明这一历史传统在法律上已经被终止。这是对男系传承原则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削弱。
男系传承内容的变动。赡养义务。赡养义务履行的性别差异在1929年《民法》中被消除。实际生活中,多数妻子同丈夫父母同住,所以《民法》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互相具有扶养义务者,除“直系血亲相互间”外,“夫妻之一方与他方之父母同居着,其相互间”;财产继承。关于子女的财产继承权,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七十二条规定:遗产继承人有数人时,不论嫡子、庶子,均按人数平分。私生子依子量与半分。1929年《民法》中,无论儿子、女儿均为直系卑属,拥有相同继承权。关于妻子的财产继承权。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三十八条: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在立继以前,得代应继之人,承其夫分,管理财产。这一规定与传统法律一致。1929年《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条:配偶有互相继承遗产之权,限定条件消失。
综上所述,民国法律男系传承的基本原则实现了从维系到废除的转变,标志是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设立立嗣专项条款,1929年《民法》对立嗣不做规定,实际是不再承认立嗣的合法性。在男系传承功能上实现了男女继承权和赡养义务的平等。而对祭祀等功能不作规定。
男系传承形式维系和消除。姓氏符号。子女:1929年《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定:子女从父姓,赘夫之子女从母姓。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子女姓氏是传承方式和符号的显性标识,体现了向哪一系“靠”的特征。这一民法明确规定子女从父姓,表明男系传承的主导性仍被法律承认。赘夫之子从母姓,实际是从女方父亲之姓(或子女外祖父之姓)。这一法律也有弹性之处,即遵从当事人自己约定。
妻冠夫姓。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妻于本姓之上冠称夫家之姓,并取得与夫同一身份待遇。1929年《民法》第一千条: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对妻冠夫姓,民国两项法律均保留传统做法,显示出婚姻形式与姓氏的一致性。
居住形式。在男娶女嫁模式下,妻从夫居是主要的居住形式,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也以从父居为主。传统法律对此并未另作规定。民国法律则将这一点作了明确表达。民国法律仍然维持男娶女嫁模式和从夫、从父居规制。
男系载体。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第一千零六十八条:凡由一家分为数家者,各家得联合编一家谱。第一千零六十九条:凡由一家分为数家者,各家得联合设立支祠或宗祠。而在1929年民法则对此不作规定。
可见,民国法律在男系传承形式上,如子女、妻子姓氏、居住方式、男娶女嫁婚姻形式上等维系了传统。但应该承认,民国1929年的法律对男系传承已经形成基本矫正,如废除无子者立嗣做法,确立男女财产继承权平等规则,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当时民众的家庭实践活动多遵循传统做法,新法律的影响是有限的,尤其在广大农村。
解放后男系传承法规全面矫正下的民众实践
解放后,新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具有推动男女双系传承的指向,即儿子与女儿均可成为家庭功能和形式的传承之人。那么,这一制度在民间社会与民众实践是契合,还是背离?
男系传承原则在乡村仍有表现,但立嗣制度失去存在空间;城市男系传承原则明显弱化。其表现为,过继、立嗣这一男系同姓血缘近亲认同规则被改变。无子家庭的过继、立嗣行为失去法律支持。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视血缘关系、具有过继形式的做法即收养近亲之子在民间社会仍然存在。随着生育数量减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后,收养血亲之子的做法大大减少。男系传承功能整体弱化,且范围缩小,仍被保持下来的做法有城乡之别。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市老年父母对子女的赡养依赖降低,照料承担呈现多元局面。但是,在农村,功能性男系传承的基本内容得到保留,即从赡养角度看,儿女双全的家庭,老年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时,父母依附照料的对象以儿子为首选。当代家庭财产的继承仍具有明显的城乡分野。农村儿女双全家庭,嫁出去的女儿获得一份嫁妆,对父母的基本产业不具有继承权。城市则出现两种行为并存的局面:一种为以儿子继承为主、女儿继承为辅;另一种为子女平等继承。当然,无论城乡,一旦诉诸法律,女儿的平等继承权会得到维护。
男系传承的形式多数被保存下来,表现为:一方面,男娶女嫁、从夫居婚仍居主导地位,农村尤其如此。客观上,在乡土社会、父母承担主要婚姻花费的环境中,男娶女嫁的婚姻形式将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它需要两个因素的改变,一是当事者从乡土社会中彻底脱离;一是男女自己积攒和负担婚姻费用,并在婚后形成独立生活单位。另一方面,子女姓氏、籍贯仍从父。整体而言,无论城乡,姓氏符号随父姓的习惯并未改变;子女的籍贯登记也多随父亲籍贯。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被多数人视为男女不平等的表现。
综上,传统时代男系传承受到法律、政策、宗规族训和民间惯习的全面维护;而在民国时期,特别是1929年后,法律、政策对男系传承的维系力度降低,但宗规族训和民间惯习依然在起作用,不过其作用方向并非均为维系,起削弱作用的规则也已产生;解放以后,宗规族训失去发挥作用的基础,民间惯习更多地在乡土社会形成男系传承氛围,法律则具有推动双系传承的功能,政策对男系传承的削弱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问题及其改进
就目前中国社会而言,男系传承行为在法律上已经失去维护力量,而在民间社会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它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如在农村,由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滞后,当代男系传承形式与诸多男系传承功能并未脱离联系。一些地区仍有较强的男孩偏好。因而,推动变革,将男系传承的负面影响进一步降低是非常必要的。
法律对作为女儿、妻子等身份的女性在家庭中应享有的权益应坚决维护;对与法律相抵触的惯习及所引起的纠纷,以法律作为基本处断原则。
淡化婚姻中的“男娶女嫁”意识,强调男女“婚姻”观念;矫正婚姻缔结中的歧视性做法和用语。强调子女,而不是儿子在父母赡养、照料和财产继承中的义务和权利;已婚者应有对双方父母履行照料义务的意识。对子女从父姓还是从母姓,家庭、社会应形成宽容对待的氛围,夫妻能理性对待。
中国当代正处于空前的社会转型中,这为传统男系传承行为和观念的根本矫正提供了契机。当然,它还需相关法律和制度加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