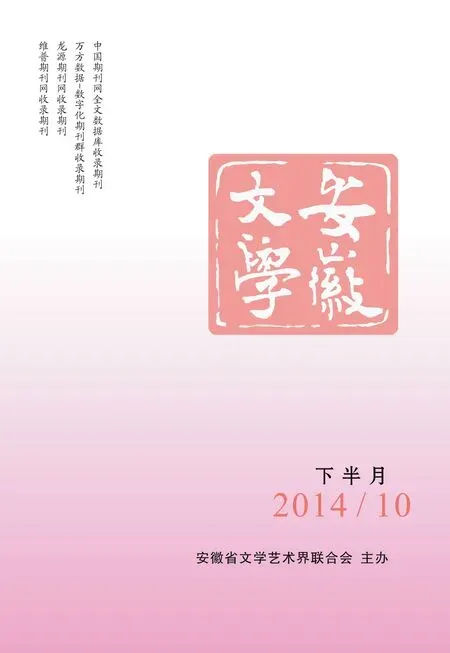晚清粤人异域书写中的理性反思
马笑梅
(暨南大学)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基础,更有着与西方长期交流的悠久历史等先天优势,进入近代的广东一领时代的风气之先,至19世纪,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位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前列。19世纪中叶,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只得被动挨打,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国家、民族的危亡迫使一部分开明人士率先开眼看世界,主动走出国门接触西方文明。在这群可以称之为时代先行者的人中,粤民的数量以及其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实质性推动作用有着绝对的优势。
这些粤人走出国门的动机或许有别,但从他们的文字记述中,我们却可以品察出这些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传统国人在与异域文化遭逢时的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
一、尴尬的时代处境
晚清的中国,风雨飘摇,时局动荡。在这一时期粤人的异域书写中,不容忽视的是他们对时代的醒觉。就时代的意义而言,晚清粤人大致已经觉悟到中国正置身于从古未有之变局,他们皆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个巨大的变局。其中康有为就曾言:“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晚清之际的中国,国门洞开,国人所遭遇的不仅仅是域外鸦片、机器、洋枪洋炮、洋人洋服的蜂拥而至,还有域外制度、思想、哲学、文化观念的纷至沓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处境,是从武力较量到文化存亡的全面危机。
从这些粤人对变局的认识反映出的是他们对时代环境的准确把握,此外,他们亦对所处的地位环境,即认识自己国家在世界全局中所占的地位有着一定的了解。如康有为所言:“大地八十万,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众治而已独乱,国非其国也;众合而己独孤,国非其国也。’”[1]康有为论世界列国分立,明晰地指出了中国的分位,他早已摒弃了中国中心与天朝意象。时代的变局与国际形势,让这些粤人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当前所处的地位,进而自国际关系中更能了解到其地位的轻微。而这一思想的转变,必将打破两千年来的历史传统。
二、现代西方参照下传统中国的自我体认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中西文化之争的讨论始终没有定论。真正说起来,晚清出洋人士是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接触的第一批人,而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种种看法,正是近现代中西文化论争的起点。
中国以农立国,数千年来重农传统早已深入人心。自近代以来,各国先后以精利的船炮与工业产品输入中国,尤其工商业发展的沉重压力使国人深切地意识到谋求工业技术的重要性。而康有为更是将这一认识直接上升到对古今历史通议的高度,其言:“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牟敌利。”[2]5西方列强,崛起于近代,全恃以商立国,中国现在处于万国林立之世,如果不发展工商业,必将永远为列强所欺压。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由共主而至周之封建,由封建转至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有着精英政治色彩与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的专制政治发展到了极致。这也难怪从如此环境中走出的粤人在接触到西方的现代平等思想时而屡屡惊叹。戴鸿慈注意到:“欧美诸国,君臣之间,蔼然可亲,堂陛周旋,宛如宾友。虽以俄皇之尊严,其廷见臣僚,以皆和色立谈,俾尽其意。此亦大易所谓‘泰交’,光武所谓‘分虽君臣,恩犹父子’者也。”[3]234西国不避讳,领袖与臣民之间开放、平等的关系令出洋粤人心神向往。
围绕中西文化伦理道德的问题,出洋粤人发表的议论很多,观点也不甚一致。依据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大多数粤人认为西方人在伦理上有很大缺陷。志刚说,西人虽重信义,但是,“虽父子亦必互存手锯”,是“好信不好学”。[4]17康有为说:“今欧美人之于父子,二十后别为自立,娶妻自由;虽岁时省亲,仅同作客。其父困绝而不必养,其母病而不之事。”[5]233在他们看来,虽然西方的政教均有可观之处,但是却多违君臣、父子、夫妇之伦的圣人之道,这些远不及中国。从中我们看出,晚清粤人多仍以儒家传统伦理为标准,道出的更多是中西文化的差异。
三、西方之精神的探索与考察
西方近代国家是在自由竞争与海外殖民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各国以富强为目标,斗智竞力,自我扩张,虽有所谓国际法,起作用的仍是实力与权谋。这与执“天下”观、行朝贡制的大清帝国完全不同。对于这样一种“国家”,绝大多数的粤人都难以接受它所奉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价值和现实状态。如刘锡鸿即认为,西方人“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谓为有用之实学哉”?[6]129又言:“水雷火炮,惨杀生灵,以此为雄,他日必反受其害。”[6]141这些议论包含着的是对西方国家只讲求实利、不论道德的深深反感。当然,彼时的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西人这一“争”的意识正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西方强盛的重要原因。对此,康有为却有清醒的认识:“当竞争之世,有使人敬畏,无使人怜悯。”[5]257他对竞争的这一认识就非常的确切。
出洋粤人在与域外各国的接触中,目睹了西方的富强,又见及与中国专制政治完全不同的西方民主政治,多为其独特的政治特色所吸引,遂由羡慕而加以介绍鼓吹。在他们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介绍时,最初注意到的即是西方的议会制度。然而,他们对其的介绍却常出现两种误解:其一,称赞议院组织是通上下之情。其二,认为西方议院制度是王政之大公无私,申说者往往比拟上古三代之公天下,国政与人民公议。然而,他们不清楚的是,西方民主的通上下之情,国政的公开,并非出于王之德政,其真正的基础在于社会契约论的施行,再进一步追溯其根源则始于西方社会对人权的保障。
四、结语
晚清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家的民族危亡迫使一部分先进人士率先开眼看世界,主动离开故土学习西方文明。其中,有着得天独厚地理与历史优势,开时代风气之先的粤人更是直接发挥了先锋的重要作用。作为时代的先行者,在学习西方、自强救国这一历程中,粤民经历了艰难的精神苦索,其首先即是对处于变局之世的时代以及被列国所环视的地位环境的醒觉。然后又有对传统中国之所以落后以及西方强盛的原因的探索与反思。而这一理性反思亦为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了充足的情感与思想准备。
[1]唐才常.湘学新报(第三二册)[M].台北:台北华文书局,1966.
[2]康有为.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卷二)[M].慎记书庄,1897.
[3]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34.
[4]志刚.初使泰西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7.
[5]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C].长沙:岳麓书社,1985:233,257.
[6]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9,141.
[7]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外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