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先生的出版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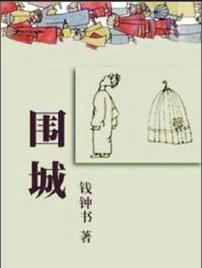

林东林,作家,策展人,业余历史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关注和发掘被主流历史观所遮蔽的人和事,著有《谋国者》《身体的乡愁》《替全世界去仰望》《情到浓时情转薄》等作品。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另一个是比钟叔河大三天的朱正。
他们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也是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还是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难友。更难解难分的是,钟叔河研究周作人,而朱正研究鲁迅,他们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适逢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出版界一时风起云涌,而湖南出版界尤甚。钟叔河主持出版了在读书界风靡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而差不多与此同时,朱正则主持出版了在文学界影响很大的“骆驼文丛”。湖南出版能执全国牛耳,以钟叔河和朱正为个中翘楚。
作为一个没读过大学的出版家,朱正的阵地还不单单是出版,他研究鲁迅,同时还研究反右派,曾以一部《鲁迅传略》和一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蜚声知识界。对鲁迅,他从年轻时的崇敬崇拜到正视平视,发现了鲁迅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对反右派,他因为邵燕祥的一篇文章开始研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诠释和还原,抽丝剥茧,条分缕析。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朱正写《鲁迅传略》、给冯雪峰写信指摘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开始,他就和文学界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眼中的杨绛比钱钟书还会写文章,他认识的邵燕祥是“鲁迅、聂绀弩之后最大的杂文家”,他耳闻的萧乾竟然是“那么一个德行”,他接触的丁玲“根本一点都不右”,因为职业和交游的关系,他为现当代文坛保留了一份自己的切身观察。
几个月前,我赴长沙拜访83岁高龄的朱正先生和与他同龄的钟叔河先生。朱正先生非常健谈,与我漫谈往事,细说流年,回忆编过的书、写过的文、见过的人、走过的路。随着朱正先生遥远的记忆和亲切的还原,我从他的写作和出版生涯中了解到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出版生态。
我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海外文学作品被译介出版,而对于劳伦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色情文学”代表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很多出版社想出却无人敢出。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唐荫荪就找时任总编辑的朱正商量,朱正一开始有些犹豫,但看到同事们热情很高,也没有反对。书出来后征订的场面非常壮观,经销商的汽车就在印刷厂门口排队,印好一批拉走一批。
朱正先生说:“后来被查了,闹了很大的风波。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那本书就是我们出了以后,当时热销,印了36万册。当时我们发了一个征订目录,发出去后武汉新华书店没有回信,没有定,等到书畅销以后他们就来人找我们,说他们要进货。我们的人说,‘给你们发了征订目录,你们不来订货,现在没有了。结果他们回去向他们的领导汇报说‘要不到书,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奚落我们,他们的领导很生气,就和熊复反映,熊复写信给邓力群,邓力群批示说要追查。熊复是武汉的,武汉新华书店的头大概认识熊复,是熊复的老部下,他向熊复反映,熊复就向邓力群反映。熊复当时在《红旗》杂志社,影响力很大,他向宣传部反映,邓力群就批了。当时邓力群也不是宣传部部长,但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候。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搞了一个关于‘扫黄打非的展览,内部展区预展时请胡乔木去看,胡乔木看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说你们这样不好,这本书不能分到淫秽读物里,这是世界名著。所以展览就撤下了这本书,后来处分我们时也没说是‘出版淫秽读物,只说是违纪。”
20世纪80年代是出版的黄金岁月
20世纪80年代,由于19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文化思想真空,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非资即社的二元意识形态结构松动,读书不再有禁区,整个出版风气也非常开放。对于那段出版人的黄金岁月,朱正先生十分怀念,也非常感喟,然而却也终究一去不复返了。
朱正先生说:“那时候风气比较好,比现在好。宣传部部长是朱厚泽,他比较宽松,人家叫他‘三宽部长,他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东西有差异的观点都表现得宽厚、宽容和宽松。我不认识他,和他也没有交往,但能感受到那种气氛。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没出很多书,时间很短,做总编辑就一年多,后来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下台了,那是我任内签发的最后一本书稿,出版后我就下台了。现代的编辑水平怎么样很难说,人家要我讲编辑经验,我说我的经验,第一我不能说,第二你不能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稿子,比如说像杨绛他们的稿子,拿来我根本就不用看,我直接下厂去排印,为什么呢?我知道我反正是要看小样的,我能够改她的文章吗?一个字也不能改的。所以说,我就不耽误这个时间了。但能够向现在的编辑去推荐这个办法吗?现在如果不看书稿就直接下厂印刷,那肯定不行。这不单是编辑的水平问题,也是作者的水平问题。现在的作者是什么水平,那时的作者又是什么水平?!”
钱钟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
谈话的时候,朱正先生会时不时从里屋拿很多书出来,他搬出一摞的“骆驼丛书”,一本本给我讲背后的故事。捆书的绳子解开之后,朱正先生一直拿在手里玩,一会儿缠绕在手臂上,一会儿系在腿上,像个闲不下来的贪玩儿童。他爱人看到后说了他一句,朱正先生无辜地说:“等下还要捆书用的。”那些书的作者都是一代大家,朱正先生聊起他们时如数家珍,借着书追忆过去。
朱正先生说:“‘骆驼丛书我一共出了20多本,现在很难配齐了,网上去淘要几千块。最早我到北京去看黎旭,问他有什么稿子给我出版,他有一些短文章,就把这本书稿给我了。我说,如果能够出一系列丛书就好了,他说我这个想法可以,他跟我说,‘你可以去找杨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请杨绛写了两篇材料,一篇写她的父亲,一篇写她的姑母。过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杨绛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找她来拿稿子。那时我刚刚上任,1985年,杨绛给我的就是这两篇,杨绛说,‘我还有一篇稿子《记钱钟书与〈围城〉》,我不想和这两篇编到一起,这两个人都死了,钱钟书还活着。一个父亲、一个长辈,都过世了。她继续说,‘不过那篇只有1.6万字,能够单独出一本吗?我说,‘行,可以出。当时的作者,那都是泰斗级的。杨绛非常能写文章,那是文章大家。学问上钱钟书是大家,但是写小说、写散文,钱钟书不一定写得过杨绛。所以有些人说,钱钟书《围城》那些故事性的情节,很多都是杨绛帮他出的点子。杨绛和钱钟书都不容易,在当时的体制下非常不容易。”
“最大的杂文家”邵燕祥
对于丁玲,朱正先生说她其实比较“左”一点,其实“她是被错划右派,她根本一点都不右,是被错判的”,而对于她年轻时的男女问题,朱正先生笑说那个很自然,“哪管她呢,谁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兴趣,老了就没有这个兴趣了”。因为做出版的缘故,朱正先生和很多文坛大家都很熟,走动往来多了,相互之间开开玩笑,也有很多故事,在他眼里邵燕祥就是一个“最大的杂文家”。
朱正先生说:“我跟邵燕祥熟极了。邵燕祥写了纪念聂绀弩的文章,他说,‘自鲁迅死掉以后,聂绀弩是中国最大的杂文家。我就说,‘聂绀弩以后,邵燕祥就是中国最大的杂文家。当时不是邵燕祥讲‘聂绀弩是鲁迅之后最大的杂文家嘛,我就说在鲁迅、聂绀弩之后邵燕祥就是最大的杂文家。邵燕祥的著作就算不是全部送给我了,大概也有一大半都送给我了——他自己签名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