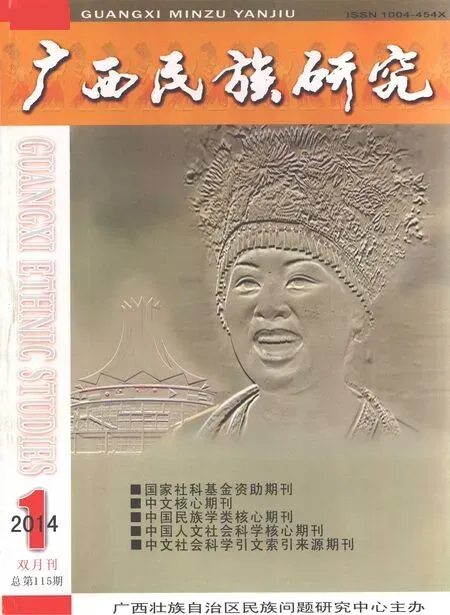壮族传统基层社会亲属与结群的若干基本特征
郭立新
壮族一般被认为发源于原本居住于岭南地区的壮傣语系的越人土著;同时,壮族的形成与汉文化的较深植入有关。①谷口房男、白耀天认为壮族是在汉族文化摄力圈内形成的。[1]45-46汉文化的植入,一方面使其族群独立性趋于淡薄;另一方面,由于其强韧的种族个性,又与汉族之间有着一定的界线。[2]68不同地区的壮族文化,又由于各自生态条件、历史过程以及与周边族群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其文化图景较为斑驳,较难找出全族共有、与汉族不一样的文化“色调”与“图谱”。[3]①覃德清把这幅斑驳景象称之为“非整合性”[4]33-39。一些学者则认为这说明壮族文化的“断裂”[5]59-61。这种复杂情况使任何欲对壮族文化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者颇感两难。或“以汉说壮”,认为壮族文化比较接近汉文化,壮族民族特色不显著;而若想对壮族文化特征说点什么时,不得不面临将壮族某些较为常见的地域性文化特征说成是整个壮族的文化特征的处境,而这种做法有时难免需要面对以偏概全的指责。虽是如此,这种研究对于理解壮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仍十分必要;特别在讨论一些较为深层、抽象和稳定的地域共同传统时,基于个案的综合比较和跨区域的整体性论述仍不可或缺。
一、文献回顾
在以往关于壮族社会亲属与结群的研究中,大多注重于父系继嗣原则、宗族范式的探讨以及进化论的解释框架,本土社会结构常在外来分析范式的偏见中淹没不显。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的作者们就开始运用宗族概念来描述壮族的家族和家庭形态。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指出:龙脊壮族“家族家庭的关系,是依据父系血统的远近亲疏、三代以内称为房族,三代以外称作门族或宗族。”[6]111“每个宗族和同一宗族内各个支系,有一个或几个类似族长的人物。……宗族对它内部成员的主要行为负有一定责任。”[6]112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通过壮泰和壮汉文化的比较,将父系血缘和宗族制度视为壮族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7-8]如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课题组认为:壮泰虽然同源,但“壮族人和汉族人一样,从宗族和家族两条线来确定亲戚关系;把祖宗视为关系的中心,采用父系姓氏;同一宗族、家族的成员供奉同一个祖先。而泰族在划分亲属关系时,以自我为中心,独立于宗族中的其他人,以尚健在的父亲和母亲来确定双系亲属关系。”[8]3237学者们大多认为壮族父系宗族制度特征的出现与汉族社会的影响有关,反映这种影响的证据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9]汉文化最有可能施加影响的途径或壮族汉化的方式,首先是地方首领和土官夤缘攀附汉人,民众从之。[1]30明清时期,在中央王朝的要求和土司们的主动攀附下,壮族土司官族的封建宗法形态达到顶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族长官位和财产宗法式的世袭继承制以及祠堂、族规、家谱等文化表现形式。[10]
一些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壮族基层社会仍保存了较多不符合父系血缘原则和宗族制度的习俗,如体现了两可继嗣原则和血族制度的招赘婚盛行[11-12],反映妇女在婚后享有较高自由度的“不落夫家”习俗等。[13-15]黄兴球[16]、覃成号[17]从这些习俗的变迁中看到了宗法制度在壮族社会的地方化过程(与国家化相对应)。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早年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将这些习俗视为壮族母系社会对偶婚的残余形式[18-19],类似的解释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黄家信的解释另辟蹊径,他认为桂西入赘婚俗盛行的主要原因有四:地旷人稀,人口密度小;血缘组织不严密;女多男少的性别比;男女关系的平等无嫌。[20]虽然所谓的人口密度与性别比例两个原因,迄今并无民族志和统计学证据的支持,但黄所说的血缘组织不严密,指的应该是父系宗族组织原则并未真正成为壮族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注意到这一事实以及壮族社会男女相对平等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说明壮族社群建构的真正原则很有可能不是所谓的父系血缘继嗣,而另有自身的逻辑。郭立新结合在龙脊壮族社会的调查,认为所谓父系血缘与母权、两可继嗣并存格局的形成,是壮族地方社会在国家化过程中产生的“汉表壮里、多重混杂文化景观”;以宗族范式研究壮族亲属制度,很容易产生“以汉说壮”而不顾壮人社会实际情况的误解。[3]
壮族亲属制度与社会结群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以亲属称谓为基础的。语言学家的作品重点描述壮语亲属称谓的语言学特征[21-22],其他一些研究则致力于通过壮语亲属称谓与汉语亲属称谓、与泰/傣亲属称谓的比较,明其异同,藉此讨论各自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如汉对壮的影响,壮与泰之间的渊源。[23-26]何霜根据壮语、泰语亲属称谓的差异,进一步比较了其婚姻形态的差异,并提出这种差异反映了壮文化与汉文化、泰文化与印度文化、壮文化与东南亚其他文化的深度关联。[27-28]亦有一些论文试图透过亲属称谓来考察壮族文化特征。李富强较早注意到壮族亲属称谓的一些“原始”特征:如母系父系不分、直系旁系不分,称谓随着年龄和角色的变化而变化;以及一些地方性特征,如排行顺序的称呼、以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有收养与打老同的习俗。[29]黄平文直接把“混称”(亲属称谓融合)视为普那路亚婚(对偶婚),将同辈之间“嫡旁”系不分作为血缘婚的证据,又从复合词的构词法中解读出“父权制”的观念。[30]这种简单套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社会进化论观点来释读亲属称谓的做法,在其他论文中亦屡屡见到。[31-32]
魏捷兹主持的从1998年开始的“云贵高原的亲属与经济”计划(与之相关的还有何翠萍主持的“交换、生命仪礼与人观:中国西南族群区域研究”计划)①这两个计划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主题研究计划“亚洲季风区高地与低地的社会与文化”(蒋斌为总主持人)的子计划。后者包括4 个子计划,除了上述2 个子计划外,还包括蒋斌主持的“进口珍品与社会阶序:砂劳越Baram 河流域的内陆与海岸族群”,潘英海主持的“文化合成:台湾平埔族群、华南畬族群与汉文化互动的比较研究”。整个计划涉及的区域包括东南亚、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的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区。参加“云贵高原的亲属与经济”、“交换、生命仪礼与人观:中国西南族群区域研究”子计划的研究者来自台湾清华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和贵州大学。研究者各自开展田野调查,并在主持人的组织和召集下,定期召开小型学术会议,就特定议题展开讨论。,开始突破宗族范式和进化论模式,将20 世纪90年代在国际上和台湾人类学界兴起的亲属研究范式引入到壮族亲属制度研究中。这项计划从亲属称谓的调查、分析与比较着手,进而探讨土地和家屋对于壮族社会建构的重要性。与宗族范式重视继嗣不同,魏捷兹等强调婚姻在西南中国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33],并关注国家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如土司制度)对于壮族地方文化的影响。何翠萍则从日常生活与仪式展演、人观与家屋的角度论述中国西南地区相关族群亲属伦理的关系模式,探讨亲属与人观、性别、仪礼、空间、交换、冲突与权力的关系,为研究者观察和分析壮族亲属制度提供了富有启发性和洞察力的概念工具。[34-35]参与这些计划的研究者,大都基于各自的田野经验,从不同角度探讨壮族社会亲属制度的内在逻辑。[3][36-40]总的说来,这些研究以更具本土性和整体性的眼光来理解壮族亲属制度与社会结群行为。
通过比较各地壮族的调查与研究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异中求同的中心型社会结构、养育的人观和以地域社群为社会构成出发点三个方面,构成了形塑壮族传统社会亲属制度和社会结群的基本结构。壮族亲属制度与社会结群的诸多地方性特征,大体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以及在文明化进程中所受儒道文化和父系亲属制度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影响中得到理解。
二、异中求同,合二为一的中心型社会
关于壮族及其先民的记载中,有产翁制、男逸女劳、招赘婚、两可继嗣、同姓通婚等习俗。招赘婚、两可继嗣已有学者介绍,此不赘述。[3][11-12]而产翁制、男逸女劳等在外人看来常常令人费解。
据宋代《太平广记》卷483 引《南楚新闻》记载:“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同样的习俗亦见于与壮同源的傣族中,如《马可·波罗游记》载:傣族“妇女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40 日。卧床期间,受诸友庆贺”。清勐寅《顺宁府记》载:傣族先民“生子三日,贵者浴于家,贱者浴于河,妇人以子授夫,已仍执焚、上街、力田、理事。”“产翁”在模拟“分娩”时,要哼哼呀呀,装出一副十分努力、痛楚的样子。待小孩出生之后,戴起头帕,捂严身子,生怕中风得病。然后,抱起婴儿,模拟给孩子喂奶。
关于壮族先民男逸女劳的习俗[41],从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到近代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皆有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观察者常诧异于壮族先民妇女居然做着那些在他们看来应该是男人才能干的活。诚如民国时期《思恩县志·社会》所言:“女子……才力亦不让于男子。凡农事工作,男子所能者,女子尽能之,且襁负其子作工于烈日苦雨中,较男子为劳。……兼能营商贸易,每墟场赶墟之人,男女各半。外来人骤然视之,颇诧异。”
在戴着有色眼镜的外来观察者(以汉人为主)眼里,这些习俗被当成奇闻加以记录,并在社会进化论的解释框架下,被学术界一度解读为原始母系社会的残余。笔者以为,这些习俗所体现的其实是壮族及其先民社会文化最深层的结构性特征之一,即将女人和男人看成是一个样,无论在社会生产还是在社会再生产中,都尽力抹消男女之间的差别,不以男女之间的差异为异,对男女一视同仁。[3]
若将这一观点放入到埃灵顿(Shelly Errington)关于中心型和交换型社会两种认知模型中进行分析,可以将其特征看得更清楚。埃灵顿通过对家屋社会中同胞关系以及婚姻交换形式的比较,将岛屿东南亚社会划分为中央岛群的中心型社会(concentric)和东印度群岛的交换型社会。其群体建构的逻辑目标,前者表现为“二分中心型”(dualistic centrism)的“同”与“统合”,后者为“中心二分型”(concentric dualism)的“异”与“交换”。[42]何翠萍分别将其归纳为“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此二类型的共同点是他们在终点上都预设了一个统一的、静止的、男女合体的理想的“家屋”的形式。但具体到解决再生产的问题时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在前一逻辑中,男女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的,异性之间只有出自同一家屋的同胞才是最理想的同构关系(孪生同胞又是理想中的理想);在兄妹乱伦禁忌的约束下,需要不断在婚姻中将夫妻变得类似于兄妹之“同”。后者则预设有男女同质的逻辑起点,需要将同构程度高的兄妹不断分开来,把姐妹嫁出去再从别处娶入妻子,通过不断的交换为同质的家屋增添“异”的力量,以完成一个家的绵延。[35]302-303
壮族属于二分中心型或异中求同型社会[3][35],家屋作为一个生命体具有男女统合的意象[43]。埃灵顿认为:中心型社会为达到求同的理想而尽力泯灭、模糊各类社会区分范畴如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性别之间的界限,漠视这些差异而着重强调相似与统合。[42]408-422在龙脊壮族社会中,虽然认为男人的劳动和女人的劳动是有差异的,对家的养育必须有男女间的劳动合作,但龙脊壮人并不把男女劳动分工建构为“男人干的活”和“女人干的活”。将夫妻关系当成兄妹关系的逻辑,直接影响了其继嗣和婚姻策略。虽然龙脊壮人模仿汉人使用汉姓、建立了班辈制度、植入过父系制,但传男或传女均可的两可继嗣仍然大有存在土壤,也从来没有因汉人同姓不婚的禁条而禁止系谱位置较远的“兄妹”之间的通婚。[3]通婚不避同“姓”和近亲通婚等内婚制度(一定辈分之外)被认为是壮族婚姻的重要特征,这里包含的逻辑是:在自己人中找对象,远比在陌生人中寻找更容易变异为己,合二为一;与此同时,通过与继嗣群边缘位置的人群的联姻,还将群体边缘亲属重新拉回到中心,起到强化群体认同和团结的作用。
中心型社会以异中求同为目标的亲属和社会整合策略,不但体现在诸如婚姻、继嗣和劳动分工上,还体现在政治上。埃灵顿分析了中心型社会建立权威的策略,认为中心型社会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有关的-欣慰的-有帮助的-同盟者-“我们”,和无关的-敌对的-可怕的-靠不住的-“他们”。在“我们”的世界中没有对“他们”的分类和认知,“我们”要么对“他们”视而不见;要么联合起来对抗“他们”。[42]415-417在这种社会中,中心一方面被视为不可分割、不能挑战、不可挑战的;却同时又允许存在不同层次的中心:大中心(或霸权中心)和小中心。“家屋或社群要么倾向于和整个社会相一致以期如印式国家一样完整、自治,要么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弥散扩展而没有清楚的边界。”[42]405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社会主体而言,在前一情境中要求向大中心靠拢求同,形成向心运动;在后一情境中却让自己本身变成为一个中心,努力让有关者向“我”靠拢求同;在“我”并不是大中心的情况下,向我靠拢意味着对大中心的挑战与分离。每个中心都可以通过制造话题和展演仪式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讲述生活的典范样式;彼此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展开竞争,被认定代表了社会典范的中心就成为大中心(霸权中心)。[42]436中心之间的竞争是通过对其边缘的影响力来达到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需要通过持续互动来维持,中心要不断证明其合法性,而边缘的效忠也需要持续地被检验,这使群体边界总处于持续的扩张与萎缩过程中。①用这种范式来观察历史上的壮族及先民与中国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很意思的,也可以用来回答白荷婷的部分质问。[44]埃灵顿还以伊班(Iban)和托努乌(Toluwu)两个族群为例,指出在这种社会中同胞/同伴的重要性、血族或两可制特征、系谱知识对于结群的重要性、我群的扩张与求同的理想、亲从子称、用植物比拟亲族关系等特征。[42]408-422
异中求同的中心型世界观,使壮族更倾向于强调团结和整合,而不是强调区分和差异。长期作为中国中原王朝边陲社会的经历,使壮人将后者异化为一个想象的花园,并作为其孕育力的来源,在此框架下,逐渐形成了养育的人观。
三、养育的人观
壮族的花园信仰和花文化、缓落家(或称“不落夫家”)①笔者认为,“不落夫家”这一个术语不准确,实际上,非不落家而是暂缓落家,所落也不一定是夫家,在两可制里可能是妻家。所以,“缓落家”这个术语更能准确地描述与反映这一习俗,并避免了从夫居说法可能带来的歧义。以及无性家屋等习俗具体呈现了在传统社会中壮族及其先民的亲属与结群逻辑中的养育人观。
各地壮族普遍存在关于花的信仰。过伟提出存在一个花文化圈。他认为壮族创世大神米洛甲被视为“花婆”或“花王圣母”,壮族生育风俗围绕着“花婆”展开。[45]邵志忠认为:在花王圣母崇拜中,人类是从花园里来的,死后又返回花园。[46]高雅宁细致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靖西壮族魔婆所主持的花园仪式和相关的花园信仰和实践的各种细节。[38]
缓落家指结婚以后到女方怀孕这段时间,嫁出方长期仍住在自己父母家,只偶尔到配偶家生活数天,一直到女方怀孕后,夫妻双方才开始长住在娶入方家中。缓落家期间,夫妻双方的交往自由,各地存在从完全不受限制,到受到严格限制不允许与配偶以外异性交往的差异。关于这一习俗的记载颇多,[41][47]如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广西僮人当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合,既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后始称为妇。”
此外,据历史记载,一些地区的壮人还有家屋无性的观念,忌讳在家屋内有性行为,甚至夫妻亦需异室而居,房事需要在野外进行,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对于上面三种习俗,论者大多以生育崇拜和母系残余的观点加以解释,但这一类解释显然难以说明行为背后的真正动因。对缓落家和夫妻异室等习俗的田野调查表明:无论是在怀孕之前,还是落家生育之后,夫妻之间都有对性生活进行回避的取向。[38]249-250[48]18笔者认为,这种回避取向只不过是花园信仰的另一面而已。既然已经通过建构一个想象的花园并把它作为生命孕育力的来源,孩子只是花园送来的,那么夫妻之间的结合即婚姻的价值就不再是性与生育,而变成为养育从花园里送来的“花”——孩子。所以,只有当孩子出生,婚姻才算是正式确立②这一观点最先由塚田誠之提出。[47]在龙脊壮族中,由于婚姻要到孩子降生才正式确立,所以嫁妆一般在给小孩办三朝时才送过来。,才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家。这才是缓落家习俗的真正原因。这个家是干净的、无性的,夫妻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共同的劳动,抚养小孩,照顾家。[3]184-192
在养育成为婚姻和成家的理由的同时,它也成为人们结群认亲的重要依据(通过养育认亲并不排斥通过血缘认亲,实际上,在壮族社会中,养育认亲与血缘认亲并行不悖)。此外,养育的人观还使得作为养育基础的劳动除了具有社会生产的价值之外,更获得了社会再生产的价值。长期稳定的共同劳动关系和共同生活(吃住在一起),亦可以象血缘关系一样成为认亲的依据。
养育的人观还突显了不同的食物在建立、表达和区分人的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或群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方面的象征价值。在壮族传统社会,不同形式的米(生米、熟饭、糯米、稻谷、禾把、谷种等),肉和酒等食物,是亲属群之间仪礼交换时最主要的礼物。高雅宁对靖西壮族的研究表明:米、肉和酒等礼物盛于一种竹编容器中。在平时的礼仪往来中,当这种容器成对使用且封闭起来的时候,就起到沟通不同家屋的作用;单独使用且不用盖子的时候,隐喻着家屋。这种容器里所装的食物有生有熟,送礼时米是生的,糯米可生可熟,肉一定是生的,回礼时都变成熟的;在此,生的食物象征的是生育力,熟的食物代表着生育力转化成的人。米饭是构成人体最基本的食物,糯米与肉则是祖先与神灵的食物,有强化精神方面的作用;米饭强调的是个人的食用,肉则强调全家、几家和全村的共享,糯米则只有在要建立特殊关系的人或者已经有特殊关系的人之间赠送。随着生命历程不同的阶段或者节日的不同,所吃的米与肉还有种类和部位的区别,比如,平时吃大米,过节才吃糯米饭;人刚死的时候,糯米饭与大米饭都可以供,一旦成为祖先,就只能在过节的时候享受糯米饭或糯米制品;吃鸡和鸭的时候,小孩吃腿,老人吃肝和屁股等。[39]1-62
同样的情况亦见于郁江北岸的壮族社会和龙脊壮族。潘春见的研究表明:在郁江北岸壮族社会中,稻米是亲属社会的文化承载者。在生命仪礼中,由特定亲属赠送的稻谷、白米和其他米制品,是成功塑造人体/家、解构人体/家、重构人体/家的亲缘合力。稻米的流动与象征是形成亲属社会的重要条件。在生命仪礼中,来自后家的稻米具有让体/家屋生殖繁衍、生生不息的能力;来自虚拟性父母的稻米具有让体强壮,让体/家屋的生命特质得到理想改造的能力;亲属间流动的稻米具有祝福、吉祥,促进家屋兴旺再生的能力;流动的谷种具有成就新家、促进新家兴旺发达、绵延不绝的能力。稻作农耕是形成亲属社会的重要基础,劳动与仪式中的性别分工与合作可以打造生命,打造家。米饭的共食与分食,是社会结缘认亲的基本法则,也是形成家屋、村落、他群与我群,建构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49]69
在养育人观的意识形态中,亲人们更倾向于吃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亲人们“生活在一起”这种理想包含了社会空间的内容,空间和地方成为结群认亲的重要依据,那些仅有血缘联系但不在一起生活的人,会逐渐失去结群认亲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可以观察到的是,壮族基层社会的构成不是以父系继嗣为出发点,而是以地域社群为出发点。[33]427
四、以地域社群为社会构成的出发点
壮族社会一般也会有自己的家族谱系和类似于父系的血缘记忆,有一定的禁婚范围。但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很多壮族社会,家族谱系的建构、家族或家门等继嗣群体的形成以及关于通婚范围的规定,都体现出高度的弹性,具有浓厚的视情境而变的策略色彩。
张江华对田东洼地壮人的世系群、婚姻和村落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当地虽然声称实行父系继嗣制度,但父系继嗣群只有嵌入到村落共同体中才有意义,跨村落的、即便能追溯到共同的父系祖先也未必确认为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同时,只要有需要,继嗣关系可以转换为联姻关系,将同一个地域范围内同一父系血缘的人群分裂成彼此通婚的社群;这种情况使得父系血缘组织在构成上有相当的灵活性和策略性,通常并不严格遵守父系谱系原则,诸如收养关系等也可以进入世系群之中。在这里,父系原则并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父系连带关系,从而整合更大范围内的人群,反而只作为一种父系关系资源,在一个地缘范围内策略性地使用。与继嗣相比,婚姻成为社会结合更重要的手段,当地的内婚制以一种普遍交换的方式展开,不断地将逐渐疏远的父系亲属又用联姻的方式重新拉近距离。无论继嗣还是婚姻,两者的相互为用都是为了构成一个地域性的共同体。虽然这种共同体可能跨越相邻数个村落,但只有村落才是最终、稳定而强有力的社会单位。[33]426
桂北龙脊壮族中部分人虽然声称也实行父系继嗣,但其家系实际上更接近两可制,其操作的灵活性更甚于田东洼地壮人。这里每个家庭都有由不同辈分的男性名字组成的谱系记忆,但是,这些男人之间的继承关系,除了血缘上的父子关系外,还有大量的收养和翁婿关系。由于这些收养和入赘的男人都必须根据新的继嗣位置改变姓和班辈名,所以,最后形成的家族谱系链条,在形式上很像父系继嗣。
汉人的“姓”是父系血缘共同体的标识符号。壮人的“姓”虽然模仿自汉人,但其内涵却有相当不相同的意味。在壮族历史上,经常出现百姓追随首领姓氏而形成“举峒一姓”的现象[50]31,显然在此情境中所谓的“姓”更多地被用作为地域集团的符号。①这种将“姓”与“地”而不是与“血”相联系的现象,亦可以在民间故事中找到。如在壮族地区广泛流传的《布伯的故事》讲到:伏依兄妹结婚生下一坨肉,便用刀剁碎,拿到野外去撒。肉撒到什么地方,那里就是什么姓(或民族),如贴在李树上,那村庄的人就姓李;贴到石头上,那村的人就姓石。正因为如此,在生活实践中,改姓也是件比较容易的事。对于龙脊壮人而言,将本寨的姓和班辈字派给嫁入的男人,含有接纳和认同的意味。由于婚入获得新的身份而改变原有姓和名这类社会身份标识符号的做法背后,显示的是一种将个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在地化处理的逻辑。通俗地说,就是到哪家山唱哪家歌,就是哪家人。“山头”或区域是不变或较难改变的,人则可以在其间流动。
这种方式一方面突显了地方性居住共同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通过单系血缘联系建立超大型跨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境下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的规模,便深受地理生态条件的制约。据黄现璠、覃晓航、覃成号等人考证:“壮”源于“僮”,后者又为“峒”之音转。峒与溪常并称为“溪峒”,是岭南地区典型地貌,指四周或两边为山,中通一水的山间小盆地或峡谷地区。汉文献中所谓“峒丁”、“峒民”指岭南地区居住于此类区域的土著,他们是壮族的重要来源。[51]9[52][53]106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溪峒稻作之民在各自地域范围内整合成为一个个小型的地方社会。由于华南地区,特别是壮族集中分布的桂西地区单个溪峒面积一般都不大,使其地方社群规模都偏小,又缺乏强有力的跨地域的亲属组织手段,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壮族先民发展出更庞大和更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五、小结
中心型社会求同的世界观、吃住在一起的理想以及地方化的结群方式,使壮族群体存在一种向心力,在这种作用力的牵引下,地方共同体倾向于向内收缩,并导致超越村落之上的社会共同体极不稳定。另一方面,基于通婚、向外寻求安全合作和劳务合作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则激发出群体内部的离心力量。使这两种力量达成平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保持合宜的群体规模来实现的。如龙脊壮人的继嗣群体——家门,就是一个操办和承担礼仪活动的组织,当家门规模远远超出或小于操办仪礼与人情往来所要求的劳务的合宜大小时,就可依家系或分或合,进行重组。正是从这种群体分分合合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壮族社会结群所具有的弹性、权谋与策略,看到其继嗣与婚姻规则背后隐含的工具性色彩。
本文虽然指出壮族结群认亲具有地方化和小型化的特征,但并不支持白荷婷关于壮族在1949年以前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文化特征的论述。[44]本文已说明部分壮族传统社会具有某种共同的深层结构。笔者以为,形塑这种共同结构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于壮族及其先民共同生活的岭南这一区域内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地域传统,如普遍存在于南岛语族和壮傣族群中的中心求同型世界观和地域化特征。另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国家化的力量,不断将岭南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文明历史进程的持续的努力,这一进程从秦帝国建立伊始就开始了,时间跨度远远超过白荷婷所研究的范畴。壮族地区曾长期通过土司这种中间代理人统治的方式,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了初步的地域整合;同时,儒家和道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汉人的父系亲属制度,也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到壮人及其先民社会中,对推动壮族群体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谷口房男,白耀天.壮族土官族谱集成[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2]塚田诚之.明代壮族的迁徙与生态[J].广西民族研究,1987(1).
[3]郭立新.折冲于生命事实和攀附求同之间:广西龙脊壮人家屋逻辑探究[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1/2).
[4]覃德清.论壮族传统文化结构的非整合性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1992(3).
[5]夏雨.壮族文化讨论综述[J].广西民族研究,1988(4).
[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7]钱宗范,梁颖,等.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1997.
[8]覃圣敏.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9]周艺.从上林县唐碑唐城看唐代桂西南壮族先民的宗族特征[J].广西地方志,2005(2).
[10]李全伟.试论广西土官官族内的封建宗法形态[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11]李甫春.驮娘江流流域壮族的欧贵婚姻[J].民族研究,2003(2).
[12]莫俊卿.融安县壮族婚俗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1990(1).
[13]潘其旭.壮族“不落夫家”婚俗初探[J].学术论坛,1981(2).
[14]范宏贵,谈琪,顾有识.壮族“不落夫家”的婚俗[J].社会,1984(4).
[15]赵周贤,张江华.一个“不落夫家”壮族社区的生育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6).
[16]黄兴球.从广西壮族民间婚姻形态看宗法制度及其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17]覃成号.试论族权对壮族传统婚姻制度的影响[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3).
[18]卢敏飞.桂西壮族原始婚姻形态残余剖析[J].广西民族研究,1989(2).
[19]赵明龙.桂西壮族“入赘”婚俗初探[J].广西民族研究,1986(2).
[20]黄家信.广西壮族入赘婚俗探因[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21]郑贻青.靖西壮语亲属称谓探究[J].民族语文,1994(6).
[22]蓝利国.壮语拉寨话亲属词的语义成分分析[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23]罗美珍.从语言上看傣、泰、壮的族源和迁徙问题[J].民族研究,1981(6).
[24]梁振仕.略论壮语与汉语的亲属关系[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
[25]潘其旭.从语言上看壮、老、泰的历史关系[J].学术论坛,1990(4).
[26]张江华.汉文献中的壮傣民族亲属称谓[J].广西民族研究,2002(4).
[27]何霜.壮语和泰语的亲属称谓看壮、泰两族的婚姻形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28]何霜.壮语、泰语亲属称谓之文化内涵[D].南宁:广西民族学院硕士论文,2002.
[29]李富强.壮族的亲属制度[J].广西民族研究,1995(3).
[30]黄平文.壮族亲属称谓的社会文化透视[EB/OL].(2006-06-30)[2013-12-17]壮侗语言文化网:http://zhuangdong.gxun.edu.cn/Docment/ArticleShow.asp ArticleID=459.
[31]尚东.从壮族亲属称谓看原始壮人普那路亚婚的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增刊).
[32]黄美新.大新县大岭壮语亲属称谓的文化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7.
[33]张江华.广西田东洼地壮人的世系群、婚姻与村落的构成[C]//张江华,张佩国.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34]何翠萍.云南景颇、载瓦人的丧葬仪礼及“竹”与“家屋”人观的形成[C]//“生命仪礼与人观:中国西南族群区域研究之一”小型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7-05-02
[35]何翠萍.人、家屋与阶序:从中国西南几个族群的例子谈起[C]//张江华,张佩国.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36]张江华.人群关系的内卷:广西田东县立坡屯POU33RUG11 的个案[C]//魏捷兹.云贵高原的亲属称谓.台北: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999.
[37]张江华.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5).
[38]高雅宁.广西靖西县壮人农村社会中ME214MO:T31的养成过程与仪式表演[M].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
[39]高雅宁.?EN1KJONG5、米、肉与靖西壮人人观[J].民俗曲艺,2005,150.
[40]郭立新.劳动互助、仪礼交换与社会结群:广西龙脊壮族村落的社群结构分析[J].社会,2009(6).
[41]杨东甫.笔记野史中的广西土著民族“男逸女劳”与“不落夫家”之俗[J].广西文史,2009(4).
[42]Shelly Errington.Incestuous Twins and the House Societies of Insular Southeast Asia[J].Cultural Anthropology,1987,2(4).
[43]郭立新.打造生命:龙脊壮族竖房活动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4(1).
[44]Kaup,Katherine Palmer(白荷婷).Creating the Zhuang:ethnic politics in China[M].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45]过伟.壮族创世大神米洛甲的立体性特征与南方民族“花文化圈”[J].广西民族研究,1999(1).
[46]邵志忠.生殖崇拜与壮族女神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1997(1).
[47]塚田诚之.广西壮族的婚姻习俗“不落夫家”之历史研究[C]//覃乃昌,岑贤安.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
[48]吴国富,范宏贵,谈琪.靖西壮族社会文化的人类学考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增刊).
[49]潘春见.郁江北岸壮族农村的稻米与亲缘[J].民俗曲艺,2005,150.
[50]白耀天.壮族姓名演变轨迹考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51]黄现璠.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52]覃晓航.壮族族称“撞”、“侬”、“狼”来源新探[J].民族研究,1990(1).
[53]覃成号.壮族族称缘起新论[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