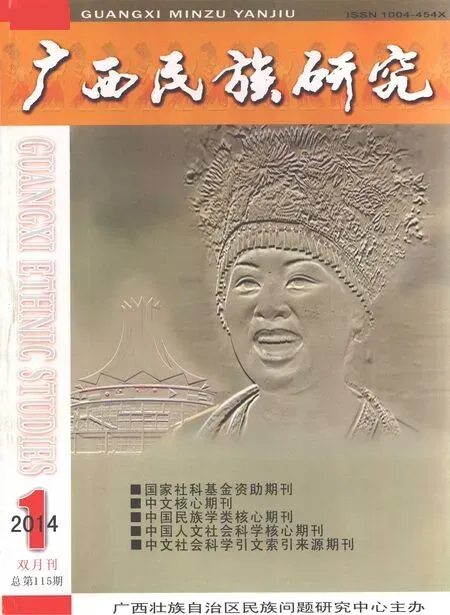水的文化隐喻及认同变迁:西江流域水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王易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历来作为重要的象征物存在,有关水利的民俗志记载不胜枚举。与世界上的丰水国家相比,我国的水资源相对有限,但却因合理用水、有效节水的用水习俗和用水管理机制而创建了灿烂绵长的农业文明。而这一习俗及机制的主要成效,其实质来自于与水相关的历史记忆、禁忌习俗、信仰仪式等文化概念图式所体现的对水的象征性管理。水在当地社会的文化隐喻延续了地方民众对水的历史认同,从而形成一种把水视为非物质文化的生活方式,保证水资源生态环境的持续和谐。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着眼于短期私利,对水环境大力改造开发,过分扩大用水目标,“水成为政治利益、经济垄断和文化景观的奴隶。”[1]155这一行为的隐性后果就是凸显水的自然性、商品性,销蚀了水的历史性、文化性,从而破坏了亲水、爱水、节水民族对水的历史认同,从崇拜认同到开发利用的水观念的改变最终导致了水资源的污染、浪费、紧缺等生态危机。水危机的出现不仅有自然生态的或技术的原因,更可能是水观念变迁等文化性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急速的技术变革并未能解决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因此,对水的文化隐喻的当下研究有助于强化人们对水的历史文化认同,重塑人们的水观念。本文以西江流域一村落(C 村)的水文化图式研究为切入点,以丰水社区的用水习俗和水观念引导反思。
C 村坐落于浔江(西江的上游,桂江与浔江在梧州汇流后为西江)流域中段的一个江心岛上,四面环水,人口密集,自明代以来由广东、湖南两地移民迁徙聚居而成。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C 村地方社会形成了一套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习俗机制和文化体系,凸显出独特的地域特征。
一、水与村落的民间信仰
在C 村村民有关水的文化概念图式中,水神信仰最为混杂多元。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大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在庙宇重建中恢复有关水神的历史记忆,完成水神信仰传统的循环与再生。以官方祭典中的真武大帝、华光大帝、龙母等为主神,掺杂进由历史人物演化而来的水神(屈原、周瑜等)及祖先神、行业神混杂起来的神灵(洪考先师等)。
C 村有两座比较著名的供奉水神的庙宇:一是里水的真武观,以真武大帝为主神,庙会日为六月初六。真武帝也称北帝,诞期在九月初九,道教中的司水之神,在两广地区广为奉祀。观内还供奉有洪圣公(洪考先师)神像:洪考先师原是广东九江鱼苗装捞户的祖师爷,清代一些装捞户迁至长洲落户,也带来敬奉洪考先师的习俗。其神位寄于真武观。民国年间,真武观、五通庙神像出游,其神位排在两庙的主神神像之后。另有三国历史人物周公瑾也被奉为水神,属庙宇重建后新增的神灵。对周瑜的奉祀应是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再塑造,应需而生,具有随意性。另一个是渡口旁的五通庙,以华光大帝和屈原为主神。该庙建于明朝中期,已有500 多年历史,曾是西江沿江一带最古老的庙宇之一,历来香火鼎盛,每年都举行一次盛大的庙会。“文革”期间曾被拆毁,庙址被公社借用。改革开放后,村民自发捐款14 万元赎回庙址重建。华光帝本是道教中的火神,长洲四面环水,常有水灾风灾,当地人敬奉他以火镇水,是当地的火神与财神,后来也被尊为西江航道上的保护神。其诞期为九月二十八日,庙会日为九月十六日。屈原被奉为湖南大人,是村落的江神、河神。五月初五日是祭祀屈原的日子。按旧时传统,以抬小菩萨游河的方式来祭拜江神,有庙宇组织祭祀和村落自组织祭祀两种方式,村民各户将祭包集中放进大纸船内,晚上在码头河滩一齐烧掉以送走灾难病痛,保一年平安。
在西江流域,龙母传说历来被推崇,龙母水神崇拜文化的根源首先应在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2-4]概括而言,应是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西江捕鱼的经济生产方式与流域水道的航行优势;掘尾龙的传说与频繁的洪水灾害;秦始皇所代表的中央权威与边陲地区的国家观念等。清代《苍梧县志》记载了梧州的三座龙母庙:一在城区大校场;一在城北桂江畔;一在长洲滨江。[5]滨江的龙母庙现位于C 村相邻的J 村,民国时期被毁,1993年重建,供岛上居民拜祭。C 村与之相距甚近,因此本村也一直没有另建龙母庙,但历来均将龙母视为河神、江神之一,通常和其他水神与祭共享。
除上述四位主要的水神外,村民还在每年的端午前举行祭祀浔江江神或河神的仪式。当地的江神水神是一复数概念,无确定的数量,也没有具体的偶像和固定的祭祀地点,一般在端午前几天(通常是五月初一)举行,避免与屈原的祭拜时间冲突。其祭仪由村民自行组织,通常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河滩地为祭仪场地。
对于村民而言,水神出身来历及其神像本身对他们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人们看重的并不是偶像的本身,而是看重偶像的保护作用。村民普遍认为信奉神灵能“旺本村地方、求平安”,“丁财旺盛、六畜兴旺、年年顺景”。把各种宗教神灵、民间信仰的神灵相互杂糅组成多元的信仰体系,源自于村民所处的濡化环境:水并非普通的自然物质,它具有一定的神秘性、神圣性,水的控制与管理往往是象征性的权威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村民对这一权威的解释是,凡是以这些水神名义所进行的捐助和集资建设都没有不成功的,这已成为村民的普遍共识。
二、水与过渡礼仪
在多样化的地方民俗中,水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地方宗教仪式中,水通常作为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或者是强调其净化功能。但在C 村,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通过仪式上,水常常作为一种身份转换的媒介,帮助人们顺利通过各种关口。范·盖内普(Van Gennep)在《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一书中说明了通过仪式(也称为生命仪礼或过渡礼仪)对于社会整合的功能性意义。它指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中,需借用一系列仪式活动进行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变更与转换。所有的通过仪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阶段模式:分离(separation)、边缘或阈限(margin or limit)和聚合(aggregation)。不同阶段受礼者的身份由分离——模糊——稳定完成去旧迎新的过程。在当地,通过仪式主要有洗三、入社、婚礼、丧礼等,而水在这一系列通过仪式过程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人需借助某种形式的用水才有助于完成通过仪式中的三个阶段,完成身份的演变,获得新的社会位置,从而度过人生危机和社会危机。
(一)洗三朝
婴儿刚出生时,由接生婆(当地人称“烧火婆”)剪断脐带,将婴儿身上的血水污迹稍加擦拭便包裹起来,并不会直接给新生儿洗澡。并不洁净的身体上穿戴着事先准备好的衣物,直接抱给婴儿的母亲或家人。直到第三日,才特地选吉时举行洗三朝仪式,以祛除从娘胎带来的污秽不洁。洗三朝的汤水用柚叶、艾叶和老姜熬就。由接生婆娘或家族中有福气的老婆婆给婴儿洗澡,脱掉襁褓,先用柚叶略浇些水到婴儿身上,用手拍打他的后背和前胸,让他有个适应过程,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入还漂浮着几片柚叶、姜片的大盆热汤中,拿柚叶或毛巾布条擦拭身子,不用其他任何洗浴品。一边洗,一边念诵喜歌。前来祝贺的外祖母等人拿着银钱、喜果等东西放进澡盆里,叫“添盆”。放入红枣时念“早立子儿”,放入莲子时说“连生贵子”。洗过的婴儿再穿戴好外祖母“睇三朝”送来的衣物。据说,经过此番洗浴,便可不生疮疥,健康成长。洗三朝的仪式并不是从纯粹的现代卫生角度而言的,这一象征性的洗浴仪式主要是表示新生儿完全脱离了胎儿期,从此可以拜祭祖先,面见至亲,正式开始自己的新人生。
(二)泼水、吹水与第一挑水
在新娘迈出娘家门槛的第一步起,就处身于一个身份模糊的边缘或阈限阶段,既不属于娘家人,也不属于夫家人。在此阶段,急需借助一些重要媒介来保护娘家、新娘的安全。这时候,水常常被当地人用来阻隔新娘和娘家的联系。一名男子端着一盆水等在门口,新娘一出门,就把水泼出去,寓意嫁出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从此从娘家分离出来,失去了以往的身份,处于新旧身份转换的阈限阶段。新娘的哥哥在正厅门口替新娘打开雨伞,并用缝衣针在雨伞上针三下,接着口含柚叶水向新娘脸上吹上三口水,再吹三口水到雨伞上。吹水仪式的操演表示阻断了新娘的灵魂留在娘家,以免使娘家不得安宁。在村民看来,出嫁前不吹水,新娘的灵魂就会留在娘家,给娘家带来灾祸。
到了夫家之后,第二天清早,新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井边上香、挑水。由嫂嫂或姑姑带路,带上香和葱、蒜、芹菜、生菜等意头,分别喻示着聪明、会算计、勤劳、生财等。挑着水桶到了井边,把意头放在井沿,贴上一张红纸,再给井神上三炷香,告知新人初到祈求井神保佑。然后向井中丢入几个硬币,表示获得井神的许可,以后都能来这井里挑水喝了。汲水时,讲究一次性汲满一桶,顺顺利利。一般要挑上两到四担(一定是双数)的水,寓意好事成双。但自从用上自来水后,许多新媳妇就不再挑水了,改成第二天清早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放满一水缸水。水放满后,新媳妇需要从昨天喜宴留下的餐具中,挑十副碗筷用新接的水清洗干净。随后还要进行一个开厨仪式,即新媳妇拿起菜刀在菜板上切一些肉菜(一般是把整只鸡切成几大块),才可以开始做饭。以挑水作为新妇在新家获得认可的首要仪式,水充当了一种获得新身份的物质媒介,协助新妇完成了自己的通过仪式。在嫁过来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新媳妇和其他媳妇一样到井边去挑第一挑水,称为汲新水、新年水、聪明水、取勤水。谁挑水的时间最早,谁就是最勤快能干的媳妇。挑水到家后,再倒进锅里,加上红枣、生姜和竹叶为全家煮茶水,能够带来健康吉祥。两次挑水使其媳妇的身份得到认可和强化。
(三)买水、放水灯
老人去世后,有一个买水净身的仪式。在死者去世的当天下午,由师公带领,孝子孝孙们袒身赤足,拿着一个小瓦钵或瓷碗,到死者生前常用的水源边买水。取水之前,师公手持香火,嘴里念念有词,向水神通禀某某去世,需要神灵赐水净身才能去往另一个世界。在师公结束祷告后,锣鼓声响起,孝子向水中抛掷几枚硬币,师公接过容器,顺着水流方向连舀三次,交给孝子。孝媳手持竹篮,内装三只碗。在水面一边晃动竹篮一边念:“一碗喂鱼,一碗喂虾,还有一碗拿回家。”取得水后,点燃鞭炮,一行人缓步回家。请与死者同性之人替其浴身,用柚叶沾水象征性地扫拭死者遗体,主要是脸和胸口。意在洗去死者生前的污点和罪孽,以洁净之躯向阴界报道,顺利通过鬼门关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
另外,出殡之时,大儿媳妇一人还要去河边挑水回家。放到堂前,供送葬回来的人净手。洗去污秽,才能进入房间,阻断死者灵魂与现世的一切联系。
下葬的当天晚上,再由师公带领孝子孝孙去河边放水灯。水灯体型较小,由竹篾做成框,外面糊上白纸,内间放置一截点燃的白烛,以前点上的是素油灯。死者由阳间走向阴间,要过“奈何桥”。在村民的观念中,奈何桥下就是一条奈河或冥河,亡灵必须渡过冥河才能到达阴间。亡灵附着在水灯上,水灯带着亡灵随河水漂流而去。在师公念过简短的一段超度经文后,孝子捧着水灯缓缓放到水面,顺着水流方向用手推开。生命之始来自于水,生命之终还归于水。
在以上的系列过渡礼仪中,水被视为一种身份转换的媒介,帮助人们渡过各种关口。因此,在村民的观念中,河水、井水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圣洁性和神秘性,这是完全世俗化、商品化的自来水所无从获致的特质。水由此而具有独特的文化隐喻,并对村民的水观念与用水习俗产生深刻影响。
三、水之隐喻与节庆习俗
水在人类学的早期研究中,通常作为部落文化的一种符号和象征物而存在,具有多样化的象征隐喻,如圣与俗、洁与脏等。对于C 村人来说,水不仅是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一种必要资源,而且作为一种身份转换的媒介帮助人们顺利通过各种关口。此外,一方面,由于与地方经济繁荣休戚相关,水激发了村落的财富想象,具有另类的文化象征意义。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的需求和渴望往往不是一种显性的张扬,C 村人借助水来进行或隐晦或直白的表达。另一方面,复杂多元的水神信仰和用水习俗,促进了村民对各种不同来源的水进行洁净与肮脏的认识与分类。
(一)水与村落的财富想象
C 村人虽然经常面对浔江的涨落,但水之于C 村村民而言,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地,水不仅是一种生态资源,还是当地的一种财富象征。在村民的观念中,“山管人丁水管财”。没有水,商品菜的种植和鱼苗的繁育都无从谈起,而且频繁的洪水能为土壤增加肥力。与凤凰村的水灾造成村落社区短缺经济的情况[6]33-34不同,C 村村民适应自然、预防洪水的方法成功而有效,以生计模式转型与及时抢收等规避水灾风险。
在西江大桥修筑前,C 村是整个岛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中心。水上运输和鱼苗装捞都甚为发达,许多家庭的经济来源都与水相关,水提供了更多的致富增收机会。由水带来地方经济的繁荣,整个村因水而兴。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C 村的经济优势地位逐渐被相邻的J 村超越,但仍然是每年市、区、镇等各级政府在岛上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的首选之地。用之不竭的浔江水和遍布的鱼塘解决了村民的灌溉、饮用等生产生活用水。由于传统的鱼苗繁殖和蔬菜基地的确立,村庄对水的需求量特别大。从村委的年度开支明细登记表的数据看,要保持秋冬季节一天至少一次和夏天一天至少两次的抽水频率,所需高额费用占了村集体的大部分开支。村里的自来水从江中抽取净化,每年需要交付十几万的水费。一旦断电,不能抽取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村民的生产生活就会与城市居民一样完全被打乱。在20 世纪80年代以前,打工经济还处于萌芽时期,“水经济”对村落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男渔女农、亦渔亦农的生产习俗与分工形式的稳定性维持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承包到户后,鱼塘养殖成为一些鱼苗养殖户的重要致富途径。根据村委会的数据统计,普通鱼塘主(承包2 口鱼塘)的年收入在8 万元左右。
从村落语言的角度分析,长岛村人“以水为财”,往往把钱与不同等量的水相联系。用“兜”、“勾”、“撇”(分别指向“十”、“百”、“千”)等充作钱财的计量单位。尽管“水”的钱财义可能源自于清代江湖社会的用法,但在粤方言区,该义项得到快速发展而成为其基本义、常用义。[7]作为粤语起源地的梧州地区,这一语言特征同样显著,C 村亦如此。当地的很多口头语言中,水的喻义与金钱和财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村民通常所说的“水头”,寓意有钱赚;经济实力雄厚,称“大把水头”、“水头足”;财源滚滚,称“猪笼入水”;找人借钱,则称“去扑水”。水在商店开业或建房等习俗仪式上的作用不可或缺:若适逢降雨,便是好的致富预兆,称之为“水头足”;若天不降雨,则需找几盘水来泼洒,以显示财富到家。新中国成立前,贺商铺开张,喜送山水镜屏,尤喜送瀑布湍流画面。按当地说法,认为高山流水冲起去吉方,有催财作用。近年来,当地商铺也流行在店铺门口放置一鱼缸,把鱼游水中视为水动财来的象征。[8]3721村落因水而兴,水推动当地的商业繁荣,自然也就成了村民表达财富的代名词。
(二)水的洁净与肮脏
前文对水神信仰和用水习俗的繁复叙述,其目的在于阐明这一信仰对村民用水观念及其水的文化图式的影响。水因水神崇拜和仪式用水而具有神圣性,在村民的观念里,水是因圣洁而卫生,而不是因为卫生干净而圣洁。对于各种不同的水源,村民有洁净与肮脏的区分。
新中国成立以前,村民的生活用水主要使用井水,靠近河岸的住户从江中挑取江水饮用。在秋冬季节,江水清澈,挑回水缸稍微沉淀,即可用于饮用、洗菜、做饭、洗澡等。鱼塘水仅用于灌溉和洗涤衣物。以前没有饲料,村民都是割草养鱼,水质还未遭严重破坏。但鱼塘地势最低,无论干净与否,所有的水都容易积聚到这里,因此不能作为饮用水。如今用上饲料后,水质变得更差,水是黑色的,经常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连洗衣服都不能用。井水由于深层渗漉,比河水更清澈,有些井水还略带甜味。在村民的眼里,深井水是最为洁净的。水在习俗信仰中的神圣力量更增添了村民用水观念中的洁净性。在相邻的J 村,至今流传的一担酒糟换一担水的故事:J 村人用米酒的酒糟换取他村清甜甘洌的井水。
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在村民看来,以前的深井水甚至是河水都要比现在的自来水干净卫生。村里提供的自来水其实很不干净,尤其在长洲水利枢纽修建以后,水量减少,水的流动性减弱,水质更差。村里自来水工程的水源就地取材,从西江河中抽水到水塔,经过漂白和基本的消毒再送到各家各户,但对矿物质的含量及细菌总数没有精确测量过。村民对村里的自来水心存禁忌,不轻易信赖,还是对以前村里打的井比较信任。因此,村民还是倾向于到以前的井里挑水,主要是饮用和做饭。其他的生活用水如洗衣、洗澡等才用自来水。对用水传统的延续及其依赖性对村民的日常用水行为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力。以前井水挑回来也要先沉淀一下,讲究的家庭会用上明矾。后来村民在使用自来水时同样讲究先储存沉淀。从水管放出来的水先储存到水缸经过自然沉淀后才使用。但一旦情急用水,也就不再那么讲究,毕竟比起河水和池塘水来说要洁净很多。
从现代卫生角度而言,以前的井水可能比村里的自来水更脏。水井没有井盖,灰尘扬土、树叶枯枝甚至蛇鼠动物都会掉落井中。下雨时,雨水直落到井里,也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能防止污水溅入。井侧有台阶,方便人们下井挑水,村民总是穿鞋而进,容易污染井水。遇到洪水泛滥,水井需要重新淘洗。
尽管存在许多方面的污染可能性,但在村民的观念里,井水还是最为洁净的,年节时还需祭拜井神,感恩水井的孕育滋养。在获得新社会身份的过渡仪式中,也缺少不了对井的敬献。新媳妇第二天早上带上红纸、香和硬币等去挑井水。逢大年初一,村里妇女去井里汲新水,在井边贴上一张红纸,点上三根香。生小孩的也要去井边祭拜一下井神,相当于向井神通报户口。自来水无法取代井水或河水作为仪式用水。对村庄用水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村民对不同水源洁净程度的认识依此为井水—河水、自来水—渠道水、鱼塘水,分别用于饮用—洗澡—淋菜等,并且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水要比之后的水干净。
长洲水利枢纽动工以来,村民对自来水的质量更为担心,平时用水习惯也相应发生变化。饮用井水的村民越来越多,在装修好的厨房里摆放水缸,用于存储井水和井水的沉淀。饮用烧开后的井水让村民觉得更为放心。一些地势较高的住户重新在院子里打制小型压水井,供应家庭的饮用水,自来水则用于日常的洗涤。一些村民仍然去村里原有的深水井里汲井水饮用。枢纽建成后,造成上游河水流速过慢,上游河水水位降低,水的流动性减弱造成河水的自我净化功能相继减弱。一些生活垃圾和杂质飘浮在江面未随水流走。C 村位于水利枢纽的下游,枢纽的蓄水对C 村的饮用水源影响很大。2010年3 月,村民把对自来水质量的担忧向村委会反映,并向长洲移民办提交一份报告。报告以饮用水恶化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处理,要求长洲水利枢纽解决村民的饮用水供应问题。在对村庄的水源水和末梢水进行采样后检测结果显示只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 级),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需要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C 村提出的补偿方案是由国家的人饮工程提供专项资金在村内打制6-8 口深水井,完成村落的用水改造。
对于C 村人而言,什么样的水是干净的,什么样的水是不洁的,与其说是一种生活常识的科学总结,还不如说是人们对当地水文化及其历史的认同,一套标识着人们对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认知体系。
(三)七夕水
七巧节,也称乞巧节,当地称之为拜七姐,原本是传统社会专属女性的一个节日。但与这一节日密切相关的一个习俗却不为人所熟知,即“七夕泡水”。在农历七月初七,全村人不分男女都到河里沐浴天孙圣水(洗七月七水,也叫“七夕泡水”),时间在中午12 点到13 点之间。每年此时,村民几乎全家出动,不分男女老幼,在市区上学和工作的都会被家人召回。届时,河中人头攒动,村民或在河中畅游,或在水边聚会宴饮,一起泡水。村民认为,此时泡水有益健康,能祛除百病,比如对人皮肤有好处,能解暑、防皮肤病等,并深信此日中午的水可以存放百年而不臭不腐不变质。在“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中,拜七姐被视为旧社会的封建迷信活动而遭废除,但泡七月七水这一习俗却一直完整地延续下来。整个泡水过程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有些人在泡水后直接用各种塑料瓶把河水带回家。妇女们则在午时到水井或河里挑七月七水,储于瓦罐中。历来村民都深信七月七水的水质能经年深月久而不腐,可用两三年之久,可直接饮用,或者用来做饭、酿酒等。用此水洗澡,可避邪祛病,还可作调药之用,夏天中暑喝七月七水很快就能解暑气,并由此衍生出许多能证明其神奇药效的故事。但七夕水有一严格的时间禁忌:只有这一时刻的水才能久存不腐,超过一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后挑回来的水就如平常水一样,没有任何功效。
四、水文化及认同变迁
水与地方民俗节庆或宗教仪式等的紧密关联,其实就是通过禁忌、崇拜等文化方式实现水的象征性管理。而这一象征性管理往往对水的现实管理产生约束力。在不灌溉水利的西北地区(以山西的四社五村为例),水资源的匮乏使得这一影响更为明显。把水视为非物质文化是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强调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以禁忌的方式禁止乱开水源,想方设法延续使用旧水源,同时注意水资源分配与用水人口相协调,把握用水的社会效益”,实现了800年缺水村庄的和谐用水,成功建设出小康示范村。[9]在部分民族地区,当地凭借其独特的传统水资源知识营建了有效的区域性灌溉体系,用传统生态智慧构建人水和谐的用水环境和机制。[10-12]其实,这些地区的独特用水环境实质就是用水教育的无形的学校。过渡仪式、民俗节庆等场景中的用水,与地方的传统民俗文化意义严格相关并世代相守传递,形成重要的地方性知识,形塑着民众敬水、爱水、保护水环境的意识与行为,这一过程其实就是水文化认同的建构历程。通过所赋予的神秘、洁净等多重文化象征意义达到对水及其历史的认同,而有助于水的有序管理与合理有效使用的实现。现代社会着重开发水的自然性和商品性,导致水的非物质文化内涵被忽视,从而引发民众对水的认同、态度、观念等发生转变。水的功能扩大化,成为市场商品或娱乐景观等。村庄及村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婚丧嫁娶等民俗仪式的流程化、现代化,使得水与人生礼仪的紧密联系逐渐淡化,世代承袭的水文化、水观念不再有成熟而完备的濡化环境和认同语境。不仅C 村,当下的许多农村社区(包括许多少数民族村落)[13-14]因社会变迁导致了水文化要素的丧失,水观念的弱化及水的使用管理及水环境保护的社会规范等的丧失。人们对水的文化隐喻的感知及其历史的认同出现某种程度的困境。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或商品的水,不再能够唤醒人们的珍惜与崇拜。水资源的浪费与污染、对洪水的恐惧与反感等负面情感与行为被放大,失却了应有的约束和管理。尤其是洪水在现代都市社会的妖魔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历来所遵循的人水和谐的传统。而丰水地区人们世代积袭的亲水情结,却往往能纠正这一片面化认识。因此,由水的观念、使用、管理及保护的相关习俗、规范、宗教信仰等构成的水文化,应作为解决水危机的重要文化基础得到充分的尊重与恢复。
[1]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申扶民.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3]陈金文.岭南龙母文化散论——兼与叶春生、梁庭望、陈摩人等先生商榷[J].宗教学研究,2011(4).
[4]黄桂秋.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5](清)王栋,等.苍梧县志[M].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本.
[6](美)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M].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7]陆镜光、张振江.香港粤语表钱财义的“水”[J].方言,2001(4).
[8]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梧州市志·文化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9]董晓萍,(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付广华.壮族传统水文化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J].广西民族研究,2010(3).
[11]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的水文化:传统与变迁——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案例研究[J].民族研究,2006(2).
[12]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的水信仰、水崇拜、水知识及相关用水习俗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09(3).
[13]郑晓云.傣族的水文化与可持续发展[J].思想战线,2005(6).
[14]郑晓云.云南少数民族的水文化与当代水环境保护[J].云南社会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