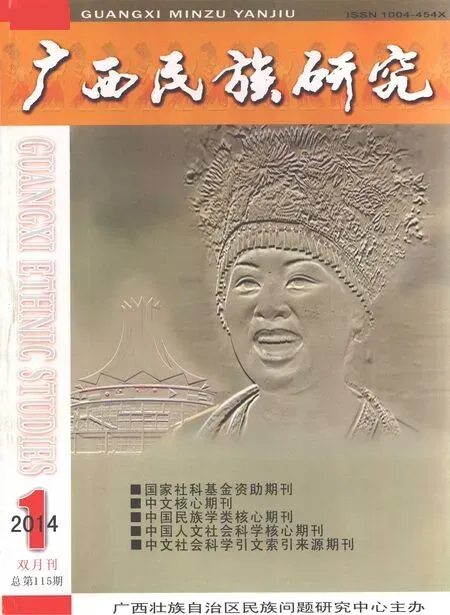中美民族政策价值比较: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从“第二代民族政策”谈起
于春洋 贺金瑞
自有学者在2004年年底提出理解我国民族关系的“新思路”以来,学界对于我国的民族问题走向、民族关系现状、民族政策功过等问题的关注程度持续高涨。进而,随着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的相继发生,学界呼吁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似乎“去政治化”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到了2011年9 月,更有学者撰文提出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对“去政治化”问题“做出了全方位的‘政策理念设计’”[1],试图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进而用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去替代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第一代民族政策”。[2]笔者认为,这种思路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甚至非常危险。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者所借鉴的所谓“国际经验教训”是建立在对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印度)的“种族、族群政策及其实践的误读和编造”[3]1基础之上的,其观点既不符合相关国家的民族问题实际,更无法适用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
本文以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尝试在中美民族政策价值比较的基础上理解我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现行民族政策建构,进而指出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定位,并以此批驳“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理论缺陷。
一、美国民族政策价值考量:实现政治解放而又止于政治解放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者那里,美国的民族政策俨然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美国民族政策所谓“成功经验”的推崇和青睐。然而,通过回顾美国民族政策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无论是20 世纪中期美国民权运动发生之前的“大熔炉”政策,还是后来的以“肯定性行动”为标志的当代美国带有多元文化主义色彩的“马赛克”政策,其本质从未突破过马克思主义“政治解放”的范畴。实现政治解放而又止于政治解放,是理解美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线索。
(一)种族歧视的民族“大熔炉”政策
“美国虽然早在《独立宣言》中就已宣称‘人生而平等’”,但是让人颇感意外和遗憾的是,“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该国一直奉行歧视性的民族政策”。[4]21-22美国民族“大熔炉”政策所倡导的种族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融合,而对于其他族裔则更多表现为种族歧视基础之上的隔离、排斥、驱赶甚至屠杀。
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宏观范式入手,作为现代联邦制国家的典型,美国的联邦制结构决定了其联邦政府全面负责全国性事务,州政府则负责处理地方性事务。这样一种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似乎把民族因素排除在国家结构建构之外,然而在实质上,这种分权模式正是“建立在白人种族政治基础上的权力结构设计”,因为从历史角度考察,美国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是建立在把黑人、印第安人等非欧洲人排除在外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把这些“劣等种族”作为参照对象,美国才得以建构起白人种族群体内部的民族认同。[3]2由此,在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美国基于对“劣等种族”的歧视而建立起了一个无论“人种、民族属性和宗教”都“高度均质的社会”[5]39。显然,这种“高度均质的社会”是以对印第安人、黑人等“劣等种族”平等权利的剥夺为代价的,从人口构成的角度看,“美国的人口,除印第安人以外,在1790年共3,929,000 人,其中698,000 人是奴隶,不被视为美国社会成员”[5]39。
回顾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民族关系史,可以发现那里充斥着大量移民群体与印第安土著居民、白种人及其后裔与黑人奴隶及其后裔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种族歧视以及对于种族歧视的反抗构成了美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线。“美国历史形成的经验是,对土著美国人进行长期战争……这一事实又继而产生了美国人的形象,不是作为刽子手,而是一个‘新兴的民族’。”[6]138-141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其他移民及其后裔身上。美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赋予这些民族以宪法规定的平等(哪怕只是政治平等)地位,此举是导致美国建国之后民族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总之,民权运动兴起之前,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政策一直是建立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上的,并千方百计维护这种种族歧视政策的合法性。显然,“美国人希望建立一个在平等原则之上运行的社会,但是不想建立一个由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7]399
(二)反种族歧视的民族“马赛克”政策
“大熔炉”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构成了美国民族政策的主流,只是在进入到20 世纪中期之后,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做出民族政策的调整,使其朝着反民族歧视、尊重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并且获得了有限的成功。由此,“马赛克式社会——取代大熔炉的概念而成了美国经历的本质……新的美国马赛克社会是一个具有种族特点的多元文化混合体。”[8]213
当代美国的民族政策主要由三个层面来构成。其一是旨在对所有民族的文化进行保护并推进其发展的政策;其二是以“肯定性行动”为核心的民族优惠政策;其三是专门针对印第安原住民的保留地自治政策。综观当代美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可以将其核心原则概括为:在承认和保护少数民族作为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的同时,拒绝赋予这些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群体的权利(除了印第安原住民)。一方面,美国用法律的形式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确保每个民族个体成员的平等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平等权利在选举、就业和接受教育方面表现明显;另一方面,除了印第安原住民之外,美国拒绝赋予其他少数民族以群体权利。“美国在法律上所宣称的平等和其他权利只属于个人,属于个体的美国人,而不属于各个民族。”[4]22这一原则在美国的联邦制国家结构设计中表现明显。美国联邦制下的各个联邦成员(州)的设立及其地域划分不以民族及其聚居地为单位,联邦成员所享有的自治权也是基于地域而非民族而建立的。因为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当文化的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暴力、自治或分离运动”[9]144。而这种联邦成员的制度设计本身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民族以地域为依凭谋求集体权利的可能性。
基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而对美国民族政策加以分析不难发现,美国几百年的全部努力只是用以捍卫政治革命的胜利成果,即维护和确保“政治国家”的统治。只是当国内不同族裔的矛盾日渐激化,危及到政治国家的统治的时候,作为维护和确保“政治解放”的一种手段,美国的民族政策才会开始有效运作。而从其实际的价值取向来看,它仅仅致力于国内不同族裔抽象的政治平等,亦即宪法意义上的公民平等,而不会致力于人与人事实上的平等,从而为“人类解放”寻求途径。而且,在这一进程之中,美国社会成员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和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则不断得以强化和巩固。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美国民族政策不可能为国内各族裔的真实平等和全面发展提供制度关怀。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论价值:对政治解放的超越
从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论的逻辑进程上看,现在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类解放”并不是一个原初性的概念,它是从“政治解放”中推演出来的。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需经历漫长的时间。要想获得“人类解放”,首先必须要实现“政治解放”,即通过“政治解放”来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一)政治解放
在马克思那里,政治解放是与市民社会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它所考察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即从欧洲中世纪时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高度契合,转变为资本主义时期两者的彼此分离。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种分离不是自发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来促成这一转变。“政治革命……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须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10]441从这一角度理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也就是政治解放”,它们是“同一个过程”,因为“政治革命打碎了中世纪封建专制制度套在人们头上的政治枷锁”。[11]8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政治解放”的基本内容。首先,政治解放使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不再屈从于宗教神权的统治,成为了“真实的国家”。这种真实的国家“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补充自己。相反地,它可以脱离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10]431-432;其次,政治解放使民主、法制这样一些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得到彰显,封建专制统治及其造成的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得以解除,人成为了独立的、自由的个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10]443;第三,政治解放在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彼此分离的同时,也促成了独立市民社会的崛起。因为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10]344。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及历史局限性。他指出,“我们不要在政治解放的限度方面欺骗自己”[10]430。其原因在于,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获得政治解放的公民“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10]344。
(二)人类解放
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类解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市民社会缺点的批判和克服,以及对于政治解放历史局限性的超越。一方面,与黑格尔把君主立宪制国家视为“历史的终结”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所实现的仅仅只是抽象的政治平等,所建立的这种“真实的国家”并没有消除人们之间基于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分工等差别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国家不仅没有消除这些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10]427;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所强调的人权并没有跨越利己主义的藩篱,“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10]437-438。因此,以所谓人权的确立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类解放,充其量,它只不过是实现了市民社会之于政治国家的独立。而“要想克服市民社会,实现人类解放,只有依靠现实的人,依靠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来完成”[12]30。由此,在消除政治国家赖以建立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克服市民社会中人的利己主义的进程之中,去实现“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人类解放”,就成为必须要去完成的工作。
进而,马克思讨论了以政治解放为前提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一般内容。人类解放将实现对于政治解放的扬弃与超越,将消除人们之间基于种种差别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把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还给每一个“现实的个人”;人类解放将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推翻使人成为被奴役、被剥夺、被异化的对象的生产关系,以及基于这种生产关系而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0]443总之,人类解放就是要把“现实的个人”从不平等、被异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人类解放的政治解放
回顾我国民族政策的探索轨迹可以发现,其所有努力都是实践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在具体政策实践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而它的指向却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政治解放而实现最终的人类解放。这一点是理解当代中国民族政策实践的关键。
(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进行我国民族政策的探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倾向于采取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方式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这一点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在1931年11 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13]92;这种以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为取向的民族政策的制定,是同我们党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创立初期,无法立足于革命的全局和国家发展的远景角度来深切思考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方式;而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干预,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很难真正做到从国情实际出发。
到了抗日战争以及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自决与民族区域自治这两种不同取向的民族政策之间进行了多次权衡和反复比较,最终把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的民族政策。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等各民族……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4]595。这里已经开始孕育着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从联邦制到单一制的民族政策思想;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负责处理民族事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关于边区境内回蒙等各民族区域自治事宜,关于境内回蒙等各民族自治区之政治、自卫、经济、教育、卫生等建设事宜”[14]943。至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成为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导性意见;进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里,专门规定了我国的民族政策,即“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正式成为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的这一探索过程,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极为重要,因为“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规范,而且形成了对这个政策主张的坚定不移的信念”[15]5。
(二)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在价值诉求
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先进分子即已举起人的解放的旗帜,并由此走上了阶级解放的道路”[16]16。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旨在解决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而制定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内容的各项民族政策,也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最高目标的。对此,完全可以从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在价值诉求中加以探寻。
1.政治价值诉求:各族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7]1作为我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各族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政治制度上的可靠保障。回顾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过程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生政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的同时,同旧社会的一切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彻底决裂,让各民族的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真正实现各族人民当家做主。而且,这一历史使命是在当时我国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还比较深、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还很大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基于这一背景,“民族区域自治就不仅是新中国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而且是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各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承诺——在新的人民共和国中,少数民族的各项基本权利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18]51。由此,实现和确保各族人民当家做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价值诉求。
2.经济价值诉求: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的落脚点是共同富裕,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要正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我国主体民族、发达地区客观存在的发展差距,并且通过各项民族政策的实施,努力缩小这种差距。这也是现阶段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之所在,因为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求更快地发展经济文化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19]246-247基于上述认识,如果我们党制定实施的各项民族政策没有缩小发展差距,没有促成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那么这种民族政策就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了。这也是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经济价值诉求的最好说明。
3.社会价值诉求:各族人民真实平等
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是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即国家基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而赋予每个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这种平等是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过了政治解放的‘洗礼’之后,穿上了‘平等’外衣的公民们,他们的‘尘世’生活实际上是多么的不平等”;“政治解放的一个实际结果,就是以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11]8-10马克思正是因为洞察到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进而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只有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除政治解放的个人私利性的基础,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20]14我们发现,与美国的民族政策实现政治解放而又止于政治解放根本不同的是,我国的民族政策在努力确保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之上,一直在致力于各族人民社会生活领域内的真实平等。各族人民的真实平等是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内在社会价值诉求。
总之,当代中国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更不容否定。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在坚持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现行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围绕我国民族政策的三大价值定位去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从而更好地实现政治解放,确保各民族各项权利的真实性和平等性,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而去努力奋斗;而不是另起炉灶,天真地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时指出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我们认为,这才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而正确的选择。
[1]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上)[N].中国民族报,2012-2-3.
[2]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3]郝时远.美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榜样吗?——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际经验教训”说世界民族,2012(2).
[4]杨恕,李捷.当代美国民族政策述评[J].世界民族,2008(1).
[5]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6]P.L Vanden Berghe.The Dynamics of Racial Prejudice:An Ideal-Type Dichotomy[J].Social Force,1958,37(2).
[7]J·R·波尔.美国平等的历程[M].张聚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8]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M].王振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刘同舫.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12]郁建兴.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政治思想初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13]陈荷夫.中国宪法类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5]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4).
[16]李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历史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04(1).
[17]李慎明.坚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J].政治学研究,2005(2).
[18]胡岩.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1(4).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任勇.民族、民族国家和人类解放: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考察[J].社会科学研究,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