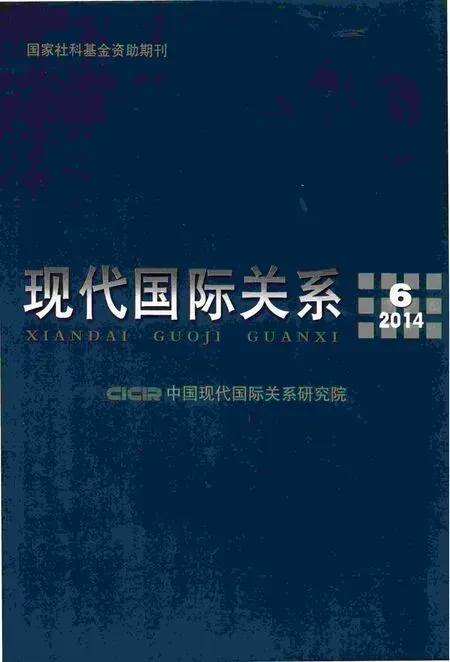“集体性失明”的学理解剖——兼议国际政治学的特质与预测方法
宿景祥
“9·11事件”及随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十余年过去了,人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认识,也产生了不少新的疑问和困惑。牛新春研究员在《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发表的“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一文,把十余年前国内学界的一些思想脊骨重新剔出,条分缕析地堆放在一起,从而赋予它们新的生命。文章指陈,当时国内学界对阿战、伊战的分析、预测和研判失多得少,并据此从理论、方法及学风等方面对国内学界这一近乎“集体性失明”的现象进行剖析。①牛新春:“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1-9页。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提醒我们有必要去反思过去的思考和判断。学术问题多属见仁见智,“集体性失明”现象既然令人感到些许惊诧、萌生疑问,就值得多做些探究和解释,以期进一步推动我们去思考到底应该说些什么、想些什么。
“集体性失明”与国际政治学特质
德国诗人海涅在“论法国画家”一文中曾提出:“评论家们的一大错误常常在于提出‘艺术家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家想做什么?或者甚至于‘艺术家不得不做什么?’也许要正确得多。”②[德]海涅:“论法国画家”,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75页。那些缺少实际创作经验,只懂得一些条条框框和定义法则的人们,往往只会提出前一个问题;唯有那些直接从事创作实践活动、深知创作甘苦的人们,才有可能提出后面的问题。学术批评和艺术批评虽然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但其所遵循的法则并无本质区别。海涅告诫人们,在评判他人的作品时,首先要准确地理解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因为一切形式的作品,都只是作者向其他心灵传递思想的象征。所谓好的艺术家或作家,就是能“用最少和最简单的象征,表达出最多和最深刻的思想”。③[德]海涅:“论法国画家”,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76页。
牛新春研究员所发表的“集体性失明”一文是学术批评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也很清晰。该文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题目,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乍看起来显得有些荒谬的命题。
十余年前,正当世界上发生“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试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牛新春研究员认为,国内几乎整个学界睁大眼睛盲目地观察和评判,“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国”。①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1页。2002年3月,美国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宣布反恐第一阶段结束后,“学术界的判断迅速逆转”,“转而夸大美国的军事、战略成就”。②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2页。当时学界似乎是形成了某些“重要共识”:“恐怖与反恐怖是未来相当长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兼顾各方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认识到,惟有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才是方向。”③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2页。这些“重要共识”很快又被逆转了!由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反对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国内学界修正了判断,认为“国际政治中心仍是单极与多极、战争与和平、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与斗争”,美国与欧洲间的“共同价值观受到质疑,联盟的基础坍塌,同盟将名存实亡”。④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2页。美国在很短时间便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学界共识是“大国力量对比更加向美国一边倾斜,一超正向独霸发展”。几个月后,鉴于驻阿、伊的美军被拖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国内学界改变了共识,认为“美国霸权出现转折”,因为“美国实力已经达到了阶段性峰值,地缘扩张冲顶回落”。⑤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2页。牛新春研究员由此得出结论:国内学界“早前关于两场战争的战略预测与事实相去甚远”。至于“事实”是什么,作者运用了隐微学的写作方法,提到当时还是有学者看到中亚已不再是“亚欧心脏”,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黑洞”。⑥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3页。
处理了战略预测问题之后,作者转向战术预测问题,再次引用了大量翔实的文献,从军事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当时国内学界在战术层面对美国的判断和预测“完全失准”,“没有人预测到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结果。”⑦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3页。
该文写到这里,已经成功地为读者勾勒出这样一个画面:十余年前国内学界在研判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时,仿佛像一群鸟儿一般,不时地、突然地、同时地,而且是一致地变换着方向。
中国学界自古便有重视学术批评的传统。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过:“文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者,亦有作者甚深而观者甚浅者。”“集体性失明”一文当属后者。这篇学术批评文章纲领明确,考订精详,显露出作者学力充盈,既好深湛之思,又能综核名实,寻章摘句,钩玄提要,确非从事偏端末节者所能比拟。正所谓事有实据,理无定形。“集体性失明”一文的立论或稍失之偏,令人惊诧,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洞察力的见解。作者写作态度严谨,思力深沉,加之议论之通,援据之确,足以自圆其说,而成难得之论。
能见泰山不为目明,能闻雷霆不为耳聪。长期以来,学术界空言无实之弊,可谓人人皆知,只是很少有人明言而已。“集体性失明”一文既然已将问题提出,就不能不提供一些合理解释。
作者随后从理论、逻辑、方法和学风这四个方面分别阐发论述,林林总总,迂回曲折,以至令人有离题万里、心生疲惫之感。直到文章接近尾声时,终于触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因素对学术“不可避免的”干扰。作者很委婉地指出:“任何国家都有政治正确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更严重些罢了。”“在中国学术界,看坏美国是正确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得严重一些、长远一些,在政治上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政治避险的捷径。”“判断美国地位下降,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可以论证多极化;而说美国地位没有下降甚或上升,会产生‘感情、立场有问题’、‘跟多极化唱反调’之嫌。”①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9页。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题目。各国有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学术传统,即便是简略地进行国际比较、寻求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式也是困难的。在西方学界,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同样是一个传统话题。从欧洲历史看,学术自产生以来,就从未与政治彻底地分离开来。学术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同样是基本的社会准则。学者若触犯这条准则,倡导与社会主流意识背道而驰的学说,质疑深入人心的普遍信念,就会被看成极为有害的行为,不仅会导致社会分裂瓦解,也会使学者自身处于险境。②[美]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著,宋菲菲译:《施特劳斯的真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4页。事实上,由于政治原因而受到迫害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但丁、布鲁诺、伽利略、托马斯·莫尔、黑格尔和费希特等等,即便是按他们各自所处年代的标准来看,也都被公认为品德高尚、慎言谨行之人。
中国知识界很早便熟知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等经典理论家们对当时盛行于西方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推崇“有骨气的”学者,即鲁迅所说的那种有骨气的“民族脊梁”,他们对于国家安危治乱具有很强的责任感,敢于直言相谏,从不逢迎而曲意发表投机性的言论。然而,宽松的政治空气,自由的思想学风,在中国过去两千年历史上恐怕从未有过。③白奚:《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第56页。“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2页。如果社会的政治性过强,日久成习,学者们便不愿深谈政治,也不愿深度思考政治。
今天的西方社会至少从形式上看,言论自由的空间和程度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否可以认为这就是纯粹的学术自由,也是令人怀疑的。冲突始终是政治的核心,只要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冲突,就无法否认政治,因而也就必然存在敌友之分。任何学术研究,只要涉及到敌友问题,就无法与政治分离。学术与政治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关系,学术试图引导政治,但更多的时候是为政治所用。只不过在西方国家,政治对学术的利用和控制方式早已被锤炼得炉火纯青,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虽然变得更加密切,却也更加隐秘。
美国的德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较近的一个例子。⑤Jeffrey Steinberg,“Leo Strauss,Fascist Godfather of the Neo-Cons”,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March 21,2003.施特劳斯生前一直潜心研究政治哲学,很少评论美国政治。他认为,自己作为流亡者,没有资格评论美国政治。⑥[美]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著:《施特劳斯的真相》,第2页。施特劳斯在世时,几乎默默无闻,他的著作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中流传。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亦即在他去世30年后,美国主流媒体突然爆发了“施特劳斯热”。有人甚至直接将当时主导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分子称为“列奥保守派”(Leo-Cons)。施特劳斯的学生们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势力的群体,掌控着美国共和党、右翼智囊、美国政府,当然还有联合国。⑦[美]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著:《施特劳斯的真相》,第24页。这一热潮也蔓延到中国学界,引发了对施特劳斯研究的重视。今天,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
相比较而言,中国学界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理应有所共识。学术与政治自始至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治中有学术,学术中有政治。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必须服务于现实国际政治斗争,这是不容讨论的。国际政治学比其他最相近的学科更贴近现实政治,因而,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不仅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也直接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政治评论,配合舆论斗争。此时,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往往都是因事命题,要求按时交稿;至于观点和结论,即便报刊编辑未加以明确限定,学者们凭借自身的专业和政治素养也多能领会,并根据政治需要包括政府的政策取向和读者的价值取向,自行把握。或许正是由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所具有的这一特质,尤其是中国政治的高度集中,学者们很大程度上在某些问题上看法齐一。这样,在平时的各种重大问题上,学者们能够形成稳定的观点和看法,就如同空中飞过的大雁一样,排列成行,整齐有序。但如果局势剧烈变化时,学者们便如同一群鸟儿,时不时地一致转向,大概就是牛新春文中所说的“集体性失明”现象。
预测的方法与“时代特征”
柏拉图曾说过,方法决定结论,方法就是结论。研究任何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其所运用的方法。“集体性失明”一文之所以能够得出“集体性失明”的结论,关键在于作者选择的议题是“预测”。现代军事问题从来就不是国际政治学者之所长,国内学界当年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关注,更多地是着眼于国际政治格局的角度。这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们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确实曾经对战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预测,也很可能确实没能准确地预测到战事的具体结果,这就使得“集体性失明”的立论自然可以成立。
“集体性失明”一文之所以讨论“预测”,更多地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其着重点在于引出理论、逻辑和学风等问题,而无意在这个问题上苛求学界。该文作者实际上也承认,“预测国际事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预测”本身并不重要,相反,对于重大事态、重大问题的阶段性变化,学者都必须要提出带有前瞻性的观点,哪怕是仅仅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
从知识论上说,一切正确的知识都必然包含着某种预见性。中国知识传统尤其重视预测或预警,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孔子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指的便是《周易》所蕴涵的忧患意识。它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提振精神,提防不测之事发生,做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精神准备。《易》还充满理性思辨,强调凭理性来寻求化解忧患之法。《易》每卦六爻之位,实质上是将事物发生发展区分为六个阶段,或者说六种状态,揭示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发展变化规律。
中国传统学术皆发自于《易》。《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按中国知识传统,学者著书撰文只有两种目的,“或以述事,或以明理”;前者是事溯以往,称“藏往之学”。后者是理阐方来,称“知来之学”。“藏往之学”看重的是学者的考索之功;“知来之学”也称“前知之学”,更看重的是“别出心裁”,因而也称“独断之学”。①[清]章学诚著、吕思勉评:《文史通论》(卷一,内篇一《书教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对“预测”、“预见”和“前知”的执著求索,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全人类的品格。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作家、启蒙哲学家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于1784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类历史哲学观念》,其中提出了一个极富想象力和天才创意的历史哲学观。赫德尔认为,人类在天赋上的一个最独特之处,即与其他任何生物最本质的不同,是直立行走。由于直立行走,人类就解放了双手,从而获得了自由、创造性和无限发展的潜力。赫德尔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能够直立行走,原因是头颅的结构适应于直立的形态,内外机体适应于垂直的重心。人的头颅之所以变成目前的这种结构,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被某些遥远的东西所吸引,时常“抬头仰望”所造就的。归根结蒂,“远见”使人成为人,“远见”也是人最本质的、内在的特征。②[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2-78页;[德]爱克曼著、吴象英等译:《歌德谈话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既然“知来之学”和“远见”如此至关重要,就不可能存在一种简单的、灵验的预测方法。因为人类如果真的能够很简单地掌握未来,那么世界也就成了一个确定了的世界,对人类来说是绝无益处的。“集体性失明”一文对预测的方法做了简明扼要的综述,尤其是详尽地解说了国内学界偏爱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说明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是精细的历史分析,甚为中肯,有针砭时弊之功。
对时局进行预测本质上是一门“独断之学”,学者必须独自做出判断。要做出合理的判断,就必须有深厚的“考索之功”来支撑。“集体性失明”一文批评了国内学界的浮躁之风,认为不少学者常常对实际情况并不真正了解,便轻易做出判断,而为了使自己的分析行得通,只能使用各种简便的方法,如近似于概率的描述,或者直接说“存在不确定性”。作者还指出学界的另一实际情况,即“专门家”偏少,“战略家”偏多。这揭示的是,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尚不发达、分科还不够精细,这主要是体制之弊,而非学者之非。
科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事实的充分观察,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国际政治学毫无疑问是一门科学。从理论上讲,对一个国家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所以得到世人最高的尊重,正是因为他们综合了以往最杰出的科学思想,并用之预测世界历史的“结局”,从而指导着人们的社会实践。
尽管“集体性失明”一文对于国内学界偏爱历史分析法颇有微词,但历史方法毕竟是或多或少较完整的一个理论体系,从中也确实产生过许多天才的思想。实际上,在世界政治领域,历史分析法很可能是唯一真正科学的预测方法,因为对重大事件的预测总是与历史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在历史时间中存在。时间不断滚动着、流逝着,在方向上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过往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通向无尽的将来,然后滚入到不可回复的过去。正确地运用历史分析法,其前提不仅仅是要对历史进行精细分析,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也就是说,要从一个合适的历史起点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还要正确地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
所谓“合适的历史起点”,就是人们常说的“时代特征”。“集体性失明”一文也提到,2003年1月《现代国际关系》杂志曾召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讨论国际局势,包括世界主要矛盾、时代主题等问题。文章随后又多处指出,国内学者一直在关注单极与多极、战争与和平、霸权与反霸权等概念。①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2页。
过去200余年来,“时代特征”这一历史观念始终牢牢主宰着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每当一个新时期来临时,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用来表述新时代的特征。“时代特征”这个观念最早是康德于1784年在“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提出的。他指出,历史研究不应仅限于过去曾发生过的某些特殊的现象,而是应思考人类总的发展进程,探测历史合理的发展规律。康德还提出一个设想,认为历史自身或许存在着某种目的,“一项大自然的计划”,投射到现在之外,照亮未来。②[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1页。德国诗人席勒1789年5月在耶拿大学开设的一个历史讲座中提出了“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指出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并非都是可以信赖的,前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也往往是残缺不全的。他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应研究“全部的历史”,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探测历史过程的大规模节奏。③Friedrich Schiller,“What Is,and to What End Do We Study,Universal History”,Translation from Friedrich Schller Poet of Freedom,Volume II,Fidelio,Vol.I,No,2.Spring 1992.费希特1806年在柏林大学开设了一个讲座,题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这句话可以认为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时代特征”的滥觞。费希特认为现在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各条线索所汇聚的焦点,应“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从自己的观点观看其他的国家和文明”。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自己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特点,表明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其他特点是怎样从它们里面得出来的。④[德]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卷四,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27-682页。
中国学界所熟知的“时代特征”概念来自列宁。1917年4、5月份,正值俄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之际,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新概念。他说:“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夺取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⑤[俄]列宁:“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533-2534页。“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⑥[俄]列宁:“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6-8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535页。“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第一代领导人一度公开否认苏联是一个国家,而是把它看成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相矛盾的过渡性政治组织形式,主张“把已经在俄国获得成功的同样的革命推广到全世界”。苏联在其整个历史中“从未正式放弃过世界革命的希望”。①[英]E.H.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60-61 页。至今“帝国主义时代”仍然是世界政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它同时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如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前者被认为是用来为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寻求合法性,后者则被认为是用来为美国不断地发动和卷入新的冲突寻找新的理由。“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尤其流行,在很多人眼中,亨廷顿的这一理论简直就是高瞻远瞩之见。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利用“文明冲突论”,将国际恐怖主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近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都归咎于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从而为其军事干预和政治介入中东地区提供借口。近年西方一些政治家对中国的崛起甚为惶恐,宣称应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对中国的势力,组成“神圣联盟”以共同“遏制中国”,而“文明冲突论”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已经过去了,现在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亚,正在构筑“西太平洋岛链”制衡中国。曾经的“当前”已经成为过往,曾经的“未来”已成为“当前”。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到底是什么?美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它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些带有根本性的议题,国内学界似乎至今也很难形成某种或多或少的共识。
结语
“集体性失明”一文临结尾处提及,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威胁的估计往往偏于严重”,“我们对外来威胁估计过高”。②牛新春:“集体性失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第9页。这说明学界从来都没有真正忘却这些议题。事实上,这些议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它们与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解答好了它,才能推动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前进。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文治历史悠久,学术思想精深。但在过去几百年里,中国国运衰微,远离了世界发展的前沿。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历史只是“外在的历史”,与其自身的流向相反,不仅没有能够拥有为之努力奋斗的东西,而且一直都为某些外在的东西所妨碍。直到近几十年,中国才逐渐步入复兴的轨道,世界历史也因此成为其“内在的历史”,并具有了“真正的现实性”。③[丹麦]基尔克果(Kierkegaard,旧译克尔凯戈尔)著、阎嘉译:《或此或彼》(下部),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790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和发展的速度,中国也更加专注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世界的发展。但由于落伍的时间太久了,长期专注于内部事务,置身于世界发展之外,处于世界发展的边缘,这种时间感和距离感,妨碍了我们对世界事物的洞察和理解能力。“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摆脱了“欧洲最落后、最野蛮国家”的面貌,实现了工业化、电气化,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的俄罗斯虽然不复当年苏联的政治经济实力,但仍不失为一个世界强国。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拥有无与伦比的辽阔国土,更多地是因为它在过去100多年来,始终未远离世界发展的中心。中国需要而且正在开始一场社会革命,学术思想的大迸发和学术研究的大发展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与知识复兴相伴随的社会革命,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革命。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历史开始进入“太平洋时代”,成为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总的来看,美国战略东移与中国崛起的过程相互纠缠在一起,但这两个进程的起点和内在逻辑都不同。这二者之间可能会相互阻碍,也可能会相互促进。目前,很难对此做出清晰明确的解释。中国学界要想掌握未来世界的大致走向,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换句话说,把这个题目弄清楚,应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最主要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