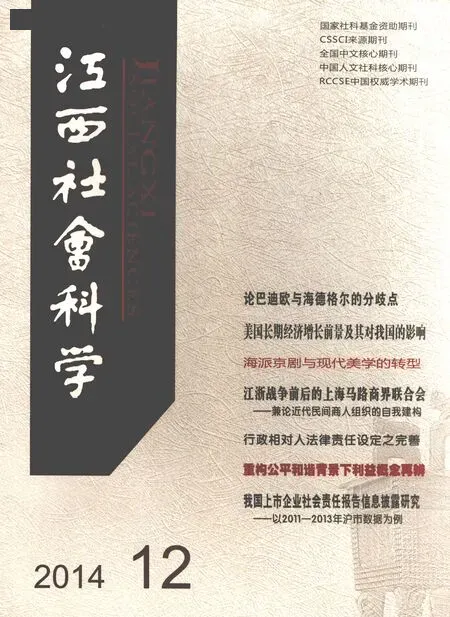论杨宪益文学翻译思想
■欧阳友珍
20 世纪是西方文论空前繁荣的时期。大量的国外理论引入我国翻译界,使我国译评界的理论意识以及批评方法科学化,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语言文字是最具有民族性的,翻译理论也应植根于民族自身的历史结构和文化土壤之中。我们既要辩证地借鉴和吸收西方理论成果,也要立足于民族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对我国本土翻译思想进行系统化整理和现代诠释。
杨宪益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大师,成绩斐然,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方面影响甚为深远。学界称其翻译了整个中国。他于2009 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译作丰厚,却没有专门的理论著作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笔者拟从他的翻译实践入手,对散见于其译作的前言后序以及翻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涉及的翻译思想进行梳理、整合,以期对这位翻译家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翻译之“道”及释“道”之难
(一)翻译本质之“道”
翻译有“器”的一面,也有“道”的一面。自古以来中西方学者都有从这两方面来研究翻译的。从形而上的层面研究翻译,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翻译的本质。关于翻译的哲学基础,哲学家贺麟1940 年在《论翻译》中指出:“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1](P48)就翻译的可行性和翻译的本质,杨宪益在不同场合谈过自己的看法。“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东西应该都可以翻译,不然的话,人类就只可以闭关守国,老死不相往来了。”[2](P82-83)既然人类的思想感情是可以互通的,那么翻译也就成为可能。这与贺麟指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翻译哲学基础同出一辙。就是说,人类思维是同一的,人类的思想感情有其普遍性,语言形式的差异不会影响到思维的内容。人性的共同性是翻译之“道”的哲学基础。人类可以用多种语言去表达同一思想,译文与原文本的关系即是一意与两语的关系。
此外,杨宪益指出,翻译活动的时空距离也不是问题,是可以弥合的。在他看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时间相隔久远的问题”,比如《诗经》,现代人还是很欣赏这些诗歌的,“原因是它们都是杰出的诗篇,将作品翻译成外语,也应该是这种情况”[3](P89)。杨宪益强调的是,文学艺术的内涵和审美具有超时空性,可以在全人类心中引起共鸣。这是翻译可行性和翻译本质的另一个重要特质。如果要翻译几百年前的文学作品,杨宪益指出:“译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时期,设法体会当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思想;然后,在翻译成英文时,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这样才能使读者读懂那时候人们的思想。”[3](P83)时空距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要想弥合翻译活动的时空距离,译者就必须“入乎其中”把自己融入原文,感知原文,然后又“出乎其外”,设身处地为读者考虑,这样原作与译作之间的时空距离才能消除,译作才有可能在异域文化语境中被接受和产生影响力。基于此,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才得以传播和交流,并成为人类公共的财产。
(二)翻译的释“道”之难
一方面,杨宪益坚信一切都是可译的,因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文学艺术的内涵和审美具有超时空性的特质。但同时,他又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存在不可译的问题,因为在文学中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构成原文的某些含义,而要把这些含义传达给文化不同的人则是根本不可能的。[3](P85)世界上的事物极其复杂,语言的表述和意蕴也是如此。总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思是普遍的,同一事物可以由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即“意一言多”,但有时也可能是“言一意多”,比如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双关语、典故、俗语、文化负载词以及蕴意丰富的诗句。这些都是翻译的难处。在杨宪益看来,由于“人类自从分成许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和语言几千万年以来,各个民族的文化积累又各自形成不同特点,每个民族对其周围事物的看法又会有各自不同的联想”[2](P83)。民族性、地方性色彩浓厚的语言形式的翻译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象很难准确、有效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群。
这里提出了某些文化意味不可译的问题,即译作与原作的文化距离问题。翻译涉及各种类型的距离: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审美的以及更多的派生类别,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距离是与翻译相关的最常见的距离。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各自的文化心态、阅读体验、审美感知等都会影响其对译作的阅读反应和接受效果,因而文化距离也就成了翻译活动中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不可译”的主要原因。翻译传递的不仅仅是基本意义,其本身还需跨越各种距离。两种语言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部分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势必产生部分可译和不可译的问题。翻译之难就在于如何合理地协调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各种距离。
在诗歌的不可译方面,杨宪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翻译《奥德修纪》时,他曾在散文体和诗体之间举棋不定,最后还是将其译成了散文,“因为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地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4](P170)。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古诗词的英译问题:是保留古体还是用现代体,抑或是另寻途径,采用散文体?杨宪益曾多次尝试用英诗格律译中国诗歌,但通过长期的翻译实践摸索,他发现,如果一定要遵循原诗的音韵格律,那么原诗的内容必然受到损伤。“每国文字不同,诗歌规律自然也不同。追求诗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内容上的不够‘信’。”[2](P84)“字有其音”,文字传神还要靠声音节奏,这点在诗歌、散文体中尤为凸显。中英文在语音上有很大的差异,英文每个字一个音节或多个音节,音节还有轻重之分,如果一定要按照原诗的音韵格律来翻译,原诗的内容必然有损失。语言距离给诗歌翻译带来巨大的挑战。杨宪益认为用外国的格律诗译中国诗歌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以诗译诗当然好,但须在不损害原诗内容的前提下,为了忠实原文的内容,杨宪益多采用散文体来翻译诗歌。
二、翻译之“器”的传承与发展
“信、达、雅”作为重要的翻译之“器”法则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但将这三个字按翻译的内在规律如此排列组合,并明确将它们作为翻译标准的当属严复。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指出:“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5](P85)这正是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特色之一:扎根于自身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从我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以自用。
对于“信、达、雅”的标准,后人都是认可的,但具体翻译实践中如何把握尺寸,还是人言人殊。杨宪益有着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四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探索,印证“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并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考量和践行这一标准。
(一)译文“信”内涵的丰富
1.忠实原文,译者克制
谈到杨宪益翻译风格时,译界普遍认为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他的代表译作《红楼梦》就是极好的例证。杨宪益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内容,不增不减。“过分强调创造性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改写文章了。”[3](P84)并且,他还认为翻译的时候译者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译者的职责就是把原文的信息尽可能忠实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译文中不应夹杂太多译者自身的观点。“我们不应过多地把自己的观点放进去,否则我们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创作了。”[3](P89)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职责重大,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从文本选择到译本生成,译者总会出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考虑来操纵原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杨宪益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他认为翻译就是翻译,不是对原作的改写,译者应以翻译伦理来规范自我,自重自律,合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者应隐形和克制。
多年来的翻译实践中,杨宪益坚守自己的翻译理念,强调译者克制,忠实传达原文内容,尽量让译文读者像原文读者一样接收到原文传达的信息,反对对原作的改写和操纵。翻译《红楼梦》时,他尽量忠实地把中国文化信息和内涵保留下来,对原文中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进行异化处理,不做改动,也不做过多的解释。相比之下,霍克斯倾向于交际翻译,自我定位为文化的协调者,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为了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期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改写、替换甚至省略。
我们来看看杨译和霍译对词语“红”的处理情况。“红”是《红楼梦》作品中的一个中心词,总共出现了664次。在中西文化中“红”有着不同的文化意味,因而两个译者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杨译用其一贯的直译,把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传入译文,而霍译则采取多种方式来处理这些“红”字。[6](P110)比如:书名《红楼梦》杨译本译为“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霍译本则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怡红公子”杨译“the Happy Red Prince”,霍译为“Green boy”;“悼红轩”则分别译为“Mourning-the-Red Studio”和“Nostalgia Studio”;等等。
2.内容至上,形式次之
中国翻译始于佛经翻译,经文重义,自是理所当然。重义也成了中国历代翻译家共同的座右铭。杨宪益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体现在诗歌翻译上。关于诗歌翻译,前文已经提到杨宪益认为用外国的格律诗译中国诗歌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由于中英文在语音上的差异,译文很难把原诗中的音乐性和节奏体现出来,所以翻译时如果一定要严格遵循原诗的音韵格律,那么原诗的内容必定受到损失。因此,为了忠实原文的内容,形式暂且放在第二位。
这种内容重于形式的诗歌翻译理念与另一位翻译大师许渊冲的理念大相径庭。两位大师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方面颇有建树,但两人翻译理念差异较大,主要在于对“信”字有不同的理解。许渊冲主张译诗除了要传达原诗内容外,还要尽可能传达原诗的形式和音韵,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翻译的忠实应包括内容、形式和风格三方面。杨宪益则认为追求诗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内容上的不够“信”,故其多采用散文体翻译中外诗歌。[7](P40)
3.文化精神,“信”之核心
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征,翻译产生的根源来自于文化间交流的需要。杨宪益曾说:“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和思想内涵,因为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都有差别。”[8](P2)这就是说,翻译不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语言背后的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文化移位对文学翻译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认为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存在一个“第三空间”,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作用。这一空间的产物即为文化杂合体,兼具两种文化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讲,译文都是文化杂合体,是翻译过程中归化和异化相互交融的产物。[9](P242)当然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比例会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变化和调整。
翻译策略的选择受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影响。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主流诗学,以及译者本人的文化态度和译者职责定位都与翻译策略的选择密切相关。就杨宪益而言,他拥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热爱,秉承“忠实原文”的翻译理念,以及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自我定位,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他在翻译实践中必定重视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保留,较多采用异化处理,如有需要,还附上脚注以弥补译文中的文化缺失。任生名教授认为,杨宪益在其翻译生涯中以忠实的翻译“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明的精神,希望通过翻译向译入语读者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灵魂,传达中国人的人生和他们的喜怒哀乐。[10](P34)
(二)译文基于“信”的可“达”
杨宪益说:“‘信’和‘达’,在翻译则是缺一不可。‘宁顺而不信’和‘宁信而不顺’都是极端的做法。要做到‘信’‘达’兼备不是容易的事。”[8](P2)在翻译萧伯纳戏剧《凯撒和克丽奥佩特拉》时,他觉得书名译成《凯撒和克丽奥佩特拉》不够通俗,但又认为不能为了通俗化而将其译成《霸王别姬》,因为担心如此一来,中国读者会有错误的联想,以为这是关于西楚霸王相遇虞姬的故事。由此我们可以解读到这点:“达”不仅意味着语言流畅,通俗易懂,还指文化的传达,即“达”意味着语言和文化的可达性,译作的可达性应该在保留原作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实现。
由于杨宪益自身的语言水平、文化修养,以及得天独厚的优势(夫人戴乃迭的出生背景和学术背景),其译文语言优雅正统、自然流畅,带有浓厚的纯正英国英语味。夫人戴乃迭是一个强有力的翻译伙伴,杨曾提起过,翻译《红楼梦》时,每遇到晦涩的文字时,夫人总是能流畅地找到英文对应词。这种中西合璧的翻译伙伴模式令人羡慕,同时翻译效果也能得到保证。在充分理解原作意义,尊重原语和目的语各自的语言规范的前提下,杨氏夫妇能够突破英汉两种语言表层结构的束缚,用流畅地道的语言再现原作的语体风格,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心理期待和语言习惯,使其译文具有可接受性和可达性。
(三)译文“雅”的时代性解读
关于“雅”的标准,杨宪益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在严复时代,用文言翻译西方作品,算是“雅”。但在今天,用文言而不用白话翻译外国作品,就是太怪了。也就是说,译者应该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设身处地考虑当代读者的接受反应和心理期待,尽量合理缩短译作与原作的时空距离、译作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理论只是社会当时的价值观反映,后人应该也必须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解读视角和内容。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前人的理论思想,才是真正尊重前人,正确理解前辈的思想。我们知道在严复时代,士大夫文学潮流占主体文化中的主流地位,“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5](P85)。因此,为了迎合封建士大夫的审美心理,劝导他们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和人文思想,严复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即顺应当时读者的接受心理与期待,以便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
翻译既然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必然遵循一定的社会习俗和规范,要想被读者接受,译作必定与当时社会主体文化中的主流诗学保持一致。在严复时代,“雅”意味着用文言翻译西方作品,那么今日的“雅”,当然应有新的所指。杨宪益认为“雅”只是“达”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原文是用极俚俗的话,翻译人偏偏要用极文雅的话来表达,这恐怕也说不上是好的翻译”[2](P83)。至此,笔者认为,对杨宪益来说,雅并非指某种特定的文体,而是指语言风格层面上的“文雅”,与“俚俗”相对,且与达紧密相连,在语言形式上表现为生动流畅、富有文采。
三、翻译:民族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英国翻译家亚瑟·威利的《诗经》英译本时,杨宪益认为它学术水平很高,称得上是一部翻译杰作,但同时也指出:“有弄得过分像英国诗歌的弊病:比如他把中国周朝的农民塑造成田园诗中描述的欧洲中世纪农民的形象。”[3](P85)这样一来,译文读起来不像反映中国情况的诗歌,倒更像英国中世纪的民谣。在这里杨宪益表达了对翻译的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理解:翻译不是机械的语言转码,而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是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忠实原作,准确传达原作的文化精神是杨宪益翻译生涯中一直坚守的翻译理念。好的译作应该尊重原作的文化特色和风貌,采用异化策略,尽量保留原作的文化习俗和精神内涵。
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还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是社会精英层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翻译的目的本身往往超越技术层面的所指意义的传递。德国哲学家、翻译思想家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种途径,即在实施翻译活动之前,译者就面临一种选择:是站在原作的立场,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让目的语读者走向原作;还是站在读者的立场,对原作进行改写,让原作走向读者。为了让英美读者真正感受到其他民族人民的所思、所想和所言,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呼吁在翻译与英美主流价值观有差异的外语文本时使用阻抗式异化翻译,尊重文化差异,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而不应肆意改写,对原作实施文化暴力。在文化策略翻译选择上,杨宪益与韦努蒂是英雄所见略同。采用异化策略,才能真正实现翻译的主要社会功能价值: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
四、结语
通过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方面对其翻译思想进行系统而客观的梳理和整合,我们认识到杨宪益深受我国传统哲学与美学的影响,继承并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内涵,从翻译的形而上本质和形而下标准、方法和策略层面来看,其翻译思想蕴含着道与器的辩证统一关系。
当前西方理论大量地引入我国翻译界,我们应该抱着客观而理性的态度,既要大胆拿来为我所用,也要对其进行合理反思。盲目跟风于西方翻译理论的大潮,否定或忽视我国本土的翻译思想都是不理性的行为。立足于我国本土翻译思想,加强自身翻译理论建设,合理地运用西方理论,才有助于我国典籍对外译介模式的探索和构建,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1]柯飞.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4).
[2]杨宪益.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A].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C].金圣华,等.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4]禹一奇.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6]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7]陈丽丽.从《琵琶行》英译试论许渊冲与杨宪益翻译思想的差异[J].考试周刊,2011,(28).
[8]杨宪益.我与英译本《红楼梦》[A].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二集)[C].郑鲁南,主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9]赖祎华,欧阳友珍.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典籍外译策略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2,(12).
[10]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