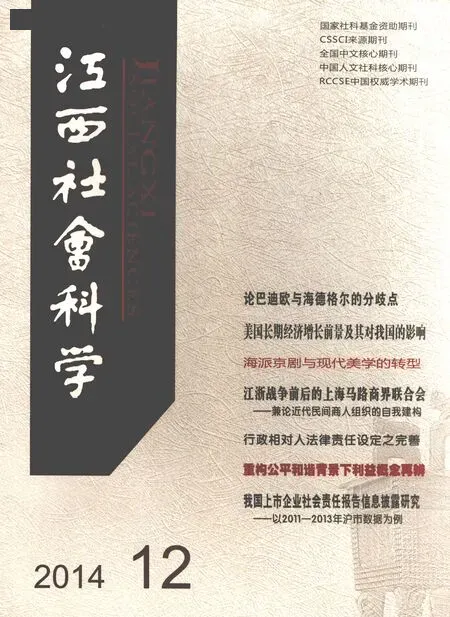医患矛盾背景下疾病概念的本质论析
■甘 进
在历史的长廊中,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不断发生变化,对这些认知的长时段考察会发现其受某一历史时期疾病观的影响。与疾病的宗教宿命观和生理病理观不同,社会建构主义宣称疾病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建构主义的这一疾病观并不否认疾病实体的存在和其生物医学特性,而是基于disease 和illness 概念的区分,强调疾病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维度,这与医学界转换生物医学模式的呼声彼此呼应。
一、疾病观的变迁
达芬(Jacalyn Duffin)认为:“从古至今,疾病都只是一种观念。”[1](P127)达芬此处所言的疾病并不单指某一具体的疾病,而是作为概念而存在的疾病。在现实生活中,当被询问“疾病是什么”时,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不是某一疾病(如糖尿病、冠心病)的医学定义或其详细诠释,而是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对疾病的总体认识,包括对疾病的产生、发展、界定和分类的总体看法,即通常所说的疾病观和疾病的本质。此时,“疾病”与英文disease 一词相对应。据此,“疾病是什么?”应被翻译为“What is a disease concept?”,而不是“What is a disease?”。疾病观具有重要作用,一旦形成便会对实际的疾病诊治起指导作用。那么人类是如何看待疾病的?对疾病的认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鉴于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疾病的不同认知,故而,对“疾病是什么?”的回答要归于对疾病概念流衍变化的考察。
整体而言,人类对疾病的认知经历了“宗教宿命观—生理病理观—社会建构观”三个阶段。很久以前,人类将疾病与上帝和星象关联起来,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神的指示和惩罚,是邪恶精神的征兆。癫痫在西方就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圣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探视。中国古人也曾认为疾病是恶魔的入侵,使用巫术来驱赶恶魔,以治愈疾病。波兰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弗莱克(Ludwik Fleck)在追述梅毒概念的起源时说:“星象说在15 世纪以前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会暗示梅毒的星象起源。……他们推测天蝎宫中土星与木星的交汇,以及位于25.XI.1484 的火星群是人类感染梅毒的原因。”[2](P2)这是因为天蝎宫负责掌管人类的生殖器,仁慈的木星在天蝎宫中被邪恶的土星和火星击败,从而解释了为什么生殖器是首个被攻击的部位。
疾病宗教宿命观的转变始于古希腊时期由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创立的医学学派。希波克拉底及其弟子摒弃疾病的宗教宿命观,抵制像传唱、咒语和吟咏之类具有巫术和宗教性质的治疗方式,致力于探求疾病的自然成因。在《圣病篇》中,他这样说道:“对我而言,‘圣病’(癫痫)丝毫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加神圣和令人敬畏,而是具有与其他疾病相同的本质和自然病因。同其他疾病一样可医治……和具有遗传性。”[3](P5)
在希波克拉底学派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宗教和巫术仍是疾病和医学知识的主要认知来源,这一局面的彻底扭转得益于17、18 世纪医学的革新。哈维(Harvey)的血液循环系统说以及随后由莫尔干(Morgagni)创立的病理解剖学(器官病理学)和比夏(Bichat)提出的组织学,使人类对身体的认识和描述不再依赖于宗教、巫术和星象的宿命论解释,而是诉诸主张身体是可控的生理机械观。到19、20 世纪,德国病理学家魏尔肖(Virchow)对细胞的病理学观察和现代基因理论使医学对身体的研究更趋于微观化。特别是医学技术的革新,使病变器官的精准定位成为可能。通过检测指标发现,细胞分子、器官组织和其结构功能的异常征象已成为常规的医学诊断手段。这一时期,生理病理观已取代宗教宿命观成为疾病认知的主流观点。医学理论和技术上的这一连串革新使医生对疾病的诊断不再基于推衍,而是基于可见的生理与病理的精准定位和一系列可量化、可检测的指标。最终,这些革新成为主张疾病是一种入侵病人的实体、强调可检测之物和身体机能改变的医学本体论者夺取胜利的武器。
自此,实体、物质、量化、指标这样一些关键词占据了有关疾病认知(包括疾病的定义、病因、治愈方法和保健护理)的制高点。从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化验、检测、实验的角度俯身看去,起初有关病患整体性和身心一体的观念已灰飞烟灭。但正当人类自信满满地为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摇旗呐喊之时,医患关系的激化、医患矛盾的突出和医患纠纷的激增却让人类在喜悦之余又不免担忧。
生物医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破除了疾病认知中的宗教和巫术成分,将人类从上帝的探视和惩罚中营救出来,却又陷入了技术至上的泥潭。在病因的诊断和检测,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日益强化质料、推崇技术,从而导致医患矛盾激增、医患关系恶化之时,疾病社会建构的研究拉开了医患关系破冰之行的序幕。与以往的疾病观相比,社会建构主义的疾病观有何不同?它又如何能淡化生物病理观中的技术维度?
二、社会建构的疾病观
对疾病持社会建构观的学者共持以下观点:(1)在会建构中,“疾病”(illness)一词已含有社会和文化的成分,因为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disease 的生物医学意义更多,故而使用illness 一词去表达疾病具有的生物医学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的含义。以咽喉炎和麻风病为例,对由链球菌引发的咽喉炎,通过药物治疗,disease 和illness 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对于感染了麻风分枝杆菌的患者,药物能抗击病毒,治疗(cure)其身体本身的不适,但治疗过程中的隔离、疾病引起的心理变化、社会的歧视以及由麻风病导致的其他后遗症是普遍存在的。对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来说,对disease 的治疗(cure/treatment)仅仅只是恢复身体常态的手段,这是重要的,但却只是健康的一部分,救治和精神的慰藉(heal and care)对患者来说也同等重要,后者正是illness 所强调的社会、文化要素。(2)疾病在其本质上不是自然的实在或者生理病理的简单呈现,而是被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定义的。福柯的医学话语对人类有关身体和疾病认知所持的建构观,以及医学知识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权力话语的论述,被社会建构主义者视为典范。福柯质疑精神病学的概念以及疯癫与健康的区分,在他看来,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社会权力话语的产物。[4]弗莱克坦言,医学事实(作为科学知识的子集)绝对不是既定的,最基础的医学实验观察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客观。[2](P3-4)为阐明疾病和医学理论的本质,他以梅毒概念的产生和衍变为例,辅以瓦塞尔曼反应(The Wassermann Reaction)涉及的翔实实验观察数据和记录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论证了医学事实其实是科学家和医学从业人员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地域等因素相互交织的时空网络中角力的产物,任何企图对这些社会产物去情景化的分析都是非理性的。
相较生理病理疾病观,疾病的社会建构观首先主张疾病的文化相对性。与生理病理观主张疾病(disease)具有普遍性不同,社会建构观更为强调病患的病痛(illness)经历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病患表达不适的方式和医生所能接受病患表达不适的方式具有某种文化依赖性,即病患表达不适的方式必须被其所在文化接受和认可,病患若以不被其文化接受的方式向医生告知自己的不适,医生会认为此人没有生病;而医生对疾病的界定和诊断也取决于当下文化中什么能被称为疾病。
其次,疾病的社会建构并不企图颠覆疾病(disease)的生理和病理机理,而是强调疾病之本性的非自然因素。与生理病理疾病观追崇疾病的生物医学特性和其可测可控性相比,疾病的社会建构观更为注重disease 和illness之间的差异性,并强调illness 层面的考察。因此,疾病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注重通过考察病患的疾病经历、疾病的文化隐喻、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以及病患在医患关系模式和医学专业知识建构中的角色,进一步研究disease 和illness 现存和变化中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含义。
再次,疾病的社会建构不是一味地追崇“术”,而是更看重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医患交流和人道关怀,即“仁术”中的“仁”。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疾病不再是症状的集合,对病患的诊断和治疗不应被分解为各类检测指标和数值,具有整体性的病患也不应被视为是需要更换“零部件”的机器。
最后,疾病的社会建构强调疾病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维度,认为疾病的意义并不是现象本身固有的,而是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中通过互动产生的。正如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对麻风病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麻风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一部鲜活的中国社会文化史。[5](P3)杨念群在“新社会史”架构下书写的“病人”,在“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之外还承载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6]
需要指出的是,在面对哈金(Ian Hacking)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时,大多数对疾病持社会建构观的学者并非他所言的激进派,而多为历史建构主义者(historical constructionist),至多是改良主义者(reformist constructionism)。[7](P21-30)
三、Disease 与Illness 之异——疾病社会建构研究之基石
上述讨论中多次出现的disease 和illness,在中文文献中均被译为疾病。这两个术语对医生和公众来说可以混合使用,但对社会学家,特别是对疾病持社会建构观的学者,却必须严格区分,因为疾病社会建构的研究是根植于被广泛认可的disease 和illness 的概念区分。因此,选择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进行疾病和医学知识研究的学者,无论是从事相关的哲学论述,还是实证研究,都需基于disease 和illness 之间的差异性。对这两个概念不加甄别的使用不仅会加深学界对疾病社会建构研究的误解,也会为实证研究埋下理论隐患。
对disease 和illness 的密集关注始于20 世纪70 年代中期的西方国家。随着精神病学的兴起,转变医学模式的呼声也日愈高涨。弗洛依德首次使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现被称为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与主流临床医学的治疗截然不同,精神分析法主张精神分析学家通过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来治疗精神疾病。这种方法不易被量化和抽取测量指标,因此无法使用仪器设备对疾病进行检测,从而在极大程度上颠覆了人类从希波克拉底时期演化而来的疾病概念和长久持有的医学哲学观与方法论。此外,由于生物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至善主义的思想不断得到强化,医学人文关怀加速消失,医患矛盾激化,纠纷频发。基于此种境况,一些学者开始呼吁转变现有的医学模式,复苏医学人文精神,由此引发了对disease 和illness 区别的讨论。康奈尔大学公共康复中心教授卡塞尔(Eric J.Cassell)认为:“‘disease’表达的是由结构或生物化学上的变化引发器官或体液受到干扰,……医生基于疾病的定义对病患进行诊断和与病患互动。病患在就医时使用‘illness’告知医生自己的不适,‘disease’则用于表达就医后的所感和对疾病的认知。Illness 是相对于人,而disease 则相对于器官或组织。”[8]在区分这两个概念后,卡塞尔认为正是医学的成功使医生在现有医学模式下的自我定位出现偏差,他们往往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疾病的治疗者(curer),而不是病患的救治者(healer)。……忘记了医生不是治疗疾病,而是治疗患病的病人。恰恰正是这一定位导致了当前医患矛盾的激化。[8]与卡塞尔观点趋同,艾森伯格(Leon Eisenberg)认为,医学人文精神的丧失,医生过度注重技术、仪器设备和实验,忽视心理治疗和社会文化的关怀,其原因在于现有的疾病理论和医学模式混淆了概念disease 和illness:“illness 是病患的感知和经历,disease 在现代医学的范式下,指身体器官和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异常。……某些时候病患患有相同的疾病(disease),但症状(illness)却各不相同。调查显示在事故中受伤的病患比在战场上负伤的病患更依赖吗啡镇痛;某些时候疾病还存在没有病症的情况,如某些高血压患者没有高血压的症状表现,但血压却被测量出高于正常值;而某些时候病患在缺乏可观察的器官病变依据的情况下感觉不适,如转换型癔症。”[9]此外,医学历史学家达芬也强调disease 和illness 之间的差异,她将听取病人反应并经医生观察诊断的异常征象称为signs,将illness 称之为病症或症状(symptoms),是病人感觉自身异常变化主观感受,如头痛、打喷嚏、胸闷等,较disease 而言,其变化缓慢。[1](P10)
稍加留意,我们便可注意到“疾病的社会建构”在大量英文文献中的表述为“Soci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而不是“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ease”。正是基于概念disease 和illness 之间的差异性,疾病社会建构的研究将关注点聚焦在“illness”,而非“disease”。对此,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在《医学的职业化》(“Profession of Medicine”)一书中指出:“当医生将病人的某些症状(illness)诊断为某一疾病(disease)时,诊断改变了病患的行为,通过将病症的含义分配给疾病,一种社会状态被添加进了病人的生物生理状态。此时,医生创造了病症,其在经验和理论上已不同于疾病。”[10](P223)该书被誉为疾病社会建构的奠基之作,弗雷德森的观点不仅为当时的医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冲突的视角,也预示了医学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弗尼耶(Alfred Fournier)笔下的梅毒除具有生物医学含义之外,还呈现了梅毒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妻子、丈夫、医生、政府、家庭和社会等多重复杂互动博弈关系的交织,以及再现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伦理冲突和制度变革。[11](P2-3)因此,社会建构主义者并不主张真实与社会建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既不事先预设疾病是被社会建构的,也不否认disease 具有的生物医学特征和实体性,但却认为illness 并不是医学事实本身固有的,而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中各方因素角力的结果。
四、医学模式的转换——疾病社会建构之佐证
希波克拉底学派将客观观察引入对疾病的治疗,开启了医生搁置病人话语和不与病患交流的“沉默的艺术”之门,不能被量化检测之物也逐渐被排除在医学范畴之外。科技革命和医学技术的快速革新又驱离了医学中固有的人文传统。在经历了医学成功和接受了当前医学模式形塑的医学专业知识教育后,医疗从业者从病患的救治者转变为疾病的治疗者,他们的关注点也从病患本身转移到了器官的病变、细菌的检测、组织细胞的变异和基因的突变等诸多可检可测之物。所以,我们经常听见病人抱怨说:医生只关心我的心脏、肝脏……,却完全忽视和漠视我和我的感受。为转变医学模式中disease 占据统治地位的格局,艾森伯格认为,要从文化维度考虑问题,通过跨文化医学研究了解其他文化的疾病理论和医学模式将有助于消除医学民族主义。[12]他在后续的文章中继续阐明疾病概念和医学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医生对病患症状(illness)的界定受到疾病概念和医学模式的影响,而疾病概念和医学模式与文化相关联,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产物。因此,在现有医学模式不完备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医学技术对疾病的诊断具有某种局限性,而精神病学的研究则能调和客观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9]卡塞尔也认为,“没有文化上可接纳的保护层,遭受疾病折磨的病患只能裸露在痛苦之中”[8]。恩格尔(George L.Engel)在1977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出转换生物医学模式的想法。他在阐述了现存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后,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传统生物医学将生物指标作为界定疾病的最终标准会导致悖论的出现,即那些积极在实验室寻求答案的医生被告知那些事实上感觉良好的病人是需要治疗的,而那些感觉不适的病人却不被认为患有疾病。……与生物医学模式不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囊括了病患、病患的感受、社会心理等各要素,充分考虑作为主体的病患、病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医生角色和卫生保健系统。”[13]当然,我们不敢妄称上述学者是社会建构主义者,但他们的观点——主张跨文化医学研究、疾病概念和医学模式的文化相关性、重视实际治疗过程的心理、文化和社会因素等等——却与社会建构主义对疾病和医学知识持有的观点彼此呼应,并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的实证研究中得以体现。
五、结语
正如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所言:“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能被有效地用于医学各方面的研究。……一些既未接受过医学训练,或未受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理路影响太深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健康和医学问题时,已不再相信自然与科学和医学之间的无缝接合,而更倾向于用社会过程去缝合这一间隙。在此意义上,他们已成为社会建构主义者而不自知。”[14](P344)而社会建构主义与医学思想的结合构成了一种可能称之为最好的医学文化史。[14](P339-340)
[1]Jacalyn Duffin.Lovers and Livers:Disease Concepts in History:The 2002 Joanne Goodman Lectures.Toronto,Buffal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
[2]Ludwik Fleck.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Trans by Fred Bradley and Thaddeus J.Tren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
[3](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作品集·圣病(英文)[M].沈阳: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2002.
[4](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第2 版)[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5]Angela Ki Che Leung.Leprosy in China:A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6]赵旭东.现代“病人”是怎样产生的?[N].中华读书报,2006-04-19.
[7]Ian 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8]Eric J.Cassell.Illness and Disease.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1976,(6).
[9]Leon Eisenberg.Disease and Illness:Distinctions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Ideas of Sickness.In:Culture,Medicine and Psychiatry.1977,(1).
[10]Eliot Freidson.Profession of Medicine:A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Applied Knowledg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0.
[11]Alfred Fournier.Syphilis and Marriage: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Saint Louis Hospital Pairs.trans by P.Albert Morrow.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80.
[12]Leon Eisenberg.The Ethics of Intervention:Acting Amidst Ambiguity.In: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1975,(16).
[13]George L.Engel.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In:Science.1977,(196).
[14]L.Jordanova.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In:John Warner,Frank Huisman (eds.)Locating Medical History.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