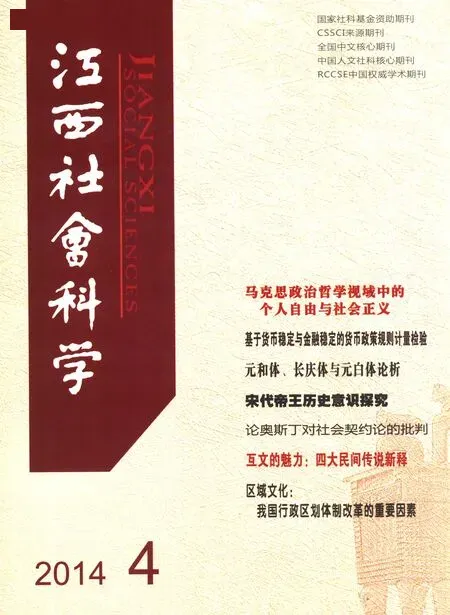文化表征之群体心理的制“动”行为
■刘讯 宋泉桦
现实生活中,群体感知大多依赖主观逻辑的概念理解,通过感官系统对外界信息进行处理,获取当前需要的主体经验。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秩序普遍表现为漠不关心,只有当信息直接作用于宿主,个体才会向其他生命体发出信号,以此表明自身所处的位置;作为在群体中“自我”的精神幻象,个体存在仅仅是时空记忆的延续,属于当下的真实,而非实在的个人。同时,条件反射性的主体经验也是相对存在,根据阅历增长随时发生改变,而受众在封闭领域内对事物的解读容易被传播者的意见左右,后期舆论环境将影响到最初传播意志在心识中的种子。
一、社会标识渐变中展现“三位一体”的精神力量
社会标识原指时代的特殊产物,在这里引申为人类集体记忆中的生命观念,它记录着一代人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人们对存在事物绝对信服的“源头”。生命的外在表现是以物质的运动方式存在的,运动的“源动力”则是来自于民族信仰的根基,或者说是家庭观念、个人感受、社会理想“三位一体”的精神现象。家庭观念是同时代人群最原始的符码,即使语言不通,也能够在相似区域内感受到文化同源的亲切;个人感受,是个体在社会中对反馈信息的综合整理,是复杂的社会人际网中因缘和合的统一体;社会理想,是主观能动性的复合期望,它缘前二者而生,极大的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三位一体”的人生构成了人类解读事物的“最初印象”,假如三者出现偏差,那么必然会加剧表征危机的形势。
(一)互动交流中的意指
实证主义民族志认为:“在反映论途径中,意义被看成是置于现实世界的客体、人、观念或事件中的,语言如同一面镜子那样起作用,反映真实的意义,就像意义已经存在于世了。”[1]尽管语言有着反映意义的功用,但是通过语言描述的事物仅限于当事人所能观察的角度,或者说任何语言表达出的意义都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只能作为时空下特殊的意义单元而存在。《符号学原理》提出语言是由两根轴组成,第一个是具有延展性的组合段平面,第二个是联想的平面。罗兰·巴特认为:“在话语之处,彼此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单元在人的记忆中联系起来,并形成了由各种关系支配的词组。”[2](P79)
词汇是人们对于已经发生过现象的描述,意义在于尽可能接近地让他人了解当时的状态。这种“再现”对后续认知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可是源于彼此境遇不同,读者会受到惯性思维的制约,形成个人解读。为了增强社会群体对同一事物的根本认同,有必须采取相关的制度控制法,即“在特定的语境下如何解释某个行为”[1]。传统观念无意识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起居,语言所指受到约定俗称的理念控制,例如东方人具有趋吉避凶的民族情结,把打碎东西称作岁岁平安,以此缓解时局下不必要的尴尬,西方人却喜欢把破败当作新的开始。由此可见,同一事件的行为即使相似,出于民族背景不同往往会被赋予本身没有的特殊含义,这个含义是根据民族信仰、民族伦理、民族交往三个部分构成的。
民族信仰,是群体共同追求的某种尚未实现的环境选择,是人们依靠的精神动力,也包括凭借想象、观察、反思形成的个人信仰;这些都能将自己极想要达到却不可能做到的形象归结为心灵的神,这种“神”的意义在于激发主观能动性,其不稳定因素则源自文化冲突。民族伦理,原指那些需要被规范的道德情操,在文化传播中实指潜藏于人类意识中的传统观念,起着客观解释文化的作用;如果能够将传播者的意图渗透到伦理的塑造中,那么后世一切的解释都会被伦理的情境所控制。民族交往,又称文化融合,意义在于调控不同文化区域内人们侧重的价值,是精神生产的交流,是文化模式的自由选择和兼容并蓄。
研究互动传播的目的,关键是理清因缘复杂的社会中,各种潜意识对当前行为的影响,发掘潜意识在传播中想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转换语言条件在后续语境中掌控整个文化交流的进程。无论是媒体还是国家和社会群体,都需要及时处理大众头脑中的流行意识,并且用大众可知的相似信息疏通国家意识、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中间可能存在的隔阂。
(二)涵指的非逻辑性虚拟建构
第一,“意识形态就是涵指的所指的形式,而修辞学则是涵指项的形式”[3](P122),为了进一步了解在社会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的态度,需要进一步深化分析事件本身的意识属性。譬如大家熟知的神话传说,它的成立与否几乎与现实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每个民族的人都相信他们的神话真实存在,或者说不成立的事件如果在群体中持续了较长时间,并且与人们现实追求的某个问题不谋而合时,这个事件就成为不能被证伪的真实事件,正如托马斯定理所定义的那样“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即为真”。后世在意识形态下只能按照相似的模式发展,如果事物超出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具体描述范围,那么即使是真理,也难以逃脱被质疑的命运。当代传播中的表征问题从历史角度观察,其实从未出现任何危机,不过在新的文化概念超越了传统的意识视域时,那种编码与解码的对抗形式就再度降临。
第二,“完全客观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放任自己的情感自由驰骋于不受限制的主观情境中”[4]。非逻辑性的虚构根植于白日梦式快感,尽管人们沉醉于自己所编织的梦境中,享受那些在现实中得不到却让自己着迷的事物,但是类似情感不具有普遍性,终将湮没在历史浪潮中。个人的非理性建构多数时候有违于真实的社会秩序,大众可以不屑一顾,不过群体的非理性建构却直接影响着社会意图,毕竟社会发展是从非理性的探索转向理性的内部调整。
二、意识形态转换
(一)相续思惑与实有
民族意识通过学习、生活与工作渗透到集体思维,在群体集会中转化成“我”的境界,表面上“我”存在于一切行为过程中,实际这种所谓的“存在”是民族情结产生的思惑延续。其中“我”所能感知的一切亦非实有,它是根植于民族定式思维的超验精神,尽管社会可以用文化符码去向它传播某种信息,但是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我”不可能完全接受外来元素,充其量也是把不可理喻的意义带到日常能够指代的范围。文化表征危机大多处于语言与表意的断裂,从根本上看就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互斥性,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作为讲述人“我”的原型介入加工,和解读者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理解,因而在“再现”某个特定文化含义时需要恢复实有的认知,即最描述对象的原始指称。
(二)非理性仪式的暗示
非理性仪式是组织传播中极为特殊的手法,它可以短时间内满足群体成员的多种层次的需要,是能对个体情绪很好释放的仪式。如教堂举行的弥撒,受洗者会在其中感受到特殊的“神恩”,暂时性对抗外在世界纷繁复杂的信息,专注于神圣事物中,陶醉于意识消融、情绪渐静的安详中。或者在集会或仪式中,主持者不断施加某种情绪导向,让与会者进入过于欢喜或悲伤的极端心态,然后周围的人彼此受到情感释放人的感染,开始无休止地向其他人吐露心声。在这个过程中,前意识会受到迷狂情绪影响慢慢消减,潜意识中的某些记忆随着主持者的需求被随时唤醒;当主持者发表意见时,参会者处于情感释放的高峰期,思维意识极度空虚,所以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想法,只有随着主导者的意图去回忆曾经类似事件,通过相似的认识极力支持唤醒集体意识的领导者。
如今的表征危机反映了民众日益增长的个人意识和当权者流逝的集权意识,当两者不能实现对话时,官方的表达语言就不再可能成为通用的表意方式。非理性仪式暗示旨在调节民众那些不合常理的念头,通过某种运动方式彻底唤醒群体的深层记忆,如叔本华认为“在性质上,理性是女性的,它只在受了以后才能给”[5](P238)。继而意识形态控制中,非理性才是人类得以发展的土壤,理性仅仅是在大变革后社会的内部调整。
(三)“自然”记忆的延伸
在传播活动中,尽管大众常常以自己的评价标准侵蚀着传统表征方式,但是“自然”依旧以记忆性保持了事物的独特。自然,其本身是独立于意识外的真实存在,记录着人类活动范围内一切行为,最接近于生命初衷的形式,难以被符号这种指示性工具所遮蔽;但“自然”的记忆却转化了不可言说的情感,在同一时间内让个体意识赋予的意义传播到大众视域。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月”代指了记忆领域里家乡的美好事物,这种能指与所指在官方领域内并没有得到制度的认可,却是由于人们记忆构造中的联想延伸出所要表达的意义。世上存在着超语言情境,当群体围绕某个象征物发生系列活动时,这个象征物不仅仅代表原指的实体,而是一段记忆再现。
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被机械复制,唯有自然,最接近于生命初衷的形式难以被符号这种指示性工具所遮蔽,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中“自然”始终保持着原真性,给予一切具有描述性的事物增添了状态属性。本雅明叹息工业时代艺术的平庸化,实际是感慨艺术所指的形式正在被机械复制的模式取代,那些独一无二的表征正在量贩化复制。他指出:“光韵的衰竭来自于两种情形,他们都与当代生活中大众意义的增大有关,即现代大众具有着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的强烈愿望,就像他们具有着接受每件实物的复制品以克服其独一无二性的强烈倾向一样。”尽管大众以自己的评价标准侵蚀着传统表征方式,但是“自然”依旧以记忆性保持了事物的独特,没有人可以超越“自然”而让事物具有生机,更没有被异化的“自然”,毕竟能够改变的是语言形式,而不是潜藏在人心中的记忆方塔。
“自然”先意识存在,通过意识转换成可被认知的信息,在交流进程中“自然”建立在运动的物质上,其活力对应了“自然”特有记忆功能。如在宗教礼拜和团队训练上,人们少不了运用大幅度的动作来强化自身某项能力,在集体中互相的超常态运动往往留给了人深刻的印象。因而任何“自然”的记忆使用少不了身体的剧烈运动,当行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出于兴奋会毫不犹豫地铭记当前的一切。传播中最为狂热的不见得是那些思想深邃的言论,让整个民族振奋的大多是让大家从头到尾都彻底运动的群体关注。
三、表征在不同领域的困境
(一)个体编码的无意识预设
表征是“通过话语符号对世界进行‘重构式’再现,并对其意义进行重新诠释的过程”[6](P90)。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同意识形态在对世界的解读上发出了异议声音,民族、群体内部确定的符号意义再临重新建构。首先是因为时代精神被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分化成了三部分,如前现代认为“眼见为实的真实观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世界”,现代则认为把差异的存在看成是正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现代却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世界,一切都存在于内在之中”。[7](P10)不同思维导向造成了语言分歧。另外,交往中编码也会受到个性语言的影响,如时下流行的网络词语“你妹”,词根上解读是你的妹妹,在大众语言习惯上却指代脏话“你妈的”,而在年轻一代中常常是诙谐幽默的语气词。显然,社会无意识感染着人们的语言习惯,看似充满内涵的词语在个人消解中或许只是发语词的延伸,一种事物的实指内涵可能在个人无意识的组织中失去原有的作用,那种新式的含义来自于个人生活的习惯。
(二)同位相移的复合认知
词汇不只是表达媒介,在历史交流中它充当记录的工具。然而,历史记录在同一事物上经常是以别样的形式呈现,如“狗”这个形象既可以用“犬”代替,也可以用“地羊”,为了押韵诗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词汇在原始位置的传统意义尽管一直被我们熟知,但是失去了特殊的表达方式就不能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历史。单一性词汇在认识上是断裂的,我们必须根据现实语境中描述的目的去判断,才能将词汇的现实与历史相联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表征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借助语言形式来解释事物特有的含义。在西方“God”具有神圣的意味,民众把它放在心里致以虔诚的祷告;在东方“神”是“人成神成”,大众会用神表现出通过努力超越自我的情感。同样的事物,却因为认知分歧产生了不一样的指代效果,证明了概念“无论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普通性,都不是被置于历史或在厚重的整体习惯中沉积由个体进行运作的结果”[8](P68)。或者说除了讲话时所处的言语情境影响着人的表达,还有超出个人意识外的群体记忆左右着文化表征。
(三)表征合法化的向度认知
表征合法化是要求文字与客观存在的事物相对应,非法化则是关于受众“原子论”遗留的历史分歧。如人们对于知识的解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前者的知道是了解外在知识的意思,属于公共知识领域;后者的不知是内在心灵的层次,属于私人理解过程。根据两者的状态来判定,知与不知都属于知识的领域,不过社会只能承认前者在公共领域的有效性,而不能对其内在知识做出统一的判断。由此可见,表征非法化主要是那些不被承认的内在知识向公共知识发起了挑战,或者说在某个区间段内公共知识不能满足大众的精神导向,以至于大众选择了用自我解读来颠覆传统的定义。任何信息在解码时,都难以摆脱主观经验的制约,尤其是“感悟”的东西,因为成长历程包含着许多不稳定因素,所以最后感悟的附加知识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它没有一个实相能支持自己的观点,却又彼此相连决定着想象界。
在当代的文化表征中,为生活而表现和为表现而表现是合法化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生活而表现是依它所生境的另类方式,如果眼前的状态发生改变,表达的内涵将与前大不相同,或者说这种认识是被赋予的精神。为表现而表现则依托于传统理念的延伸,所要表现的就是该表达方式的直指。马尔库塞说:“在人类现实中,所有为获得其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殚精竭虑的存在,都因此是‘不真实的’和不自由的存在。”[9](P103)表征危机涉及的不只是语言上的变革,还包括心理重建,乃至意识形态的转化。为了进一步了解其生成要素,研究群体心理的动能控制,是有效调节群体情绪、传播主体价值的必要途径。
[1]李鹏.表征与合法化的双重危机[J].当代传播,2013,(1).
[2](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Geertz,C.Thick Description,in c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 ,Basic.
[5](德)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李成铭,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6](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7](美)艾尔·芭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8](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