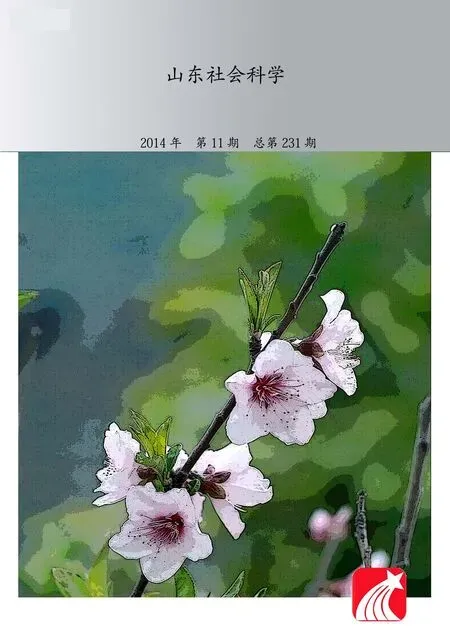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
曹 霞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指出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阶级,其内容主要包括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目标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暴力手段等等。*[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成仿吾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37页。虽然马、恩后来对于阶级理论进行过修正,但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20世纪中国主要吸纳了其中的“革命”、“对立”、“压迫”等内涵,在其表述中,阶级对立和等级观差不多等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加压迫的概念”。*[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从1927年到“十七年”,阶级话语在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几度变迁。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阶级话语是如何成为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的?政党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起着怎样的支撑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思考及其创作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左翼文学:阶级话语与革命阵营的想象
阶级话语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词汇,肇始于192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时期。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它和共产党革命一样以大革命失败为起点,“因此被革命政党所接受,成为后来正统革命文学史的蓝本”*程凯:《革命文学叙述中被遮蔽的一页——1927年武汉政权下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言论》,载《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这意味着“革命文学”从一开始就与政党政治形成了一种“合力”关系。
在对阶级话语的吸纳、打造和塑形等方面,革命文学深受共产党观点的影响。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共产党特别不满于“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的狭隘与动摇,指出革命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但没有能改造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这成为革命文学中阶级话语表述的基点。与此同时,革命文学批评家还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意识斗争”、“分离结合”和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对“小资产阶级”进行想象性和否定性评价:“要就滚到无产阶级的阵营里来,要就滚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事实上没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一条路可以给予大众走的!”*钱杏邨:《从东京回到武汉——读了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以后》,载《文艺批评集》,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73页。郭沫若和冯乃超直接断定小资产阶级是“忧愁的小丑”[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注]麦克昂:《桌子的跳舞》,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阶级”一旦与历史和政治的“进步”相联结,便获得了强势的超级话语权力,以及超越现存秩序的道德正义性与优先性。
在左翼批评家看来,无产阶级文学是阶级和意识斗争的体现,作家应当超脱于审美性和艺术性,真正实现阶级意识的强化与内化,从而投入推翻现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革命中。因此,“写什么”被提到了比“怎么写”更为重要的位置上,“阶级”被频繁使用,成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中的重要标准。钱杏邨提出文学应选取表现无产阶级斗争、富有革命意义的“尖端题材”[注]钱杏邨:《新文艺与女性作家》,载《文艺批评集》,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96页。。他认为孙梦雷《英兰的一生》技巧上相当成功,可是“在思想方面失败了”、“在时代的面前落伍了”,原因就是小说在取材上“仍旧迷恋过去的骸骨”,没有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时代精神”。[注]钱杏邨:《英兰的一生》,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9页。钱杏邨不满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认为这类人物生活优裕,与社会底层和革命时代没有接触,只有软弱的感情而缺乏坚强的意志和理智。他批评丁玲《在黑暗中》的人物“大都是为感情所支配着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而在沅君的《卷葹》和《劫灰》中,“人物的思想仅只是为热情所支配着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的没有社会依据的自由思想,只是偶而的感兴”。[注]钱杏邨:《新文艺与女性作家》,载《文艺批评集》,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91、114页。“左联”决议更是将“题材”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学要以“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41页。等为主要题材。可以看出,从将阶级话语引入文学批评一开始,批评家就着力于提取“阶级”中的政治含义并强化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与功能。
从“阶级”角度切入作品,最终目的不是修剪作品中的“异质”,而是为了改造作家的身份认同和阶级属性。按照马克思关于知识分子是靠有闲财富养活、不生产价值的理论,知识分子在阶级话语秩序中的地位非常尴尬。对“阶级”的“正本清源”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化的政治和现实中的身份想象与认同焦虑。自诩“革命”的批评家将阶级话语当作“辨认”政治身份的武器,对曾经的文学革命和知识分子身份进行批判。李初梨将五四视为“资本主义意识的代表”,将其后的文学视为“小布尔齐亚意识的结晶”,认为都当在清除之列。针对甘人为鲁迅的辩护,他运用阶级分析论质疑鲁迅的阶级属性:“鲁迅究竟算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1928年第4号《文化批判》“新辞源”中有一个词“珰·吉诃德”,比喻那些时代的落伍者,这一期的《文化批判》成为“珰鲁迅”专号。在“阶级话语”的“甄别”下,鲁迅被断定为“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注]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甚至被视为“封建余孽”和“法西斯谛”的“二重性的反革命”[注]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8-579页。。叶圣陶、鲁迅、郁达夫、张资平则被“捆绑”在一起,被视为“倾守保守”与“没落”的知识阶级。[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这种由“阶级”出发对作家作品进行评判的批评模式侵蚀了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而代之以政治功能,遮蔽了不同美学与创作风格之间的差异。
那么,如何才能改造作家的阶级立场,使得他们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呢?左翼批评家将作家的主体体验视为“无产阶级文学”之源,认为关键在于“意识”问题,因而要求智识阶级必须努力获得“普罗列塔利亚特底意识”,如此就是一个“普罗阶级底意识形态者”,就可以“制作普罗艺术”。[注]沈起予:《艺术运动底根本概念》,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3页。这种断定将问题转换为了“如何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有人指出一个有效的途径是“接近工人”,这对“思想的改造”“大有裨益”[注]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的情形》,载《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还有人提出了“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注]香谷:《革命的文学家!到民间去!》,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的口号。随着具有亚政治化特征的“左联”的成立,阶级的“净化”工程悄然启动。“损害”无产阶级形象的作品受到组织内的严厉惩罚。据有关人员回忆,在《开除蒋光慈党籍的通知》中,理由之一就是被批评为“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注]谌宗恕:《左联文学新论》,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的《丽莎的哀怨》。对“五四”文化精英和本阵营作家尚且如此,对持“文艺自由论”、“人性论”的“第三种人”、梁实秋等人,左翼文学批评家更是高举“阶级”大旗,将其放置于时代政治的对立面予以“清理”。
在以阶级为标准的批评体系下,那些描写“工人”或“农民”及其“革命意识”的小说被纳入“无产阶级文学”而受到批评家的推介。文艺原则与政治判断被糅合起来,向读者受众揭示了一种可被通俗理解的革命内涵。钱杏邨在承认龚冰庐的短篇小说“技巧虽没有成熟”时,更多地是赞赏他以工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别具一种风味”,“有一种相当的吸引读者的力量”。[注]钱杏邨:《谈谈冰庐的短篇》,载《麦穗集》,落叶书店1928年版,第18页。在分析戴平万的作品时,钱杏邨认为这在目前“比较能令我们满意”,原因是作家以“全身全心全意识集体化了”的农民为主要人物。[注]钱杏邨:《关于〈都市之夜〉及其他——戴平万的短篇的两个主要的描写对象》,载《文艺批评集》,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257页。丁玲在转变写作方向之后创作的《水》远比她早期小说粗糙,但它以1931年中国16省的水灾为背景,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表现农民的反抗,充满了高涨的革命精神,被冯雪峰褒扬为“从浪漫蒂克走到写实主义”过程中的“新的小说的诞生”。[注]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载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经过批评家的反复阐释,阶级话语里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压迫者/被压迫者”、“进步/反动”等成为批评实践中的重要修辞,从而营造了文学中阶级话语的二元对立面相。
在左翼文学时期,由于现实生活中的阶级状况和革命理念并不明确,批评家关于“阶级”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想象成分。他们将“阶级”整合进文艺批评观念,以维护其文学和革命观念的政治合法性与纯粹性。批评家从“阶级”角度判断作品是否“进步”和“革命”,由此滑向对作家阶级属性的判定,最后对作家的立场和思想进行清理。在这种政治批判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具有强力监督和反击功能的“照妖镜”、“游击队”。[注]何大白:《革命文学的战野》,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9-500页。不过由于此一时期的“革命”主体及其文学要求尚未澄清,也并未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形成根本性的动摇,“阶级”的界定和内涵还有游移性与模糊性。此外,左翼文学批评家多是以文学阵营成员的身份进行批评实践的,而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思考和怀疑又给阶级话语留下了想象空间,使得这一话语并未完全溢出文艺领域的范畴。
二、延安时期:阶级话语与政党伦理的渗透
与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时期相比,延安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相对完整的政党形态和伦理。在《讲话》的指引下,在批评家和延安舆论力量的多重建构下,阶级话语不仅成为区分阶级属性的标准,更被用来作为清理“异己”、整合“我们”阵营以达到党派需求的工具。
与二三十年代文学受政党政治影响的批评实践不同的是,在延安时期,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和等级制促成了“卡理斯玛”(Charisma)的出现,即因“特殊的力量或品质”[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而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可的领袖人物,他能够通过支配物质、经济、政治等资源而实现文化霸权的统治。王富仁先生认为,左翼文学虽然在40年代受到压制,但它的话语形式还保留着,只不过在这个话语形式背后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注]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而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所代表的政党伦理成为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指明了“阶级性”与“人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样一来,“人性”无不带有阶级色彩,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概莫能外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理论中的“二分法”区分了不同阶级和阵营,抑“小资产阶级”而扬“工农兵”,并正告延安作家:“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讲话》结尾,毛泽东阐述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等问题,给了“小资产阶级”以严厉的当头棒喝: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这实际上将“小资产阶级”从“我们”和“人民”队伍中清除了出去,置其于“无产阶级”的对立面。随着《讲话》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的《解放日报》以及中央总学委、中央宣传部等各级机关的建构,再加上周扬等人的积极阐释,以《讲话》为核心的文艺话语成为评判、指导解放区文学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因此,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评价问题上,延安时期比革命文学时期更具有“政策”和理论依据。1942年2月27日和4月3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叹息三章》和《诗三首》,其间弥漫着他擅长抒写的徘徊于寂寞孤独而又企冀于奋起前行的情绪。诗歌发表后引起了批评家的争议,虽然意见有所不同,也有批评家为何其芳作出辩护,但在“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幻想,情感和激动底流露”[注]吴时韵:《〈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19日;贾芝:《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由吴时韵同志的批评谈起》,《解放日报》1942年7月18日。这一判断上几乎都是一致的。莫耶的《丽萍的烦恼》描写知识女性丽萍与军人丈夫在精神和思想观念上的冲突,被批判为立场错误的“反党小说”[注]赵戈:《莫耶,真正的女兵》,《飞天》1986年第8期。,发表小说的《西北文艺》被停刊。这些作品受批判的共同原因在于,按照批评家的“阶级”观,它们所倡导的情绪是不“健康”的或“落后”的,只能让读者陷入消极悲观,弱化了《讲话》提出的“无产阶级”美学的“进步”精神与革命特质。在批评家的反复运作下,“阶级”成为批评实践中的霸权词汇,它代替意识形态执行着对文艺界和思想界重新编码的政治功能。
延安时期,运用阶级话语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清理的典型当属王实味事件。批评家从《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中引申的例证、围绕文本进行的论述与毛泽东和康生的政治判断“合围”,文本批评最终成为对作者本人的批判,为王实味的政治处理提供了文本依据。蔡天心反复强调由于王实味没有“阶级”立场,才会将“政治家”与“艺术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与其他阶级的政治家相提并论。[注]蔡天心:《政治家与艺术家——对于实味同志〈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之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陈伯达在“托派”王实味前面加上了无数与“阶级”相关的形容词:“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斯基主义。”[注]陈伯达:《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周扬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中宣称了两个阵营的尖锐对立:“托洛斯基王实味不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大众服务,都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而其实则是真真实实地为了剥削阶级与黑暗服务。”[注]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日。通过王实味事件,延安时期的文学批评作为政党意识形态工具的功能初步成熟和完备:即按照政治化的结论,在文本中有意识地寻章摘句和有目的地过度阐释,强化“阶级敌人”的“错误”,从而完成对意识形态的“印证”。这种提取文本中的“罪证”以证实其“罪名”的批判方式在“十七年”的萧也牧批判、胡风集团案等政治运动中屡见不鲜。
在二三十年代,批评对于作家并未产生过多的干预或介入影响,而在延安时期,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批评者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否则难以得到重返“我们”阵营的许诺。周立波曾在文艺整风前创作出备受何其芳称赞、充满浓郁诗情和温馨情感的《牛》、《麻雀》等小说。经过文艺整风和对《讲话》的学习后,他批评自己过去没有接近农民,不熟悉农民,以致所写的作品题材不够“重大”,与现实结合不够紧密。[注]周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有的作家无从完成或困惑于“思想改造”,只好选择搁笔或转换写作方向。何其芳说自己从1942年以后就没有再写诗了;[注]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载《何其芳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5页。莫耶在受批判后转向创作部队英雄事迹,但在建国前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注]严寄洲:《忆莫耶同志》,《飞天》1986年第8期。1944年,到延安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赵超构敏锐地捕捉到了具有审查监督功能的“批评的空气”:“延安人所说‘批评’的意义,就是用多数人的意见来控制少数人,在主观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评的作家,事实上也不会有。”[注]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社发行民国三十三年版,第137-138页。在他看来,这种批评已经干涉并损害了作家主体意识及其创作才能。
与左翼文学相同的是,延安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改造,只是它带来的“阶级改造”更加彻底,“到民间去”也被更为明确的“结合”论所代替,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十七年”。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提出“笔杆与枪杆结合起来”的口号,号召大家到部队和民兵里去,实现文武的结合。[注]《笔杆与枪杆结合起来 文化人到部队中去!》,《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1943年3月,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文艺工作者50人开会。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依照《讲话》的精神提出“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相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注]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会后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肖三、艾青、塞克等赴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并进行劳军,陈荒煤到延安县工作,刘白羽、陈学昭到了部队和农村,草明在陕甘宁特区体验生活,周立波主动申请加入王震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这种“结合”使作家的创作题材和风格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丁玲不再“干预现实”、“暴露黑暗”,转而描写歌颂无产阶级工农兵,如被毛泽东誉为“新写作作风”[注]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 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的《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在阶级话语与政党伦理的“合力”下,渺小、有限的个人将投入集体(“我们”阵营)视为一种超越个体局限的阶级乌托邦。
如果说,左翼文学时期的阶级话语还只是批评家个体或以文学团体名义作出的评判,那么在延安时期,“阶级”则成为政治权威的理论依据和“文艺政策”的直接表达,甚至成为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政治生命进行判决的标准。随着政治力量的深入推进,以阶级话语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以满足党派意识形态需要为宗旨,在功能和属性上都趋近于“文化生产场”中的“低级位置”,即越来越“倾向于服从外部权力的要求”,由此反使自身的地位处于更加恶化的“非自主性被支配和统治的地位”[注][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9页。。这种政治化取向使文学批评遵循着以下的批判逻辑:政治权威定性——文学批评“跟上”——群体性批判运动——“改造”或打倒批判对象。有了绝对权威的首肯,批评家的主体能动思考能力被消解了,一种以政党权力与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批评话语被建构起来。在从党派向新的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阶级话语有利于新型意识形态的崛起和建构,但也使文学批评深陷于“不能自主”的泥沼。
三、“十七年”:阶级话语与国族意识形态的建构
1949年,随着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阿尔都塞将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比于前者,后者的效用主要集中于精神和思想统治层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只可以是标志领地的界标,而且也可以是阶级斗争——常常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场所。”[注][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在将“工农兵”视为国家政治基础的新中国,随着简便易行的以“阶级出身论”区分社会阶层经验的推行和主流意识形态屡屡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阶级话语成为批评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规范,以及建构社会主义文艺新秩序与国族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与延安文艺生存形态相同的是,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也是以《讲话》为圭臬、由共产党直接主导的政治文化实践。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指出除了《讲话》之外,新中国没有第二个文艺方向,“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他还明确规定“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和“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0、96页。1949年8、9月间,上海《文汇报》发起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何其芳在具有定论性的文章里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作家写什么样的人物“不仅是一个题材问题,而且正是一个立场问题”[注]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4期。,充分体现了其背后国族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持向度。
如果说延安时期的文艺批判还只是局部化和个体化的话,新中国的文艺批判运动则通常是由上而下、波及全国的大规模的规训与惩罚行动。文学批评因其“战斗性”和可控性而成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批判运动大都是在“阶级”基础上获得了政治合法性:“萧也牧批判”针对“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武训传》批判”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路线;“《红楼梦研究》批判”针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教育和宣传等非暴力手段,层层传达“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声音,引导民众完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十七年”中,根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指令,文学批评注重的是作品是否描写了阶级路线斗争。那些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人公的温情主义或者不符合阶级斗争原则的作品都受到了批判,如《腹地》、《关连长》、《青春之歌》、《“洼地”上的战役》、《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等。在主流批评家的强大压力下,批评对象必须根据既定的结论和批评文本进行自我批评(检讨),承认自己思想立场上的“阶级”问题,否则不能过关。《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遭到批判后,郭小川检讨自己“只能抒一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情,根本不会抒人民之情”[注]郭小川:《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曹禺沉痛检讨自己的“阶级”立场:“思想有阶级性,感情也有阶级性。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来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注]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不断运作,阶级话语逐渐被内化为作家自觉遵守的写作原则。
在带有强制性的规训批评下,作家对文本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力图使之达到“洁净”和纯粹的“阶级”标准。1960年,广东作协多次召开《金沙洲》讨论座谈会,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小说中无论是“党的光辉形象”刘柏,还是落后分子郭细九,都不能代表各自的阶级。作者于逢对小说进行了修改,他将党的跟随者视为英雄,对不同意见者进行了丑化,使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在初版本中,郭细九、师爷胜等是走自发道路的落后人物,在修订本中他们成为现政权下的反对分子甚至反动分子。修订本还删减了公社支部书记黎子安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增加了他和群众一起抗旱的情节;刘柏在初版本中性格犹豫不定,在修改版中则变得更加坚定;此外还增加了郭有辉对“革命阶级”的抵触性,使这一人物的“中间”状态被大为压缩。《创业史》、《青春之歌》等文本的修改也在“阶级斗争”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强化。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博弈中,后者不断溃退直至“消亡”。作品中的“异质”色彩消失,融入了阶级斗争的“合声”之中。
对文本的修改尚属于“规训”范畴,而比这更为严厉的是文学批评对作家主体的“惩罚”功能。依托于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可以从作家的外部生存环境对其进行高压控制,堵塞作品的出版渠道,剥夺作家的创作权力。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形成了“批判/被批判”、“控制/被控制”的不对等关系。萧也牧在受批判后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此在文坛销声匿迹;阿垅的《诗与现实》受批判后,连写抗美援朝的诗歌也不能完全发表;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被批判后,文章发表不了,遭遇的是“同志们的冷淡和机关领导的训斥”[注]《作协严重脱离群众》,《文汇报》1957年5月31日。。如茅盾、老舍、曹禺等弃笔或改变题材风格的作家更是数不胜数。更为严重的是,在“十七年”起伏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旦遭到过批评,即使当时侥幸过关,也摆脱不了“死在第二次”[注]黄秋耘:《风雨年华》,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的命运,萧也牧、海默等人的结局均是如此。当这种惩罚被模式化和流程化以后,它针对的不仅仅是不符合阶级话语的作家作品,还具有强烈的“侧面效果原则”:“对于受惩罚的人,这是最小的惩罚,而对于想像这种惩罚的人,这是最大的惩罚。”[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以致于对批评的恐惧在作家中间形成了一种烈性传染,最终导致了“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疼不痒,下笔先看行情”的可怕的新“革命世故”[注]萧乾:《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人民日报》1957年6月1日。,对作家主体的创造力和独立性造成了巨大的戕害。
在“十七年”中,对于作家的思想和身份改造几乎成为生活中的日常程序。文艺工作者能不能和工农兵“真正结合”被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这与《讲话》的阶级二分法如出一辙,只是此时这种判断由于依托了单位制度而对文艺工作者具有行政约束力。从丁玲拿着户口迁移证喜笑颜开地走在乡间道路上,到“丁陈反党集团”之后她跟随丈夫陈明去北大荒“改造”的个体命运的变化;从1951年文艺整风之后全国文联动员巴金、曹禺、贺敬之等知名作家到朝鲜前线和工厂农村中去深入实际斗争的“采风”,到1957年之后大规模的“反右”、“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文艺工作者都无比虔诚地希翼“在斗争中自我改造”[注]《全国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文艺报》1952年第5期。。李季、柳青、草明等作家身体力行将全家都迁到了边远农村、工厂和矿区,立志“扎根”于工农兵生活。革命文学时期的“到民间去”和延安时期的“结合论”至此才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这种“改造”最终褫夺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身份,更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生命的尊严。
在“十七年”中,以“工农兵”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题材创作成为主流。在意识形态的支持和批评话语的反复阐释下,“工农兵”的形象、“革命”精神和审美趣味等成为批评文本的重心。艾芜的短篇小说集《夜归》通过家庭生活歌颂“劳动模范或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批评家以“清新的喜悦之感”形容读完后的感受。[注]巴人:《闲话〈夜归〉》,载《巴人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对于《喜鹊登枝》、《创业史》、《三里湾》等符合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事业”的“农业合作化”题材,批评家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能使人们深切感受到“我国农村人民生活的无限丰富性”[注]巴人:《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载王克平、钱英才编:《巴人文艺短论选》,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对于“革命小说”,批评家关注的是作品是否描写歌颂了“英雄人物”和“革命胜利”。他们高度赞赏《红日》的“意义”在于“歌颂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战士”[注]齐鲁:《喜读〈红日〉》,《文艺报》1958年第14期。,《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成功”原因是“刻划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正面形象”[注]方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读〈野火春风斗古城〉》,《文艺报》1959年第1期。。批评家以“阶级”标准衡量作品,高度肯定作品中的新时代英雄人物形象,使“题材论”和“人物论”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评工具和评价体系,以建构社会主义文艺和意识形态新秩序。在社会主义新文学的舞台上,经常被演绎的不是文学的独立原则,而是“文化政治”和“民族政治”。
四、结语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拥有文化资本的文化生产场处于权力场内部的被统治地位,并且时时受其影响。布迪厄指出,“文化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等级化的两条原则之间斗争的场所,两条原则分别是不能自主的原则和自主的原则。”“不能自主的原则”指文学的政治和功利化社会原则,有利于“在经济政治方面对场实施统治”的人,“自主的原则”指文学的独立原则,比如“为艺术而艺术”等信条。两条原则的斗争结果取决于权力场中的占据者。[注][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从1927年到“十七年”, “阶级”、“斗争”、“革命”等政治词汇充塞批评文本,成为批评实践的关键词,文学批评的“自主的原则”远不敌“不能自主的原则”。在阶级话语的评判标准下,作家主动或被动地向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意识形态靠拢,希翼得到国族政治的接纳与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的生命力遭到破坏,成为依附于他者的“次主体”或“无主体”。阶级话语的干预不仅使作家失去了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也使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日益流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中“自我”与“个体”话语的丧失。与此同时,文学批评自身也被“阶级”话语掏空而成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漂浮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