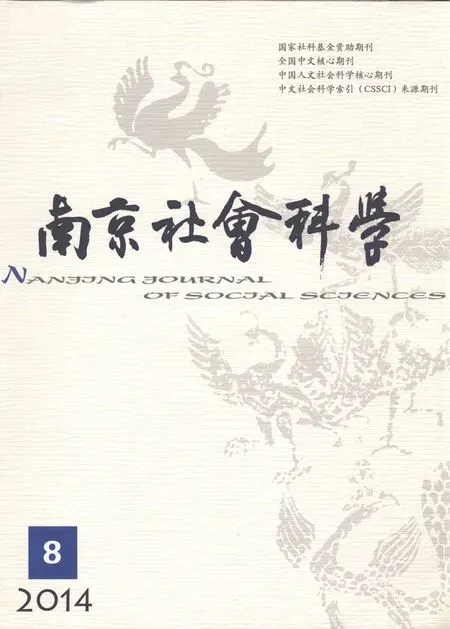自我、身体与他者*——胡塞尔“第五沉思”中的交互主体性理论
朱耀平
自我、身体与他者*——胡塞尔“第五沉思”中的交互主体性理论
朱耀平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第五沉思”突然转向对他者问题的长篇大论的探讨的基本动机,在于消除人们对“先验还原”的唯我论后果的顾虑和质疑。根据胡塞尔的看法,我体验他者的存在过程,就是下列这样一个过程:基于他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性,我将我的身体所具有的“意识性”,以“类比”的方式转移到他者的身体中,从而把他者的身体看成他的意识的外化——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把他者的意识与我的意识一样都看成肉身化意识。通过这样一种胡塞尔称之为“结对”、“统觉”或“共现”的过程所实现的他者的建构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使我能够把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对象同时也看成是为他者的内心生活所体验的对象。这也正是以“我思”或“自我”为立足点的先验现象学摆脱唯我论困境的出路之所在。
胡塞尔;先验还原;唯我论;自我;身体;他者;交互主体性
众所周知,就胡塞尔生前已公开出版的著作而言,他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系统论述主要出现在《笛卡尔式的沉思》①特别是其中的“第五个沉思”中。就此来看,只是在胡塞尔进入晚年之后(1930年前后),交互主体性问题才成为他哲学思考的“重头戏”。但这决不意味着胡塞尔到了晚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早在“观念Ⅰ”②时期(1913年),交互主体性对胡塞尔来说就已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原因在于,“观念Ⅰ”通过先验还原所确立的被称为“一切原则之原则”的立足点——先验自我、纯粹意识或“我思”③——始终伴随着唯我论的幽灵。交互主体性理论则是胡塞尔为了驱赶那个幽灵所不得不反复念叨的咒语。关于这一点,或许胡塞尔本人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1929)一书中的如下叙述或许是最好的注解:“早在1910-1911年冬季和夏季学期的哥廷根讲座中,我就已经将关于如何基于交互主体性克服先验唯我论的要点提出来了。然而,如果要真正弄清上述问题,那么,尚需对其中包含的诸多难题逐个加以研究。在多年之后我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即将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一书中对这个理论进行简要的说明。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将对这个问题研究所获得的明确结果付梓。”④《笛卡尔式的沉思》(法文版)在胡塞尔生前得以如期出版,不过,胡塞尔上面提到的出版一部关于交互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明确结果的计划,却没有付诸实施。原因在于,胡塞尔在接下来的那一年忙于进行另外一项研究计划。⑤不管怎样,胡塞尔的上述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他提出交互主体性理论的内在缘由以及《笛卡尔式的沉思》在其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提示。
一、《逻辑研究》中的交互主体性问题
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胡塞尔来说,交互主体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先验还原所导致的唯我论困境所引发的。从时间上来看,胡塞尔对这个问题的公开阐述出现在1910-1911年哥廷根大学的讲座中,也就是“观念Ⅰ”出版前两三年。当然,胡塞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进行。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1-3卷)⑥的编者耿宁(Iso Kern)认为,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的具体研究始于1905年。然而,即使在更早出现的《逻辑研究》中,也并非完全看不到“交互主体性”的踪影。固然,如果把先验还原所导致的“唯我论”困境看做交互主体性理论的内在缘由,那么,由于《逻辑研究》并没有像“观念Ⅰ”那样把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因此也就不存在通过交互主体性摆脱唯我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没有以任何哪怕是“外在的”方式触及交互主体性问题。实际上,《逻辑研究》“第一项研究”关于语言表达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孤独的内心独白中的不同功能的论述中,“对他者的体验”这个在胡塞尔中后期才得到充分发挥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核心概念,至少已经是有迹可循。
在语言表达的特性和功能的问题上,胡塞尔的思想显得很复杂。他一方面强调语言表达因其表达某种含义而与仅仅对它物起指示作用的标志(如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不同;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在某个人孤独的内心独白中,语言表达才是纯粹的“表达”,而在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中,语言表达不仅仅是表达,同时还是“标志”,即对于听者来说,说者口中发出的声音不仅仅具有需要他加以理解的意义,同时还是说者试图向他表达的那种“意义”或“内心体验”的标志,就像说者的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对听者来说是前者的内心活动的标志一样。
只要听者听得懂说者所说的话,他也就能够知道说者试图向他表达的“意义”或内心体验是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在胡塞尔看来,在此之前,听者首先必须把说者作为一个向他说话的人来“感知”,即必须把说者口中发出的声音看做是他的内心体验的标志。另一方面,对胡塞尔来说不容置疑的是,听者决不可能在原初的意义上拥有说者的内心体验,即听者并不拥有对说者的内心体验的“直观”。既然听者并没有对说者的内心体验的“直观”或“感知”,那么,他把说者口中发出的声音看做其内心体验的标志,即把说者看成一个向他说话并借此向他传达某种内心体验的人来感知,又何从谈起呢?《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没有也不可能对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作出回答,甚至没有明确地将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综上所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逻辑研究》已经触及了“对他者的体验”这样一个对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这种触及从深度上来说是很有限的,具体表现为:
首先,它不是基于先验还原所导致的唯我论困境提出来的。就“对他者的体验”或“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决定着先验现象学能否摆脱唯我论困境而言,由于《逻辑研究》并没有实行先验还原,因此,它对“对他者的体验”这个问题的触及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触及。
其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逻辑研究》没有对下列这个困难的问题作出回答——在听者不可能拥有对说者的内心体验的直观的情况下,何以能够把说者作为通过向他说话来传达某种内心体验的“他者”来感知?一方面,听者决不可能具有对说者的内心体验的直观,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听者把说者作为“他者”来体验,那么,在听者不拥有对说者的内心体验的直观或感知的情况下,他如何能够把说者看做一个具有一定的内心体验的他者来感知或体验呢?《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显然尚不具备解决这样一个迫在眉睫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的思想资源和手段,因此只好满足于对其保持一种鸵鸟心态。
二、先验还原的唯我论困境
与《逻辑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交互主体性或他者的建构问题却是《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核心问题。实际上,《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第五个沉思”的篇幅几乎是前四个沉思的总和,这绝非出于偶然或随意,而是与他者问题在胡塞尔哲学中的极端重要性有关。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者问题是“先验现象学的试金石。”⑦先验现象学把“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思”作为“一切原则之原则”,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1)“他”与“我”的区别何在?(2)建立在主体的复数性基础上的世界的客观性何在?就“他者”这个概念对超出自我反思之外的真理和实在性起着奠基作用而言,它在胡塞尔哲学中扮演着与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类似的角色。⑧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第五个沉思”突然转向对他者问题的长篇大论的探讨的基本动机,在于消除人们对在“第四个沉思”中得到详细阐述的“先验还原”的唯我论后果的顾虑和质疑。先验还原把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归结为它们对于自我的意义,归结为自我的意向活动的结果和成就;所有一切差异和所谓的“他者”都从自我的活动中所产生,又被自我所吞没。胡塞尔的下述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先验还原的上述结果和意义的自我供认:“先验还原把我与我的纯粹的活生生的意识体验以及建立在它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基础上的统一体联系在一起。显而易见的是,那样一种统一体与自我不可分割,因此属于自我这个有机整体的一个内在环节。”⑨受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启发,胡塞尔把将它自身建构的对象包括在内的“先验自我”称为“单子”,以先验自我为立足点的先验现象学因此有了“单子论”(Monadism)这样一个新的名称。然而,这样一种单子论却不仅仅是一种“一元论”(Monism),而且似乎与“唯我论”(Solipsism)如影随形。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如果想要摆脱唯我论的幽灵的纠缠,就必须对“他我”是如何从自我中产生的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胡塞尔的“第五个沉思”无异于一场“刀尖上的舞蹈”——一方面,胡塞尔必须在对他者的产生过程的说明中贯彻先验还原的基本原则,坚持把“自我”作为立足点;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说明自我所体验到的他者是真正的原始意义上的他者,而不仅仅是自我的“复本”。简而言之,胡塞尔必须说明那个既离不开自我又完全不同于自我的他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三、“第二种还原”与自我的肉身性的确立
胡塞尔所面临的也就是“他者在‘自我的本己领域’中的产生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的问题。所谓“自我的本己领域”(die Eingenheitssphäre),即排除了对他者的任何预先设定的自我所拥有的一切体验。⑩
自我的本己领域是“纯粹的”,因为它排除了一切直接或间接与他者的存在有关的体验。例如,像“客观性”这样的概念或体验,因为它隐含着他者的存在,因此便被排除或悬置起来了。这样一种排除或悬置是在已有的对“自然态度”的悬置,即所谓的“先验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它是一种新的悬置或还原,不妨称之为“第二种悬置”或“第二种还原”。
就自我的本己领域排除了对他者的任何预先设定而言,它是纯粹的、抽象的,然而它却并不空洞,反而是一个“具体的统一”。原因在于,“即使在消除一切外在于我的东西的设定之后,某种类型的世界仍然被保留下来,自然被还原为‘为我之物’——而‘我’则是心理-生理学意义上的、既有身体又有灵魂的自我,自我凭借他的身体而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说,即使在排除了对他者的设定之后,我仍然拥有我的身体,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我的身体与别的物体的不同,我借助我的身体仍然能获得对“自然”的各种感知和体验,我甚至还能拥有对我自身的身体的体验。简而言之,在肯定的意义上,第二种还原与第一种还原(即先验还原)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将“自我”拥有身体这样一个以前曾被忽略但却确定无疑的事实凸现出来,而这个事实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它的前反思性质——它是“我在”而非“我思”——却使它得以成为胡塞尔解决他者问题、摆脱唯我论困境的突破口和立足点。
作为对“关于他者的预先设定”的消除,第二种还原是一种“抽象”,是减法;但就这种还原第一次将自我理解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非与身体无关的、幽灵般的精神实体而言,它又是一种“充实”,是加法。在实施第二种还原之前,胡塞尔已经对康德“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我思”意义上的“自我”概念(第一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了两次扩展:(1)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第32节,胡塞尔将作为活生生的体验之流的空洞统一体的自我扩展成为具有一定的养成、信念、价值取向和欲望的自我(第二种意义上的自我);(2)在接下来的第33节,胡塞尔将上述第二种意义上的自我进一步扩展成为将由其意向对象构成的世界包括在内的自我(第三种意义上的自我),并将这种意义上的自我称为“单子”。单子之为单子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它是不占有空间的精神实体。然而,第二种还原却第一次使身体作为自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凸显出来。自我第一次成为总是寓居于某个身体之中有血有肉的“自我”,这可以看作是对“自我”概念的第三次扩展,而这次扩展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出前两次之上。
第二种还原或自我概念的第三次扩展的直接意义在于:自然不再仅仅是直观的对象,而成为我的肉身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自我入乎自然之中又出乎自然之外,自然入乎自我之中又出乎自我之外,正是这种以身体为基础的内与外的辩证法使既入乎自我之中又出乎自我之外的他者的建构成为可能。
四、他者的建构之一:意识的肉身性与“结对”的可能性
我对他者的体验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他者往往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面前;另一方面,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直接拥有他者的内心体验。他者的内心生活对我来说是“不可见的”,否则的话,“他”就将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与“他”就将合二为一了。
在我无法直接拥有他者的内心体验的情况下,我是如何得知他者的存在的呢?现在假设某个他者突然闯入我的视野中,这时,我做出“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他者”的断定的直接原因是,我看见了他的身体。那么,我通过他可见的身体断定他不可见的内心生活的存在的根据何在呢?
当我看见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时,我不会认为在它们那里存在着“他者”;当我看见一匹马或一个人时,我却不由自主地认为在我面前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他者,原因在于,人或其他有意识动物的身体在我看来具有不同于无机物或无意识的低级生物的特点,这个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它们直接受到某个意识的支配。”
然而,实际上,我并没有“看见”他者的意识对他的身体进行支配的过程;我能够直接体验的,是我的意识对我的身体的支配。在我看来,我的身体不同于任何别的物体的特点恰恰在于,它直接受我的意识的支配。我不凭借任何别的物体就能移动我的身体或其中的一部分,例如抬起我的手臂,我的意识本身就构成我的身体运动的原因;与此不同的是,只有以我的身体为中介,我才能移动别的物体。也就是说,我的身体总是踩着我的意识活动的“节拍”起舞,它随着我的意识活动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它与我的意识活动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它可以说是我的意识活动最主要的“外在表现”,它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意识活动的存在方式。简而言之,它是我的意识的“肉身化”或我的“肉身化意识”。正是通过我的身体,我的意识才得以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才得以成为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幽灵”。
一方面,自我之为自我,在于我是我的身体的主宰者;另一方面,我的身体因直接受我的意识的支配而呈现出与无机物或植物及其他无意识的低等生物不同的特性。如果他者的身体也呈现出与我的身体相同的特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同样受到某个与我的意识类似的意识的支配,那个意识就是“他我”或“他者”。他者之为他者,在于他是他的可见的身体的不可见的主宰者,正像自我之为自我,在于我是我的身体的主宰者一样。可见,他者身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性,是我断定他者存在的最终根据。这也正是胡塞尔下述这段话所试图加以阐明的核心观点之所在:“让我们假设另外一个人进入我的感知领域中。在实行了向本己领域还原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在由我的源始自然构成的感知领域中,出现了一个物体;就其属于我的本己领域而言,它只能作为我自身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一个内在的超越性)来看待。由于在这个自然或世界中,我自己的身体是唯一能够作为有机体(起作用的生命)以源始的方式被构建起来的物体,因此,尽管在那儿存在着的另外一个物体也被看作是有机体,然而,它作为有机体的特性并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被我亲身感受到,因此是派生的。基于此,显而易见的是,仅仅是基于存在于我的本己领域中的他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性,他者的身体才具备了以类比的方式作为另外一个有机体来看待的动机和基础。”胡塞尔这里所说的“有机体”或“生命体”(Leiblichkeit)与生物学上所说的有机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包括植物以及一切尚不具备意识的低等生物。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对于胡塞尔来说,有机体的特点在于它受到某个意识的直接支配,尽管这种支配也有可能是以不自觉、“下意识”的方式进行的。保罗·利科认为,胡塞尔的这段话是在整个“第五个沉思”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因为它对“我如何得知他者的存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从以上所述中不难看出,对“我对他者的体验”起关键作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我的身体与我的意识的内在统一性——如前所述,我的身体不同于任何别的物体,它因直接受我的意识的支配而成为其外在表现和存在方式,这样看来,在我的意识与我的身体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笛卡尔式的“心身平行论”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克服;第二,他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性。具体来说,我体验他者的存在过程,就是下列这样一个过程:基于他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性,我将我的身体所具有的“意识性”,以“类比”的方式转移到他者的身体中,从而把他者的身体看成他的意识的外化——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把他者的意识与我的意识一样都看成肉身化意识。这个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把他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看成两个具有同等意义的物体,从而使它们两个成为“一对”,这也正是胡塞尔把这个过程称为“结对”(Paarung)的原因。在下面这段话中,胡塞尔对此作了集中的阐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的身体一直在那儿存在着,并且从感觉上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除此之外,同样能被我以源始的方式亲身感受到的是,我的身体还拥有‘有机体’这样一种特别的意义。现在,如果在由我的源始体验构成的领域中,出现了一个与我的身体类似的物体——这个物体因其所拥有的各种规定性而从现象上与我的身体结为一对,那么,看来不言而喻的是,那个物体将通过‘意义推移’(Sinnesüberschiebung)而同样获得‘有机体’这样一种意义。”这就是说,尽管我只能以源始的方式拥有我自身的体验,但我将把他者的身体作为我的肉身化意识的相似物,并且把它看成另一个“自我”的表现。这个把我的身体作为肉身化意识所具有的特性“转移”或“投射”到他者的身体之上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结对”。
结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结对,我并没有以源始的方式拥有他者的活生生的内心体验。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结对的意义,因为正是通过他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的结对,才使得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他者的身体呈现为他者的内心体验的“标志”,从而才使得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结对”——他者可见的身体与他不可见的内心体验的结对——成为可能。
五、他者的建构之二:作为被动综合的“统觉”或“共现”
最后提到的这种意义上的结对实际上不过是“能指”与“所指”这种更为普遍意义上的结对的一种特殊形式,胡塞尔本人不称之为“结对”,而称之为“共现”(Appräsentation)或“统觉”(Apperzeption)——虽然拥有一定的内心体验的他者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见的,但我可以基于他可见的、向我直接呈现的身体间接“把握”到他的存在,这样一种基于直接呈现的间接把握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统觉”或“共现”。这两个术语的主要作用在于将通过“感性直观”(即Perzeption或Präsentation)向我们直接呈现出来的东西与建立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共现”或“统觉”间接把握到的东西区别开来。胡塞尔强调的是,只有通过共现或统觉,我才能超越我的直接的本己领域,“设定”或“断定”他者与我同在。
就对他者的存在的设定或体验而言,统觉或共现是必不可少的,但后者并非是对他者的体验所特有的,因为在我对外界物体的感知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就已经包含统觉或共现。正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六项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在外感知中,对象也并没有“完全地”作为其实际之所是呈现出来,它仅仅从正面或从某个视角以省略或“部分显现部分遮蔽”的方式被给予。因此,每一个感知都是“直接呈现”与“非直接呈现”(即共现)的混合,“与前者相对应的是对象在这个感知中作为完全程度不等的投影被给予的部分,与后者相对应的是对象未被给予的部分”。对于一座房屋,我能直接看到的,只是它处在前面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以看作那座房屋本身的投影),但通过这些部分,那些我不能直接看到的背面也被我设定为与直接向我呈现出来的前面“同在”。如果我站在不同的角度观看那座房屋,那我将得到各不相同的感知体验,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看到的是同一座房屋,即把我从不同角度得到的各不相同的感知体验都“理解”为对同一座房屋的感知。这样一种“认为”或“理解”也就是所谓的“统觉”或“共现”。
作为一条认识途径,统觉或共现的特性在于它既非直接的感性直观,亦非逻辑推论。它是一种联结、综合或统一,但这种联结不是康德所说的知性通过范畴进行的主动的联结,而是感性的、被动的、不自觉或下意识的联结。一个小孩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终于知道了剃须刀的用途,但他并不是通过自觉的比较和推理得知这一点的。一般来说,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第一次遇见的事物,我们都是根据它们所属的类型来认识的,尽管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个(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见过的事物,但我毕竟见过类似的事物,因此,几乎一切日常经验都包含着某种“类比推移”——即将我们对某类事物原来就已经获得的认识转移到新的对象上,并对这个对象的性质和意义获得预知性的把握。所有这一切都在没有自我的自觉参与的情况下以下意识的方式发生在被动性领域中。虽然这种“被动综合”似乎处于较低的层次,但对胡塞尔来说,这不应成为怀疑其可靠性的理由,因为它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是一切更高层次的综合统一的前提和基础。
但问题在于,与一般意义上的特别是在外感知中发生的统觉或共现相比,对他者的共现或统觉似乎存在下列这样一个明显的缺陷——它无法像我们对房屋的背面的统觉或共现那样通过视角的转移得到证实。正如胡塞尔本人所指出的:“共现总是包含着通过相应的起充实作用的呈现(例如当物体的背面变成前面时)加以证实的可能性;然而,在对他者的共现中,对他者的源始体验的类似证实却从先天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
但在胡塞尔看来,如果仅仅基于这一点就怀疑对他者的统觉或共现的可靠性,那未免过于草率了。实际上,“我对他者的共现或统觉”有其不同于外感知中的统觉或共现的证实方式——它是通过他者不断变动着的行为的“和谐一致”得到证实的。
根据胡塞尔的看法,就“我通过统觉或共现所把握到的他者”是“我的源始的本己领域”的意向相关物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与之相似的是,我当下通过回忆所把握到的“过去”也是对我的当下即时体验的超越。换言之,“过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当下体验的“他者”,而回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统觉或共现,即将已经过去的事情“当下化”。
那么,我如何才能使这种“当下化”得到证实呢?显然,在我无法将我的现时体验(即我现在对过去某件事情的回忆)与已经消逝的过时体验(即过去某个时候对那件事情的“即时体验”)进行对比的情况下,我只有求助于我对那件事情的各个彼此有别的回忆之间的“和谐一致”。与这种情况相似的是,我对他者的体验的证实正是通过我所观察到的他者的身体运动的“和谐一致”实现的。胡塞尔把“我对他者的体验”与“我对过去的回忆”进行对比,指出它们二者实际上具有类似的证实方式,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消除我对他者的体验的“玄想性”。如果我们并不怀疑对过去的回忆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怀疑对他者的体验的可能性?它们二者都无法在我们的源始的本己体验中得到证实,而只有通过我们的各个即时体验之间的“和谐一致”得到证实。既然如此,它们二者或者同样不靠谱,或者同样靠谱。
六、他者的建构之三:“我在这里,他在那里”——对他者的超越性的进一步论证
他者与自我的不同首先在于我的身体是以“在这里”的方式被给予的,他者的身体则是以“在那里”的方式被给予的。其次,他者之为他者,在于他并不是“自我的复本”,在于他具有与我不同的体验,原因在于他的身体与我的身体处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上,因而二者具有不同的空间视角;尽管二者可以通过身体的移动相互交换其位置,但严格来说,二者不可能同时具有相同的视角。再者,作为另一个自我,他者或他我是同样拥有其本己领域的“单子”,在这个单子中,对我来说“在那里”存在着的他者的身体以源始的方式作为“绝对的这里”,即他的一切意向作用的核心被体验。
然而,问题在于,即使通过结对、统觉或共现将他者建立起来之后,他者的身体也仍然与我自己的身体一样被体验为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物体,换言之,就我是一个单子而言,我的源始的本己领域中的一切都以“在这里”的方式存在着,而不具有任何“在那里”的异己成分。本己与异己不可能同时存在于我的本己领域中。既然如此,我基于我的本己领域通过结对、共现或统觉建构起来的他者何以见得是真正的“异己”意义上的而不只是“自我的复本”意义上的他者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基于我的本己领域中的某个物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性“设定”另一个超越于我的本己领域之外的另一个“自我”(即他者)的存在?在下面这段话中,胡塞尔试图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作出使人信服的回答:“既然‘在那里’存在着的他者的身体与‘在这里’存在着的身体进入了结对联系之中,并且作为通过感知被给予的东西成为共现即我对与我同在的‘另一个自我’的体验的核心,那么,根据‘结对联结’应有的全部意义,‘另一个自我’必须被共现为一个现在以‘在那里’的方式存在着的‘自我’,即它以‘当我处在那里的时候……’的方式存在着,而我自身的自我,以连续不断的自我感知的方式存在着的自我,则是一个以‘在这里’的方式存在着的自我,因此,另一个不同于自我的‘自我’就被共现了,那原本不相容、无法同时共存的两个自我就变成可以共存了:原因在于我的源始自我通过起共现作用的统觉将一个不同于他自身的‘自我’建构起来了。这个被建构的‘自我’从其本性上来说就不要求也永远不可能通过‘直观的呈现’得到充实。”结合胡塞尔在别处所做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上述这段话还包含下列意思:在我的本己领域中,某个“在那里”存在着的物体(即随后被看做他者的身体的那个物体)是与“在这里”存在着的我的身体类似的物体。既然以“在这里”的方式被给予的我的身体受我的意识的支配,那么,顺理成章的是,那个类似的物体也受某个意识的支配,即那个物体是某个他我的身体;并且对我而言“在那里”存在着的物体,对他而言却是以“在这里”的方式被给予的,即他我与自我一样都是拥有其本己领域的“单子”,而他的身体则是处在他的本己领域中以源始的方式被体验为“在这里”存在着的物体,就像我的身体以“在这里”的方式被给予。总之,他者虽然是基于我的本己领域通过结对或共现建构起来的,但作为我的本己领域的意向相关物,他者同时又超越于我的本己领域之外。因此,正如胡塞尔反复强调的,由“我”建构起来的他者并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象征或摹本,相反,它就是他者本身,而我所实际观看到的,也正是他者的身体本身,只不过这种观看是基于我的视角进行的。
在笔者看来,胡塞尔关于“他者的建构”的结对理论的问题不在于那样的他者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而在于:他者是否真的像胡塞尔所倾向于认为的那样通过结对才第一次出现,还是结对本身就已经预设了他者的存在?实际上,结对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是能把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某个物体与其他物体区别开来并把它看成是他者的身体。但“把某个物体看成他者的身体”这件事本身不就已经预设了他者的存在吗?通过已经预设了他者的存在的事实来证明他者的存在,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可见,在他者的建构的问题上,胡塞尔需要加以进一步澄清的毋宁说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结对使他者的建构成为可能,还是结对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他者的存在的预设?
七、他者的建构之四:“认同性综合”——唯我论的摆脱与客观性的建立
但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作者来说,他者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问题或许远不如下列这个问题重要:“他者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我对他者的体验”)如何使我得以超出我的本己领域之外,或把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对象看成同时也被他者所体验的客观对象?对胡塞尔来说,只有在最后提到的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之后,以笛卡尔式的“我思”或“先验自我”为立足点的先验现象学才有望彻底摆脱“唯我论”幽灵的纠缠,而这也正是他的《笛卡尔式的沉思》特别是其中“第五个沉思”的初衷和目的之所在。
根据胡塞尔的看法,在排除了对他者的设定的情况下,我对包括他者的身体在内的一切对象,都只拥有最低层次的体验。而通过结对或共现所实现的他者的建构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使我能够把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对象同时也看成是为他者的内心生活所体验的对象。就拿“他者的身体”这个对象来说,作为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物体,它以“在那里”的方式被给予(我);然而,在将他者建构起来之后,他者的身体就成为超出我的本己领域之外,以“在这里”的方式被给予(他者)的物体。这就是说,由于对他者的设定,对于同一个对象,我会先后获得两种不同层次的体验,即:首先把它作为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对象来体验,然后再把它作为超出我的本己领域之外同时被某个或多个他者所体验的对象来体验。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认同性综合”(die identifizierende Synthesis)的作用,我会进一步获得这前后两种体验的对象是同一个对象的“体验”或认识。这样一来,原来仅仅处在我的本己领域中的对象,无论是他者的身体也好,还是任何别的物体也罢,就成为同时也(能够)被某个或多个他者所体验的对象。这也正是以“我思”或“自我”为立足点的先验现象学摆脱唯我论困境的出路之所在。
不难看出,在上述过程中,所谓的“认同性综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来说,尽管前后发生的两种体验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并且从时间进程上来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意向对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获得“它们是同一个对象的体验”的体验——进一步来说,当新的体验产生时,我仍然保留了对此前发生的体验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被动地”、不自觉地“觉察”到前后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即“觉察”到它们二者具有相同的意向对象。
在胡塞尔看来,作为“认同性综合”的结果,通过他者的建构所实现的“世界的客观化”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因为前者是我们的意识生活的基本环节之一。我能够对某件已经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即把我通过回忆再现出来的某件事与过去发生的某件事看做同一件事),能够把不同时间进行的证明看成是对同一个定理或公式的证明,也正是由于“认同性综合”的作用。因此不难理解,所谓观念对象的永恒性或“超时间性”,实质上是它们的“无时不在性”。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永恒性就是指我们能以某种方式意识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对这个定理的证明或运用是对同一个定理的证明或运用。
上述这样一种交互主体性理论是否无懈可击?它是否真的能够达到使先验现象学摆脱唯我论的目的?恐怕胡塞尔本人对此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尽管如此,后人对这个理论仍然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意识的本质与心身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突破。
注:
①Edmund Husserl.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The Hague,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1973.
②Edmund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The Hague,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1950.
③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4页。
④Edmund Husserl.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Halle:Max Niemeyer,1929, S.215.
⑥Edmund 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1-3.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3.
〔责任编辑:金宁〕
Ego,BodyandtheOther:Husserl’sTheoryofIntersubjectivityin“theFifthMeditation”
ZhuYaoping
The basic motive of Husserl’s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 which he put forward in his Cartisian Meditations, is to eliminate the suspection to the trend of Solipsism in the transcendental reduction. According to Husserl, only a resemblance connecting the other body with my body within my primordial sphere can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conceiving “by analogy” that body as another organism. Thanks to such a kind of conceiving by analogy, which Husserl also called as Pairing, Apperception or Appresentation, the sense of “ego” is transfered from my body to the body perceived over there, and the Other is established,through which the objective belonged to my sphere of ownness becomes the same objective experienced by the Other. For Husserl, the plight of Solipsism faced with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is thus overcomed ,at least to some degree.
Husserl; transcendental redution; solipsism; ego; body; the other; intersubjectivity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胡塞尔遗稿中的心灵哲学”(13YJA720029)的阶段性成果。
朱耀平,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江苏苏州 215123
B811
A
1001-8263(2014)08-0060-07
——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时间观的继承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