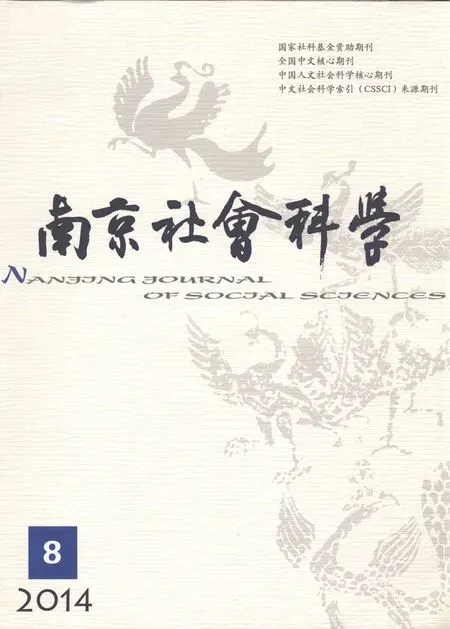合作性治理语境中的政府能力厘定及其提升路径*
张 宇
合作性治理语境中的政府能力厘定及其提升路径*
张 宇
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减弱或治理行为的弱化。在合作性治理语境中,政府能力的适用领域应当具有明确的边界限制、政府能力的发挥应当基于有限制的权力行使、政府能力的外显应当是有效能的元治理公共角色。政府要在合作性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必须进行政策创新,打破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营造合作型治理环境,弥补急剧转型的社会断层;推动公共信息透明共享,减少合作共治的阻滞;构筑社会财富共享机制,谋求弱势群体的公平待遇等。
合作性治理;政府能力;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是我国社会合作性治理基本框架的经典描述。对处于转型和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一创新性治理模式很难直接用“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或“强”、“弱”政府管理理论来解释。究其因由,主要在于西方新型公共管理模式以提高政府效率为初衷,并力图回应公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质疑而逐渐成熟的理论体系;而当今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却是以实现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终极目标。不同的目标归属决定了我国社会合作性治理的模式应有其适合中国语境的独特性。为了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社区与居民都需要提升自身的能力,“政府统管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或应该由政府承担却又不管,均为不当。”①事实上,依据从政府主导向社会、社区层面参与的演进逻辑,政府能力不仅是社会合作性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决定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决策、方式与程度;也是政府权力清单的厘定以及向其他多元主体分权的依据。因此,在新的社会治理框架中对政府能力进行新的更具契合性的界定,有其重要的现实意蕴:政府的规模可以变小,但力量却绝不能减弱。同时,依此找出针对性的政府能力提升路径:对于那些只有政府能够完成的职责,政府不能轻易授权;对于那些能够与社会合作治理的事务,政府则需坚守其元治理之职;对于那些家庭和社区层面可以自为和自理的事务,政府则应充分授权。质言之,未来的公共事务治理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均衡能力基础上的“强政府—强社会—强公民”的合作治理图景。
一、政府能力的强弱之辩
政府能力强弱一直都是学界争论的重点,其焦点主要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有限、政府的权力应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政府是否应该全能等问题,虽历经几个世纪却未能达成共识,论辩最后聚焦于强政府论和弱政府论之争。
从早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李斯特到凯恩斯直至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菲利普斯等都是强政府论的支持者,赞成政府强力的干预和顶层制度设计对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阿瑟·刘易斯认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其境内的政治秩序。②亨廷顿也提出了“强大政府论”,他认为,“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③。托马斯·格林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替代自由放任式的自由,认为政府(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耗,政府(国家)行使更多更大的权力,为全体成员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促进全体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能力和力量的发挥,社会中存在的自由才能够大增长,每个成员才会越来越自由。唯此,政府(国家)不仅要干预经济生活,而且要干预社会生活,包括干预土地买卖、强迫实行教育、保护工人福利健康等。④凯恩斯在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下更是提出:“政府(国家)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全社会的利益……政府行为的目标是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⑤而到了70、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是必须的,合作行为比个人主义最优行为所选择的结果更好,而政府是推动和促进合作的重要力量。他们相信政府可以而且应该为稳定经济而设计政策⑥,政府干预可以加速市场力量对经济的复苏、保持经济稳定、恢复经济主体的投资信心和影响公众预期等。但他们主张的政府干预是适度、温和的干预。
弱政府论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主张在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应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市场机制的运作在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造成了令人惊奇的统一。“……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⑦,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作为“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应该采取放任的自由政策,而不能介入经济活动与个人事务。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渐露困窘,政府干预对于危机也无能为力,因此,弱政府的思潮日盛。弗里德曼肯定了福利国家的初衷,但对其执行结果感到失望。在他看来,越来越强大的福利国家摧毁了自由市场给人们带来的繁荣。如果市场是自发和自足的,政府干预就显得毫无必要。“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性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⑧哈耶克认为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整体设计和建构的做法只能是一种理性的“致命的自负”⑨,将会“通往奴役之路”;政府只能在那些私域可能受到侵犯的地方发挥作用,否则政府统治经济将会不可避免得导致极权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同样存在隐患,政府可能存在自己的利益追求或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恰是出自政治制度”⑩。诺思提出了“政府悖论”,即“政府(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后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因此,减少政府干预和建立有效产权制度是消解政府悖论的关键。诺齐克强调自由的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主张建立一个最弱意义的政府。而萨托利则认为政府即便干预,其结果也很有限。当然,他们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只是强调政府只从事那些有正当理由应当从事的活动。
强政府论和弱政府论各有其强力的理据且对政治实践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在中国,“精简政府”和“小政府”的设想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推广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但又难以通过具体的设计来实现,政府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政府希望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寻求治理方式的突破,回应民主化的诉求,向社会充分授权,从而提升其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社会的不甚成熟,公民参与过程中非理性与无序状态的出现,使政府不得不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也对政府能力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社会既有理论的要求,这也是十八大报告中“政府主导”之论述的主要缘由。事实上,为了推动不同的权力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过程,政府的作用是绝不能小觑的,要使政府与社会能够真正地进行合作性社会治理,用一般性的“强”、“弱”难以清晰界定新型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应然能力和功能,需要保留强弱政府理论各自的合理内涵,对政府治理能力进行重新的阐释,进而为未来的社会合作性治理奠定政府层面的能力基础。
二、社会合作性治理过程中的政府能力厘定
社会治理过程为政府能力的重新界定提供了一种变革现实的框架,是一种积极的建构以及对传统的唯一主体角色和地位的一种反思,它试图突破原有的话语场域,重新寻找政府行为的基点和评判标准。从地位上来讲,政府不再居于中心地位,而是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较为平等的存在;从管理范围上来讲,政府不再延伸至公民生活的每个角落,而是从那些社会能够自我治理或合作治理的事务中抽身而出;从管理的手段上来讲,政府不再只是控制和支配,而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合作行为的推动者和激励者;从管理的强度上来讲,政府不再力求大而全,而是力求所管理之事务在结果上的有效性。政府的能力由此有了新的内涵阐释,即一种有边界、有限制、有效能的元治理的能力。
首先,政府治理能力的适用领域应当具有明确的边界限制。“就其作为秩序化统治的一种条件而言,政府是国家的权威性表现形式。其正式功能包括制定法律、执行和贯彻法律,以及解释和应用法律。”但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变迁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程度提升,政府的活动范围有了巨大的拓展,政府的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构建公共福利体系以及制定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是因社会公众的需求而产生的,政府从存在的那一天起所管理的对象就是那些社会机体无法完成的公共事务。从政府存在的理由进行政府管理领域的划界可见,政府无需也不应介入所有公共事务,而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存和自由而存在并运行。回到政府合法性之根本以及政府的起源,基于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个体的同意组成的共同体在采取任何公共行动之前都要获得个体的同意,因此,政府总是受到约束的,政府的职能应该有明确而适当的边界:政府无法、无需也不可能全面干预社会公众的生活;但对于那些社会层面无法自行有效解决的问题则必须有所作为,如公共危机事件的出现或国防外交政策的制定等。强化并提升政府能力首先需要政府回归到那些本来就应该由政府作为而却因政府事务过于繁杂被忽略的职能之中,同时从那些社会公众可以自主治理的事务中抽身,转而成为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者。
其次,政府能力的发挥应当基于有限制的权力行使。由于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个人自然权利的让渡,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以不侵犯任何个体为前提保证共同体中个人权利的实现。因此,政府权力总是受到个人自然权利的限制,并尽全力保护个人权利,在此过程中生成的权力延伸需要得到社会成员的同意与进一步授权。如果出现没有合法性依据的机构膨胀和效率低下的情况,则会直接影响政府主导地位的合法性。《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行是我国限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尝试,从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规范性地制约了政府的扩张,有利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也适应了社会治理创新对管理主体多元化的需求。但是,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并不对立,政府需要使自己在有限的边界内最大限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以“有限政府”提供“无限服务”,即使用有效的公共资源,在法律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冲突,使社会公众在自由的公共空间里幸福生活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有效运行政府的有限权力形成了一种强政府治理能力。
再次,政府能力的外显应当是有效能的元治理公共角色。政府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并不是无限的,需要坚守制度设计的元治理角色。元治理指的是作为“治理的治理”,旨在对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重新组合治理机制。杰索普指出,“虽然治理机制可能获得了特定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职能,但政府还是要保留自己对治理机制开启、关闭、调整和另行建制的权力。”政府需要通过程序设计确立哪些人、通过哪些方式、使用何种治理工具将公共资源分配给谁,进而保证结果的正义。无论如何,政府至少要在政治上设计民意表达的多元途径,提供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主体表达异质性需求的可能并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让关于政策问题的论争得以进行;在社会生活上完成外交、国防等纯公共物品供给,并制定元政策使其他种类的公共物品得到恰当和充足的供给;在经济上为培育市场竞争与发展制定规则,消除垄断,强化监管;在行政管理上保证对权力的全方位监控,确保信息公开并促使人力资源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际间合作上培育区域性和国际间联合、寻求全球性目标。这些领域政府不仅需要保留自己的权力,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从而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三、社会合作性治理过程中政府能力的提升路径
在社会合作性治理的语境中,对政府能力的重新界定意味着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使自己扮演好有边界、有限制、有效能的元治理角色,在那些社会组织、市场、社区、公民等其他治理主体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显现出自己的有效性,进而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契约失灵、社会失灵以及志愿失灵等其他主体的种种内生性的缺陷。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才能够真诚地与其他主体平等对话合作,建构起社会合作性治理的框架。基于此,政府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地采取行动,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治理主体。
第一,进行政策创新,打破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一项技术或制度系统的演变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过程,即一项技术或一种制度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而被选定,其自我强化机制就会使其沿着既定的路径或轨道演化下去,即使面临更优的替代技术或制度选择,既定的路径也难以发生改变。”这种路径依赖,无论良性与否,均为社会、政治、经济长期演化的结果,其形成的惯性不通过强力的阻止而不能中断,由此,政府必须要承担起打破传统制度路径依赖的主责,这也是衡量政府能力有效与否的主要标准之一。因为其他的合作主体,如社会、居民、社区、企业都无法对传统制度的运行自发地采取无争端和无利益冲突的集体行动。如果听任旧的社会管理模式中某些制度的非良性路径之惯性一直延续并发生作用,势必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产生冲突,也会造成社会公众对政府能力的质疑,甚至会影响公众对新的制度的信任,从而影响新的治理范式下的合作。就政府而言,需要采取的行动则是结合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公民为中心制定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从而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中断原有政策平衡的作用。比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关于“公共利益”争议的司法仲裁和允许农地入市以及宅基地流转的创新型政策都是政府基于服务的理念对现行土地制度的突破与创新,打破了原有土地制度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上的局囿;允许外来人口的子女就近入学和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部分消减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公民教育权上的持续性差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政策设计有效地分流了星级公办医院的就医压力,平价药物的供给和贴心就近的服务改变人们的就医行为选择。
第二,营造合作型治理环境,弥补急剧转型的社会断层。可以预见的是,社会合作性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行动,其实施依靠的是“……一种‘三位一体’——调节机构、契约政策、公共讨论论坛,即一种关于标准、项目合作伙伴和发达的商洽模式的明确谈判,也就是对协调、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褒扬以及促进程序和所提供服务的差异化。”也就是说,社会合作性治理是充分考虑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别化利益诉求的。如果期望政府不再高高在上,而成为亲民的有真诚合作姿态的治理主体之一,就需要引领社会共同营造一种合作性治理的环境,即民主参与和协商对话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灵活应变折中型的政策设计,以及有利他取向的积极投入政治生活和社区事务的居民,彼此围绕政策议题形成互动;有共同谋求公共利益的动机、愿意在个人利益上退让;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连接分散的原子化个体进入公共话语场域。当社会急剧转型,社会分层不断明显,阶层间流动因制度设计、不同阶层所占据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非流动性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固化,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断层现象的出现,部分社会个体没有进入上一社会阶层的途径,又缺少原有阶层的特质,他们成为了边缘群体,游走在城乡之间、大小城市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由于没有附着在某一社会阶层的能力或意愿,他们的利益诉求被感知的程度很弱,对于合作性治理环境的形成是一种反作用力。其中一种不可忽略的社会断层表象出现在网络世界,部分网民不愿融入现实世界,过分依赖虚拟社区而生存,因而无法融入合作性治理之中,即使在虚拟世界中他们也常常欠缺理性和有序,从网络论坛中对公共观点非此即彼的判断与辩论可见一斑。这种反作用力的消解绝非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能够承担的,因为政府是元政策的制定者,负责制定集体行动的规则和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其元治理角色不可替代。如果要想弥补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断层,将原子化的个体都聚集在公共场域之中,不因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任何少数群体的诉求,只有由政府从元政策的层面来预设每个人的在场和每个人的表达可能,将游离于外的不遵从及反对转化为参与的程序、规则、行动及意愿。
第三,推动公共信息透明共享,减少合作共治的阻滞。信息是一种权力。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建构和公共权力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分享的前提,信息持有状态的改变势必带来权威和权力状态的变迁,只有获取了公共信息,才能谈得上民主和公民参与,才有多元主体的合作。在社会合作性治理的语境中,要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就要打破原有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形成公共信息共享机制,从而使不同的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时能够充分实现其知情权。信息对于政府的结构和能力而言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含义,在政府作为唯一管理主体的时代,集权式的管理模式本身与信息的封闭及垄断相契合,官僚制作为常用的组织形态往往会形成对信息交流的扭曲,每一层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有存在过滤或改变原有信息的可能,精英式的决策模式使政府没有寻求完全信息和与利益相关者分享信息的动力,因此民主和合作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当网络技术发展以及合作时代到来,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有着了解信息的动机且能够零成本或低成本获取某些信息,进而拥有公共权力,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正是顺应了这种信息状态的改变。但是,公共信息并不会就此自动地流动起来,相反会遭到来自政府或原有信息垄断者的阻挡,如政府在原有的管理体系中完全可以设置网关和网管来持续信息的垄断。那种以为网络和信息社会必然带来权力分享的观点多少带有“科技管理主义”的色彩,政府通过信息垄断获取的权力和权威仍需要政府自身来打破。事实上,只有政府主导政治系统的开放才能打破信息原有的疆界,消除信息垄断造成的权力分享障碍,使信息呈现透明与流动的质态,为合作共治提供条件。政府应负起推动公共信息流动、透明、开放、共享的主责,政府从集权走向民主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信息垄断的改变,尤其是与公民分享那些民生性政策议题改变了政策议题从中心—边缘的信息传播转为无中心的信息全方位流动,是来自顶层设计对公民参与和公共协商的一种回应,政府的这种行动对于其他主体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其他治理主体也会理解公共信息的本质,从而不试图垄断信息资源,才能建构起与他者真诚、平等相处以及合作的治理图景。
第四,构筑社会财富共享机制,谋求弱势群体的公平待遇。多元主体合作进行社会治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众的基本权利,改善民生性服务的供给模式与效果。公共行动者在合作过程中需要一个互惠和公平的价值指南,即人人共享、普遍受益、个个有尊严,其内隐的逻辑就是中国梦所包含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政府应当通过顶层设计构筑社会财富共享机制,引导和实现这些理念。实际上,只有建立了社会财富共享机制,才能提升社会的合作程度,提高社会粘性。“正是通过建立在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潜能性基础上的社会联合,每一个人才能分享其他人表现出来的天赋才能的总和。”质言之,“共享”就应当“结束牺牲一切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普惠的核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能力、也有可能的途径获得社会财富的分享;而要想实现个体的尊严,就要消除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不能允许某个群体或个体过于强势而存在垄断或绑架公共政策的可能。目前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实然的差异已然形成,政府可以适当选用强制性政策工具,如管制、公共企业与直接提供等手段,通过政策优惠引导或规范群体间差异的消弭,如通过提高公共企业收益进入社会保障的比重使最大多数人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通过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扩大范围、提升效能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挖掘个体的潜能;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向弱势群体的倾斜、加大各类补贴使受惠者比重最大化。对于持公平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公平的价值观高于对效率的追求。同时,在制定民生性政策时,着重关注那些居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推动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地区间、民族间的均等化,在基本权利和基本生存条件上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保证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各类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成为了一个政府是否有效的衡量标准,政府有责任设置一个底线保护其公民不因金钱、地位、出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被排斥在外。
注:
①【美】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国外政治学》1988年第1期。
②参见【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20、516页。
③【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序第5页。
④何汝壁、伊承哲:《西方政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1页。
⑤麻宝斌:《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⑥【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6页。
⑦【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页。
⑧【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
⑨【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⑩【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吴良健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责任编辑:宁岩〕
OntheClarificationofGovernmentAbilityandItsImprovingPathintheContextofCooperativeGovernance
ZhangYu
The cooperation among multi-social governing subjects does not mean the weakening of government ability or enfeebling of governing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for government ability should have clear boundary limit, the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bility should be based on restricted power enforcement, and the embodiment of government ability should play the public role of meta governing. 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take the lead in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t should make policy innov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path reliance of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create cooperative governing environment to make up the social fault caused by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e transparency and sharing of public information to reduce the retardant against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to construct social wealth sharing mechanism to seek for the equal treatment towards the vulnerable groups.
cooperative governance; government ability; path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提升公民政策参与有序性的路径研究”(14BZZ02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重大民生决策中公民参与的有序性研究——基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角”(13YJA810018)的阶段性成果。
张宇,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江苏扬州 225127
D035
A
1001-8263(2014)08-009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