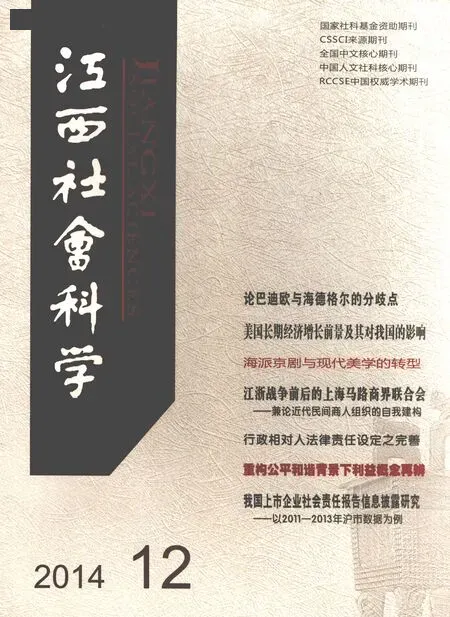明代内官社会交往关系管窥——以内官墓志撰写为视角
■李建武
内官为服侍帝王而产生,其活动范围理应限于宫墙之内,与文武官、士庶百姓本无交往之需。内官仅可供职役洒扫,“夫太监谓之内臣,当居近侍,各边乃是外地,无烦远出”[1](P214)。内官之名与实应当统一,“盖既曰内官,但应处内”[2](P705)。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吸取前代内官干政专权的教训,特别注意内外官勾结的危害,试图将内官活动限定在宫内,职责限定为洒扫等事:“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3](P552)此后明太祖曾多次强调内官只可在内廷洒扫、使令的功能,洪武十年(1377),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3](P1860)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御史缪樗等上疏言八事,其一也谓:“皇明祖训:内官之设,止于供事内府。”[4](P108)诸多限制措施正是对内官角色的规范与控制。在明太祖的严格控制下,内官仅奉命行事,“皆不敢有所干窃”[5](P7765)。内官角色与活动范围基本被限定在内廷。
但此后,明代内官不断突破原有定位,或作为皇帝代表致祭各地宗室丧葬,或被赋予监仓、监工、监军等责任,甚至一度成为镇守内官而固定驻守地方。总之,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极广,触及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此过程中,内官与外官(文官、武官)、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从内官墓志的撰写就可窥一斑,明代内官墓志史料价值极高,一方面其内容全面具体,涉及内官入宫、进学、授官、升迁或贬谪等主要经历,有助于加深对内官本人及其生活状况的了解,并得以补充其他文献对相关史实的缺载。另一方面其记载较为准确,如人名、官职名称、生卒时间等,可与其他文献相互校正。
目前学界已整理出很多内官墓志,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香港学者梁绍杰辑《明代宦官碑传录》(香港大学中文系,1997 年)及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等,为更方便地利用明代内官墓志提供了条件。然而专门对此类墓志进行研究者较为欠缺,此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某些墓志的考释方面①。明代内官群体数量庞大,明宪宗时内官已至数万,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副都御史彭韶言“监局内臣,数以万计”[5](P4856)。明亡国时“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走”。如此众多的内官自然会产生数量可观的墓志,但由于保存等原因,目前可见者较少。本文拟以所收集159 通内官墓志为研究对象,专门对其传主、撰者、辑录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代内官墓志撰写为视角进而探究明代内官的社会关系。
一、墓志传主以上层内官为主
墓主是否请人撰写墓志,属个人行为,并无身份、等级等方面限制。而从目前存世墓志看,虽传主身份无明确限制,但以有品级的上层内官居多,亦发现个别无品级内使的墓志。按供职地点,明代内官可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北京内府任职者。墓志碑刻共128 通,记载传主126 人②,关于其身份统计如表1 所示。由表1 可见,以太监为主的内官上层占墓志传主的绝大多数。无品级之内使仅两位:一位虽无品级但立有大功,该传主为云奇,“洪武间内使守西华门”[6](P414),时丞相胡惟庸谋逆,云奇因阻止明太祖銮舆赴其府第,以不敬被殴死。卒后赠某监左少监,“嘉靖乙酉王公堂守备之明年,偕高公巡视孝陵垣墙,道经公墓,感厥忠义,咨诸同守备秦公文,复请于朝,加今赠致祭”[7](P5147),得以加赠司礼监太监,二公“欲树碑茔域,衷委君而问铭于春”。若非其忠义可劝,后世断不加赠,而墓碑亦无由得作。另一位为交南人谢徕,永乐十六年(1418)被选入内庭,曾掌内官监事,宣德“戊申,改莅承运库。至乙卯,迁兵仗局”[8](P87),正统时又管成造军器等事,自永乐至正统皆曾有差使,按理当有品级,惜志中未载,仅按内使记之。

表1 北京内府任职墓主身份统计
其二,各王府内官。王府内官供职于各王府,绝大多数终老于王府内,然后埋葬于王府所在地;遇到特殊之原因(如嘉靖皇帝以藩王即位),王府内官亦可转为北京内府内官。本次共收集墓志碑刻31 通(不含买地券),所记传主共31 人③,其身份统计如表2。

表2 王府内官墓主身份统计
笔者所见王府内官墓志最早者为卒于宣德八年(1433) 之张镔,最晚者为崇祯十七年(1644) 之牛□,几乎纵贯整个明代。所涉及之王府有:秦府,15 人;蜀府,7人;德府,5 人;周府、汝府、辽府、肃府④,各1 人。其他地区王府内官尚未有墓志见世,如明代宗室在江西者有宁王、淮王、益王等三王,但在今人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所收106 块明代墓志中,竟无一块内官者。
秦府与蜀府人数较多,这与二府内官埋葬地点集中有关。二府内官群葬、聚集而葬现象突出,从弘治年间开始,秦府内官埋葬集中在长安县金光里,据现有墓志记载,起自侯介,其于弘治十四年(1501)二月“葬于长安县金光里之原”[9](P363)。正德六年(1511),典服正李英卒,其义嗣内使鱼跃张腾“奉葬于长安县金光里,敕赐崇仁寺之西”[9](P372)。嘉靖年间埋葬的秦府内官均葬于此,秦府承奉副王泾,嘉靖二十一年(1542)卒,“是年二月廿一日葬公金光里冈,从侯、康二公之地”[9](P383),所言侯、康二公是指前秦府承奉正侯介、康景。之所以葬于一处,是因为王泾是康景之嗣,“康公嗣续者今承奉正凤冈张翁,次即公,次门正白润,中使王鹏”[9](P383)。所言“凤冈张翁”即张沂,继康景之后任秦府承奉正,嘉靖三十二年卒,仅记“葬长安”[9](P394),未见具体地址。张沂之嗣子张学任秦府门官,嘉靖四十三年卒,葬“长安金光里,从恩父承奉正凤冈张翁之兆域”[9](P402),可知张沂亦葬于此。隆庆六年(1572),秦府承奉副杜珝卒,亦葬于“长安金光里新阡,盖公预为之者”[9](P404)。由侯介开始,后有李英、黄润、康景、张德、王泾、崔廷玺、张沂、张学、梁禄、杜珝等10 余人均埋葬于此,俨然成为秦府内官指定埋葬地。究其原因,一则该地与敕赐崇仁寺相邻,寺院附近是内官理想的地点;二则负责办理丧事之内官亦是前任内官之嗣,裙带关系明显,聚集而葬以求心理之安慰。根据出土地点,成都蜀府内官亦存在群葬现象,近年在成都高新区一次性发现6 座内官墓,红牌楼发现9 座内官墓。
综上可知,明代内官墓志以有品级之内官上层为主。一方面这与明代处理宦官丧事的方式有关系,上层内官通常由朝廷命官办理,而底层内臣丧事处理比较草率,“非有名称者例不赐墓”[10](P64)。另一方面与上层内官的身份地位有关,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广阔,结识的文臣雅士自然较多。
除官员品级外,内官个人品质也是墓志得以撰写的一个重要因素。褒扬忠义是此类墓志的主题,他们多作出重大牺牲而得到朝廷的追赠,撰写墓志等活动由朝廷负责。前述云奇即是如此,本无墓志的云奇因后世的加赠致祭而得以留名。墓志传主赠衔尚有一例:御用监左少监阮浪因对景泰帝易立太子之事不满,阴有复立沂王朱见深之谋,被人告发,拷掠至死。英宗复位后,特赠御用监太监,并请大学士李贤作墓表以纪行实,“司设监丞贾公安犹虑公之行实未尽系于世”,属人“为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7](P5149)。
内官倾向于寻求有名望的文官为其作志,并且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部分内官在生前已预作准备,建造寿葬的同时请熟悉的文人预作墓志,以纪生平。
二、墓志撰写者以文官为主
内官卒后,由其义嗣子侄或同事内官持行状请铭于人,而所请之人亦有考虑,或与内官生前共事过,或内官任职地点之名宦,或内官家乡之名宦。墓志撰写者主要有两大类。
(一)在京文官:以翰林院官员或内阁大学士居多
明代内官根据品级之高低在去世后享有不同的待遇,高者如司礼监太监,皇帝会赐钞以助葬,任命品级较高之内官办理丧事;品级低者则丧事之办理规格等方面均不如品级高者。北京内府之内官通常由内官监负责丧仪,而撰文则必属文化水平较高之翰林院,工程营建属之工部,如天顺二年(1458)十二月,尚衣监太监阮某卒,“内官监昭典丧仪,翰林院撰文,□□安厝”[11](P82)。
李贤是所见墓志中首位为内官作墓志的大学士,乃因阮浪于景泰间谋复沂王太子位,天顺复位后,加赠太监而为之作。此后,多有内阁大学士为内官作墓志者,如万安、刘翊、刘健、李东阳、徐溥、张居正等。不过内阁大学士所作之传主一般为司礼监太监或与皇帝关系密切者。其中为内官撰写墓志最多者为杨一清,共有4 篇,分别为《明故御马监太监邵公墓志铭》(邵恩)、《明故司礼监太监张公墓志铭》(张永)、《司礼监太监梅东萧敬墓表》(萧敬)、《明故内官监太监李公墓志铭》(李堂)。
王府内官通常无请翰林院或内阁学士作志者,仅有一通例外。于慎行《穀城山馆文集》卷十八有《汝府承奉春泉李公墓志铭》,传主李鏻乃大兴人,与撰写者于慎行(山东东阿人)既非同乡,又没共事过,乃因李鏻之下属“本绅辈以张文学元吉状请铭,则志其大都而勒之铭”[12](P559)。
(二)内官之同事
内官供职内府,文官供职外廷,本无交集,但明代内官很早即突破内廷范围,出外活动,这样就提供了二者接触的机会。在行事过程中,内官与文官产生了同事关系,最显著者为镇守内官,例如成化五年,太监阎礼卒,虽葬于北京,但去世前乃在镇守四川任上,其墓志由四川按察使郭纪撰文,左布政使马显篆盖,右布政使杨文琳书丹。张邦奇为南京守备太监吕宪所作墓志,乃因吕宪分守湖广行都司时,张以御史提学湖广,“见庙宇黉舎,崇闳坚饬,甲诸郡邑,问之诸生,咸曰太监吕公之成之也”。张邦奇并拜访吕宪,由此相知:“予出访公,则古貌奇格,谦冲而肃乂,燕对移时,不一作世俗语。予叹曰:内贵中固有若人也乎。”[13](P38)内官监李慎,嘉靖十八年卒,张邦奇为其作志,因“正德己卯,予以御史按楚,公时镇守其地。……余方疑公御余乃以余为知己,不亦达哉,铭其可辞”[14](P305)。成化十四年,镇守宣府等处太监弓胜卒于治所,翰林院庶吉士李经撰墓志称:“总戎周公以同事之故,为延吾友门静之、朱用吉经纪其丧。既含敛而殡之,二君以总戎公之意,诒书具事状京师,请铭其墓。公于予有官临宾礼之义,不可辞也,谨按状而书之。”[11](P97)由共事而产生对内官品质之认可,是文官消除顾虑而撰写的前提之一。
相对于北京内府任职内官,各王府内官活动范围更为狭隘,仅局限于王府所在之地。其墓志撰写、书丹、篆额通常均由该王府长史司官员负责,他们同供职于王府,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所记事迹也多为撰者亲见者。弘治十四年,秦府承奉正侯介卒,其墓志铭由秦府右长史强晟撰文,左长史原宗善书丹,致仕左长史吴文篆盖;弘治十七年,康景卒,墓志由秦府左长史强晟撰文,秦府致仕左长史吴文书丹,秦府致仕左长史原宗善篆盖。由王府其他官员撰写者较少,如嘉靖四年,蜀府中贵永忠卒,由蜀府经筵侍讲千户黄嵩撰文,蜀府义庠教读先生罗薪书丹,蜀府冠带总旗李瑶篆额。
除王府官外,王府所在地之名宦亦是王府内官墓志撰写者来源之一。他们多是王府所在地之籍贯而任职于外地,如蜀府门副腾英之墓志铭由“云南曲靖府知府赵永桢撰文,陕西布政司参政郑怀德书丹,四川都司都指挥佥事张龄篆盖”,门正苏荣之墓志铭亦由“云南知曲靖军民府事里人赵永桢撰文,山东布政司左参政成都许淳书丹,福建按察司副使锦官李志刚篆盖”。隆庆六年,秦府承奉副杜珝卒,墓志由“应天府尹长安王鹤撰并书篆”,王鹤籍贯西安,与杜珝任职地相同,而时任应天府尹。万历二年,蜀府门正宁武卒,由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成都刘世魁撰,户部郎中成都周淑书丹,户部员外郎成都何举篆,三人皆成都籍。由王府所在地之名宦撰写墓志,充分体现出王府内官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关系。
除上述两大类外,墓志撰写者还有墓主自己和僧人两种。内官一般出润笔费请他人作墓志,即使生前所作寿藏记或寿藏铭,亦多由他人作。所见墓志仅有一例内官自撰者。御马监太监段聪“先卜宅兆于祖茔之右,兹缘正德改元之春,遂并治归藏之所”[15](P186),署名为“正德改元丙寅岁三月二十八日守愚子自记”。该墓志出土于段聪家乡三河县。之所以选择自撰,一则由于内官对当时墓志撰写的弊病深为不满:“窃见近世人有年至耄耋讳言终事,或身死财散而卒无所归者,又有濒死而嘱其子孙遍求显官名儒,铺张德业以自夸诩于人者,予两病焉。”[15](P186)一则乃因该内官文化水平较高,九岁入内廷,“天顺丁丑遣就翰林院官读书,甲申选司礼监书办”。明代内官接受教育已为世人所知,而选充司礼监书办则可见其文化修养之高,因而对自撰墓志充满自信。
在所见墓志中,有一通内官墓志撰写者为僧人。明代内官多信奉佛教,僧侣成为内官社会交往的重要成员,其中不乏文化高僧为其撰写墓志者。天顺三年二月,司礼监太监兴安卒,由僧人至全撰写墓碑,右春坊右庶子刘珝书丹,监察御史王越篆额。至全之署名为“□□万寿戒坛传戒宗师、兼敕赐寿光禅师、□山第一代住持、奉诏内旌选校□□□□金台至全”,题为《大明故司礼监太监兴公之碑》,在历叙兴安生平后,亦有铭,与墓志铭无异。由僧人作志,盖是由于兴安崇佛、信佛,碑载兴安“晓谙禅学,深悟理性……以所获金帛修营梵宇……每岁饭僧,率以为常”[16](P15)。由关系密切之人撰写墓志应是明代内官墓志之特点。
不过,相对于内官积极寻找撰写者,以文官为主体的撰写者则显得比较被动,他们通常不会采取主动姿态,但当内官本人或其亲属持状以求时,他们也不会推辞,呈现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
三、墓志收录背后的顾虑
除撰写方面的顾虑外,墓志的收录与流传也是文人顾虑之一。文集是文人作品的载体,理应是文官为内官所作墓志的最大来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该159通墓志中,仅有23 通散见于文集中⑤,以罗玘《圭峰集》收录最多,达5 篇之多,记载传主3 人。张邦奇、毛伯温、程敏政及张居正文集中各有2 通。其余数部文集仅收录一通墓志铭。文集收录内官墓志数量较少,不排除底层文官并没有机会给内官撰写墓志的因素,但亦存在文官为内官撰写墓志而文集不收录的情况。虽然有上述文集收录内官墓志,但根据现有墓志看,被收录于文集之中仍属少数。据《李东阳集》(周寅点校,岳麓书社,1985 年版)记载,其共为他人约作有195 篇墓志碑铭,无一篇内官者;但据现有墓志资料看,至少有两篇:《大明故司礼监太监高公墓志铭》(梁绍杰《宦官碑传录》第153 页)、《明故尚膳监太监傅公墓志铭》(《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第155 页)。正直者如刘大夏亦作有《大明故内官监太监杨公墓志铭》(梁绍杰《宦官碑传录》第131 页),但文集中并无收录,类似情况尚多。
为内官撰写墓志曾导致官员仕途受阻。嘉靖年间,大学士杨一清为内官撰写4 通墓志,其文集均无收录,盖因其为内官写墓志而被人攻击,最终被迫削籍归乡。杨一清与内官张永之相知曾一时传为佳话。正德五年四月,宁夏安化王叛乱,二人一同受命平叛。由此二人相知,杨启张以诛瑾之谋,卒获成功。嘉靖七年,张永病逝,杨一清被推为墓志撰写者之不二人选。杨一清为张永所作墓志铭达2800 多字,是发现墓志中字数最多者。《名山藏》卷七十二记载,杨一清嘉靖年间屡次进退,“其明年坐受故安定伯张容金钱,为其兄太监永墓志,削籍家居,久之,疽发背卒”。杨一清为太监张永作墓志是其削籍家居的直接原因,但并非是因为收受金钱,而是因为被人告发,事关清誉,“先是永用一清计去刘瑾,一清数言永才,而永亦才一清于武宗,得入内阁,以故一清为永志墓,永有家人继宗,容责治之。继宗告容,辞及一清,因坐获罪,而一清悒悒死”[17](P182)。万历年间沈德符亦为杨一清喊冤,认为该墓志不过铺叙生平,并未过分谄媚,“余读杨文襄石淙所为司礼太监张永墓志,不过铺叙永平生宠遇及征安化工寘鐇、随武庙南征宸濠与诛刘瑾之功,他无所增饰。……乃张萝峰谮杨受永弟容赂黄金二百两,因而谀墓,遂追所受润笔,尽夺其官爵,致杨疽背死,噫亦甚矣”[18](P164)。
个人清誉是文人不愿收录内官墓志的因素之一,内官被文人视为“刑余之人”,历来不耻为伍;并且前代内官干政、乱政之例极多,若与内官交往,则易被视为“阉党”。而历史记载主动权掌握在文人手中,在此顾虑下,宦官的历史被按照文人的方式进行了描述与改造,部分被隐藏,部分被删除,“宦官自己的历史记忆被有意无意地删除了”,朝官与宦官政治上的往来为历代史家所诟病,这就“决定了士大夫本人及其后代在为其编写个人文集时普遍不会将为宦官墓志做撰这样‘不光彩’的事辑入文集,以毁一世清明”。[19]
文官为内官撰写墓志更深层次的顾虑还在于现实环境的不利。严禁内外官交结是明朝家法之一。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也积极吸取此前历代内官干政专权的教训,特别注意到内外官勾结的危害,因此严禁内外交通,下令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大明律》将“交结近侍官员”列为禁令之一,规定:“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20](P35)即使到明朝中后期,在内外官勾结已经人尽皆知的情况下,只要斗争需要,这条法律仍然会被搬出来使用。“夺门之变”后,于谦、王文罪名之一即交结内官王诚、舒良、张永等朋党;曹钦谋反后,都督佥事翁邵宗“素与反贼曹吉祥交结”而被降为指挥使[21](P6810);嘉靖初,王琼亦被以“交结近侍”之名论死,经申辩得减充军;崇祯皇帝登基后,专门颁谕,“逆党魏忠贤、崔呈秀表里为奸,把持朝政,变乱祖制”[22](P11),下令外官严禁交结内侍。现实之环境对文人收录内官墓志不利。
面对此不利的环境及可能招来的非议,不予收录就成为诸多文人的选择,由此造成原本数量众多的内官墓志不存于世,仅可从残碑断垣中收寻一二。
总之,因内官身份的特殊,明代内官墓志撰写与一般文官、武将等的墓志存在很多不同。从传主身份看绝大多数为上层内官,而文官中则不然,既有高官大臣,也有九品小吏,甚至生员、处士皆有墓志存世。从撰者与传主的关系看,同朝为官者居多,其私下关系如何则很难断定。而文官墓志中,多直接阐明撰者与传主的亲密关系,毫无忌讳。但内官墓志撰写者明显有很多顾虑,即使有德才兼备的名宦为内官撰写墓志,其个人文集收录者却非常有限,其他文献亦寥寥数篇,由此导致明代内官墓志的流传不若一般墓志广泛,今人所见则主要依靠考古发现的出土墓志。从内官墓志的撰写也可以发现,明代内官的社会交往范围非常广泛,完全突破了明太祖的“家法”限制,不再局限在内廷。内官受皇帝差遣赴各地镇守、监仓、监工等,均为内官走出宫廷、与外部世界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外内官并非一味高高在上,而是努力扩大交往范围,积极地融入地方社会中,通过多种方式来加强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最终得以安身地方,完成皇帝赋予的使命。
注释:
①主要研究成果有:邵磊《南京出土部分明代宦官墓志考释》(《学耕文获集——南京市博物馆论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墓志释读相关研究还有邵磊《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东南文化》,2010 年第2 期),周裕兴《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 辑,1999 年),王清林《明御用监太监赵西漳墓志考》(《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 辑,2004 年),蒋成等《明蜀藩太监墓志集释》(《四川文物》,2001 年第4 期),徐明甫《明两京司礼监太监牛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2 期)等。墓志基础上研究成果尚有齐畅《明永乐朝军功宦官刘氏兄弟史事考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
②按:墓志数量与传主数量不一致是由于内官既有墓道碑,也有墓志铭,如白江,《圭峰集》卷十三有《故内官监太监白公墓道碑》;同书卷十七有《故内官监太监白公墓志铭》。傅容,《圭峰集》卷十三有《故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傅公墓道碑》,同书卷十六有《故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傅公墓志铭》。
③按:该统计传主为临终在王府内任官者,未包含因嘉靖皇帝即位而由王府内官转为北京内官者。
④按:《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 册有一通《赐典宝胡朝墓志》,无撰、书、篆者之署名,但出土于甘肃兰州。《明英宗实录》卷18 记载,正统元年六月己未,肃王赡焰奏:“太祖封先王,建王府于甘州,今移兰县。”可知,胡朝为肃府典宝。
⑤罗玘《圭峰集》载《故内官监太监白公墓道碑》(卷十三)、《御马监左监丞博啰墓志铭》(卷十五)、《故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傅公墓志铭》(卷十六)、《故内官监太监白公墓志铭》(卷十七)。张邦奇《靡悔轩集》载《明故南京守备内官监太监吕公墓志铭》、《奉敕提督浙江市舶司事太监赖公墓志铭》及《明故南京守备司礼等监太监潘公墓志铭》。毛伯温《毛襄懋文集》卷六载有《内官监左少监李公墓志铭》及《明故御马监太监梁公墓志铭》。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有《太监郑公寿藏记》及《太监何公寿藏记》。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九有《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卷十三有《辽府承奉正王公墓志铭》。其他尚有朱有燉《诚斋録》《承奉正张镔墓碣》;李贤《古穰集》卷十五《御用监左少监赠御用监太监阮公浪墓表》;陆深《俨山集》卷七十二《司设监太监董公墓志铭》;岳正《类博稿》卷十《明故御马监太监刘公墓志铭》;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卷十九《明故司设监太监陈公墓表》;李攀龙《沧溟集》卷二十二《明德王府承奉正张君碑》;严嵩《钤山堂集》卷三十《南京守备晏公墓志铭》;于慎行《穀城山馆文集》卷十八《汝府承奉春泉李公墓志铭》;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十《司礼监掌印云峰高公墓表》。
[1](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9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明)贺钦.医闾集[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明太祖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明孝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A].明代传记丛刊(第140册)[M].台北:明文书局,1991.
[7](明)焦竑.国朝献征录[M].台北:学生书局,1965.
[8]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9]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0]佚名.明内廷规制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梁绍杰.明代宦官碑传录[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7.
[12](明)于慎行.穀城山馆文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7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明)张邦奇.靡悔轩集[A].续修四库全书(第133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明)毛伯温.毛襄懋文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3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6.
[15]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17](明)何乔远.名山藏[A].续修四库全书(第42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齐畅.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J].史学集刊,2008,(4).
[20]怀效锋.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1]明英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2](明)孙承泽.山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