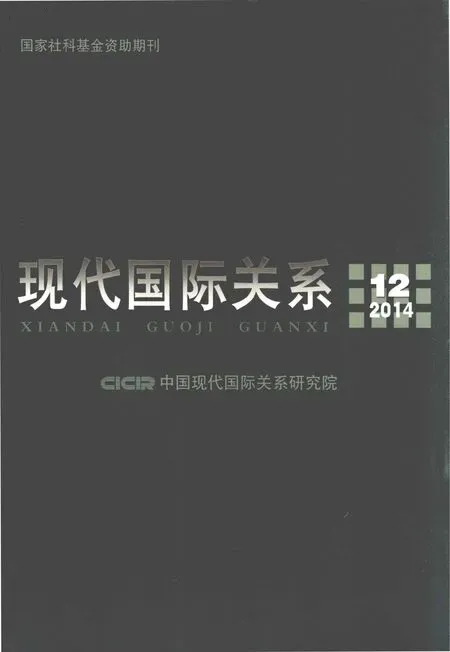试析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
张继业
高度失衡与高度互利共赢一样,一直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那么,中美经济关系缘何失衡?失衡如何不可持续且不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危机以来这一关系为何出现再平衡走势?中美经济再平衡前景如何?面临何种挑战?中国应做出哪些政策选择?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从历史演进、现实发展的角度,对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做一深入分析。
一
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中美经济关系不断拓展深化,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涉及两国经济方方面面的高度经济相互依赖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所谓的“中美国”、“中美经济超融合”。①参见: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l?Think Aga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aury 5,2007;Zachary Karabell,Superfusion:How China and America Became One Economy and Why the World’s Prosperity Depends on It,Simon&Schuster,2009.毋容置疑,这一关系有着高度互利共赢的一面,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经济增长与民众福祉提高;但其又有高度失衡的一面,体现为两国经济往来中要素流动的相对单向性。贸易关系方面,2008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2633亿美元,②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12日)两国贸易关系更多表现为中国向美输出商品;投资③为了便于分析,本文采用狭义的“投资”概念,仅指直接投资。金融资产投资则放在金融关系中分析。关系方面,主要是美对华直接投资的单向流动,2008年美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为539亿美元,中国在美相应资产仅为12亿美元。④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13日)金融关系方面,一边倒地表现为中国大量购买美元资产尤其是美债,2001年中国持有美债786亿美元,2008年增至7274亿美元,期间中国所持美债占所有海外持有美债的比例由7.5%升至23.6%,⑤数据来源于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treasury.gov/ticdata/Publish/mfhhis01.txt.(上网时间:2014年9月15日)而同期美金融机构主要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身份对华股权金融投资,到 2008年其所持中国证券资产仅为532亿美元。①Elena L.Nguyen,“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Yearend 2010”,https://www.bea.gov/scb/pdf/2011/07%20July/0711_iip.pdf.(上网时间:2014年9月16日)
中美经济关系高度失衡与高度互利共赢一样,都缘于两国国内高度失衡、但又高度互补的经济增长结构,长期看这一失衡不利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首先,经济上,中国高度依赖出口、投资的增长结构与美国高度依赖消费的结构极为匹配。美旺盛的消费需求促进了中国出口,拉动了中国出口导向型投资增长,而中国出口所获得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又反补美国,通过购入美元资产满足了美国由于过度消费、储蓄过少所不断膨胀的对外融资需求,使之有能力继续消费中国商品。在中国依赖出口、投资结构下,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而美国跨国公司不断将产能转移到中国,美国内“去工业化”、投资与出口减少,又加剧了其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由此,中美两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衍生出中美间涵盖贸易、金融、投资多领域的经济关系失衡;反过来,两国经济关系的失衡又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国内失衡。如此循环往复,使双方都越来越逼近国内经济失衡的极限,进而很可能导致两国经济陷入困境。比如,在中美金融关系失衡下,中国购债行为拉低了美国内利率水平,客观上为其维持并强化负债消费增长模式提供有利条件,而随着债台高筑、高度债务杠杆化、高消费经济发展到极限,或将引发金融危机,或将影响美元资产信誉、使美海外融资困难,最终将重创美国经济;反过来,由于美元贬值或美进口骤降,势必极大冲击中国经济。而在中美贸易关系失衡下,美国过度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强化着中国出口、投资导向型经济,使得中国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等一系列经济失衡难题加剧,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硬着陆”,这反过来亦将使美国经济受到冲击。
其次,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的影响还进一步外溢到政治、安全方面,影响两国关系稳定,包括:美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对华强硬派反复拿美对华巨额贸易赤字“说事”;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债令美国会担忧中国以抛售国债为武器、影响美国家安全;在中美投资关系失衡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较少,两国经济互利共赢的果实难以广泛惠及美普通民众,客观上不利于抑制美国内反华情绪上升;中国则无奈于其不断累积的美债等低收益美元资产,焦虑于美国“财政悬崖”、“量化宽松”等影响资产价值及其偿还,等等。总之,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安全上考虑,中美经济关系的高度失衡都不可持续,都有再平衡必要。但是,金融危机前两国经济不错的表现,令双方更关注经济关系中互利共赢的一面而忽略失衡一面,两国经济关系始终延续并强化着高度失衡模式。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中美经济关系呈现明显的再平衡走势,两国经济往来中要素流动从相对单向流动趋于朝双向流动转变。贸易关系上,尽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绝对值上看仍在扩大,2013年达2953亿美元,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华进口额原有基数过大的原因,事实上,与危机前相比,美对华贸易逆差增幅显著缩减,2009~2013年逆差年均增幅为7.8%,低于2004~2008年13.5%的年均增幅,其中2013年逆差仅比2012年增加1亿美元。其主要原因在于,危机后美对华出口保持较快增速,而对华进口增速放缓,使得出口快于进口这一危机前就存在的走势进一步强化。2009~2013年,美对华出口年均增幅16.6%,明显高于年均10.5%的进口增幅,较之2004~2008年,年均出口增幅与进口增幅的差值由5.2%扩大至6.1%。这几年美对华出口不断攀上新台阶,2010年达1155亿美元,2013年达1605亿美元。②以上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或根据该网站数据计算所得,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17日)以上数据清晰显示出在中美贸易往来趋于双向流动下两国贸易关系的再平衡走势。投资关系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开始保持高速增长势头,2013年中国在美存量资产达80.7亿美元,较之2008年的11亿美元增长近7倍;同期,美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则较为平稳,2013年美在华存量资产为615.3亿美元,较2008年的539.2亿美元增长14.1%。其结果是,尽管美在华存量资产仍多于中国在美存量资产,但是差距快速缩小,2008年两者比值为49∶1,2013年收窄至7.6∶1。双方投资更趋于双向流动,2012年中国对美投资流量首次超过美对华投资流量,两国投资关系再平衡走势已很明显。①以上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或根据该网站数据计算所得,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17日)金融关系上,危机至今,中国持有美元资产总体上仍在增加,但购买步伐明显放缓,特别是在购买美国债方面,中国所持美债占所有海外持有量的比例由2008年的23.6%降至2013年的21.9%,2013年以来中国月度持有美债量基本在1.27万亿美元上下浮动。②以上数据来源于美国财政部网站或根据该网站数据计算所得,http://www.treasury.gov/ticdata/Publish/mfhhis01.txt.(上网时间:2014年9月18日)另一方面,美国购买中国金融资产步伐在加快,所持中国证券资产由2008年的532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1193亿美元,增幅高达124%。③以上数据参见Report on US Portfolio Holdings of Foreign Securities,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October 2013,p.36.因此,总体看,虽然中国所持美金融资产仍10倍于美国所持中国资产,但随着两国对对方金融资产的投资呈现不同的增长节奏,中美金融关系正逐步由失衡向平衡发展。
二
中美经济关系缘何出现再平衡走势?正如前文所述,两国经济关系的失衡缘于两国国内经济增长结构的失衡。反推之,两国经济关系再平衡也主要是缘于两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就中国而言,危机至今,虽然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很大,但消费对增长贡献明显增大,出口的贡献则显著下降。危机前的2007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9.6%、42.4%、18%,此后 6年消费贡献率分别为 44.2%、49.8%、43.1%、56.5%、55.0%、50.0%,净出口贡献率则分别为8.8%、-37.4%、4.0%、-4.2%、-2.1%、-4.4%。④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上网时间:2014年9月18日)显见,危机前以出口、投资为主的中国经济增长结构逐步朝再平衡方向发展。就美国而言,虽然结构调整力度远不及中国,其个人消费对GDP贡献率危机至今仍维持在68%左右的水平,但增速放缓。危机前6年美国年均消费增速达到3.0%,而此后6年这一数值降到1.1%。与之相应,个人储蓄率由2007年的4.2%升至2013年的9.8%。⑤以上数据经计算所得,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9&step=1#reqid=9&step=3&isuri=1&903=137.(上网时间:2014年 9月 19日);The White House,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March 2013,pp.355-362.同期,净出口对美国GDP贡献率由-4.7%升至-3.1%,出口贡献率由11.9%升至14.2%,⑥The White House,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March 2014,pp.366-367.其过度依赖消费的增长结构无疑在朝着平衡方向缓慢发展。
中美两国国内结构的再平衡使得危机前两国经济关系高度失衡局面得到很大改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占比由危机前最高点10.1%降到2013年的2.1%,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比则由-5.8%升至-2.3%,⑦Wayne M.Morrison,China’s Economic Rise:History,Trends,Challenges,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August 21,2014,p.37,http://fas.org/sgp/crs/row/RL33534.pdf.(上网时间:2014年9月20日)这一改善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出口更少、进口更多,而美国则是国内需求增长缓慢、出口更多、进口更少,由此中美贸易更趋于双向流动、更趋于平衡发展。同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减少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增幅放缓,这必然导致中国从大举购买美债转而稳定乃至减少持有美债规模,这又推动了中美金融关系再平衡。
更深层次看,既然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主要缘于两国国内结构再平衡,那么国内再平衡的动力又源自何方?或者说,是什么根本性因素通过推动国内再平衡促成了两国关系再平衡走势?政策性因素并非主要原因。中国方面,危机后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及海量货币流动性,主要着眼于短期经济增长,并不利于长期结构调整。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新蓝图虽将极大促进结构调整,但其以2020年为目标,至今并未全面展开。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虽然也强调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宣称美国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消费向更多依靠出口、投资转型,⑧The White House,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February 2010,pp.29-38.并出台了“出口倍增计划”、“选择美国”计划等,然而释放出数万亿美元流动性的美联储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令美总体经济政策呈现出扩张性色彩,更侧重于刺激消费、拉动增长,这对于结构调整显然不利。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这一周期性因素、中美两国要素禀赋变化这一结构性因素才是促成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两大原因。
首先,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令美国自2001年以来以过度借贷、资产泡沫为支撑的高消费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在债务去杠杆化效应下个人还债压力增大,随着房价下跌美国家庭财富急剧缩水,而实体经济复苏缓慢又令收入停滞不前,这三大因素联动互振,使得美国消费增长缓慢,经济增长结构被迫向再平衡方向发展。与此同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之后的欧债危机严重冲击全球实体经济发展,令危机前高速增长的全球贸易大幅下滑,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无疑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欧盟、美国这两大中国最大出口市场的经济陷入困境,极大影响了中国出口。由此,外部经济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进一步彰显出中国出口、投资导向型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并倒逼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其次,要素禀赋这一结构性因素的显著变化也是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以来,在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禀赋中,劳动力价格低廉一直是使中国经济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禀赋优势。正因为这一优势,国际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出口加工平台、大规模向中国投资、转移产能,中国本土企业也利用这一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与投资,中国遂形成并不断强化着以出口、投资为导向的高度失衡的增长结构。就美国而言,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一个不断被“碾平”的世界里,美国在劳动力成本要素上的禀赋劣势,以及资本、技术优势被同步放大,其结果就是美跨国公司为利润最大化在全球布局供应链,将自身资本、技术优势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相结合,大规模向中国等国转移制造业产能。在此过程中,美国内投资被挤出,同时更需要通过进口满足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因而催动美国内过度依赖消费的失衡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总之,正是基于要素禀赋的不同,中美形成了最终导致两国经济关系高度失衡以及导致各自高度失衡的经济增长结构。
然而,危机前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中美要素禀赋却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方面,其经济数十年高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2013年人均GDP已达到6900美元,①Wayne M.Morrison,China’s Economic Rise:History,Trends,Challenges,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August 21,2014,p.6.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收入提高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减,比如2000年中国平均月薪是94美元,仅是墨西哥的30.2%;到2013年中国平均月薪升至694美元,比墨西哥高出50.5%。②Wayne M.Morrison,China’s Economic Rise:History,Trends,Challenges,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August 21,2014,p.10.与此同时,发展水平与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令中国长期以来在技术、资本等要素上的劣势得到很大改善,在一些方面甚至有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包括在装备制造、通讯信息等产业上的技术优势,以及拥有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的资本优势,等等。经济要素与禀赋优势显著变化令中国原有经济增长结构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续性加剧,倒逼结构向更依赖资本、技术、创新,更依赖消费的再平衡方向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中美经济互动模式的显著变化。比如,以耐克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逐渐将在中国的产能向劳动力价格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并相应减少了中国对美出口、以及美对华直接投资;而中国国民收入增长增强了民众购买力,为美国扩大对华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在资本、技术要素上的显著改善,直接造就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对于技术、品牌、市场的进一步渴求,推动它们踊跃对美投资。凡此种种,均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向再平衡方向发展。美国方面,近年来其要素禀赋也发生显著变化。一是以“页岩油气革命”为代表的美国能源革命,不仅增加了其能源自给率,而且大幅降低了其能源价格,如2013年美天然气价格仅为欧洲的1/2、亚洲的1/8③转引自“美天然气价格仅为亚洲1/8专家:低气价难以持续”,中国新闻网,2013年7月3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3/07-03/4996890.shtml.(上网时间:2014年9月20日)。二是危机后美国内薪资增长停滞不前,以及新兴国家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明显改善了美劳动力禀赋劣势。以上变化,无疑增强了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了美国内再工业化进程,有助于拉动美投资增长,同时“再工业化”增加美国内制造业产能,也意味着美进口的减少、出口的增加,这些均有助于美增长结构向更平衡方向调整,从而牵引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这尤其表现在美禀赋优势的增强、结构调整,不仅令一些在华美企将部分在华产能回抽美国内,更增强了赴美投资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由此推动了中美投资关系更平衡发展。
三
展望未来,大的趋势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将继续向前发展。首先,牵引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源动力——两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将不断深入发展。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影响、中美要素禀赋变化这两大因素将继续起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仍难以消弭。全球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欧债危机有所缓解但欧盟很可能长期处于增长缓慢的“通缩”状态,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很大程度上是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的结果,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与增长结构调整双重挑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4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甚至认为,世界经济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低增长率的“新的常态”。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内瓦),《201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3 页,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tdr2014overvie w_ch.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日)这些因素均倒逼中美两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中美要素禀赋将延续之前发展趋势,从而继续促动“再平衡”。由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认为,未来20年,随着中国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速度放慢以及中国老龄化发展,劳动力供给将下降、成本将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资本、技术积累将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将更趋于向资本、技术密集方向发展。②The 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PRC),China 2030,2013,pp.377-384,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2/02/27/china-2030-executive-summary.(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日)国际能源署预测,2015年美将超越沙特成为世界头号石油生产国,美天然气产量将由2014年的6810亿立方米增至2018年的7970亿立方米,2035年美将实现能源自给。③“U.S.Natural Gas Production to Accelerate Next Year:IEA”,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2013/06/20/u-s-natural-gasproduction-to-accelerate-next-year-iea/?__lsa=18c9-4a96;“IEA Predicts the U.S.Will Be the World’s Largest Oil Producer by 2015”,http://instituteforenergyresearch.org/analysis/iea-predictsthe-u-s-will-be-the-worlds-largest-oil-producer-by-2015/.(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日)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美国单位时间劳动力价格将由2013年比中国高55%缩小到2015年的39%。考虑到美国总体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中国,中美实际劳动力价格差距将进一步缩小。④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Made in America again:Why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the U.S”,August 25,2011,https://www.bcgperspectives.com/content/articles/manufacturing_supply_chain_management_made_in_america_again/.(上网时间:2014年9月20日)
另一方面,政策性因素将为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注入新动力。中国方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序幕。随着改革开放新蓝图逐步付诸实施,至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将朝着更均衡方向不断发展。中国将主要在四个方面推动“再平衡”:一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仅为53.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4年3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6/c_119791251_2.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30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农民进入城市,提高其收入水平,极大拉动消费需求。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2013年中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为46.8%,远低于美国75%的水平,甚至还不如印度55%的水平,⑥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219.服务业在中国有很大发展空间,而服务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之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更能吸纳就业人口。大力发展服务业对于增加就业、提高国民收入、促进消费、推动结构转型将有较大促进作用。三是利率、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长期以来,中国存贷款利率双低、能源价格相对低廉,令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倾向于资本而非劳动,既抑制居民收入提高、影响消费,又反补资本并发出扭曲价格信号、刺激投资,从而加剧经济失衡。市场化改革将推动存贷款利率“双升”、能源价格回归市场价格,这将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加投资成本、抑制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再平衡。四是社保、医保改革。这将扩大保障覆盖面、提升保障水平,从而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推动消费增长,同时抬升利率,抑制投资,有利于经济再平衡。美国方面,主要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货币政策收紧,以及“自动减赤机制”实施,将使宏观经济政策由扩张性转向中性,从而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下降,有利于美经济再平衡。2014年11月美联储完全退出“量宽”,此后2015年将多次上调利率。随着超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收紧,此前受海量流动性刺激而上涨的股市、房市价格很可能停滞甚至下跌,美国家庭财富将随之缩水,而因股市、房市上涨而有所修复的家庭负债表可能转而恶化,再加上美国“中产阶级”收入长期停滞,美消费需求增长将受极大抑制,倒逼美经济增长更依赖出口与投资。而从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10年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削减计划,将削减就业,其对消费抑制作用也显而易见。仅2013年度,“减支”即令美国减少了约75万个就业机会,拖累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增长达0.6个百分点。①The White House,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March 2014,p.48.
未来数年,在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共同作用下,中美国内经济增长结构将持续处于再平衡进程中,中国将更多依赖消费驱动增长,美国将更多依赖出口与投资驱动增长,这将使高度依赖出口与投资的失衡的中国增长结构,以及高度依赖消费同样也是失衡的美国增长结构均进一步朝更均衡方向发展。
其次,中美国内再平衡以及其相互间高度的互补性,将推动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朝着再平衡且互补方向发展。贸易关系上,国内再平衡进程中,中国更注重消费并大力发展服务业,与美国更注重出口高度互补,这将重点体现在美对华消费品货物出口、服务贸易出口上。长期以来,美国对华出口货物,除农产品外,主要集中在飞机、机械、矿产等满足中国进一步投资、出口需求的货物上,消费品出口比例较小,例如,2011年美对华消费品出口仅占其全部对华货物出口的1.9%。②Stephen Roach,Unbalanced: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p.236.未来随着中国国内消费总量不断增加,消费品质不断升级,美国对华消费品出口有望大幅增加。此外,美国在服务业方面产业优势突出,服务贸易出口一直是美对华出口强项。2013年美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已高达377亿美元,其占对华贸易总额的比例由2007年的16.9%升至2013年的23.4%。③以上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网站或根据该网站数据计算所得,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日)显见,未来随着中国服务业大发展,在金融服务、旅游、留学、医疗等很多领域,美国对华出口还有望大幅增加。以上美对华出口的增加将进一步收窄美对华贸易逆差,使中美贸易关系趋向平衡。投资关系上,中国将减少对投资增长的高度依赖,在国内被挤出的投资势必在海外寻求新投资目标;而在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美国将更多依赖投资驱动增长,有较大的吸引海外投资需求,两者高度互补。这将重点体现在中国对美高科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上。具体看,当前中国海外投资正经历一个由主要投向能源、资源领域向多元化投资转型的阶段,未来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升级,对海外高科技产业投资势必不断增加,美国因其技术、品牌、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上的优势,将成为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投资的主要目标国。事实上,这一趋势已有所显现。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宣布的赴美高科技并购金额高达60亿美元,其中包括对摩托罗拉、IBM的收购。④Thilo Hanemann and Daniel H.Rosen,“High Tech:The Next Wave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merica”,Asia Society,April 2014,p.9.此外,美国主要建设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交通、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未来20年将集中进入更新换代期,这方面投资需求预计高达8万亿美元。⑤Daniel H.Rosen,Thilo Hanemann and Anna Snyder,“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US Infrastructure”,October 23,2013,http://rhg.com/reports/assessing-the-opportunity-for-chinese-participation-inus-infrastructure.(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日)这将极大吸引既具有产业竞争优势又有资金优势的中国厂商赴美投资。总之,未来随着中国对美投资的快速增加,中美投资关系也将更趋于平衡。金融关系上,国内再平衡将使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将使经常项目顺差增幅减少甚至出现赤字,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对美金融投资步伐放慢甚至减持美元资产;期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金融业改革开放政策不断付诸实施,包括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以及上海自贸区建设等,将会有更多美国金融资本融入中国、分享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红利。作为新一轮金融改革开放试点,“沪港通”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启动,美国诸多金融投资者即跃跃欲试欲借道香港投资大陆金融市场。①“美国投资者等待沪港通开闸,外资绕过QFII限制入华”,《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29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hkstocknews/20140829/030420154433.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3日)总之,未来中美金融投资双向流动将不断加快,中美金融关系也将更趋于平衡。
四
尽管未来中美经济关系朝平衡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但两国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再平衡无疑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这决定了两国经济关系再平衡进程也将是长期的、渐进的,期间不乏挑战。一是中美国内结构调整不同步的挑战。由于中国结构调整紧迫性更强、政策力度也更大,而美元霸权地位所带来的海外融资便利性、长期以来以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根深蒂固的政策思维模式等,令美国内结构调整有先天惰性,一种很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中国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快于美国,由此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下降速度将远快于美国对外融资需求下降速度,这种速度差很可能导致美海外融资困难,其直接后果便是美债利率大幅攀升、美元以及美债等美元资产加速贬值。事实上,这将以一种强大外部压力的方式倒逼美经济转型、进而加快中美经济再平衡进程。但问题是,这种加速度的再平衡可能引发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乃至又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最大的负面影响莫过于由于持有美元资产存量巨大,将面临巨大的资产缩水,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
二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挑战。未来10-20年,中美政治安全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这既表现为中美围绕亚太主导权的角力,又表现为因两国实力更接近(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美国)所加剧的新兴大国与既有霸权国间的结构性矛盾,还有两国在网络、太空、深海等战略新疆域的激烈竞争,等等。而同期,美国将很可能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中产阶级”困境、政治社会“极化”、世界经济第一地位被超越等一系列挑战加剧而萌生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如此,中美经济再平衡期、国际权力转移期、美国战略焦虑期“三期”重叠,将不可避免地使中美关系中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使政治因素影响中美经济再平衡,并对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构成挑战。比较可能“出事”的是中美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一方面,“再平衡”将使中美贸易流动向平衡方向发展,长期看有助于抑制美国内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但问题是,一段时间内,尽管美对华出口增长很快,但由于美对华进口原有基数过大,将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仍巨大,特别是在未来美总体对外贸易逆差趋于收缩情况下,美对华贸易逆差占比甚至可能进一步提高。一旦与美国内战略焦虑感以及就业岗位转移海外、收入停滞等民生问题产生共振,就可能激化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甚至不排除美国会对华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再平衡”进程中,中国企业将进一步投资美国市场,高科技企业将是重要的收购目标,同时国企又是中国赴美投资主力军之一。事实上,当前美对华投资保护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中国国企受中国政府控制,通过收购美高科技企业、从而获得一流技术,不仅在中国政府资金、政策支持下做大做强,对美跨国公司构成严峻挑战、削弱美国际经济竞争力,而且国企是中国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其在美商业行为很可能危及美国家安全。总之,未来若干年,政治安全因素外溢将使中美经济再平衡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三是其他挑战。金融方面,中美关系再平衡进程中,将有更多美国金融资本流向中国,其中不乏短期投资炒作的“热钱”,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不断推进、实体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预期不断强化背景下,“热钱”很可能在短期内借金融投资渠道大举进入中国,这虽将加速推动中美金融再平衡,但其对中国金融稳定构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不容低估。投资方面,除了政治因素将影响中国对美投资外,缺乏双边投资协定保障、两国在各自国内经济体制、市场规则、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巨大制度差异,甚至中国海外形象问题①2014年9月18日在本文作者与美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怀恩·莫里森的一次座谈中,莫里森表示,他最初对于2013年双汇收购“斯密斯菲尔德”一案在美成为热点问题并在国会遭遇较大阻力感到惊诧,因为双汇是民营企业、且收购目标也非高科技企业,收购基本不会对美竞争力、国家安全构成负面影响。莫里森认为,其背后原因涉及中国形象因素,美国民众担心中国企业入主美肉类企业将影响美国肉制品的食品安全,而且中国消费猪肉制品量如此巨大,收购将使更多肉制品出口中国,抬高美肉价、使美国人没有肉吃。都将成为中国赴美投资乃至中美投资关系再平衡的挑战。
中国在顺应并积极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趋势的过程中,既要促进国内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又要争取进一步深化拓展中美经济融合,进一步做大两国共同经济利益的蛋糕,构建一种建立在更平衡基础上的更持续、更健康、更互利的新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为此,中国第一要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高度出发,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国内经济再平衡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切实加强政策对再平衡的支持力度。既要稳中求进、积极落实十八大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新蓝图,加快国内经济再平衡步伐,从而进一步牵引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又要善于利用中美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互补性,利用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助力国内经济再平衡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第二要加强对美政策沟通与协商,努力使两国在再平衡过程中相互呼应、协调合作,减少因“不同步”引发的挑战;同时,为确保美债等美元资产安全,也为促美加快国内再平衡,可考虑在与美方沟通好的情况下,逐步、分批、小规模地减持美元资产。第三要着力抑制政治安全因素对两国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负面影响,包括加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并尽早付诸实施,以制度保障减少美投资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重点推动中国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赴美投资以减少政治敏感性,同时多考虑如何创造美民众就业机会、多惠及美国民众。第四要有序推进中美金融再平衡,确保国内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