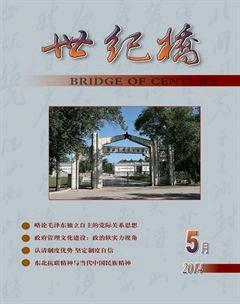浅析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中的“乡村”形象
石金焕,王玥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青文学较之前的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知青作家与非知青作家的并存,“知青岁月”的回忆与“知青岁月”的想象共同建构着知青文学,正因此,对“乡村”的呈现便出现较客观和理性的审视。本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个别作品的分析,探讨了“乡村”形象在知青文学叙述中的新变——贫穷与苦难、愚蛮与落后、淳朴与善良,而这主要通过民性、民情、民俗表现出来。在“丑”与“美”的展示中表达了知青文学对“乡村”的深入理解与认知。
关键词:知青文学;贫穷与苦难;愚蛮与落后;淳朴与善良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的“怀乡”后,90年代以来的知青文学对“乡村”有了更为理性和客观的审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刘醒龙的《大树还小》、韩东的《扎根》、《母狗》、《知青变形记》、杨剑龙的《汤汤金牛河》、梁晓声的《知青》、芒克的《野事》、野莲的《落荒》等。这些作品或以“乡民”视角,或以“知青”视角对“乡村”的民性、民情、民俗进行了全面的关注。“乡村”在这里不再是宁静之地,而是裹挟着更为古老的愚蛮文化,伴生着更为苦难的贫困,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人性之地。
一、贫穷与苦难
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贫穷似乎是每个乡村都脱不掉的一件外衣。缺粮、缺水、缺钱使乡村沉沦在苦难之境苟延残喘。
韩东在《知青变形记》中借知青罗晓飞的眼审视了乡村的贫穷。罗晓飞插队的老庄子穷的只有一头老耕牛,全庄人视为生命。村民睡的床上铺的是稻草,枕头是稻草下面垫个土墩,席子有破洞,连被子也是破的。“挂面”“面疙瘩”“米饭”都是款待客人的奢侈品。一家之主要是死了,他的孩子女人则成了队上的负担。老庄子的人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种贫穷中,还要承受特殊年代王助理等人的盘剥。与韩东同样,梁晓声在《知青》中也以“知青”视角审视了“乡村”的贫穷与苦难。陕北的“坡底村”是个缺水、缺粮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人世世代代与苦难、贫穷为伴。他们喝的是黄黄的水,所谓洗脸、洗脚就是同湿毛巾擦擦。鸡蛋在这里是奢侈品,赵天亮初到陕北落脚在王大娘家,为了款待客人,王大娘拿出了唯一的财产——十二个鸡蛋,换了半斤挂面、一点酱油和醋、几盒火柴。面对贫穷坡底村人想改变命运,知青赵曙光领着村民搞副业挣钱打井,知青赵天亮送给了坡底村人几头羊,但这些努力都受到了“极左”政治的制裁和迫害,这使乡村的贫穷和无望变得亦发醒目。与坡底村的缺水不同,山东沿海的小渔村虽然不缺水,但也改变不了贫穷苦难的命运。这里的人养不起大船,紧靠小船在近海养殖海带勉强生活,而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之下还要承受台风的肆虐。
无论是韩东还是梁晓声,他们对“乡村”的审视都是将其放在特殊年代之下。“乡村”的贫穷带有着生产力落后、经济萧条、政治束缚的色彩,而刘醒龙则跳出那个年代,转而关注“文革”后的乡村。《大树还小》中的秦家大垸是贫穷的,“大树”的姐姐因为弟弟没钱治病,出外打工不得以委身如今已发达的知青“白狗子”,断送了自己的青春。
除了这些作品外,《汤汤金牛河》、《扎根》、《双驴记》等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写了“乡村”的贫穷与苦难,这是知青文学不可回避的主题。然而,对这一主题的反复呈现“激起的不是主人公对乡村竭力的批判,而是他们改造这种现状的激情。”[1](P.81)知青罗晓飞、赵曙光、武红兵等人或用自己的智慧或用生命帮助乡村摆脱贫穷和苦难。这种对贫穷苦难的描写为 “乡村”负上了苍凉、萧条的气氛。
二、愚蛮与落后
贫穷激起了知青和乡民改革的热情,但在改革进行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却是深入乡民思想深处的愚蛮文化与落后意识。
韩东喜欢在自己的知青作品中塑造农民的内在思想状态。在《扎根》中借老陶家“城市物品”将农民的愚昧、落后意识表现出来。对于老陶家的东西,农民们会不辞辛苦地围观、议论,甚至摸胸口吐唾沫,以此表示惊奇、不理解。而最让她们感到惊奇的是穿衣镜,她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到老陶家照镜子,一边照一边推搡打闹,“笑得牙龈毕露”。如果说这种落后和愚昧还算可爱的话,那么《母狗》和《知青变形记》则将这种愚昧推至近于野蛮和荒诞的境地。《母狗》中的三余人总是嘲笑、窥视、觊觎知青小范,他们认为“反正和城里女人睡觉不吃亏,睡一个赚一个,……不睡白不睡。”最后,小范因受不了三余人的“秽语”服毒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得以返城。三余人对小范的“回城“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为了让自己在精神上获得胜利,三余人一致认为小范是被校长“操”后才回城的。与“三余人”的精神胜利法不同,老庄子的人则更注重“生”的实惠。范为好将弟弟范为国失手打死后,面临着牢狱之灾和失去亲人的双重痛苦。为了生存,老庄子的人策划李代桃僵的逃生机会。他们在福爷爷的操纵下,利用范为国的尸体伪造了一个知青罗晓飞畏罪投河自尽的事实。而知青罗晓飞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范为国,他要继承范为国的一切。罗晓飞如果接受了这一事实,他就能逃脱“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并且使自己、范为好、范为好的妻子,范为国的妻子重获“生”的权利,否则,这些人的一切将被毁灭。在近于戏剧化的“变形记”后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沉重,一种愚蛮文化重压的窒息,一种所谓“秩序”的悲哀。刘醒龙在《大树还小》中借秦四爷的坎坷经历阐述了农民麻木、怯懦的文化性格。秦四爷在文革中因与一名女知青恋爱同居遭到了知青们的疯狂报复,尽管女知青文兰是自愿的,秦四爷还是被抛入大狱,这毁了秦四爷的一生,也毁了文兰的一生。如今当年的知青白狗子们重返下乡地,但他表达恨的方式却是“避而不见”,只是最后在坐不坐知青的车进城看病时,秦四爷才做了一个算是大胆的报复:“坐他们的车,他们能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坐!”[2](P.107)这句话是秦四爷憋了一辈子的大胆一吼,但它背后掩藏的却是秦家大垸人的愚弱、怯懦。
对农民这种思想状态的关照是90年代后知青文学创作的一个突破,这与80年代大部分作品对农民的美化相对照,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农民的精神弊病,从而为乡村形象附上了沉重的灰色调。
三、淳朴与善良
二十世纪90年代后的知青文学对“乡村”贫穷与苦难、愚蛮与落后进行阐述的同时,也看到了乡村的另一面——民风的淳朴、乡民的善良以及知青与农民间的互助互爱。
芒克在《野事》中开篇便借村妇与队长间的调戏取乐渲染了麦村民风的淳朴、自然。“只见小白鹅一扭身一声尖叫,接着她就死拽住麦大壮的胳膊并招呼那帮娘们一哄而上把队长按倒在卖场上,那麦大壮即刻就被她们扒掉了裤子……。”[3](P.17-18)韩东《知青变形记》与芒克《野事》不同,他以压抑的笔写了村民间的“团结友爱”。为了保住范为好一家和范为国的妻子,老庄子的精神领袖福爷爷以老迈之躯去承受王助理等人的“枪托”殴打,同福爷爷一样,全体村民替范为好、范为国的妻子保守秘密。虽然,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可以看出村民的团结、友善。梁晓声在《知青》中则把这种善良、淳朴升华为农民与知青、农民与农民间的互敬互爱。知青冯晓兰因是“黑五类子女”,经常受到李君婷等人的批斗。坡底村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叮嘱王大伯“晓兰住你家,你该庇护,那就得庇护点儿她。”[4](P.83)与坡底村相映衬的“山东屯”,虽然生活环境极其艰苦,但这里的人与坡底村人同样都是善良的。上海知青周萍因成分不好做不了兵团战士,回到了“山东屯”做一名插队知青。对此,女支书梁喜喜将饮泣的周萍揽在怀里,并安慰道:“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主要关怀的一名知青。谁欺负你,告诉我,看我不收拾他。”[4](P.212)梁喜喜的关爱让失落的周萍找到了新生的动力。农民对知青的关爱让我们感到了乡村的温暖,而农民与农民间的互爱,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厚重。韩奶奶是村里的孤寡老人,村人像亲人一样去关爱她活着的每一天,去送别她临终的那一刻。王大伯不顾病痛要为韩奶奶吹丧,支书渴望韩奶奶临终前的召见,妇女们则哭成一片,而韩奶奶最后也没有忘了将自己仅有的几块棺材板捐给村里。坡底村人的情与爱深深地打动了每一名知青,唤起了他们对爱与美的信念。“今天我们都受到了触动——人家坡底村人互相能有那份儿亲情,再空虚再无聊再烦闷,也不能再用批斗别人的方式来排解了!”[4](P.238)武红兵表态道。就连最娇气的李君婷也表示“这一点,我也能做到。”在坡底村人的影响下,最消极的武红兵与最自私的李君婷恋爱了,而且还为了保护村人的生命和财产牺牲了自己。乡村的开放、天然释放了人性,乡民的善良淳朴凝聚了生的力量,这一切使乡村度过了重重困苦与坎坷,以亘古不息的力量延续生命,走向新生。
贫穷、苦难、愚蛮、落后、淳朴、善良这些相互矛盾的词汇所搭建起来的乡村形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青文学对“乡村”的一个审视,其中可能不乏过度丑化与美化的成分,但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它毕竟表达了一种“真实”。
参考文献:
[1]马绍英.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 意义[J].延安大学学报,2009,(5).
[2]刘醒龙.大树还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芒克.野事[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
[4]梁晓声.知青[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