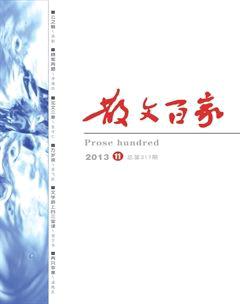烤红薯的大嫂
赵丽霞
城外紧临国道边的一幢两层楼院,曾经是我们单位租赁的办公的地方。自单位搬来之后,楼右侧有片闲地,原来杂草丛生,荒芜已多年,转瞬,摆了好几家露天小吃摊。以面食俱多,有手擀面,饸饹面,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简单,实惠,便利。我上班因离家远,便成了这里的常客、熟客。
有一天,我正喝面,没几口,忽然嗅到了一股香香的、甜甜的还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由远及近——啊,那是一种我熟悉的、童年的烤红薯的味道儿呀!放下碗筷,伸长脖颈,环视周围,在偏僻的一角,果然见一樽大粗圆桶杵在那儿,周身被硬箱纸用铁丝紧扎着像裹了层外衣,许是为了阻防炉内的热量散失太快吧。旁边站着一位貌似农村的中年妇女,上着一件红格宽肥的长袖围裙,头蒙一块蓝方巾,一下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又黑又大,亮闪闪,很美。她的右手戴着一只绿棉手套,伸入炉内,摸索着,神情专注。猛一抬头,看我正陶醉地注视着她,有些不好意思,赶忙为我挑了一个刚出炉最大的,问我中意不。我笑笑,算作默许。她边称边说是自家沙土地里的,比水烧地种的好吃,还说家里刚刨了几棵椿树锯了根,无他用,就背来试着烤。这时,我才发现她脚下一个柳筐里盛了一堆显然用斧头劈好的枝枝片片。据说椿树叶和皮药用价值相当大,想必经椿树根烤过的红薯也同样会被熏染到。“头一天出来,嘴笨不会说”,大嫂像在检讨着自己。我的眼却直盯着她拎起的秤盘里那块正嗞嗞冒着香气的红薯,生怕一不留神它会飞。大嫂说我是她的第一个顾客,称完就又给添了块小的,也没算钱,就连算好的零头也给抺掉了。大嫂这人,可真实在。大嫂不是夸,她家的红薯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吃:红皮白瓤,干面细甜,再经椿树根这么一烤,由里而外嗞发着一种特殊的香气,慢慢自然地浸润到人的骨子里,酥酥的,麻麻的,然后,不饮而醉。
吃馋成瘾,只要嗅到那味儿,我就无法抗拒,怎么吃都不厌。
有几日没看到大嫂,我便如坐针毡,胡思乱猜,不知是她家中有事,还是生病了。一有空我就丢了魂似的往外跑,一趟又一趟。近两月有余,还是没见她的身影,不安也就变成死心塌地,但总觉得仍有份牵挂悬在心尖。正当大嫂的故事已彻底落幕,不经意又再次徐徐拉开了。只是这次登场亮相的不单是她自己,身边还多了个“小龙套”——矮矮的,八九岁模样,瘦尔巴几,在那拽着大嫂的衣角拧摸来拧摸去,嘴里“叽里呱啦”不住地嘟囔着,听了老半天也没听清一个字。仔细打量着这个小家伙:他的头始终歪斜着,两只眼也被挤兑得不一般大;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大嫂,他就会要命地大叫,两只细得火腿肠般的小胳膊立马伸开,勇敢地挡在大嫂身前,俨然一个保镖的姿态。啊,一个脑瘫孩子!我看得心酸。大嫂爱抚着小家伙的脑袋低垂着头,看都没看我一眼介绍:“我小子。属虎,叫虎子”。说罢,从烤炉上拿起一块红薯,不等递到虎子手里,虎子便一把疯抢了过来,一口塞下去半截,噎得他上不来气。大嫂脸色都变了,赶紧拍着他的后背:“慢点慢点”。我觉得自己有点多余,便默然躲开了。
带着个不正常的孩子,不仅影响大嫂干活,也闹腾得周围不得安宁。一些过往的行人想在此歇脚吃饭,不等客人落坐,虎子便调皮地从地上捡起砖头瓦砾胡乱扔,吓得客人扭头就跑。虎子的怪异行为激怒了那些摆摊的同行们,他们一口一个“傻蛋”叫虎子,还想法百计捉摸着如何将这娘俩撵出他们的地盘。比如,用不知哪搞来的假币和大嫂兑换。大嫂觉得自己和虎子在这给别人添了那么多麻烦,心存愧疚,很是热情。当大嫂把钱拿到银行去存时,才知道受了骗。大嫂气不过,拉起虎子挨个找他们理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承认,还都凶巴巴地反咬一口说大嫂诬陷。瘫在地上的大嫂,抱着虎子,好一阵痛哭。虎子不知啥时抄起烤炉上夹红薯用的那把长铁钳,朝着一个正在猫腰盛面的主人头上狠狠地敲了下去。锅里的面汤顿时变成了红色,所有在场的人都傻了眼。结局便是大嫂受骗的钱不但没要回来,反而又搭进去一叠子的医疗费,大嫂决定收摊不干了。听来我们单位办事认识大嫂的人说,虎子刚出生没满月,虎子他爸就向家里人推说,要出去打工回来给虎子好好看病,这一走,就没了人影儿,也没和家里任何人有一丁点联系,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听此,除了气愤,心情越发沉重。为了能留下大嫂,思来想去,还是送了她一台验钞机,并教她如何识别假币。这一招还挺管用,再没人敢来糊弄她。倒是有两家欺负过她的趁夜打道回府,再也没露面。以后,我每天只要忙完手头活儿,就想法把虎子哄到单位来。虎子本来就不老实,见了报纸就撕,拿起水杯就砸,常常把办公室搞得跟战场一样。我们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成了虎子的勤务兵。闲了,这个教虎子跳舞,那个教虎子说简单的话,甚至还给他讲故事。说到精彩处,他就拍着小手,笑得更响,蹦得更欢了。一晃就天黑,大嫂来领虎子时也会把一天没卖完剩下的红薯遇谁都硬塞,尝尝尝尝。大伙拗不过,也就不再谦让,趁不注意偷偷把钱塞入她的衣兜里,毕竟大嫂也不容易。
就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产期一到,我便回家休养。再上班时,单位已搬回了城里。从此,琐事缠身,便没再回过那儿,也没再吃过烤红薯。直到儿子入托那年,只要一看到街上有卖烤红薯的,伸着小手就够着要,不买就撒泼。这时,不由衷我又想起了大嫂,不知她还在不在那儿,虎子还淘不淘。终于又回到了从前的老地方,空了的那个角上堆着人一般高的垃圾,散发着刺鼻的烂臭味儿。仍有不甘,几经往返。又一个秋末,大老远嗅到了那股熟悉的香味儿,那么熟悉,脚步更快了。眼前的大嫂简直不敢让人认,才几年不见,她的头发几乎白成了雪,脸色像涂了层蜡,那双灯似的大眼睛如同两口枯井,陷得那么深。身边没了虎子的嬉闹,这里静得可怕,我到处找。大嫂第一眼看到我,先是惊了一下,不等我开口,她似乎已读懂了。“虎子”,她脱口而出,我急着想听下去,她却顿住了,眉头锁成了疙瘩,仰着天,许久,“已经打发走了”。声音很小,沙哑,低沉,但我听得很清。我的喉咙里顿觉有件硬物被卡住了,吐不出,咽不下,窒息得难受。虎子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会闹腾了,再也听不到别人喊他“傻蛋”了……我木木地呆在那儿,缓不过劲儿。我不敢看大嫂,怕。“虎子会喊妈妈了”,大嫂的声调有点拔高。我却再也忍不住,转过身,指缝间淌下来的全是虎子那无邪的笑……
之后,我要离开家乡调往异地。临走前,和已蹿得比我还高的儿子去向大嫂告别。她捧了一捧刚烤好的红薯,把车前筐塞得满满的;又把没有烤上炉的半编织袋新刨的红薯夹在了我的车后座上,并找来绳子牢牢捆绑结实。说离得远以后就吃不着了,再说城里现在都兴电烤炉,没咱这炉火烤得好吃。我打趣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还是跟我进城烤红薯吧,吃不上你的烤红薯,我和儿子可咋活?”她笑着长叹:“不啦,守家在地的,心里舒坦。”虽然后来回去得少,可每次一回去就会抽空去看她。眼瞅着她的身子骨一次比一次差,身边又没有一个能照顾她的人,不免对她将来的晚年生活有些担忧。辗转,想起对门老王:刚办理了退休手续,老伴于几年前去世,儿女现在都已各自成家,两人岁数又差不离,且没负担。老王曾向多人透露有意再续个老伴儿,于是便托人把信儿捎给了大嫂,没有回音,我也没再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