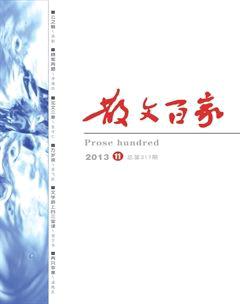祖宅
徐祯霞
祖宅在下梁。
我能记事的时候,下梁不叫镇,叫公社。祖宅就在下梁公社王坪三队,这是当时的行政建制。在外人眼里,他们不这样称呼,他们将王坪三队称作是“徐家大院”。说起“徐家大院”,很多人是知道的;但说起下梁公社王坪三队,知道的人却甚少。
在过去的年月里,祖宅一直都是老家的标志性建筑。在我的童年,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与别的地方别的村庄都不相同。但是究竟是哪儿不同,我却又说不出具体的缘由。
祖宅坐东朝西,背靠一座高大的青山;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土地,足有六十余亩,绵延向两边铺开;土地前面是一条长长的河流;河流紧挨着的是一条公路,一切都是那么的有序,层次井然。祖宅正落在村庄的中央,视线非常开阔。这个地方,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处绝美的住所,想必我的先辈在建房子之初,是找了风水先生看过的。
祖宅究竟有多大,现在我已说不清,只记得有狮子门楼,有堂屋,有厅屋,有南北厢房,有正房;自外至内,进身很长。
我出生的时候,那所宅子已经不能完全地属于我们家了,因为,在我出生之前,我们的村子经历了很大的变革,当然最主要的是针对我家的。
在这里,我向大家交待一下我们的身份,我家是地主,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这样的一所大宅子,所以,在土地改革这场土地革命运动中,我们家自始至终是这场运动的主角,分田、分地都与我们一一有关。
于是,祖宅被分割了,有我们曾经的佃户,也有外来的难民。在这些外来人口中,有从凤凰镇上来的,也有自西川下来的。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地域来的人,他们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而此后,他们便成了与我们共生共栖的乡亲。记得,在这所房子里居住的,有好几家都是五保户,也有我们的佃农,以及我们家里曾经的佣工。
在这场运动中,老徐家的人每户只分到了一间房子,其余的全都腾了出来,供村里旁的人居住。我们家也不例外,只分得了一间偏房。听母亲说,当时,她才嫁到父亲家不久,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兄妹三人,于是,一间房子只得隔成几间用。
祖宅变得七零八落了,但是祖宅的大气和隽永依旧还在。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爱去天井院子里玩。那时,天井院子里住着两户徐姓人,一家是我二房的堂哥,一家是我三房的堂哥。二房的堂哥我没有见过,据说在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二嫂倒是一个贤德之人,谦和恬静,与母亲交好,她个子不大,裹着一双小脚,走路有点慢,且身子一扭一扭的,是一个典型的旧社会的妇女。三嫂比二嫂小许多,也幸运许多。在这里所说的幸运是她没有被裹小脚,而且可以大声地随意地讲话。显然,她的精神没有被禁锢,她是一个身体和心灵都很自由的人。最最主要的是,她有一位勤劳憨厚的丈夫,这是她幸福的根源。
两位嫂嫂待我都很亲,每次去了,她们总是会尽可能地给我找一点吃的,有时甚至是一粒花生豆。当然,这也是我爱去天井院子里玩的理由之一。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对于天井院子的喜爱,这种喜爱发自骨子里。我喜欢天井院子那粗粗的廊柱,在我幼年的时候,我就常常喜欢伸出双手去抱住它,虽然我一直都抱不住它,从一小半到一半再到一大半,但最终也没能将它全部的抱住。
天井院子是祖宅的主体,它由四间正房、南北厢房和厅屋组成,正房居住着四房人家——三嫂二嫂,还有两个五保户,这两个五保户就夹在我们和三嫂二嫂的中间。而我们要去天井院子要经过一个长长的陇道,那儿还有一道门,当然,门在那个年代形同虚设,并没有实际的作用。
祖宅最精致的地方,便是正房。它有高高的廊檐,有粗粗的圆木柱子,有镂空雕花的门窗,有阔大的天井院子。它所有的房子都是用大青砖砌成的,那些青砖质地细腻,方方正正,大小一致,都是二尺长一尺宽,所以砌出来的墙面很是大气美观。从正房下到天井院子有两个长条形的石阶,这些石阶都是由一块整的石头雕成,上面能明显地看到雕刻的斜纹,起防滑的作用。天井院子边上都有排水沟,也都是由宽大的石条镶砌而成,齐整美观。两边是两溜厢房,厢房比正房的位置低。从正房下到厢房的地方也依旧有两列石阶,边上也依旧是由宽石条砌就阶檐。这些整的石条总会带给我一些奇怪的想像,让我想像到祖宅里面的人是否也是像电影或者是电视里的人那样生活。
天井院子通向外边的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我想这是防下雨湿脚或者是脚上带泥。两边是用鹅卵石铺就的几何图案,有圆形的,有椭圆形的,有三角形的,美观有序而不零乱。在我爱幻想的脑子里,天井院子应该是供这所宅子里的人玩乐的地方——男人们在这里喝茶、打牌,女人们在这里聊天、带孩子,甚至可以在这做针线活。现在,这个院子里总是人声鼎沸,在以前,这儿肯定也不会寂寞。
厅屋前面有一个大大的回廊,足有一间大房子的面积那么大,它被后来居住的人用来堆放杂物和棺材,也被人们隔成灶房。回廊外面是一个石头门槛,约有两尺高,刚好供人可以自由地出进。在以前,这是有门的,只是后来,居住的人多了,门反而有些碍事,就被人给卸掉了。
厅屋外面还有两溜房子,一直向前延伸到门楼跟前。中间是一个非常大的庭院,向阳开阔,平平如席。门楼上有很大的石头狮子,有石头的门凳,有石头的门槛,有朱漆的大门。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朱漆的大门被人卸了,石头狮子也被人砸了,唯一留存的是两个石头门凳和一个石头门槛。及至后来,这些也被村里的人挖走用来砌成猪圈或者是阶檐了。
于是,祖宅一天一天地变得面目全非。它被众多居住的人改造,扩建,因为在多数人眼里,生存是一件最实际的事。而居住在这座宅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主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可厚非。
祖宅在村民的改造下慢慢地与整个村庄开始融合并接轨了。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光变迁中,唯一可以留下岁月印记的是那座四合院,是它还在记录着一个村庄的历史和文化。
据说,我的祖籍在安徽,由于连年水涝,土地和房屋皆被摧毁,无以生存,我的祖上就逃荒来到了柞水;在柞水流浪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处所,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居住,就在此开垦荒田,筑屋修路,定居了下来。没承料想,这竟是一个富饶之地,庄稼丰收,人畜兴旺,几多年的光景,竟成了一户富庶之人。于是,他们大兴土木,建下了这样一座宅子。及至后来,一母生兄弟八人,儿又生子,子又生孙。族内竟出了五个大学生。人丁兴旺,财源广进,成了当地耕读传家富庶一方的大户,“徐家大院”便因此而得名。
当时,族中读书人极多,很多人都是在三四百里外的西安读书。那时,没有盘山公路,也没有高速公路,走的是现今旅游景区秦楚古道。据说,走一趟西安需要三天。秦岭山高林密,野兽众多,一个人是断然不敢走的,需要两到三人同行方敢上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族人也仍在坚持读书。这在我来说,一直是一件引以为荣的事。
我的爷爷是个私塾先生,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他们都得益于祖上的教导。我也以生在书香门第为荣,虽然彼时我家族中的很多人都已不再,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在我身上得以传承。
大哥的婚礼是在祖宅中进行的,由于我们成分不好,大哥晚婚,结婚时年已27岁。在当时,早已列入大龄之列。因此,大哥的婚事是我们最大的喜事,母亲请了村里的队长来为大哥主持婚礼。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大哥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大嫂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短袖。在祖宅正屋的廊檐下面摆放一张条桌,大哥大嫂及主婚人站在台上,村里的乡亲们全都坐在或者蹲在天井院子里。婚礼很简单,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也算庄重,这是祖宅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
在童年的村庄里,祖宅自始至终是整个村子的核心场所。村里开个大小会,村长一声吆喝,村人们就集合在老宅里。雨天,村人们也会蹲在老宅里,侃个大山,唱个小曲,拉个二胡,寂寞的雨天便变得精彩纷呈。祖宅,于我,印象是熟悉而深刻的;于村人,也一样是熟悉而深刻的。因为它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村里的标志性建筑。
终有一天,我离开了祖宅;终有一天,我与祖宅再也不能朝夕相见。祖宅离我便一天一天地远了,但是祖宅的记忆却无论如何无法抹去。时隔多年,那点点滴滴、那纷繁杂乱的过往、那儿时的欢娱、那发生在祖宅里太多太多的悲与喜,它们无法与我剥离,它们无法与我切割,它们已经成为我记忆深处最无法忘却的念想。
假日或者年节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心里惦记的依然是祖宅,我会独自一人去看看祖宅,看看我留在那里的童年和青年岁月。
祖宅由于没有得到合理而妥善的保护,慢慢地衰败,零落。它真正的零落是自堂家的二嫂过世之后。1980年代末,村里兴起了明三暗六的住房,很多人家都弃了旧房,盖起了这样的房子——白墙,假二层的暗楼,醒目高大且洋气。相较以前的老宅,会时尚且赏心悦目。我的堂侄子们便弃了老宅,搬进了新建的房子。于是,祖宅中的最中间的正房便荒废了起来。后来,很多的人家也搬离了祖宅。祖宅愈发显得凋落、颓败,那些青砖砌就的墙已显斑驳,那些镂空雕花的门窗已经严重破残。再走进祖宅,尽是衰败与凄凉。满院的荒草,及至膝深。屋上的瓦松长得老高,肥硕而茂盛。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天井院子里拔一拔那些疯长的荒草,让天井院子石板路和周边的鹅卵石图纹依然显露出来,然后靠着那圆木廊柱静静地发呆。在发呆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假如祖宅能够保留,该有多好,这应该是一个古建筑的遗迹,或者是一种文化的滞留。而我也仅只能是想想而已,因为在这片土地,除了记忆,我已一无所有。我是女儿,嫁出去的人,对于这儿,我不再有任何的话语权和支配权,我只有徒留伤感与惋惜。只是看着祖宅一天一天地衰败,我竟然有说不出的心痛。因为,它除了是一种文化,除了是一种古建筑遗迹,它更是我的根。
我最怕见到的事是祖宅的倒塌,那于祖宅,将是毁灭性的,意味着这一所古老的宅子自此将不复存在。但这一天还是来了,夏天,我回了故乡,又来看望了祖宅,祖宅北面的厢房已经坍塌,房顶上的瓦砾与泥土还有那些椽木檩料也已经掉落,在天井院子里铺下了一大片,满目凋落与残败,尽显凄凉与萧瑟。祖宅的一半已经成为废墟,再也无法作为房子的形象完好存留。听说,不久这儿将搞开发,祖宅必将被夷为一片平地,取代祖宅的将是一片别墅群。此后,祖宅只能成为记忆!
祖宅将去,我写下此文,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