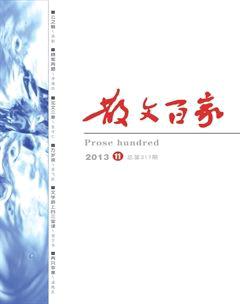大山深处的织女
聂昱冰
在太行山的深处,有一座千年古镇,名字叫王碯。它距离最近的城市邢台,也有一百多公里。这个小村庄位于海拔六百多米的半山腰,站在村口,把头仰成近180°的角,能看到云雾遮挡的山顶上那座被村人世代供奉的奶奶庙。在村子里,沿着弯曲而狭窄的小路朝前走,几乎每一条小路的尽头都是悬崖。
这里的山层层叠叠,无边无沿,一眼望去,你会觉得即使肋生双翅,也飞不出这群山。这里的日落让人荡气回肠,日向西堕,山势巍峨,一轮浑圆的、已经几万岁的、熊熊燃烧着的太阳,与已经几万岁的、嶙峋而幽暗的山,又完成了一次生命的交错。这里的夜晚悬挂着满天星斗,南极、北斗还有那一组组只在教科书上见过的星图,清晰地闪耀着,纯净明亮。
这里的男人,用了几百年光阴,把一座座山开垦成了梯田,然后又年复一年地在梯田上劳作;而这里的女人,则日复日、年复年地守着一个家和一台织布机。
我是在这个小村庄中,生平第一次见到了“还活着”的老式织布机——因为村子里的织布机仍旧都在吱吱呀呀地工作着,那声音单调却又饱含韵律,仿佛一直在讲述一个古老的传说。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一幅原本存在于传说中的画面,一段已然随历史远去的音乐,此刻,却明明白白呈现在了我眼前、响彻在我耳畔。
这是一个标准的农家小院,一排正房,两侧厢房,正房对面是两间低矮的小屋。小屋门口种着一棵苹果树——按照这里的风俗,家家院中都要种一棵苹果树,寓意平平安安。小院打扫得纤尘不染,夏日上午的阳光照在已有二三百年历史的石头墙壁上,留下斑驳的光影。在光影的正中心,是一扇已经变成了乌黑色的木头窗棂。青色的石、绿色的树、乌黑的年轮、透明的阳光,在这一刻聚合在了一起,让小院刹那间拥有了一种远古神殿般的深邃。
可在院子角落里,却有一个用碎砖头垒砌的小花池,花池里种满了从山上挖来的无名野花。一杆杆嫩绿的枝梢上,盛开着一朵朵大红大黄的花。厢房门旁,堆叠着一小片杂物——坏了的椅子、生锈的农具、残缺的木梯,它们上面都覆着厚厚的灰尘。
这简陋的花池、颜色俗艳的花、不知聚集了多少年的杂物,好像破坏了小院的沧桑之美。但认真想一想,却又觉得,这些才是小院真正的生机和灵魂,因为它们让一切变得真实了。如果没有它们,这院子只是一所房子;有了它们,院子才有了故事。
而我们,恰是一群浪迹天涯、寻找故事的人。
织布机摆在阳面的屋子里,一块浅色的花布窗帘挡住了刺眼的阳光,窗帘上的花色深浅不一,所以投到屋子里的光线也就浓淡不一。时而有风拂过,光线随之变幻,再看屋中的一切,都仿佛隔了一层摇曳的水波。
织布机的机身高度超过一米八十,长度超过两米,宽度也有一米多,全部由整根树干组合而成。一根根碗口粗的原木,剥净树皮,打磨光滑,交错纵横穿插在一起,连接处都是榫卯契合。因为使用时间久了,有些凹槽的边缘处已经有了裂痕。
“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老东西,有二百多年了”,主人道。
对这个年龄,我深信不疑。正是因为年代久远,这些木头的表面都已摩挲得光可鉴人;有些地方,还因为负力太久变得弯曲,就像老人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得粗大的手指关节。
这台织布机与这个家族相伴了二百多年,它一定记住了这二百年里家族中每一位女性的双手和容颜。现在,它的主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
此刻,这位年轻的妇人就端坐在织布机前,一边织布,一边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从始至终,所有对话都没有影响到她织布的节奏和速度,她的目光也一直停留在眼前的棉线和布匹上。
妇人恰好坐在了窗前的一片阴影里,头发挽成了那种最简单的发髻,上面别着一个鲜艳的塑料发夹,留着齐眉的刘海,穿着一条黑绸和碎花布拼接的连衣裙。她的发髻、发夹、裙子,本都是街头最常见的式样,包括她的容颜,都是一个最普通的乡间农妇,可现在,却因为这台织布机,她变得非常非常不同了。
妇人的双脚控制着踏板,双手交替操作着梭子和那根推动整个织布机工作的巨大横梁。所以她必须端坐,双膝摆放端正,腰背和脖颈都挺得笔直,双肩自然下沉,双臂每一下伸出、收回都沉稳有力。但手指又必须轻柔灵活,才能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并且保持匀速循环。这样的体态,让她自然而然就拥有了一种端庄娴雅的气度。
她的面容沉静如水,安然淡定的目光始终胶着在眼前那方寸之间。她右手边放着一盆清水,水中浸着六个枣木制成的梭子:每个梭子都是一尺多长,比手掌略宽,枣核形状。梭子腹内装着彩线——这些线已经在水中浸泡了一夜,被水浸透的棉线织出布来更密实,妇人这样解说道。
梭子的外壁打磨得光滑如镜,六个梭子就依次在她眼前这片方寸天地之间来回穿梭——从右向左滑过白色的纬线丛林,拉一下横梁,“哐当”一声,再由左向右滑回来,再拉一下横梁,又是一声“哐当”。
几个来回,几下声响,一寸花色鲜艳的布匹就织了出来。伴随着她的动作和声音,织布机另一端那个巨大的缠绕着白色棉线的卷轴一点点变细,她脚边堆积的彩色布匹一点点叠高。从清晨到日落,从少年到白头,一代又一代,山里的女人,就这样把光阴编织成了生活。
我站在织布机的另一端,久久望着她。在织布机的中央,几百根白色棉线高高挑起,分成三层,每一根细线都穿过不同的针孔悬挂在三根交错着的横杆上,于是我和她之间就仿佛有了一层半透明的屏障,只能透过白线中间的缝隙,看她张弛有序的动作和专注的神情。白色的光影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边界,我再一次被带入了历史的长河。
几千年来,古老中国的土地上,有过无数台织布机;每一台织布机前,都有过这样一个普通但却坚毅的妇人。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子的母亲也有过这样一张织布机,她为了训导儿子,用剪刀剪断了我眼前这几百根细细的白线,然后再一一接起。
还是这些普通但却坚毅的妇人,就这么年复一年纺着,织着,把地里的棉花纺成线,把线织成布,再用这些布换回一家老小的被褥衣裳、柴米油盐,让家中有了温暖、色彩和滋味。所以在古代神话中,那些让人心动的仙女一定都是特别善于纺织的——织女,七仙女……因为只有家中有一个会织布的女人,这个家才算是有了家的模样。
还是这些妇人,她们穿着母亲织的布衣长大,到了婆家后,依旧守着织布机,织出一家大小的衣着用度, 织出儿子的聘礼、女儿的嫁妆。
我们借宿在另一户农家,家境较为贫寒,女主人才五十来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褐色的脸庞上皱纹很深,花白的头发已经稀疏了。她丈夫早逝,自己身体有病,女儿很早就外出打工,挣钱养家、供弟弟上学,和我们交谈的时候,她反复提到这件事,对女儿的愧疚溢于言表。她也在织布,她说这些布一匹都不卖,全都留给女儿作嫁妆。
深山中的清晨,最早醒来的一定是鸟儿,可几乎就在我听到第一声鸟鸣的同时,隔壁房间中也传出了织布机那韵律鲜明的声响:“哐当,哐当”。
我走到隔壁,女主人果然已经坐在了织布机前。依旧是那件已经很陈旧的粗布上衣,依旧是那张布满深深皱纹的褐色脸庞,依旧是那一头凌乱的灰白头发,可此刻她整个人也同样充满了安然和端庄。
浆洗过的白线绷得紧紧的,密密悬挂在她眼前。几个梭子装着彩线在她的指尖跳跃穿梭,每一个来回,世间就又多了一寸花色鲜艳的布匹。
我捧起堆叠在她腿边的布,花色美丽,纹理细密,这是山里女人最炙热的梦想——要织出最好、最美的布,给女儿作嫁妆!让女儿风风光光地出嫁,让婆家所有人都知道,她有一位心灵手巧的母亲,所以,她一定也是一个最贤惠能干的新娘。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山里的女人们织布是没有固定花样的。布的花色,全凭她们在织布的过程中用眼睛看,然后凭着自己对美的感悟去选择下一种颜色。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从来没有织出过两匹完全相同的布。每一匹布上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这些织布的女人:虽然外表都一样普通,可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
而这些女人也和她们织出的布一样,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走出大山、登上大雅之堂,但却实实在在地守护着太行深处的男人、孩子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