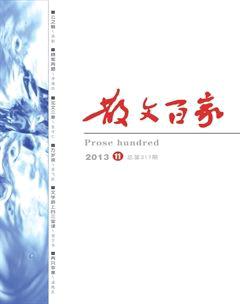怒放的康巴诺尔
胡学文
七月。
北方。高原。坝上。康保。
我来了。
其实应该说我又来了。
我来过多次,康巴诺尔于我并不陌生,但每次的感受都不尽相同。康巴诺尔如同塞外的四季轮回,有着多姿多彩的美。
第一次是二十多年前。
康巴诺尔在张家口的西北,是沽源近邻,直线距离不超一百公里。时间穿越回二十年前,那时到近邻做客并不容易。要么先到张北,要么先到太仆寺旗,情形颇像男有情女有意就是缺少牵线搭桥的,总有些波折。我须清早从工作的乡镇出发,差不多午后到达。康巴诺尔是想象中的样子,至少距想象很近。或许是见惯的风景,或许是听惯的乡音,亲近之余又略感失望。没有未知,没有神秘,像那些朴实羞涩的村姑,面纱不是掀开一角,而是根本没有。但返回沽源的途中,惊喜不期而至。我没见过那么大的雪,不像鹅毛,更像鹅扇。客车如蜗牛,司机和乘客多有抱怨。我像不小心偷得了姑娘的芳心,担心别人发现,又担心别人没有发现,躲闪的眼神浸着贪婪。我在目视中进入那个世界——没有任何杂质的世界。我就是一片雪,在茫茫天宇飞舞。
或许是这个原因,每次到康巴诺尔,我都期待着不期而遇,期待着预想外的收获,似乎没有落空的时候。
康巴诺尔蒙语的意思是美丽的湖泊,康保取其谐音,我很早就知道,并且一直以为是。这次到康保,方得知县名出自《尚书·康浩》“用康保名”,取富足安宁之意。康保的来历,竟然如此久远。然而,我更喜欢美丽的湖泊。没有理由,就是喜欢。当然,我可以说出很多条,但我不说。为什么要说呢?站在康巴诺尔大地,我宁愿任性,宁愿放肆,宁愿怒放。
因为,康巴诺尔就是怒放的花朵。
最大的惊喜是康巴诺尔湖。美丽的湖泊,不是空穴来风,浪得虚名。同行的诗人冯印涛说,藏语也解释得通。二十多年前的初遇,康巴诺尔湖水域丰阔,后日渐瘦小,像多病的小姑娘。我曾担心,康巴诺尔湖会不会从草原上消逝,像世界上许多湖泊那样,最终只作为名字和回忆的存在。但眼前的康巴诺尔湖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比我上次看到的丰腴了许多,湖水之洁净更是完全超出想象。
康巴诺尔湖是逆着时光的奇葩。
见证者并不只是我,还有它们,更重要的是它们——栖息或迁徙于康巴诺尔的鸟类。良禽择木而栖,美丽的康巴诺尔,吸引大量鸟类在此繁衍栖息。康巴诺尔湿地已发现的鸟类有一百四十多种,如鸿雁、乌雕、金雕、黑鹳、大鸨、遗鸥等。遗鸥数量最多,有三千多只。遗鸥也在日渐消逝,全世界仅存一万两千多只。康巴诺尔湿地的遗鸥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一。遗鸥会不会像康巴诺尔湖,逆着时光行走?或许,这正是它栖息在此的缘由。
天空蓝得像康巴诺尔湖水,康巴诺尔湖水蓝得像天空,水天一色,天水共景。云朵在天空游移,也在康巴诺尔湖漂移。在这天然的巨幅水彩画中,美丽的遗鸥在嬉戏。遗鸥是中型水禽,体长约四十厘米,嘴巴和双足是鲜艳的红色,头部是纯黑色,飞翔时翅膀尖端也呈黑色,间有白色斑纹。遗鸥的相貌像极了喜剧演员。嬉戏是遗鸥的生活,也是这些精灵对康巴诺尔湖的回馈。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重温千年前苏轼的《浣溪纱》,感触良多。遗鸥或许会为时光可逆佐证。
但愿。
康巴诺尔没有漫漫长夜,因为每个夜晚都有二人台演出。很多人分不清二人台与二人转,以为二人台和二人转是同胞姐妹。其实,区别很大,虽然二者均生于民间、长于山野。二人台是戏曲,是元曲的遗风流韵。剧情往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大俗又大雅。“康保二人台”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自然因其光彩和迷人。
我当然喜欢二人台。喜欢曲调,更喜欢品咂它的味道。
二人台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小时候,每年冬天村里都有二人台演出。随便一片空地,搭起篷子——有时篷子也不搭——就是戏台。没有电,自然谈不上灯光。所谓的灯,是浸了煤油的棉球。暗夜中,冒着浓烟的火球被甩起来,如灿烂的玫瑰。火势渐弱,再往煤油桶里浸,猛又扬起,挤作一团的人受了惊吓,被侵占的舞台顿时扩大许多,观众不经意间成为演员。
每个夜晚看二人台,实在有些奢侈。可我不得不说,我喜欢这种奢侈,我享受这种奢侈。二人台的相貌和神情极其欢愉,但骨子里却是悲情的。这与它生长的地域和形成的历史不无关系。坝上苦寒贫瘠,风吹草低,却鲜见牛羊。因人烟稀少,清乾隆嘉庆年间,迁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上坝,秦腔、晋剧、道情、社火、秧歌也随着来到草原,与当地的蒙古长调、民歌、坐腔等艺术形式融会揉合,演变成集化妆、表演、说唱、歌舞为一体的二人台。
那个晚上,演出的二人台既有传统剧目《挂红灯》、《五哥放羊》,又有新编剧目《压糕面》。传统剧目,我童年时代就耳熟能详。听过多少遍,我自己都说不清了。如果可以,我更愿意听《拉骆驼》。我听过的二人台曲目中,《拉骆驼》无论曲调还是唱词都有着击穿人心的东西。看二人台也需要想象,在对过往和人生空白的想象和填补中,更能欣赏到它的精妙,心的荒漠处会有花草疯长。有二人台陪伴,时间过得很快。据说有人专程到康巴诺尔看二人台,有上瘾者,也有好奇的验证者。
大俗、大雅,欢欣、悲情,含蓄、奔放。油水不溶,二人台的奇巧奇妙就在于把对立完好统一,无须斧凿,浑然天成。不妨听听《双山梁》,羞答答的姑娘这样唱:
听说是哥哥你要来
我给哥做上一顿
羊肉稍稍面条条现炸油糕
猪肉大烩菜
……
哥哥你走来小妹妹不让你走
拉住你那胳膊腕腕
拽住你那小手手
一把推你炕里头
……
猪肉石是康巴诺尔又一朵奇葩,最具视觉冲击效果,是想象的盛宴。
康巴诺尔产石头,我第一次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不吃惊,但颇意外。印象中,石头属于山川河流,而不属于草原;就像鹰隼属于天空,而不是森林。如果说湖泊是草原的明珠,猪肉石算是草原的梦幻吧。唯有梦幻令人无尽想象。
康巴诺尔的石头,有玛瑙石、风凌石、集骨石、菊花石、戈壁玉、玉髓等。 猪肉石是枝头最耀眼的那一朵。
走进奇石一条街,我再次书生气地想,为什么叫奇石一条街呢?应称作梦幻一条街。在康保东坡肉石前驻足,毫不夸张地说,需要费很大劲儿抑制暗涌的口水。
既是盛宴,饕餮何妨?放肆品尝吧。五花肉,红烧肉皮,红烧猪肘,带皮红烧肉,烤猪耳,烧猪心,粉蒸猪头肉,熏猪蹄……自然的鬼斧神工加上人类的奇思妙想,材质虽然单一,盛宴却是活色生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东坡肉石”,据说与康保东坡肉石是姐妹石。不知台北东坡肉石产于何地,但我宁愿相信,定与梦幻有关。
石头的盛宴,梦幻的长廊。
我来了。
我又走了。
我没带走石头,但我带走了梦幻。
说到康巴诺尔,自然想到草原。卧龙图草原是康巴诺尔的豪放之花、野性之花,让人想到骏马与苍鹰。绿草如茵,可惜骏马不再奔驰。但在如洗的碧空,苍鹰依旧翱翔。
接近中午,阳光如瀑,几乎难以睁眼。就在眯眼之际,我瞥见了那个黑点。它不动,几乎是凝固的。我闭了会儿眼,想看得更清楚些。待目光撞碎阳光,它却不见了,似乎被瓦蓝的天空融化掉了。我相信自己没看错,少年的我与它常常是这样相遇的。它,只是一个点儿。我总是特别好奇,那么矫健的生灵,怎会在空中静止不动?离地面那么远,如何发现并精准捕捉猎物?儿时的我,常常躺在草地上凝望天空,看白云无穷变幻,自然也为了等待苍鹰。亲眼目睹苍鹰捕击猎物,平生只有一次。更多时候,它只是嵌在天空的一个点。
我再次睁大眼睛。仍然没有。它一定飞得更高了。没什么奇怪的,卧龙图草原属于它,它却不属于卧龙图草原。
在卧龙图草原与苍鹰相遇,或曰重逢,尽管如同昙花一现,刹那绚丽,瞬间沉寂,但是足够惊喜。多么想如少年时代,躺在草地上静静等待。曾几何时,消失成为平常。而苍鹰还在,应该开心的吧,而不是遗憾。
七月。
我告别了康巴诺尔。
我寻见了记忆,追回了时光。
——林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