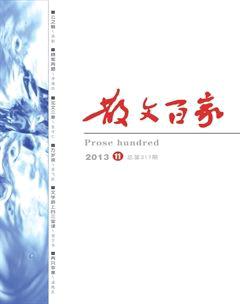走进平安庄
叶雪松
一
这是个看起来普通,地理位置却十分独特的村子。
说它普通,百十户人家,这样的村庄,在齐鲁大地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得到;说它地理位置独特,是因为地处高密、胶州、平度交界处,鸡鸣三县,俗称“三分子”。平安庄,是解放后改的名字。
有胶河和墨水河从村前庄后蜿蜒流过。胶河在村北,墨水河在村南,如两条舞动的绸带,将平安庄紧紧裹挟在中间。这两条河往东北方向流四十里,在一个叫咸水口子的地方汇合在一起,然后注入渤海的万顷碧波之中。
然而,看似宁静的平安庄实在不平安。
胶河古称胶水,这条河“河道迂曲委折,宛如羊肠,弯道大者似马蹄,小者呈牛轭,中下游河道迁徙无定,流域内洪涝频仍,今高密境东、北两隅之土地,多系此河冲洪沉积而成(引自《高密县水利志》)”。平安庄,在胶河的一个小小的弯道处,加之有赶来凑热闹的墨水河,经常把平安庄推向洪水的风口浪尖上。
临水而居,多是风水宝地。“河流拐弯处,必有贵人住”。1955年,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就诞生在这多灾多难的地方。水尚德,主智。谁能不说,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启迪了莫言的文学智慧呢?这两条流淌着平安庄村民喜和忧的河流,也承载着一代代村人的幻想和希望。
其实,早在莫言成名之前,民间的这一说法似乎被事实所应验。一是莫言旧居西侧相距3米的老宅,曾经出了一个国民党时期的海军中将;另一位大人物曾任武汉市副市长等职,旧居位于莫言旧居东18米处。莫言是胶河拐弯处出现的第三位“大人物”。
2014年初夏时节,我有幸赴高密参加“红高粱之约”第二届全国情感主题散文创作研讨会暨大赛颁奖会。在会务组的安排下,和畅的惠风里,我的双脚迈进了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原名叫三分子而今叫平安庄的小村子。和那些文学的朝圣者一样,我也想到这里感受一下莫言先生以其故乡大栏乡为原型用文字构建起的“高密东北乡”,浸染一下这方水土的灵润。
从县城坐车大约一小时,就到了大栏乡。走过石板桥,翻过两座小土坡,下了大巴,沿着一条狭长的土路一直往前走,一间红瓦黄墙的土房便出现在视野里,当地的友人说,这便是莫言曾经居住过的旧居。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农村——土墙、农舍,残旧的屋瓦、原始的村路,以及泥土弥散在空气中的芬芳,呼地一下,向我扑来。
如果不是院墙上挂着的刻有莫言旧居的挂匾的提醒,没有人会相信,这竟是一个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莫言出生生活过的地方。
我叩响了旧居院门那扇斑驳木门上锈迹斑斑的门环,然后,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在“吱吱呀呀”的响声里,走了进去。
二
院子里一小块不足一亩的开阔地。据说,以前院里的野草都长得跟人的小腿一样高。现在,众多来访者的到来,将小院的土地踩实了。
莫言故居,是几乎用泥墙砌成的五间联排农家平房,伸手可及屋檐。我在想,就是这个狭窄低矮的门,无数次出入莫言瘦削的身影。比较有趣的是,屋顶的左边是青瓦,占四分之一;屋顶的右边是红瓦,占四分之三。门是斑驳老式的木门,贴着一副褪了色的红底黑字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据说,管家有先人在光绪年间中过探花。莫言有今天,似乎吐纳先祖留下来的灵气。
村子里的人,包括莫言的亲朋,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当年做过临时工、打得一手好算盘、闲时常躺在棉花垛上眼望蓝天、后来又当上兵、只读过五年书的管谟业竟然成了响当当的大作家。谁也不知道,这个“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的乡下农民,写作是为了一天吃上三顿饺子、娶石匠的女儿为妻。这种理想,现在看来比较“低级”,在当时那个连过年都吃不上饺子的年代,却无疑已经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想象力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对自己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逆来顺受的青年农民,谁会像他这么狂妄呢?
一只紫穗槐条子编成的筐子,映入我的视野。
我的眼前,仿佛浮现起年幼的抹着鼻涕、身材瘦小的莫言抄起这只筐子一溜歪斜地蹿上了屋后的胶河大堤去挖一种叫“齐齐毛”的野菜充饥的情形。
老宅是1911年建成的,1966年进行了翻新,屋内早已无人居住。“这里承载着莫言太多的记忆。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结婚,生育。”淳朴操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的莫言的二哥管谟欣介绍说。1987年拍《红高粱》时,莫言的母亲还住在这老宅里。
虽说旧居有五间房,但都比较狭小,除了一块“莫言旧居”是新摆放在正门内的桌子上外,其余看似搬走后没打理过的痕迹,依然照旧:房间里的炕头还在,一台莫言结婚时买的老式收音机还在,积满灰尘但曾炊烟袅袅的灶台还在,莫言生活了33年的气场还在。
屋里有些昏暗。此时,从木格窗外射进的阳光正巧将炕上的一面筛子照得金黄。我坐在了东屋的土炕上,感叹不已。同行的当地友人告诉我,这面被透光木条窗格裁成黑白图案的土炕上,当年曾陆续降生包括最小的莫言在内的兄妹4人。
“1955年,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莫言曾如此来形容自己的出生。
是呀,莫言生在了土上,从此,就和家乡脚下的土地融合在一起。在莫言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间悲欢,都在一个叫做“高密东北乡”的地方展开。在莫言看来,高密东北乡是有声音有颜色的,颜色是红高粱的红,声音当然是茂腔。“我辍学比较早,生产队里就叫我放牛,经常在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唱两句茂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县茂腔剧团经常到乡下巡回演出。在场院里搭一个土台子,四乡老百姓都来了,那是一个隆重的节日。春节前后,农闲时,每个村里头都有自己的业余剧团,也会排演一些茂腔戏上演,几乎人人都会唱三句两句的。我想茂腔是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我们的道德教育、人生价值观、历史知识,都是从茂腔戏里学到的。”
高密当地有句民谣:“茂腔一唱,饼子贴到锅台上,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到指头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但也能看出当地人对茂腔的喜欢程度。莫言也是个茂腔迷,自己有亲身经验。他当兵两年后第一次回家,一出车站检票口,就听到车站门口小卖部放茂腔的带子,一下子热泪盈眶。至于她唱的什么,跟他没什么关系,一听那旋律,就感觉到过去的一切都回来了。
所以,莫言说:“我与农村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是土地与禾苗的关系。”莫言在一首名为《故乡忆旧》的打油诗中写下:“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想不快乐都不中。”在高密文学馆,进门处便悬有莫言的左手书:“高密东北乡,生我养我的地方,美丽的胶河滚滚流淌,遍野高粱,高密辉煌,黑色的土地承载万物,勤劳的人民淳朴善良,即便远隔千山万水,我也不能将你遗忘,只要我的生命不息,就会放歌为你歌唱。”
字里行间流淌着的那种对故乡的快乐追忆已跃然纸上。其实,谁的心中,又不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密东北乡”呢?尘土的印记,从莫言来到这个世界起,就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身上。
三
东北乡,亦称“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是指莫言笔下的一个乡镇,是莫言小说许多人物的成长地方与主要活动地域,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异曲同工。莫言是以其故乡大栏乡为原型用文字构建起的“高密东北乡”。
东北乡是莫言的文学地标。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东北乡一下子成为人们心目中向往的文学圣地。正因为莫言是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中不难找到故乡的影子。故乡的人和物事,被莫言信手拈来,都成了他笔下的描述对象。
在距离莫言旧居以东约10分钟车程处有一座青纱桥,位于高密市东北部胶河孙家口村村后。1938年3月15日,高密抗日游击队根据可靠情报,在此伏击了途经这里的一个鬼子车队,歼敌39人,击毙了在平型关大捷中漏网逃脱的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缴获大批战利品。该战役就被莫言写进了小说《红高粱》。我想,那些抗日的军民中,就有莫言笔下血性十足的“我爷爷我奶奶们”。
作为此役重要历史见证的青纱桥,成为之后张艺谋拍摄电影《红高粱》的主要拍摄地之一。一座桥,见证了“三颗星”走向世界舞台。
1988年,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金熊奖,导演张艺谋声名大震,演员巩俐走上国际影坛,作家莫言也一举成名。人们认识《红高粱家族》,更多的或许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的一部作品《红高粱》。影片中,巩俐所扮演的九儿从桥上跑过、拼命追赶心上人的片段,至今让人无比动容。而这座石板桥,如今依然横卧在大栏乡的一条小河沟上。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在莫言的天马行空里,高粱的辉煌和爱情的激荡,带给读者怎样的冲击?
2002年,已经蜚声国际文坛的莫言,其旧居就引来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探访。当时,高密方面给他安排了不错的酒店,但大江健三郎坚决要求到莫言的老屋,在土炕上睡了一晚。青纱桥伏击战时,大江健三郎才是吚呀学语的三岁郎。半个多世纪后,当他睡在莫言的土炕上倾听夜籁的时候,这个对战争颇为反感、写过原子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长篇小说《个人体验》的大作家,内心的思绪也一定是复杂的。在这个年近七十的老人耳畔,会不会也响起清脆的枪声?死在青纱桥下的那39名日军中,会不会就有他的父兄呢?遭受伏击前的这些士兵们,会不会也看到过淳朴的村民们抬着花轿娶媳妇的场面呢?
上世纪50—70年代曾经种过高粱的他,对于高粱的看法和很多高密人一致:生于涝碱地,旱点也能生长,生命力顽强,完全不像棉花、小麦那样娇贵,撒上种等着收就行。红高粱的这种特性,也培养了很多高密人坚韧、朴实、率真的性格。与那些生活在森林或山地、草原的居民相比,高粱地里长大的人,肯定不一样。对于红高粱有着无限向往的人,往往会对平安庄有太多的期待和想象。同行的当地友人说,这里没有大户人家,没有厚重、冗繁的传统民俗。民风淳朴,村民大多性格豪爽,为人低调,与红高粱表现出的气节,不谋而合。
我们下了大巴,街上很寂静,偶有几个村民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丝毫的惊奇。从他们的衣着和手里的农具,以及脸上平和的表情,我发现,他们并没因为村子里出个大作家而炫耀。我问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问他认不认识莫言。年轻人笑了笑:“认识呀,一个特别好的老头。”看着年轻人骑车离去的背影,品味着他幽默诙谐的话。我在想,在家乡人的心里,莫言,是他们心中的骄傲,更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没准,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和莫言光着屁股一起在胶河里抓鱼的小伙伴。
四
东北乡地理位置就是在高密的东北,河崖、胶河以北、大栏乡这一些地方。这个地方因为地势低洼,地下水极其丰富,往下打一两米就能出水,以前还经常涝。而且土地偏碱性,即便是现在也不能用地下水浇灌,浇三两次土地就会板结,很难调理过来。所以,耐碱抗旱的高粱自然就成了乡民们种植的首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是红高粱最辉煌、最多产的时候。而后,随着玉米等作物的改良,高粱因为口感太差,逐渐被淘汰了。
现在,因为有了莫言和他的《红高粱》,当地政府要下大力气打造“红高粱”文化品牌。我想,这个想法没错,应当大力提倡,不过,我认为,无论什么,都应适当有个度。
莫言笔下“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的东北乡是在上个世纪,当地政府不惜赔本也要种植万亩红高粱,是不是要把握个度?
我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针对高密将大规模种植高粱的消息,我打听到,万亩高粱地只是当地管委会负责人的个人想法,尚未经过任何的科学论证。
在我看来,莫言旧居泥墙外微风轻拂下的白杨树,故居外的乡村土路,旧居内每个布满灰尘的物件,以及莫言家种种的原始的东西,都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原汁原味的东西,就是地气。
如果,旧居被水泥钢筋建成的住房所取代,乡村的土路被柏油路所取代,那还是那个那座滋养他灵感仍像酵母一样在创作中发酵的乡村吗?
高密应该还是那个高密,东北乡应该还是那个东北乡。原始朴素的东西,就是大美。难怪高密市政府要拨款50万为莫言旧居修缮时,被莫言的老父亲婉言谢绝。看来,这个九十多岁高龄的乡村老人很有见地。
上车前,我站在新建的石桥远望胶河,突然,一个美丽的古朴的情形映入我的眼帘。远远的,一个身着红衣的年轻女子,正蹲在河边漂洗衣物。手中的棒槌一下下击在河边青石板上,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受到惊扰。那清洌的河水,远处碧绿的树林,以及女子映在河中的倒影,汇成了一幅宁静悠远的乡村图画。
真美!
还是给莫言留一个宁静的气场依旧的乡村吧!
——以高密茂腔为例
——于毛泽东旧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