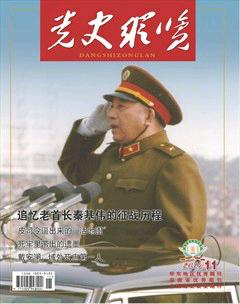宋玉凡的非凡经历
陈大斌


宋玉凡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基层干部,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符离农村。他虽官位低微,却经历过一些历史性事件。
宋玉凡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农家,“土改”中入党,合作化运动中被提拔为“脱产干部”。在实行“责任田”那段时间,曾任符离区委委员,但更多时间在该区王楼村任职,先是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担任划小了的王楼公社党委书记。
1961年春天,符离区开始实行“责任田”,大家都兴奋异常,全力推行。但“责任田”只实行了一年就奉命纠正,区委的干部们都想不通。3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中共符离区委书记的武念兹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改正“责任田”的决定。会场上气氛凝重,讨论时人人沉默不语。冷场好一会儿,只见宋玉凡站起来“开了头炮”。他一开口就让大伙儿大吃一惊:他提出,立马派人上北京向毛主席反映情况!
宋玉凡提出这样的建议,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日思夜想拿定的主意。他不紧不慢地向大伙儿说:改正“责任田”的命令是新省委下的。可他们新来乍到,怎么会急着干这件事?我猜想,这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又为啥要改正“责任田”呢?我看主要是有的领导人不了解下情。所以,咱们先不忙说怎么改正“责任田”,最当紧的是立马派人上北京,当面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实际情况。毛主席他老人家最讲实事求是,若是他了解“责任田”对发展生产的好处,知道老百姓这么喜欢“责任田”,就一定会让咱们继续干下去!
此言一出,马上就有人响应,要求区委即刻派人进京。可派谁去呢?有人说,主意是老宋出的,要去就老宋去。老宋说:“让我去我就去。咱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实行‘责任田后的变化,老百姓的心思,我都了解。见了毛主席我就仔细对他老人家拉拉。”
有人担心地问,要是毛主席不同意咱们的意见呢?宋玉凡说,那就据理力争。我也敢当面把咱们的意见仔细给他老人家汇报汇报。
这边大家伙儿说得热烈,那边武念兹则陷入了深思:这个办法行吗?进了北京就一定能见到毛主席吗?再说,真的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谁能保证他不紧张、激动?结果把应当报告的情况说个七零八落,那不就糟了吗?真要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申述意见,不如坐下来认认真真写封信,把咱们这里的实际情况、“责任田”的好处、群众的要求,都充分写出来。
武念兹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出来,大家纷纷表示这样更妥当。于是,武念兹决定,由他带头,区委全体委员自愿签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这就是日后惹下滔天大祸的符离区委全体同志上毛泽东“万言书”!
后来这封信遭到批判。在区委会议上,武念兹说,这封信是我提议写的,又由我主持几次修改写出来的。这个检讨应该我来做;上级要给纪律处分,也该处分我这个“首恶”分子,其他同志都是胁从者,按政策可以“不问”。他还没说完,宋玉凡就嚷起来!这事不能让书记一人顶缸!如若开初没有我出主意上北京见毛主席,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封信!要说“首恶”,我才是真正的“首恶”,要处分也应处分我。开除党籍,回家种地我都认了!可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一门心思要让老百姓吃上饱饭。这怎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不久后,省、地、县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来符离调查“万言书”的“出笼”经过。宋玉凡在接受调查时直截了当地说,“责任田”没有错!他还请求调查组批准王楼公社继续实行“责任田”。他说,让一个公社实行,错了也翻不了社会主义的天。调查组严厉批驳他的“谬论”。宋玉凡则针锋相对,说谬论不谬论也不能光凭你个人说,“责任田”里庄稼摆在那里,社员家里的余粮摆在那里呢。你们一天到晚高喊集体好,从五几年办合作社时就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让社员过吃面包喝牛奶的日子。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们去弄出一个靠集体生产让社员吃面包、喝牛奶的典型来,哪怕是一个小队也好啊!调查组气急败坏,说宋玉凡是个顽固分子,蛮不讲理,坚持错误,死不悔改。
1962年6月,邓子恢看了符离区委的“万言书”后,派张其瑞为组长的调查组来宿县农村调查“责任田”,王楼公社王楼大队是调查点之一。而宋玉凡当时正是王楼公社的党委书记。
张其瑞等人来到王楼公社做实地调查时,宋玉凡提供一切条件让调查组广泛接触社员干部,充分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同时敞开心胸向他们讲了实行“责任田”前后的切身感受。他说实行“责任田”不只是增产点粮食,更重要的是使农村集体经济中从合作化以来多年一直无法解决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张其瑞调查组在王楼看到的听到的,使他们对包产到户“责任田”有了正确的了解。调查结束后,他在《安徽省宿县王楼公社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中说,责任田有力地解决了集体农业发展中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评工记分、农活质量不高,公私争肥争劳力,社员集体生产中出勤不出力,不积极劳动生产等痼疾,有效地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生产发展。
中央农村工作部调查组在王楼公社的调查报告,已成为中国农业改革历史上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资料。这份报告所列事实及阐述的重要观点,可以说与宋玉凡在王楼公社的实践及思考有着直接关联。
以上这两个方面表现出宋玉凡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从实际出发,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作风,实在让人钦佩!
2002年春天,笔者在符离区王楼乡期间再次拜访了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
老人耳背,谈话要大声对着他耳朵喊。但他头脑清楚,说起合作化、公社化和“大跃进”那段经历,仍然是记忆清晰,激情满怀。
如今,宋玉凡在宿县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性事件中的表现,已引起党史、地方史研究者的重视,而最让乡亲们感念的“政绩”,还是他担任王楼村领导时实行的“阴阳田”。
所谓“阴阳田”,是在合作化过程中,在给社员划自留地时,千方百计给农民多留点耕地。宋玉凡说这是给老百姓留下一条保命的活路。王楼实行的也是集体经济,但老百姓自己耕种的“私地”不比集体耕地少多少。这种明公暗私的办法被称为“阴阳田”。它与全国各地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不相同,这是宋玉凡一手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土办法。
为了了解“阴阳田”,我与宋玉凡有一次长谈。正是这次谈话让我真正认识了宋玉凡。
我们的这次谈话就像是拉家常。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穷,保证人人吃饱饭就是件天大的事。不让一家人挨饿,这是每个当家人最起码的责任。成立了高级社之后,农户的土地牲口都归了“大堆”,几十户、上百户人家一起干活过日子。一个社的社长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你要带好这几十、几百户人家种好地,让人人吃饱肚子,这容易吗?后来王楼乡又办了高级合作社,一下子成立近千户的大社!好几个村庄,几千口子男女老少,就靠合作社养活了。当社长的肩上责任可就大了。当时人们忙着敲锣打鼓,呼喊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好像好日子就在眼前。可我打心眼儿里疑惑。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几亩地,牲口还是那几口牲口,地里还是种着小麦、杂粮,只说声合作化,地里就能多打粮食?那好日子就来了?
宋玉凡说,当时我就想,这么大的家业,这么多人的日子,管家的可得多个心眼,得留点后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几百上千户的人家留条后路。当时高级社章程规定可以给社员划“小园地”种蔬菜。我们这一带有些矮山浅沟,地面较广,耕地比较多。我就在自留地上做文章。上级规定每人一分自留地,我就偷偷地再加上半亩。当时有人说,种菜要那么多地干啥?我说,农民有谁会怕地多?不种菜不会种粮食?又有人说了,合作社生产发展了,还愁没有粮食?我听了这话吓了一大跳。一个当干部的,没有一点防灾的心,这还了得!我问他,你咋知道有了合作社就年年风调雨顺,季季丰收?若有了灾荒怎么办?几百口人,嘴连在一起有几丈长。那么大个窟窿,见天得多少吃物才填得满?多给社员一点地,让他们种点粮食,一旦遇上灾荒不至于挨饿!当时有些年轻人听了就笑话说老宋是小农的穷日子过惯了,脑子过死,目光太短。可我觉得这才是农家过日子的正道。
宋玉凡接着说,合作社头一年庄稼种得并不好,大伙都说,集体化优越,可我知道,我们农业社当年并没有比单干时多打粮食。看来社员光靠合作社这一头不行。1958年春天,我就来了个“憨大胆”,让社员各家各户自己刨荒地,自种自收全归自己。这年麦季又是歉收,我就再大点胆子,把没有种上的集体耕地划给每家一亩,规定每户只要给大队交100斤山芋干子,余下的出产全归自己。可是地刚分了不久,1958年9月就来了人民公社化。当时符离是一个大公社,王楼村只是一个大队。分了地的事,要不要向公社报告?一报告就得将地收回归公,大队几个干部经过一番密商之后,宋玉凡拍板决定:这事得隐瞒下来;分了的地也不能收回,收了粮食还是按事先的规定,每亩交给大队100斤山芋干子,余下的全归社员自己。
宋玉凡感叹道,干了一辈子农村工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几年。那叫什么日子啊!一声“大跃进”、公社化,农村工作、农家日子就全乱了套。到处“大兵团”作战,赛着吹牛皮,家门口的地都荒了,还吹“大丰收”。我真的不明白,地里没打下粮食,当干部的自己真的就一点不害怕吗?几百户几千户社员缺了粮食,那得出多大的事?“大跃进”开始后,我还是抱定老主意,让社员尽力多刨荒地,凡集体没种的地,不管生荒、熟荒,谁刨出地来就归谁,谁种出粮食归谁收。几年下来,王楼村家家都开了不少地,都存上了点粮食。1959年冬天大灾荒一起,邻村邻社邻队都病饿死了一些人,我们王楼大队就没饿死人。符离公社(后改为区)老书记武念兹让我拿出点粮食急救。我们拉了几车山芋干子送过去。
宋玉凡这一手自作主张的“土政策”,在关键时刻救了一方百姓性命,至今当地人都忘不了。
* * *
其实,宋玉凡能有这样一番作为,并不是他有多高的思想理论水平,更不是对后来的大灾荒有什么先知先觉的预见能力。他出身于农家,与广大农民心心相通,他从农民的朴素认识出发,怀疑“大呼隆”集体化能不能搞好生产,养活这么多社员。他遵照农家储粮备荒的古训,按照庄稼人过穷日子的常例,给社员们留下一条“后路”。坚持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实际出发,对农民的命运负责,这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最为可贵的品德!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