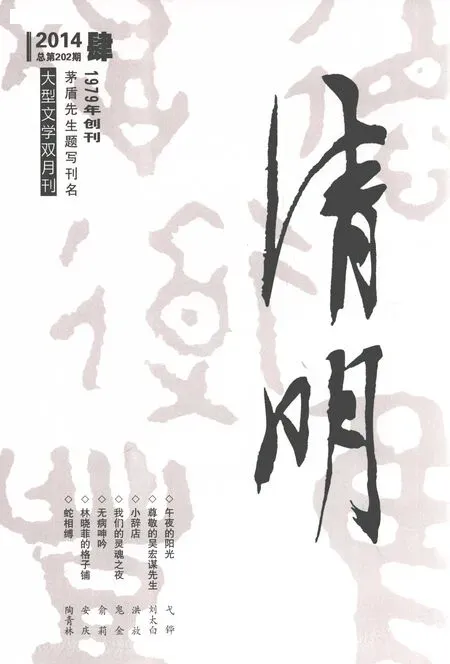外乡人
李成
外乡人
李成
两个安庆人
写下这个标题,我还有些踌躇,我不知道应该写作“两个安庆人”还是“一个安庆人”,因为那第二个安庆人我似乎所知不多。
这两个安庆人都是“下放学生”。这是我们那里对“下放知青”特有的称呼,即使他(她)早已过了当学生的年龄。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响应领袖号召,自愿或被迫从城市来到乡村插队接受再教育和锻炼,准备大有作为的一群人。但是,农村的艰辛岂是那么容易就能习惯得了的,他们来到农村没参加几天生产劳动便纷纷逃离,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做了代课教师,最不济的也当上了赤脚医生。
我认识的第一个安庆人,就是我们村小学的代课教师。他主要教什么课,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学校的一些“副”课——体育、音乐、劳动什么的,总是由他来上。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但我已经常去学校,因为我的父亲也是这所小学的一名教师。他一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那种没什么“正形”的,严重一点说就是玩世不恭。比如上课没有几分钟就跑回办公室来,不是一屁股坐到这个老师的办公桌上,就是斜靠到某位女同事对面的木椅上,还把脚架到桌上抖动,再不就是从别人的抽屉里翻出一枝香烟叼到自己的嘴上,大多时间都涎皮笑脸,嘻嘻哈哈说笑个不停;加上他长着尖尖的下巴,留着蓬乱的头发,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实在是难以叫人喜欢,但他却总能缠人,喜欢围着你打趣逗乐,让你哭笑不得。
我第一次和他直接接触是因为看上了他的一本白纸簿,那就是一本由他自己用白纸装订起来的厚厚的笔记本,但确实装订得好,非常整齐,我一看见就喜欢上了,非要找他要。我原以为他不会给我的,但他却慷慨地送给了我,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然而父亲知道了,却非要我还给他不可,我只得忍痛割爱,送到了他的面前,他对我眨眨眼,快活地咧开嘴巴笑了。我第一次觉得他的嘴巴真是大了点。
上了学,我对他有了一些敬畏之心。但到底他不是带我们的主课,我们接触倒也不多。他还是那么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时有促狭、滑稽之举,逗人一乐,自己也开心,有时甚至捉弄到学生头上。有一次上体育课,他迟迟不来,我以为不用再上了,就待在教室里看小人书;看了一会儿,却发现有许多同学已不在教室里,而站在了操场上,只见他——我的这位安庆老师一跳一跳从廊檐下走过来,手里竟然拎着一把老虎钳子。他站在我们面前,要迟到的同学自动站出来,我们都没有动。他就用老虎钳子夹住这几个同学,将他们一个个“拎”到操场中间站着,疼得他们直龇牙咧嘴。临到我,我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以为父亲跟他是同事,我又是从小跟他相熟的,他多少会给点面子,可是,他才不管这些呢,毫不留情地夹着我的耳朵也把我拎了出来。他喝斥了我们一顿,又带我们玩了一会儿,就回到办公室去了。
过了几天,我家的一头半大的猪得病死了,母亲舍不得扔,就用烟火将猪肉熏制了一遍,准备食用。父亲透露了这一消息,这位下放老师便自告奋勇要来我家帮忙,结果是父亲和他都喝得微醺,酒是我去供销社打来的红薯酒。我去的时候,他还向我做了个鬼脸,眨眨眼,快活地笑了。喝醉了的他显得十分可爱,像一团糯米糍粑歪倒在椅子上,脸颊通红通红。
但是,我没想到他还能唱戏。那些年过春节,大队总要排演一部“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什么的,这一年排的是《杜鹃山》。其中的一角温其九,大家都认为非我这位老师莫属。他是唯一的参加这次表演的教师。他竟一改往日拖拖拉拉的作风,每天准时到大队部排练;有时天下大雪,他仍踏雪前往。我们都是围观者,想跟他开开玩笑,他竟不跟我们多纠缠,认认真真地在参演的人当中做着动作,练习唱腔,有时还客串一下鼓手、琴师,一本正经,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他在戏台上,将表演的角色拿捏得十分准确,将一个猥琐而又狡黠的温其九扮演得惟妙惟肖,在各个村庄公演时,博得乡亲们阵阵喝彩;唱也唱得字正腔圆,清晰透亮,其风头甚至超过了“柯湘”一角,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顿时改观。事后有人猜测,他是在追求那个扮演柯湘的女演员,不知是否属实,因为此事没有下文。
后来,知青返城,但不知为什么,他仍然在我们那里滞留了一段时间。但毫无疑问,他是十分渴望能够早日回到他生长的故乡——安庆的。据说,无奈之下,他闹过一次上吊,但是很快被人发现,获得解救,他本就是有意这么做给人看的,最终当然是如愿以偿回了城。在此之前,我时或看见他于周末站在公路边拦车回家省亲。他家里有什么人,我从没听人说起过,所以一无所知。
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当年我这位老师还健在否,有时候想起来,倒是颇为挂念。他有一个不赖的名字,叫“漱石”,而且还能演戏,本来应该过得不错,却成了简直可以入《滑稽列传》式的人物。
另一位安庆下放学生也是老师,在另一个叫“余桥”的小学。我父亲后来也从本村小学调往那里,所以他们也是同事,我也得以认识。他那位漱石老师要年轻,长得也帅气多了,身体健壮,正如他名字中的那个“虹”字,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青年。每次我去父亲的学校——一般都是傍晚,总看见他跟其他的青年教师在操场上打篮球,一帮年轻人穿跨栏背心,在篮板下你争我抢,龙腾虎跃。他打完球回来,一边去打水,一边跟我打招呼。我们并没有多交谈,毕竟我比他小许多,虽然我内心里有交流的欲望。
他给我的印象是好像交际比较广泛,各个知青点的知青他都比较熟络,所以,我从他那里借到过一两本在知青当中流传的小说。而且,他还为我们家搞过一两千斤无烟煤。那时农村烧煤是比较少的,不容易买到,所以我一个夏天都有活儿可干了,那就是和煤球。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妹妹们在家吃过晚饭,当天黑定的时候,突然听到院里有轻轻的叩门声,问是谁,却传来父亲压低了的嗓音,我打开门,见父亲和这位叫“虹”的安庆老师及另外一人正急急地抬着一个什么物件,神秘兮兮地进了屋子;进来后把东西放好,父亲招呼他们喝茶、吃饭,但两位连凳子都没有坐,就匆匆告辞、消失在夜色当中。这情景,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比如地下党或特务接头。他们走后,父亲打开那有纸板包裹的物件,我才知道是台缝纫机,不消说,也是这位安庆老师给帮忙买的。为什么这么神秘,盖因当时正批判“发家致富”也。
还有一次,父亲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脚上穿的皮凉鞋,这在当时乡村亦是稀罕物儿,父亲便提出要买他的这双皮凉鞋,这位老师二话不说,就脱下来递给了我父亲,也收了两元钱;不知是因为父亲觉得穿这样的鞋子有点“奢侈”呢,还是以为掠人之美到底有些不妥,穿了几天又要还给人家,那年轻人仍二话没说,又将那两元钱还给了我父亲。所以父亲和我都对他颇有好感。
这两位安庆来的老师先后回到安庆后生活得怎样,都成家立业否,日子过得顺心否,均不得而知;当然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还会想起在我们那里度过的一段艰苦岁月。
如果哪一天,我们还能够见见面叙叙旧该多么有意思呀!
我们村里的上海人
事先既没有一点预兆,也没有任何传言,忽然有一天,村头的打谷场上来了一大簇人,有村里的干部,还有几位一看就知是来自外地而且是来自城里的陌生人,以及两大平板车行李,村里人都被惊动了,纷纷聚拢过来,这时大家才知道本村来了一家下放的上海人。
上海,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啊!时年六七岁的我似乎已经听说过这么个地名,但潜意识当中总觉得那是海外某个虚无飘渺的地方,这一家“下放学生”是不是真的就从广阔无际的大海上乘着轮船碾波冲浪,然后登岸才来到我们这个打谷场上呢?我想那是一定的。在我眼里,他们这一家真好似天外飞来的仙客。
但是,就是仙客飞到了我们这里,也要暂时受点委屈。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村子当中的一间公屋里;缺少家具,由村里人东凑一件、西凑一件勉强对付着用。好在这些仙客——一个个体体面面、干干净净的,非常清爽,但并不是娇客,没有蹙眉苦脸,而总是面带亲切、自然的微笑,也从没有抱怨,双方都获得了好感,这一家上海人就这么在我们村里落下户来。
过了好多天,我们才弄清这一家人的关系。这是一家三代六口,中间的一代中年男人姓潘,而老人是他的岳母、岳父(但这岳父却是老潘妻子的继父),此外就是他的妻子小英和一双儿女。这双儿女是姐弟俩,比我略大几岁。老潘中等身材,妻子跟他差不多高,都长得比较白净、秀气,那姐弟更是粉妆玉琢似的,看上去很让人羡慕。老潘的岳母个子不是很高,但一看就知精神很好,诸事都由她张罗,十分勤劳;而那个继岳父身体却是明显不行,很少出来走动,卧于躺椅的时候多。随后,我们当然也打听到他们一家遭贬谪下放的原因,似乎是——老潘岳母的原配(也就是小英的亲爸爸)原是个资本家,已病逝多年了,然而仍牵累他们至此,也真是复杂,真是让人感叹。
天上掉下来这么一家,原本闭塞、偏僻的乡村吹进了一缕缕“海外”的气息,这让人觉得新奇、振奋。有事没事,我们这些孩子,甚至还有大人们都爱凑近他们,听他们讲上海大城市的故事。那时,已在村头为他们建了一溜三间土房,门场也还开敞,他们吃饭时就将小餐桌摆在场上,我们凑在一旁听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话,那真是很有意思的事。他们都是老上海了,但是青青和平平却告诉我们,不仅他们,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没有把上海的每一条街道都走到,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对周围几个村庄都那么熟悉,甚至县城有几条街巷也都说得上来,他们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竟然……上海,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城市呀!
生活安顿下来,他们——主要是老潘两口子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了。他们是怎么劳动的,我们小孩子当然不很清楚,但也感受到他们是积极的,因为村道上经常可看到老潘头戴草帽、赤着脚走过的身影;打谷场上,小英也披着头巾,跟村妇们在一起翻晒稻草。而且老潘还当过机械工人,懂得一些技术,村子里的脱谷机、抽水泵坏了,他还自告奋勇地前去修理,村里人对他们都有好印象。但偶尔也听到他们闹出的一些“笑话”,比如耨草的时候,他们不知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在禾田里进退两难;插秧的时候,一般是不能将左手肘搁在膝盖上的,那样妨碍速度,但他们不仅做不到,而且还带一个小马扎坐在田里。想来也真是难为了他们,他们在城里生活了半辈子,哪干过农活啊,就是我们这些后来上了学的学生娃,回乡劳动不也不习惯,不也很狼狈吗?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老潘的岳母,花甲之年了,不仅忙着家务,照顾病人,还开辟了一个菜园,天天带她的外孙女、外孙去灌园播种,甚至还帮村里看场。村子里的这家上海人日益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更亲近这家的姐弟俩。在我们眼里,他们真像是来自图画中的小孩,都长得那么漂亮,白嫩的面庞,大大的、灵动的眼睛,透出格外的聪明。正是他们,让我们听到村子以外的许多事儿。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俩尤其是平平,总要给我们讲上几段童话故事,什么狼外婆啦、小红帽啦、白雪公主啦、美人鱼啦,甚至还有一些鬼故事,有时让人欢喜得不行,有时又让人紧张得不得了。你听:“……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狼外婆把那个小女孩哄睡了后就要起来,拿起她的小手,放到嘴里,咯嘣咯嘣……”哎呀,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要走开,走回自己的家去,然而,最后的结果呢?最后的结果像一枚诱人的苹果,吸引着我挪不开步子,只得一动不动凑近他们听下去。
很快,我发现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他们竟有好多好多的连环画!这真是要叫我们欢呼雀跃了。平平每天拿出两三本连环画跟我们分享,大家把头簇拥在一起,甚至把光线都遮住了,中间那个手执图书的人便不耐烦地想叫众人分开来一些也做不到。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已经认识了几个字,但我有一个不好习惯,就是看什么书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声来。那一天,大家正在一起看《张思德》,我又边看边念:张思德到山中烧炭,发现炭窑里的火灭了……这一念又惹得众位小伙伴烦了,他们便要赶我走。我因为年龄最小,平时就有些与他们玩不到一起,这回备加感到冷落,就怏怏而去。但那些图书对于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我要自己拿到手里看几乎是不可能,我一时怅然,竟生出了去偷几本回来的念头,而且真的付诸实施了,还叫上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我们趁平平家没人时闯进去做了一回偷书贼,我还记得偷来的两本连环画当中有一本《巴黎公社》。两本书偷来,看了几天,或许是过了次瘾,或许到底是做贼心虚,也觉无聊没趣,便自己将此事张扬出去,等到平平来问,便主动缴还。这似乎是我唯一的一次偷书勾当,至今还不免觉得惭愧。
一年年过去,我们逐渐长大。老潘家里也有了一些变化,他那个岳父不幸去世(我不清楚是否就葬在我们那里),老潘夫妇搞了两年生产,又帮村里搞了一些副业。正是在这当中,他结识了一些朋友,便到本县另一个叫天林庄的公社当起了修配厂的工人,又还了他的本业,妻子随后也跟着去了,但他的岳母和一双儿女仍留在我们村上。平平也上了我们就读的那所小学,学校开会的时候,我甚至还跟他坐在一起听过会。但在课下,他更是我们的孩子王,他常常带着我们捞鱼,捕鸟,做游戏,和邻村孩子干仗;他也和我们一样,夜间在村子里奔跑,躲迷藏,在乡村那宽广的碧绿的田野间,他身上那城市孩子与生俱来的清水芙蓉一般的气息似乎减少了一半,另一半完全与我们融合在一起。
其后,平平的姐姐青青也随父母到那个修配厂就业,平平在我们村又耽搁了一两年,这时,社会形势已经大变,下放学生回城已是大势所趋,平平不久就返回了上海,据说后来参军到了部队。而1982年前后,我还在县城里偶然遇见过一回青青,见她还是那么苗条、清秀、不同凡俗,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几句后就分别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和她的父母。
但不知为什么,老潘的岳母,仍在我们村里住了好几年才返回上海。其时我已经上了大学,还问过她有关平平的近况。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能干的老太太即使一个人生活也将一切安排得一丝不苟;没有事的时候,她就戴上老花镜,坐在窗前那张老伴从前躺过的躺椅上,就着光线读一本老版的弹词。
村里有个右派
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他。他不是我们村庄里的人,但他偶尔进出我们村子,手里还提着一只铁桶,有时还握一只鬃毛刷子,脚步轻快,态度谦和,见了我这个小孩子也打招呼。人们告诉我,他是“右派”。我好像已经知道,所谓“地、富、反、坏、右”都是坏人,但我从他身上并没有看到坏人的迹象,相反,我还多少感受到知识分子特有的那么一种确实有点不同于农民的文化气息,说漂亮一点,就是觉得他似乎还有那么几分儒雅。
他是一个漆匠,走村串户应约给人家的家具刷漆,所以他的身上总带有一些油漆的斑点,与他相遇,也能从他那儿闻到一种很浓的油漆与烟草混合的气味。不知为何,我竟开始和他搭腔。有一次我问他最近来我们村子还多吗,他回答是不多,现在也没有多少人做家具。我从父母的闲谈中听到一两句关于他的议论,说他本来是一名教师,而且还当过城里某所学校的校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成了“右派”,离了婚一个人四处漂泊。我联想到他说的活计不多的话,竟无端地有些为他的生计发愁。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出现在村庄里,脚步仍是那么轻快,仍是满面笑容。那时,我已十一二岁,已经开始喜欢书喜欢文学了,我就试着与他探讨读书与写作的事。他告诉我:他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而且在《人民日报》上登过大半个版呢。我顿时惊讶起来,心里对他升起一种崇敬。我当然想追问文章的题目与内容,他的回答却较含糊,似乎不愿多谈,就快步从我身边走了。我一直在忖度他是否是因为文章而得祸的。
此后,我似乎有一两年都没有见过他,不知他消失到了哪里。其时已近七十年代的末期。但忽然有一天,他又出现在了我们村口,而且这一次他是长住下来了,就在村头租了一个单身青年的一间偏房,就此开始新的生活。其实,他的所谓生活非常简单,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坐在一张四方桌旁,或歪在挂着被油烟熏得乌黑的蚊帐的床头,抽着劣质香烟,喝泡在铁瓷缸里很浓的粗茶,朝痰盂里吐痰;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有时也目光炯炯,不知在想些什么(多少年后,我见到大作家聂绀弩的照片,觉得他们的形象、气质还真是有几分相像)。最初还偶尔见他锁上门,去给人家刷漆,后来简直就是“金盆洗手”,再也没有出去过一次。
但他似乎也从没为生计发愁,从来没跟我说过“没钱”呀、“苦”呀之类的话,甚至也不怨张怪李、指天骂地。他只喝他的茶,抽他的烟,吐他的痰,脸色焦黄,牙缝皆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如此度过。跟他的房东,偶尔还说两句轻松的玩笑话;有时看上去,他们的关系甚至像父子。
其时,政策已开始松动,社会上已有传言右派都要复职。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给他落实政策。他便开始左一封右一封地写申诉信,工工整整用毛笔抄好,装在信封里,亲自送到邮局或代销店的邮筒里。但是,似乎所有的申诉信都石沉大海,未起什么作用。
他因为住在村头,跟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来往。所食也很简单,我常见他只是在一个活动的缸灶上烧点稀饭、面条。只有我家对门念过几年私塾的二姑爷偶尔路过,会进来跟他谈谈闲天。他们可能谈的是历史、世道、人生命运什么的,可惜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过了两三年,附近一所小学的一位民办教师升到初中教英语,每天从学校来回都要经过他门口,这位老师也恰好是从城里削职回乡的,二人同病相怜,自是一拍即合,每次都要聚谈很久都不散,有时还互相送送。他们时而头凑在一切低声私语,时而又相视大笑,甚至笑声传得很远。不知底细的会觉得莫名其妙,当然他们也不会在乎,因为我们村里过去都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毫无疑问,他们共同的话题就是向上申诉,互相通报又听说谁谁复职了。
或许是因为等待得太久了,我都为他感到了绝望,但他似乎还是不急不火地坐在那里,每天喝喝茶,抽抽烟,抑或也扫扫地,擦擦桌子。就这样无所事事,让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忽然有一天,我看到他在一叠纸上抄出了一组诗歌,也是用工楷抄得很整齐、漂亮,一望即知是一首首七言律诗;我以为他是抄自《唐诗三百首》,一问他,才知不是,而是他自己作的。我颇为惊叹,我没有想到他还会作诗。我简单看了看他的诗,觉得还是蛮通顺,略有一点古雅(这是因为用了典故)之气,但意思大致能懂,诗的调子跟他的整个人有些相似:是灰色的。
一开头就似乎煞不了尾,他一首一首地作下去;而且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抄好后封进信封,说是要给报社投稿。他要我找来旧刊物,我给他一本《人民文学》,他将刊物的地址抄在信封上,然后叫我在上学途中将之投进信箱。我给他代投了好几次,可是连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他仍然是并不失望,继续投,仍然杳如黄鹤;好在那时的投稿是不需贴邮票的。
有一次,我实在好奇,就将他没有封口的投稿信打开,仔细读了读他的诗,觉得写的也没有多么了不起,无非是歌颂当代圣人,感叹自己命运乖舛,盼望雨露甘霖降临,同时多少也带一点激愤和呼吁公平的意思;我甚至以为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诗”,于是,我也模仿着写了几首七言八句,同样抄在稿纸上,署上自己的大名,也同样投寄给了《人民文学》。
结果当然和他的“作品”一样石沉大海。可是自此倒激起我读诗、“写”诗的热情,我把所有能找到的旧刊物上的新旧体诗歌都找来读了,逐渐地模仿那些作品,开始了写诗的探索。没想到这样的探索会一直持续三十余年。因此,要问我在诗歌写作方面遇到的第一位师傅是谁,那么我必须承认就是这个右派。
这以后,我更频繁地出入他的房间。他在晚年写诗越发勤快,甚至他的屋子里都挂满了诗幛——他每写完一首,都抄到纸条上,贴在墙上,然后津津有味地自我欣赏一番。
后来,他终于获得了平反。因为年龄关系,他也没有重返教育岗位,还住在我们村,只是按月领薪;他也不再住村头——那个青年房东已从山里找了个老婆,要结婚,他只得搬进村子中间一间幽深的小屋,其时我已经上了高中,我找到他新住处,但只去过两三回,交谈的也少了。我见他的墙壁上不仅贴着诗幛,而且还挂上了一幅带对联的中堂。
他更加深居简出,但仍有闲话传出,说他喜欢与村妇调笑,甚至动手动脚(大约是搂搂人家肩膀、拍拍人家后背什么的),或许是境遇到底比过去好了一点,他又有了所谓生人之趣,我听后也就一笑置之。
没过几年,他就消失了,不仅是从这个村子里,而且是从这个人世。
我听到这消息,不知为什么,心头反而微微感到有那么一点轻松。
过客
村庄不是城堡,它从来都是开放的;四面八方的人,只要不怀恶意,它都欢迎,起码是不反对的,都可以自由地在这里进进出出。
这些村庄里的过客,大多是做点小生意的,如卖零货的货郎,如贩鱼苗的“鱼花”子,其他还有卖鸡雏鸭雏的,收购鸡毛、鸭毛、牙膏皮、废铜烂铁的,推销树苗的……这些外乡人不知来自跟我们相隔多远的地方,操着略与我们不同的口音,说是为了赚点小钱,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是为我们服务。这些,我都记录在我的一篇拙作《一岁货声》里了,但是还有一些“过客”,我不曾记录却也是不应忘记的。
黄技术员,据说他老家在邻县怀宁,但工作单位却是我们县的农科所(农技站?)。他被派到我们村庄来指导农业生产,是因为我们那里生产落后,抑或是生产队里的头儿闹不团结呢,不得而知;反正,他来到了我们村庄(但好像没有住宿过,甚至没见他在谁家吃过派饭),有时是骑自行车,有时是步行到我们村子。他是身材比较高大而动作比较利索的那么一个人,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他长着一副北方人似的长方形脸庞,五官端庄,表情严肃而有时又不失温和。他经常出现在村巷里,和生产队的头儿一道分派和指挥农活,也一道出席社员大会,还是主持者或主要的讲话者。也就是说,他就像是代理队长。而且,在他手上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他的努力,我们村庄很快架了电线通了电,二是由单季稻改为双季稻。这两件都是比较烦难的事,但他指挥、安排得井井有条。我记得为了把水稻由单造改为两造,要找到合适的稻种,他带着头儿们从什么地方买来种子,并且就在我家屋后的一块空场地上挖了两个长方形的大坑,把稻种放进去进行实验(看是否适合本地种)。晚上,在坑边架起电灯照明,把浸在坑道里的稻种都铺盖上稻草、苫席,黄技术员和有经验的老农守在边上,经常要揭开稻草、席子察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到底是将良种育成了,我们村的亩产也上去了。但好像他那技术员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从此再也不见他在村里出现。后来,又听说他调回了本县。但村人对他颇为怀念,很长时间都念叨“黄技术员在的时候”。我母亲也说他是历年来下到村子里来工作的最好的干部,可惜至今村人只知其姓,不知其名,更不知他后来如何。
另有一些过客更是来去匆匆。比如有一个黄昏,村道上出现一个背着布囊,拿着雨伞的中年汉子,走到正在路边玩耍的我们中间,问是否可以找一个歇脚的地方,他要为村里做一点事。问做什么,答说可以除去白蚁。他认为我们村子里一定有白蚁侵害。还真是的,我就知道我们村庄有些人家的房梁屋椽都被白蚁蛀蚀了,以致屋子岌岌可危,我回家跟母亲说了,母亲说可以在我家落脚歇会儿。他就把行囊放在我家,而自己却又到村里了解情况,获得了左邻右舍的支持,并为他安排了住处。第二天,他到处探察,还真发现了大白蚁窝,掘开来,那么多白蚁聚集成堆,看了都让人不寒而栗,头皮发麻。除了这一窝白蚁,据这个外乡人说肯定还有。最后又找见了没有,而且给了这个人多少报酬,我没有听到下文,抑或时隔多年忘记了。但三十多年前,确实是有这么个人来到我们村庄办了这么一件好事。
像这样的不速之客还是有的,有的还可称得是“艺人”。曾经有一个说大鼓书的,也不知从哪里来到我们村子,自报家门,要为大伙儿说大鼓书,而正好我们村的会计对民间文艺颇为爱好,自然答应并予以接待。傍晚,吃过晚饭,这个艺人就在打谷场上支起鼓架,一声梆子响,便开始说唱起来,吸引全村老少都来围观,听他说起前朝往事:《薛仁贵征东》《樊梨花下山》等,声若洪钟而语音悠扬,可惜还是有点外乡口音让我听不太明白,但是,我由此触摸到千百年来在乡里一脉相传的一种文化,所以,我后来读到陆游的绝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感到特别亲切,犹如亲临其境。
在村子里,我偶或还能见到算命“先生”,当然都是盲人,由一个半大的男孩牵着,他自己也拿一根竹竿,在地上点点戳戳,摸索着走来。村里有人想问问前程后世,就会迎上去,把他请到树阴下,报上生辰八字,他就捏着手指,不停掐算起来,口里念念有辞,说的都是“天干”“地支”的名词,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至于所言有多少道理、有多少可信,那只有天知道了,我母亲也不无诙谐地说:“掐掐八字,养养瞎子嘛。”
那时还不时有一些修补器具的过客经过村庄。如补锅的、磨剪子、铲刀的、补伞的,他们挑一个小担来到村口,一声吆喝,即有村民拎着破锅破伞出来找他们修理。据说,旧社会还有锔碗的,到我生长的年代早已不见。现在的乡村估计连补锅、补伞的也不会再有。不过我在北京,倒还偶尔见到磨剪子、铲刀的,不知我们那里是否同样还有。另外,那时还见到“打白铁”的,就是将白铁打成水桶等器具,一般跟补锅这一行当合为一体,我们本村也有青年学会这手艺而走四方谋生的,有的甚至就客死外乡。由此可见,走南闯北、走村穿巷的谋生确属不易。
当然,孩子们最喜欢的外乡人还是爆米花的。一头挑着风箱,一头挑着爆米花的铁罐,来到村头就支架起来,等待村人拿大米和玉米来“爆”。那是把大米或玉米放进那葫芦形的铁罐,通过手摇旋转着在火上烤,烤到一定程度(罐上有表)就停下来,将铁罐翘起,一头伸进一只长长的篾箩,用力一搬它那翘起的铁耳朵,“轰隆”一声,刚才的大米、玉米就成了香喷喷的米花;如果放进糖精,则每一粒米花都有了甜味。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爆米花就是很好的零食,所以,那爆米花的一来,孩子们就总是踊跃上前。只是临到“爆炸”的一刹那,一个个又都习惯性地跑远一点,捂上耳朵……
这些小商小贩在村里来来往往,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认为,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一部分,所以回忆起童年,回忆起童年的乡村,又怎能少得了他们。
责任编辑赵宏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