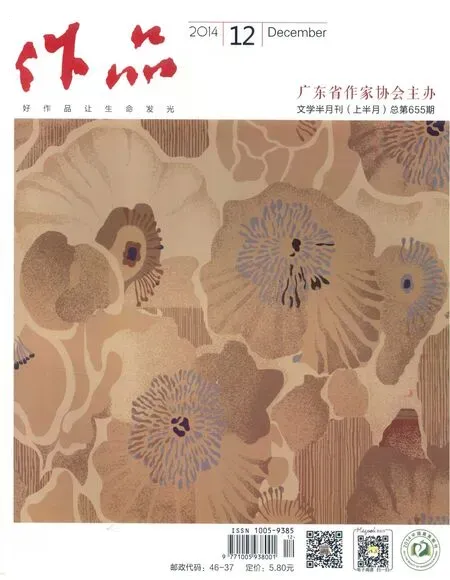另一种信与疑
文/李德南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这个“现代的”社会信仰一种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念,认为新的必然比旧的好,现代的一定比古典的好,城市生活肯定比乡土生活好,前瞻自然比回望更有价值。现代社会的疆域还在不断扩大,似乎要将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容纳其中。然而,在李之平的这一组诗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生活,是另一种的信。这种信,是一种反现代性的信,它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怀疑。
“现代的”价值观念里,还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效率的追求。它被形象地表达为“时间就是金钱”。受此观念的影响,我们被提醒要抓住眼前的和将来的一分一秒。《在伊犁牧区发呆》中,我们却看不到类似的紧迫感,也不必因为这种紧迫感而不断地行动并通过行动来获得什么;相反,“发呆”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方式。“我”与瓜果树木发呆,与动物一切发呆;“我”,还有自然,都不再急于行动。正是在这种发呆的状态中,“我”发现了另一种存在的方式与价值:
与他们在一起
消除了岁月的轮回和时间的畏惧
消除了这些年对生命的认识和记忆
——我开始真正认识它们
于是,另一种信就显现了。在这种信里面,不再有对时间的恐惧,自我与自然中的一切由此而得到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此发生变化。认知的、体验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我”自身,不再局限于现代人所念兹在兹的“自我”,而是包括“马,牛,羊”。虽说“我”仍旧无法完全突破自我在认知上的限制,只能以“我”观人,以“我”观物,认为:
这些大型哺乳动物
与我们那么相似
你瞧它们不比人懂的爱少——
只要有机会,便表达对孩子,爱人和兄弟的情感
亲昵动作温存细腻
但是,这里面毕竟有微妙的变化——包括“马,牛,羊”在内的自然,不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获得了与“我”一样的平等身份。李之平所看取事物的目光和姿态,不是俯视,而是平视;相应地,“我”不再以大自然的主人或立法者的身份自居。
人不是大自然的主人或立法者,那么,“我”是倾向于认为众生平等吗?也不是。“我”发现,等级和秩序仍旧是存在的。这在《草原牧羊犬》一诗中有所体现。“我”发现,奔跑于草原之上的牧羊犬只有一个职业,那就是管理牲畜,当好牧主人的奴仆。“在大型哺乳动物面前/它忽然成为首领/是多么得意的事”。由此,“我”对那个并未现身的现代都市和牧场这一“世外的世外/是清新之后的清新/世人不能统战的阵地”的区分以及对后者的肯定,就更多是从审美的、价值的层面来考虑,而不是基于事实上的差异与高低。
在这一点上,“我”的运思,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审美现代性的惯常思路,而且多少有些的暧昧和矛盾。“我”的信和疑,都带有某种预设的性质;“我”对牧区生活的肯定,并没有足够多的来自事实方面的支撑。不过,这些诗作的作者,确实是在很诚实地说出她自己的感受,因此她诗作中的牧歌情调,并没有一贯到底。在《日影飘过的下午》、《坐在伊犁尼勒克森林公园》、《它们的背影》中,对牧区生活的极度赞美的思路开始有所扭转。《它们的背影》和《草原牧羊犬》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牧羊犬的生活在作者眼中是充满愉悦的,然而,当作者将她的目光投向尼勒克的羊时,她发现了牧场世界里幽暗的一面:一群羊背着太阳蹒跚走来,注意到陌生的“我”出现,那个瘸腿母羊开始躲闪着,踯躅不前。“我”从羊母亲的眼中看到了它对人的提防,同时发现,虽然“从后面看,它们都像人一样,/一步一步弹走/前蹄落下,后蹄抬起”,但是羊与人之间,最终不过是吃与被吃的关系。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的餐桌上冒着热气,
那时候,可有一滴泪留在远方的心里。
“我”所想象的牧歌式的谐和,由此被打破了,被证实为一种预设,是一种幻觉。在《秋夜杂诗》中,李之平进一步写道:
窗外飞满了悲凉的事物,
我只关心时间的安宁。
比如存在法则中的合范与进道,
那些未曾表明的惦记和忠贞。
李之平关于牧场生活的描述,实际上是从牧歌情调开始,却以反牧歌情调的形式结束。这种反转最终所呈现的,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困境。这种困境的真正根源,在于乌托邦的不存在。也就是说,不管社会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只有善而没有恶,只有美而没有丑。我们只能期待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无法期待一个绝对完美的社会。李之平有志于表达一种不同于现代发达社会的信与疑,但是自身也在另一种形式的信与疑的争执中。不过,这种分裂的抒情与想象,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是我们省思生活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