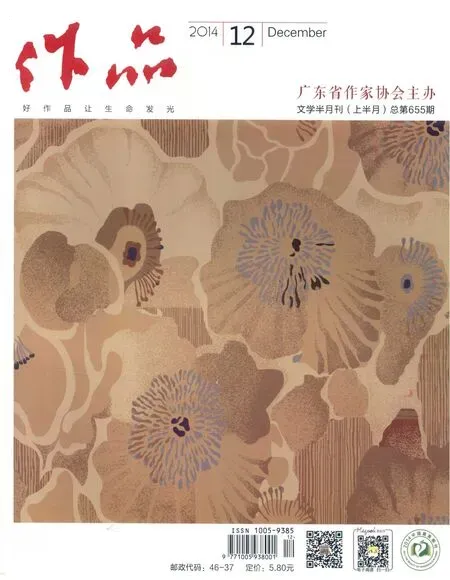母亲的教育哲学
文/金 岱
妈妈是教育家
我妈妈是个教育家。
时下说谁是什么“家”,有两种含义:一是在某一行当内确有大的名头(不一定是真有大贡献);二是加入了某某“家”协会,只要加入了,便阿猫阿狗都是“家”。我们小时候,那被批得死去活来的“成名成家”,拿到今天来看,实在是可以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我说我妈妈是教育家,则全不是这两种含义上的。我妈妈没有“大名头”,恐怕也没有加入什么“家”协会,例如“教育家协会”(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协会)。不过,我妈妈做了一辈子的中小学老师,做过南昌市法院前小学的校长,很长时间一直任教于江西省省会城市南昌最好的中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绝无匹敌的)南昌二中。妈妈懂教育,真懂教育,妈妈有她的教育哲学。
我现在也是近六十的人了,我妈妈的孙子,也就是我的儿子也已经三十岁了,而且我已经做过了三十多年的大学老师,我现在所说的“懂教育”,或者真懂教育的“教育家”,是个什么意思,你听了相信是比什么都明白的。
当然,如果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角度来看,妈妈的教育哲学,其实践成果实在平平,她的三个儿女不过都是普通平凡的知识分子,在普天下诸多望子成龙的父母的眼中,大抵是要不以为然的。不过,我并没有说我妈妈的教育哲学多么新鲜,多么神妙,会是个什么“让子成龙”的法宝,我只是想说,我妈妈的教育哲学,是平常而容易被轻视,被忽视的。且在我看来,也是颇有点趣的。
跟:家庭教育的自由与自然原则
我读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正碰上了1966这一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这一年。学校瘫痪了,我们都成了野孩子,除了每天看揪斗,游街,漫天盖地的大字报之外,则是疯玩我们孩子们自己喜欢玩的在大人眼里是绝无营养的把戏。而且,就当时看,什么时候有学可上,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现在能看得很明白,对她的这个小儿子,我妈妈当时心里想些什么:怎么办,可怎么办?连小学都没有能够毕业,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
“腰缠万贯不如身有薄技”,这话大概正是在那个时段在我的心里生了根的,且一定是因为妈妈的唠叨,一定是。学点本事,得学点本事才好哇。我想不起来,妈妈这是对我说的,还是她的自言自语,甚或只是她的内心独白?但是我的印象却分外真切。
天可怜见,我终于喜欢上了装矿石收音机,而且不久就升格为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妈妈当时一定有点大喜过望,她小儿子到底玩上了一种算是有点营养的玩意儿,她大加赞赏,大加鼓励,不惜血本,跟在我的这种喜好后面,尽其可能地掏腰包满足我的这方面的不断升级的购买欲望。以至于我后来都有点疑心,我究竟是喜欢装收音机,还是喜欢去那时的半导体商店买那些个新奇的二极管啦、电阻啦、电容啦?可是只要是我去买装收音机的玩意儿,我妈妈无论如何囊中羞涩,都会毫不犹豫地给,给,给。这与她在家中还相当富裕时居然让我穿着姐姐的花皮鞋去上学,使我羞不欲生,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我爸爸是1967年元旦去世的。爸爸在时,拿的是高知工资,在那时当是相当可观的,且我父亲还有稿费的另一部分收入。然而,我父亲实在是个虔信“儒教”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家族主义者,他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寄回了老家,供诸多他根本没见过大概也闹不清人数的侄孙们读书,以至于父亲一倒,家里竟没有任何积蓄。而我妈妈有三个儿女,我姐姐和哥哥当时都在读大学,父亲在时,家里经济状况良好,不可能有助学金,父亲于文革中离世,文革中却不再有申请助学金的可能。要养活两个大学生和一个小学生的三个儿女,作为一中学老师只有七十多元月工资的妈妈在经济上的窘况可想而知了。我听过妈妈关于在借钱无门中想破脑袋借钱度日的许多唠叨。
然而不久,我的兴趣不知怎么的又转移到了摄影这种更为奢侈的玩意儿上了。可这也是有营养的爱好哇。我妈妈继续跟上,虽然,她绝没有办法给我买一台当时恐怕要数百元一台的照相机,但她把我带到了她的一位同事那里,这位南昌二中的当时还较为年轻的老师,正负责着学校里的“革命”宣传工作所需要的洗相室。有一阵子,我被那间暗室里的各种液体及其底片的神奇显像弄得神魂颠倒。
好在,这么个奢侈的兴趣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又爱上了别的。一次在我们家附近的操场上,我被邻居家一位哥哥的美妙的二胡的乐声打动了,而且直达心灵深处。我爱上了音乐。不过,这位哥哥建议我学那时看起来更有前景的小提琴,并把我带到了江西省农垦文工团的吴老师那里,正式拜师学琴。
妈妈又跟上了。这也是有营养的兴趣,而且,妈妈当时心里是不是想,这说不定是一个能让她的小儿子养活自己的大有营养的兴趣呢(事实上,我确实差点就走上了让小提琴养活自己的路)。
妈妈的跟上,永远都是有实际行动的。妈妈毫不犹豫(其实我并不知道她有否犹豫,只是感觉她动作特别快,也就是二话没说的那种样子)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花了五十多块钱,也就是她月工资的近四分之三。这在当时我们家庭经济拮据到要借钱度日的情况下,简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动作。我当时小小年纪的心里,就有了不小的触动,更不用说懂事后回忆起这事的无限感慨来了。迄今,每思及此,我仍常有鼻酸泪噙的感觉。
只要是学东西就好!这是妈妈的口头禅。只要是有营养的兴趣爱好,妈妈永远紧紧跟上。
只是后来想起来有点觉得奇怪:作为一位有经验的中学语文教师(且她还有诸多各科的同事),妈妈既然如此担忧她的小儿子将来如何养活自己,为什么不安排、强制我学点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就好了,想起来,小时候,凡父母主动要我学的东西,没一样我是肯好好学的。
说不定,这本身也是妈妈的教育理念所致。
妈妈永远只是跟在我的后面,我兴趣上什么了,喜欢上什么了,只要是有营养的,妈妈就跟上,尽其所能,甚至不惜血本,鼎力支持。但是她绝不走在我的前面,安排我,强制我,强迫我,绝不。
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与时下在“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由的万千家长们的教育理念真可谓天差地殊。
我的一位朋友的孙儿,现在还刚刚一岁,已经开始上早期教育班了,一个星期两天,一年要一两万学费。而我周围的上幼儿园的孩子们,上十数个兴趣班的绝不在少数:举凡钢琴、舞蹈、下棋、台拳道、游泳,甚至跳绳,几乎没有不上学习班学的。时下中国的孩子们,每一个应该都不比国家总理轻松,可谓“日学万机”。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个班,都是父母安排,强制的,且是去“学”,而不是去“玩”。
悲乎,今天中国的孩子们,一生下来就要上学了,而且还有更早的,还在母腹中就不让闲着,要听经,听儒家经典光盘,受远古的圣人的“教化”!
回想和比较起来,我妈妈的“跟”的教育哲学,其重要性实在非同小可!
“跟”,教育的“跟”在孩子后面,就是“跟”在孩子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后面,就是坚决否弃父母成为孩子之独特人生的“专制君主”的恶劣传统,给孩子以创造自己灿烂人生的尽其自由的广阔空间。此乃教育的自由原则。
“跟”,教育上的“跟”在孩子后面,就是“跟”在孩子的天性后面,“跟”在孩子作为独特个体的生存境遇后面。从较为抽象一点的层面讲,也就是不僭越自然,肯定自然先于人为——对我们的传统道家思想作一点改造的话。此乃教育的自然原则。
赞:家庭教育的欣赏与欣赏什么的原则
我是个傻孩子,这一点我自小就明白(现在则是个傻老头,这一点今天自然是更加明白)。
我姐姐,我哥哥,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但是不管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我蒙胧中体会到的大人的心里,我都隐约感觉到,我将来是否也能成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甚至能否成为一个普通大学的大学生,都似乎是个危险得紧的事。
在我们家的三个孩子中,我无疑是最受宠的。我最小,比姐姐和哥哥都要小很多,不仅父母宠我,姐姐、哥哥甚至更为宠我。但我是最傻的孩子,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实。
大概是认为我傻,我妈妈但凡逮住我的任何一点小小的优点,便要好好的欣而赏之,便要人前人后地大肆夸奖我。
树木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树木对土地的需求也不同。在选择树种时,要因地制宜,适树造林,是提高苗木成活率的基础。除了环境对幼苗成活率的影响外,树木生长的整个过程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因此,优先选择乡土树种作为人工林树种是苗木选择和育种的基础。在选择母树时,应选择生长初期的母树,因为它们的生长初期已经完成。栽培周期短,营养丰富,能满足树种数量和质量的需要。在育苗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苗木选择不同的方法。同时,根据栽培进度,应保证林木苗木的水肥供应,以保证苗木成活,促进苗木生长。
今天,对于孩子,鼓励为主,批评为辅,或赞赏胜于责备的道理已然普及。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可是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或者说是“大批判”的时代,全国上下,无论老少,人人时时有错,甚至人人时时有罪,人人时时自危,孩子们亦不例外,特别有意识地用赞赏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并不是常情。
即使在今天,人们已习惯于鼓励孩子,然究竟道理何在,恐怕也知者未见得多,未见得深。
依我看,孩子的成长,即所谓懂事,最基本的,就是能依人生目标理性地管理自己,譬如马套上了笼头,能循目标受控行为,当然,马是他控,人是自控。而如何才能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如马被套上笼头一样,能依自己的人生目标自控行为呢?赞赏,鼓励,表扬等等,其效用(且是不经意间地,自然而然地效用),远胜过批评、责骂,甚至打罚等等的强制。“甜头”——胜利感、成就感,乃是最易让人生上那努力之“钩”的诱饵!
比赞赏还是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方法:物资鼓励,还是精神上的赞赏效用更大呢?我的看法是,就家庭教育而言,精神上的,方法得当的赞赏——准确而真诚地欣赏与赞许,效用远大,远长于物资的(当然也不是完全否认物资的奖励)。“准确”很重要,不准确的胡乱赞赏,便是欺骗,必害了孩子(今天有位名星,孩子纨绔得厉害,醉驾,打人,轮奸,劣迹斑斑,母亲却赞其“心里干净”、“单纯”之类,这种态度最终把孩子送进了深渊);“真诚”更重要,首先是真诚的欣赏,真真切切的欣而赏之,然后才是赞许,孩子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健康地成长起来。事实上,依我看,父母对孩子的准确、真诚的赞赏,是会逐渐内化为孩子对自己的赞赏、激励的人生习惯的(当然必须是恰如其分的),这种无意识地积极内化过程,实在重要无比。套用近些时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帮助孩子积累“正能量”。
而欣赏,赞许,鼓励孩子什么,则是更大,更核心的问题。今天的家长们,最常听见的是,孩子在学校里得了个好成绩,于是奖励之,且通常是物资上的。
我妈妈则不然,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受到过任何来自妈妈的物资上的奖励。同时,我也没有任何妈妈对我在学校里的成绩发表评论的记忆。当然,在我成长的关键期,根本就没有学习成绩这么一码事,连学都没得上,何来学习成绩这码事?且在那时,就是有学习成绩这码事,也绝不像今天这样是致命的大问题(今天,孩子们在中考时,就有一考而被决定一生命运的相当大的可能。)
对我的人生起过决定性作用的来自妈妈的赞赏,是这么一个故事。
一次,家里浴室的一个水龙头坏了,坏得突然而猛烈,水流喷射出来,湍急不止,很快淹没了浴室,漫进了内房,并往楼下漏水,情势颇是紧急,要不了几分钟,自己家和人家家就全都要“洪水滔天”了。当时只有妈妈和我在家,妈妈显然束手无策(当时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居住的大学一切瘫痪,水电工都是没法找的。即使找得到,水情紧急,破坏会颇是严重),我却不知从哪儿来的灵感,迅速找了根绳子将水笼头绑住在水管上,又找来一根小木条,插在绳子当中,旋转起来,绳子逐渐崩紧,很快,笼头就被固定了,水喷就停止了。这里所用的当然是旧式木匠用的锯子的原理。那时我应当是十二、三岁。这样的小急智,虽然也是有点不错,可远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发明。
然而,妈妈却兴奋得了不得,那看着她的小儿子的欣喜、赞赏之情,我永远也忘不了!妈妈人后人前地讲,长久地,反复地讲,以至于成为家庭里的一个伟大的传奇故事,同时不断升华:这是活学活用,是举一反三,是了不起的灵感,是创造性,创造性!——我想创造性,作为一种人生的最重要的价值,就这样植入了我的心底深处。
今天,已快满六十的我,未见得做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创造,至少在现实的层面上,不会有人认为我是个什么重要的创造者,然而在我自己,却毫不怀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永不停歇地追求创造的人生,创造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最根本的目标,也是最基础的动力。我一生眼疾缠身,中年双目失明,事业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拘怎样的境遇,至少到目前,还从未放弃过奋斗和努力,停止对创造的追求,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对创造性之人生价值的已然植入无意识中了的认定。而这一认定的第一根火柴,也许正是妈妈对我的那一小小的灵感的充分赞赏。赞赏的如果不是一时的功利上的取得,而触及的是人生的深层价值,便是家庭教育之赞赏原则的至高境界。
“创新”这个词,时下也已成了一个滥词,不过,人们通常是在创新于利益的竞争的意义上予以理解,而不在人生的价值与动力上予以理解。
当然,对创造性的无尽追求,也带给我人生无数的烦恼与痛苦,其负面效用与正面效用也许相差无几,不过这是另一码事。总之,在这一点上,我要说的似乎应该是,乐也赖老妈,苦也赖老妈,总之横竖都得赖到她老人家头上。
导:家庭教育的暗示与如何暗示的原则
无论是永远“跟”在我身后的妈妈的目光,还是“跟”在我的各式各样的兴趣之后的妈妈的竭力支持,还是“跟”在我的天性之灵光闪烁之后的欣喜地赞赏,都是一个“跟”字。一句话,父母应该做的就是,永远“跟”在孩子的后面,永远不要走在孩子成长的前面,人为地控制他(她),扭曲他(她),异化他(她)。
不过,父母的家庭教育,似乎也应该有“导”。然而我妈妈对我的“导”,似乎也是另一种“跟”。这另一种“跟”的意思就是,即使是走在前面的“导”,也主要的不是强制、命令,而是暗示,以暗示的方式达至潜化,即潜移默化的效果。家庭教育中的暗示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一种无意识层面的对话,顺着孩子天性的那类暗示,将会润物细无声地,自然而然地被接受。这样一种“跟”的意义在于,它能有机地传输给孩子有价值的培养信息,却不影响孩子的自信心态、自立意志与自主能力的成长。
暗示及潜化的第一要义,自然是身教。身教已是常识中的常识,然而人们多半并不意识这实际是一种经年累月,无处不在,微妙有机,最为深入的暗示力量。就家庭教育而言,身教确确实实重要无比。这里不再赘言。
暗示及潜化的又一要义是唠叨,当然也可以说是言教,不过这种言教,主要地不是或正言肃色或循循善诱地长篇大论(并非全不需要,年轻时一次在火车上读《傅雷家书》时曾潸然泪下。后来想许是因为文革开始的第一个元旦,我刚刚13岁,便再也不可能听到父亲的教诲了),自然更非疾言申斥之类,而是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的出于深彻的关切牵挂的叮嘱之类的唠叨。
天底下没有不唠叨的父母,天底下没有不嫌烦父母唠叨的孩子。所以,我可不敢说唠叨是我妈妈特有的教育哲学。
不过,我以为,为孩子成长所需要的,适度地唠叨,对于孩子确实有极为重要的暗示作用。世上的事,尤其是人格习惯的养成,多半是知易行难,持之以恒的暗示我想是有助于孩子的良好的人格习惯的塑形的。
我小时候,多少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尤其对妈妈,反抗心理特别强。我最烦的就是妈妈的唠叨,常要跟妈妈顶嘴,吵架。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许多行为与你当时最嫌烦的妈妈的唠叨其实并无二致,或者说正相吻合,妈妈的唠叨实际上是起了莫大的作用。以至于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对孩子的唠叨,大抵跟妈妈的唠叨也差不了多少。
在我妈妈,以暗示的方式进行潜化的又一手段,我现在想起来,乃是她对我塑造的我父亲的形象。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之前,与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也颇是有限。父亲大约一星期回来一次,他在南昌市郊外的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工作,这地方今天已属热闹非常的市中心,当时却是路途甚远交通不便的郊外。父亲总是很忙,教学、写作、采访、出远门开会,事实上一星期未必回来得了一次。因此,我和父亲之间是有某种距离的,而妈妈看来正是用好了这种距离感。妈妈让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可以说是伟岸无比,尽管这种塑造在形式上很可能往往是以埋怨的口气出现的,可是在那些埋怨的口气里却分明透着为之无比骄傲的底色,因此也就分外有力量。例如妈妈会埋怨父亲把钱都寄回了乡下供侄孙们读书,可是你能听出这种埋怨里面却是一种对父亲慷慨性格和重情重义的赞佩。
其实,父亲在世时,我对父亲的反抗心理甚至是超过对母亲的反抗心理的,可是父亲去世后,我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了父亲的写字来;而父亲留下的寥寥几页写在小小信笺上的有关小说研究的笔记成了我反复阅读的经典,成了我学习小说写作的入门读物。至于人格上的影响更不待说,以至于已近六十岁的我,会时常感叹,究竟是遗传的力量,还是榜样的力量,我在人格上和性情上竟会如此像父亲。
当然,妈妈也“塑造”自己。关于她自己,她说得不多不细,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她说她自小打乡下出来,兵荒马乱,人生坎坷,国内国外,颠沛流离,实际上并没有太正式地完成过多少系统的学业,然而,她却做成了小学校长,更做成了南昌市最好的中学的可以说是很优秀的老师。我和妈妈之间是没有距离感的,可是妈妈说起自己的奋斗历程时的那种自豪感,却给我极深的印象。
说到底,人生有什么?庄子云“其生若浮”,一切皆过眼烟云,唯一可宝贵的,也许正是人生历程中因奋斗本身而来的那么一种自豪感。
母亲是空气
日常中,我们从不感觉和想到空气,更不觉得空气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不会以为在空气中自由自在地呼吸是一种多么大的享受,多么大的幸福。
可是你如果高原缺氧,更假使你忽然窒息,你就会感觉到空气了,感觉和领会到空气的绝对、至高、无比之重要了,感觉和领会到能自由自在地呼吸是多么大的享受,多么大的幸福了!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妈妈忽然就去了的。在医院的急救室里,病床,吊针,还有其它什么,忘了,只记着我抚摸着妈妈的头发,央求着医生救活我的妈妈。可是我的妈妈在一瞬间脸容庄严无比,我知道,她离我们去了。那年我23岁。
妈妈是忽然脑溢血。
回到家中,家里的空气冻住了,我感到窒息。
闭上眼睛,总觉得妈妈还在喊我吃饭,唠叨我该换衣服了,该收检桌上的东西了,埋怨我又把什么弄丢了……然而一睁开眼睛,空气却是冻住的。我似乎无法呼吸。
过了好多天,空气仍不能解冻,且像是越冻越死。因为看见家里的灰尘在迅速增厚,那是妈妈在的时候从未见过的,我一直以为,从盘古开天地,家从来就是这么一尘不染的。增厚的灰尘更加堵塞了我的呼吸。
我这才明白,母亲就是空气,而空气是比食衣住行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更为重要的东西。
好在,小坡上妈妈的目光始终跟在我的身后,我虽然已经走得非常遥远,非常遥远了,可或回头或不回头,我都能感觉到,妈妈仍站在那小土坡上,她那忧虑里闪烁着希望的目光,跟在我的身后,一直,一直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