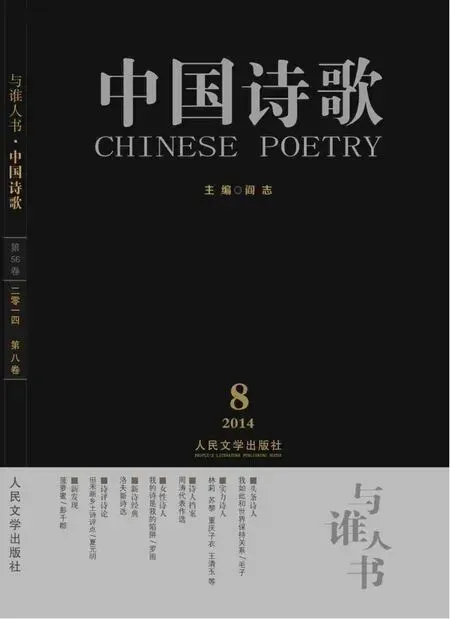闪耀在双语峰峦的诗美之光
——《田原诗选》艺术散论
子午
闪耀在双语峰峦的诗美之光——《田原诗选》艺术散论
子午
田原是迄今为止华人作家中(健在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双语诗人之一。此外,杰出的华人双语作家主要有: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旅法剧作家、小说家、文论家高行健(他分别用中文和法文两种语言写作),旅美小说家严歌苓(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作)等。田原则是一位旅日诗人、翻译家、教授和学者,曾获日本最高诗歌奖第60届H氏奖和日本第一届“留学生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他曾站在学理的立场毫不隐讳地指出:“我总认为文学的表现能力首先取决于自己母语的表现能力。像读者普遍认为的里尔克的法语作品和布罗茨基的英语作品不如他们的母语作品出色一样。”(田原《在远离母语现场的边缘——浅谈母语、日语和双语写作》)他甚至非常谦逊地称自己在日语面前“永远是一位不成熟和笨拙的表现者”。
笔者也曾参加过几次中外学术活动,每当涉及到一些学理性很强的理论词汇时,就连最优秀的翻译家也会弄得相当狼狈和尴尬。据此,我认为,敢于攀上并在险峻的双语峰峦上耕耘的写作者,有理由赢得双语国和更广泛的人们的尊重。《田原诗选》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语言秩序下完成的。他的诗歌除了几首写于中国,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写于岛国日本。用田原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于远离母语现场的异国边缘”。他的诗作智慧而空灵、深邃而澄明,语言充满弹性和张力,无论是立足于现实生活情景的哲思之维,和突入艺术向度纵深地带的独特心灵拟象及综合,还是对死与命运的永恒梦境所进行的词/像二重奏,都以其在双语写作领域的不懈探索和实实在在的成功,闪耀出璀璨绚丽、多姿多彩的诗美之光。
1.哲思之维——向生活情景真诚敞开
《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孚指出诗在表现客观物象时应该达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郭璞诗句)的境界。这既是对作品总体艺术水准的要求,也是对作品细节及局部性叙述的一种技巧指标。田原诗歌的第一个触点,便是毫不犹豫地把其哲思之维向现实生活情景——即当下的具体生活细节、场境等真诚地敞开。他像是一个在生活河流中勇敢、坚定、不倦的淘金者,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天地、山川、城市、乡村和平凡人事的融入、感悟,从而将现实社会和人的生存提升到一个哲学的、文化的思想维度。一如他在黎明前看见一列火车正在轰隆隆地向前奔跑,于是,他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以下作为一个时代的承担者(俨然是个“青年医生”)的思考。“我们喘息着,呼吸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在我们青春的躯体里气喘吁吁/像在我们健康的体魄里患了哮喘病/而我们都是懂得她病因的青年医生/……她被在太阳下成熟、饱满的向日葵的籽粒命中/而这棵向日葵曾经是我们心中的太阳神/我们是沐浴着它的光芒长大的一代/小时候我们围着它跳舞唱歌/长大了我们仍把它敬仰和歌颂/她却倒在了血泊里。倒在了无根的向日葵下//一座新坟就这样在我的心中/隆起,它高过了中国所有的山峰”(《黎明前的火车》)。
历史的使命感和敢于为时代承担、为苦难承担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使田原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沉甸甸而高贵的品质。阿拉伯大诗人、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阿多尼斯指出:“不可能想象一个诗人会全盘接受现实世界,对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持接受态度的诗人,他所创作的诗歌是没有价值的。变革和叛逆是诗歌根本性的核心。”是的,田原正是在这一意义层面将自己对现实人生的融入、反思和批判,置放在一个凸现历史和文化跨度的宏大、广阔的哲学视野之下。例如他对某一时间刻度上的“此刻”这一时段的独特心理感悟,既体现了他一贯奉行和追求的诗美的“感性”意味(他认为“诗歌的魅力来自感性”),又反映了他诗歌语言的智慧及深层思想擦痕,虽然这一心理感悟的最初触点乃源自一个黑人女歌手“高亢的歌声”——
“紧贴墙壁的旧式音响正在沙沙地播放着/一位黑人女高音的歌,高亢的歌声/我能想象她丰腴健美富有节奏的身段/骑着斑马在非洲如火的阳光里奔跑/从地球的一面到另一面/马蹄声如雨,淋湿所有沐浴着音乐/生长的植物”(《此刻》)。诗作从歌声开始联想到歌者的形象,继而从歌者的形象联想到一匹斑马乃至众多斑马,又从斑马的蹄声联想到地球另一面的热带的雨声和被雨水淋湿的正在生长的植物……等等。诗人的思绪沿着“声/形”对称的多重交叠、变奏形式一路向前,具体地说,就是沿着“声1(歌声)→形1(人的形象)→形2(马的形象)→声2(马蹄声)→声3(雨声)→形3(植物的形象)”这一线性结构层层突入,使声音、形象和情景三者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最后,诗人的笔锋突然一转,把这些现实生活情景、画面推向了一个哲学的制高点:“此刻是此刻就足够了/没有谁能够认清此刻/此刻是过去的过去/此刻是未来的未来”。尤其像“此刻是过去的过去”和“此刻是未来的未来”这两个警句,在上面诗人所营造的黑人女歌手声情并茂的特定情景里,到了这儿竟令人猝不及防地戛然而止,无疑是为了营造并抵达类似布莱希特戏剧那样一种“间离效果”。而这两个警句所爆出来的力量犹如万钧雷霆,震撼人心!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或“心灵”(Geist)显现于艺术、宗教和哲学三阶段。到了哲学,精神就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也就是真实世界发展到了它的终点。当田原置身于某座名山或某个岸边,他总是以一种充满文化意味的哲思来展开自己的词/像时空。“我一直在意的是它/在夏末就早早披雪的平原/那被白云擦得越来越白的峰/竟然没被那么多的目光和赞叹声暖化”(《富士山》)。这便是诗人从富士山所感悟到的深层哲学意味:它不轻易地被那些世俗的“目光和赞叹声”所“暖化”和迷失。它之所以能够崛起和雄立在本州岛中南部(距东京约80公里),并成为日本的第一高峰,正是因为它崇高的境界及内在品格早已超越了世俗的尺度。“很多人都觉得它已经死了/其实,它的生命恰恰活在/人们的无知中/……只有很少人才悟出了/它的象征中隐藏着历史的疼痛”(同上)。他不但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突出了富士山深刻而丰富的人文精神,“它的生命”恰恰“活在人们的无知中”,并令人信服地抵达了这座名山隐藏在历史层面的“疼痛”,而且,他还以一个哲人的智慧破译了海、河根植于泥土里的生命“秘密”:“岸就这样的诞生了/它柔嫩得像婴儿的肌肤/草的根扎进岸边泥土的沙子里/结出大海和大河的秘密”(《如歌的行板》)。
显然,田原对客观世界的诗性把握或本质认识,是建立在具体物象和具体情景之上的“自物而心”、“由形入神”。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理性的,凡是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其本意便是肯定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统一。田原深深懂得,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着其自身的辩证法。如“对万物一视同仁”的风,田原这样写它:“风是大地上惟一的法官/它对万物一视同仁/风是手臂,又是利斧/它轻敲着问候所有的窗户/它劈倒无人敢碰的老树”(《风》)。诗人眼里的“风”,不但能够在石头里留下“脚印”,同时,它还把自己的汗水“滴落在大海里”,甚至更在“人类的脉管里”永不停息地“疾走”。他在诗中隐隐透出了这样一种信息:风的距离是人类所不能企及的。相比之下,本来也疾走如风的“马”,竟在田原独特的词/像互生的诗美时空里,和“我”的距离却永远保持着“九米”(在这里,“我”是指诗中的抒情主体,并非直指诗人自身)——
“马和我保持着九米的距离/马拴在木桩上或者/套上马车去很远的地方/马离我总是九米//……很多草都枯萎了/马咀嚼着还散发出清香/那清香离我也是九米”(《作品一号》)。这一通过语言预设方式而确立的“九米”距离,也许正是田原诗歌审美中独具“黄金分割”法则的心理距离,以至多年后他的语言节奏和心象节奏仍保持着这种日久而弥坚的源自诗美原旨的庄严:“马和我之间的距离/很多年来不延长也不缩短/从活生生的马到青石马/我们之间的距离/永远都是九米”(同上)。这个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的沉甸甸的“永远”一词,实际上已超越了时间副词在语言学层面的传统词性功能(结构)及表意功能(张力)。
宋代大诗人杨万里宣称:所谓好诗就是“去词去意而有诗在”。这实质上是用一种曲笔来强调言外、象外之境才是诗的化境(亦即最高境界)。美国现代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乔治·桑塔亚那也曾说过:“最伟大的诗人都是哲思的。”优秀诗人田原处处散发出语言机智、人文厚度和艺术芬芳的诗歌,便是自觉地把诗的触点、哲思向具体的现实场景及生活细节直接敞开和融入的。他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具有思想深度的诗人,往往是把深邃的思想不动声色地隐藏在他‘结构和形象化’了的语言之中——即思想、哲理等都是在他的艺术化了的诗句中经了发酵产生出来的。”无疑,他的诗歌也是“把深邃的思想不动声色地隐藏在他‘结构和形象化’了的语言之中”的成功典范。
2.艺术向度——独特的心灵拟象和通感式综合
田原的诗歌触角非常敏锐、丰富而细腻。有时候,不经意映入眼帘的一座山、一只画中的小鸟,或者从远处飘来的一声琴韵、一下钟声,也会引发诗人无尽的思考、感悟和诗美升华。这正是一个真正诗人所应具有的艺术天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费奇诺称:“心灵、视觉、听觉能把握遥远的事物,所以属于天空和精神;而嗅觉、味觉、触觉只能感受非常接近它们的事物,所以属于大地和身体。”当然,在诗歌的世界里,我们既要有属于天空的心灵、视觉、听觉,以“把握遥远的事物”,又要有属于大地的嗅觉、味觉、触觉,以感受与它们“非常接近”的事物。
正如一个普通的冬天又来到了田原的面前,这时他正驻足于岛国与往日毫无二致的吉野山上。但诗人此刻的心灵已被一场逼近的雪意整个儿融入了白色的呼吸。“白烟散尽/远处的一座山林开始变白/一场雪正不紧不慢地飘向我们/我感到了,冬天寒冷指爪的/逼近,尖利和无情”(《吉野山印象》)。“吉野山”这一视觉和触觉形象(前者是“白烟”、山林“变白”;后者是“寒冷指爪”、“尖利”),经由诗人的心灵通感迅即转换成一种鲜活、空灵的听觉意象:“透过鸟儿们的聒噪,我听见山民/亲切的呼唤。从柿树上滑下来”。后面的“呼唤”声竟从“柿树上滑下来”,则又转换成了一种真切、栩栩如生的视觉画面。这是一幅多么神奇而美妙的山中雪景啊!事实上,这首诗已在诗美层面抵近了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
如果说,《吉野山印象》一诗主要是把诗人直接看到的视觉形象通过心灵通感转换成一种听觉形象,那么,《晚钟》一诗则主要是把诗人原本听到的听觉形象通过心灵通感而转换成一种全新的视觉形象。“我听见它飞动和落下的声音/激越似瀑布泼倾/轻盈如柳絮飘动/它碰到云,云是一朵绽放声音的花朵/它落入田野,庄稼沐浴着它拔节”。诗的开头,诗人听到的钟声仿佛是经过“飞动”和“落下”这两个动作(过程)所直接形成的声音(结果),接着,这一听觉形象(钟声)便转换成一种视觉形象:从“瀑布泼倾”到“柳絮飘动”,再到云——“一朵绽放声音的花朵”,它“落入田野”,于是庄稼“沐浴着它拔节”。
在诗歌的这一词/像链条上,诗人并不满足于把钟声的审美落点仅仅锁定在“视觉—听觉—视觉”的二级通感值阈。诗的后面,诗人突然把笔锋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而将诗歌的审美诉求一下提升到了对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反思。“我想起钟声里的一场暴动和起义/也想起钟声里的阴谋和革命/黑暗的岁月,钟声是钟声/光明的日子,钟声还是钟声/时间无法改变它的音质/它却改变着时间和日子”(《晚钟》)。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诗人在听到钟声并将其通过心灵的两次复合拟象后,一步步把读者引向了“黑暗”和“光明”两种时空及语境的思考。原来,诗人对“钟声”的最初触点是把它作为“时间”的一个对应拟象(钟声正在和已经“改变着时间和日子”)。
实际上,田原对时间这一特定抽象物的心灵拟象是相当广泛和丰富的。他时而将时间概念拟象为风、云、季节、河流,时而将时间形态通感成钟声、瀑布、柳絮、花朵,有时则干脆将时间现象设定为鸟、小虫、雪或夏天。“它斑斓迷人的羽毛上/或许镶嵌了太多的阳光/它全身热得烫手/如浓缩了整个夏天//……野性的大地、逶迤的山峦和滚荡的河川/陆地上的风景可能会使它望而生畏/但它一定不会在地平线上迷失/因为那里埋葬着许多它祖先们的化石//……它将代表我在西边发言/它将代表我提前唤来春天”(《金属鸟》)。在田原眼中,这只已被艺术化和哲理化了的“金属鸟”,它羽毛“斑斓迷人”,全身“热得烫手”,就像浓缩了的“整个夏天”、“野性的大地、逶迤的山峦和滚荡的河川”等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意象,组成了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的词/像方阵及人文景观,并把它推向了一个立体、多元、缤纷、绚丽而异彩纷呈的全新境界。
与钟声较为接近的“可视性”听觉形象,则是“高贵地占据着”城市一角的钢琴。田原常常与它对视、默想和倾诉。“钢琴很像一匹怪兽的骨架/高贵地占据着城市的一角//……钢琴的轰鸣是乡村一棵大树上的声音/也与虫子在田野里的歌唱/非常接近//……钢琴总使我缅想起远离城市的树木/被伐倒后豁然阔朗的天空/和树木被刨去根后/遗留在大地上的深坑”(《钢琴》)。在这里,诗人把弥散着心灵节奏和语言擦痕的钢琴,拟象为充满历史沧桑感的“一匹怪兽”的神奇“骨架”——它与田原的精神家园和诗歌理想息息相通,构成了诗人心灵深处新颖独特的美学“骨架”。
顺便插一句,田原《钢琴》中这一神奇的“怪兽的骨架”,与笔者写于1983年的《港口城市》中的“蓝鲸巨骨”恰好形成了一对相互映衬、互为对照的孪生意象。虽然此二诗的题旨及表现对象略有不同,但在诗歌的“比物取象”层面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所强调的“离形得似”、“则天成化”的诗美原则,便是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即写近物不至由形所惑而浮浅,写远景也不至因求全而技穷),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外是指象外、韵味之外)”。无疑,田原独特的心灵拟象和通感式综合,在新诗的“词—象—意—境”三级诗美跃升中突入了司空图“韵外之致”的空灵境界。
3.永恒梦境——死与命运的二重奏
现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作家、诗人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力。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依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指出:“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我们可以立即认出‘至高无上的自我’,就像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个故事的主角一样”。在田原的诗歌中,有不少诗篇都写到了这一类的梦,和与梦有关的树。“在梦中,我无法推断/树被强行移植的命运//……树是我梦乡温暖的驿站”,“树在梦中消失后/马车陷在泥泞的路途”(《梦中的树》)。这棵“百年大树”在诗人的梦中,竟长成了一颗非常独特的“绿色牙齿”。当这棵绿色牙齿般的大树在梦中消失后,诗人却仍然“祈祷树在远方结出果实”。这正是弗洛依德所说的,每一个梦和幻想都代表着他“未被满足的愿望”,和“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这一类的“心理活动创造出一个与代表着实现愿望的未来有关的情况”。
在田原的另一类写树的诗作中,我们分明感觉到这些树总是隐隐透出一种深沉的死亡意识。“树是我们死后的衣服/它以各种形状套穿在我们/僵硬的身上……树木总摆脱不了/被轻而易举毁于一旦的宿命//……为什么我们死后要穿着树木的衣裳/被埋在地下,难道不正是我们灵魂的/归宿,渴望着在地下与树木的根/拥抱一起吗?”(《树》)在诗中,不但树木摆脱不了总是“被轻而易举毁于一旦的宿命”,而且人在死后,也避免不了和被毁的树、树木的根“拥抱一起”的结局——树成了“我们死后的衣服”,并以“各种形状”套穿在“我们”“僵硬的身上”。直到后来,与树木的皮肉、根茎,与树木的魂融为一体。这便是诗人眼中所看到的树木的通常形态。可以说,这一“树”的形象便是源自田原心灵深处的一个永恒的梦境。
而枯树作为树木的一种特殊形态(死亡形态),当它进入诗人的眼帘和思维,竟能“长成了周围和我一样年轻的树木”。这是一棵同样被毁于一旦的伤痕累累的树,“一棵千年的枯树”,“它被剥光的躯体/干裂的伤痕无法愈合/它的毛发和牙齿早已脱落/长成了周围和我一样年轻的树木”(《枯树》)。诗一开始,表明它显然是已经死了的千年枯树,但在诗人那有如梦幻般的叙述视角中,这一死亡的树木形态以及死亡现象本身也获得了“心理活动创造”(弗洛依德语)层面的审美意义。我们再比较一下田原诗歌中的其他形态的树,如生长在万木葱茏的春天里,沐着和风丽日的枯树:“春天里的树都绿了/枯树还是冬天里的样子/我常在春天散步/总是不自觉地就走近了它/站在树下,望天/天清澈而又湛蓝//……在春天叶片的遮掩里/枯树是惟一真实的风景/枯树/生命的旌旗”(《春天里的枯树》)。在这里,诗人不仅仅把目力锁定在枯树作为通常意义的死亡形态,而且把它提升到一个“惟一真实”而崇高的精神境界——“生命的旌旗”。一些树木在春天里枯死了,竟还可以其精神的不朽照耀生者,让绿色蓬勃、让春天永恒,使现实保持其(惟一)真实的“生命的旌旗”。
甚至,田原在一位少女曾经自杀的地方,竟也把这一隐含原型意味的“树木”形态(心理形态)带到了现场。“外面起风了/我一下子变得孱弱并被吹弯/像风中直不起身子的小树”。此刻,诗中的抒情主体(也带有诗人的影子)使自己陷入了树的死亡意识。“我注定不再写诗了/木然如一具行尸走肉/仅带的一支笔比上膛的枪/沉重。穿过长长的过道/穿越一个季节,身上/落满了十二月的阳光”(《我来到一位少女自杀的地方》)。抒情主体对死的体验是多么真切、细腻和深刻。“我听见很多声音/风的声音、天空的声音/鸟的声音、石头里的声音/很多声音都似在嚎啕”。在田原的这一类诗作中,树和人的死都是一种由新陈代谢、自然荣枯等形态所组成的命运的律动。在《树》、《梦中的树》和《枯树》等诗中,这一意象分别表述为“宿命”(“被轻而易举毁于一旦的宿命”)、“命运”(“被强行移植的命运”),或“灵魂的归宿”(“难道不正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在《春天里的枯树》一诗中,则表述为一种事物的必然性。如“它们(鸟)从枯树上飞走”,“肯定还要飞回来”,并在“枯树上栖息”。又如“它的根,也许正腐烂在/看不见的土里/但,只要空中有风/它枯瘦了的手指/便会弹奏出铿锵的旋律”。这些千年大树,或年轻的绿树与孱弱小树,它们枯死了,却仍然以某种方式活着。这就是它们发生在春天或冬天,以至一年四季里的共同命运。
这一“以死了的方式而活着”的命运意识也体现在诗人的其他诗作里。如蝴蝶,“死去的蝴蝶是美丽的/她的美丽在于/死了比活着时还显得安详//她的死让我想起许多美丽的词句/但什么样的词句都无法描绘出她的死亡”(《蝴蝶之死》)。如一只小虫,“这只来历不明的小虫/长着一双透明的翅膀/径直爬向我的鞋帮/它也许不会伤害我或爬进我的体内/但我还是轻轻一抬脚/不动声色地/将它踩死”(《傍晚时分》)。又如高尔基之死,“1936年5月28日/在去哥尔克村的途中/你拐去墓地与儿子对话/……1936年5月18日/以你名字命名的飞机的坠毁/似乎预示着一种昭示/一个月后的6月18日/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可夫死了”(《高尔基之死》)。再如坟墓,“死去的人安葬在此/悲伤和回忆/将从这里出发//……坟墓不是死去的/它是长在地平线上的耳朵/聆听和分辨着它熟悉的跫音”(《坟墓》)。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由田原独创的这一“以死了的方式而活着”的生命理念(或命运意识),乃是中外诗史上所未曾有过的一种独特的诗美形态。
关于人与命运的问题,世界文明自古希腊以来(中国则自孔孟、老庄以来),一直是先哲们思考和探索的最基本和核心的命题。从文学史的角度说,人与命运的问题也是世界文学几千年来几个最重大而永恒的主题之一。英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宇宙论科学大师史蒂芬·霍金,曾在其《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等科学巨著中,指出宇宙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同样是可以预测的。他说:根据P—膜模型,利用薛定谔方程计算出将来的波函数,而使我们在“量子的意义上具有完整的宿命论”。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则指出:“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遵循严格的必然性而发生。这是一个先验的、因而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此我把它称为可论证的定命主义。”根据笔者的研究,田原是世界华文诗苑中第一个集中地思考并以诗歌形式探索命运母题的诗人。他在诗中所展开的关于死与命运的“词/像”二重奏,就像一个融入了终极拷问色彩的永恒梦境。我们从中可以译读出诗人心灵深处一个对现实进行某种“校正”,从而实现并超越了“自我”的弗洛依德式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对文艺创作活动的“境界”说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境界主要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具体地说,就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纵观田原的诗歌创作,他的大多数作品已经抵近或具有了这两种境界。如《作品一号》中的“我”和“马”:“马离我总是九米//……很多草都枯萎了/马咀嚼着还散发出清香/那清香离我也是九米”;又如《吉野山印象》中的“我”和“一场雪”:“一场雪正不紧不慢地飘向我们/我感到了,冬天寒冷指爪的/逼近,尖利和无情”。这两首诗作都表现了抒情主体“我”和抒情物象(前者是马,后者是雪)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联想、象征和幻化了的艺术旨趣,显然这营造的是诗美的第一种境界(即有我之境:以我观物)。再如《春天里的枯树》中的“枯树”:“它的根,也许正腐烂在/看不见的土里/但,只要空中有风/它枯瘦了的手指/便会弹奏出铿锵的旋律”;《晚钟》中的“钟声”:“它碰到云,云是一朵绽放声音的花朵/它落入田野,庄稼沐浴着它拔节”。在这些诗行中,诗人的身影和抒情主体“我”的直接感喟、思考等带有主观痕迹的符号元素已经完全消隐,而直接让景物和场境自己呈现、变幻和交叠,这无疑已抵达了诗美的第二种境界(即无我之境:以物观物)。
诗人田原曾指日语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汉语,当属于世界语言中的“快文化型”。他认为“对语言的敏感和好奇,以及对语感、语序、语境、语音、语速的合理处理是造就诗人不可或缺的条件”。而田原恰恰是驾驭语言的行家里手。他正是凭着自己的“翻译经验和日语写作”天分,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富、有效的诗歌写作经验,找到了一个坚实可靠的“新的立足点”。或者也可以说,他终能清醒、理智地“从母语的(某种)局限中挣脱出来”,并“获得了站在另一种语言上旁观和审视母语的机会”。据此,田原在日语和汉语这一具有积极互动意义的双语诗歌创作中,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功。因而,我们有理由坚信,田原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他的双语修养及其人文视野。随着田原在诗歌创作、翻译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不断开拓、耕耘,他定会在双语写作领域一步步接近崇高的峰峦,并以其深邃、绚烂的诗美之光照亮一个新的里程。